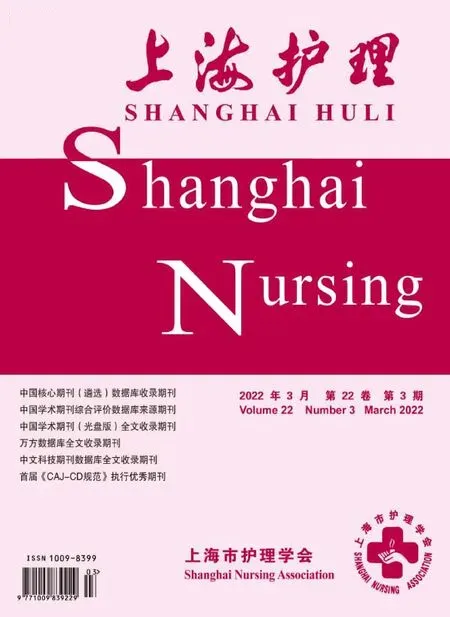三級醫院護士死亡態度現狀分析與靈性教育實施探討
林 毅,高巧麗,謝冬靜,謝 玲,殷 實,徐英華
(1. 江南大學無錫醫學院,江蘇 無錫 214122;2. 無錫市人民醫院,江蘇 無錫 214023)
有研究顯示,三級醫院住院患者的死亡率可達0.838%(0.485%~1.738%)[1],這使得護士在臨床工作中經常暴露于患者死亡的過程中。對死亡的恐懼是人類普遍的心理狀態,護士需要技巧和經驗來應對這種恐懼,因為護士對死亡和臨終患者的態度可能會影響其在患者生命最后階段所提供的護理質量[2]。那些無法面對死亡恐懼的護士會躲避照顧臨終患者,或與患者及其家人保持最低層次的溝通[3]。而臨終患者及其家人常面臨強烈的孤獨和無助感,迫切需要護士的存在、溝通和照顧[4]。為了使護士能夠向臨終患者提供優質的護理,其必須首先應對自己對死亡的情緒、想法和態度,這將有助于護士提供更高質量的身體和精神護理[5]。目前雖然已有不少對護士死亡態度以及影響因素的調查分析,但圍繞死亡態度5個維度進行具體分析且立足于調查結果提出改善臨床護士應對死亡態度方案的仍然較少。本研究旨在通過調查三級醫院臨床護士的死亡態度現狀,以期為相應的護理教育、政策和干預提供參考,以幫助臨床護理人員確立科學、積極的死亡態度,從而提高臨床護理工作質量。現報道如下。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采用方便抽樣法,于2019 年3—5 月選擇江蘇省無錫市人民醫院的護士作為研究對象。納入標準:擁有護士執業資格證書;工作1 年及以上;自愿參與研究,并知情同意。排除標準:調查期間罹患重癥疾病;非一線工作的護理人員。
1.2 方法
1.2.1 調查工具
1.2.1.1 一般資料調查問卷研究者參照國內外相關文獻的基礎上自行編制一般資料調查問卷,主要包括性別、年齡、工作年限、工作科室、宗教信仰、婚姻狀況等一般人口學資料,以及關于死亡的過往教育情況、以往是否有照護臨終患者的經歷等個人經歷。其中,關于死亡的過往教育情況含“從沒接觸過關于臨終和死亡的知識”“沒有學習過專門的關于臨終和死亡的課程,但在其他課程中有涉及到相關內容”“學習過專門的關于臨終和死亡的課程”3個選項。
1.2.1.2 死亡態度描繪量表采用唐魯等[6]漢化并經文化調試的中文版死亡態度描繪量表修訂版(Death Attitude Profile-Revised,DAP-R)。該量表包括死亡恐懼、死亡逃避、中性接受、趨近接受、逃離接受5 個維度,共32 個條目;每個條目采用Likert 5 點計分法,由“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別計1~5 分;以各維度得分的高低判斷被試者的死亡態度,得分越高則說明越具有該維度的死亡態度傾向。鑒于各維度題量不等,將得分除以條目數得出維度條目均分用以比較。量表 Cronbach’s α 系數為 0.875,各維度 Cronbach’s α系數分別為0.825(死亡恐懼)、0.811(死亡逃避)、0.575(中性接受)、0.832(趨近接受)、0.767(逃離接受)。
1.2.2 調查方法采用問卷星線上調查的方式。研究者將問卷所有題目導入問卷星生成二維碼,問卷首頁為知情同意書,研究對象必須選擇“同意”后方可進行答題,答題部分設所有題目為必答。正式調查前,研究者在醫院護士微信群內說明此次調查的目的、意義及調查注意事項和起止時間,后將二維碼發送至微信群中由護士自行填寫。共有803 名護士自愿參加本次調查,回收有效問卷803份,有效回收率為100%。
1.2.3 統計學方法數據由問卷星導出后,研究者檢查無缺失數據后錄入SPSS 21.0 進行統計分析。計數資料用頻數、構成比描述,計量資料用均數±標準差描述,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或方差分析,護士死亡態度的影響因素采用多元線性逐步回歸分析,以P<0.05 視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臨床護士的一般資料納入分析的803 名護士中,女性占96.76%,年齡21~55 歲,工作年限1~36年,工作分布于重癥監護室、呼吸內科、門診及相關科室、婦產科、急診科、胸外科、腎內科、骨科、消化內科、神經內科、血液科、泌尿外科、神經外科、腫瘤科、內分泌科、心血管內科、老年病科、肝膽外科、眼科、風濕免疫科、腔鏡微創外科、心臟外科、甲乳外科、體檢康復中心、手術室、胃腸外科、普外科、五官科、血管外科共29個臨床科室,94.52%的護士無宗教信仰,64.88%的護士為已婚,8.47%的護士從未接觸過死亡教育,65.13%的護士沒有專門學習過死亡教育但其他課程有涉及,63.89%的護士以往有照護臨終患者的經歷。
2.2 臨床護士的死亡態度得分情況803名護士中文版DAP-R 各維度得分中,逃離接受維度條目均分最低,中性接受維度條目均分最高,詳見表1。
表1 803名臨床護士死亡態度各維度得分情況(分,)

表1 803名臨床護士死亡態度各維度得分情況(分,)
項目維度得分維度條目均分死亡恐懼21.57±4.86 3.08±0.69死亡逃避16.14±3.70 3.23±0.74中性接受19.62±2.60 3.92±0.52趨近接受30.57±6.22 3.06±0.62逃離接受14.99±4.04 3.00±0.81
2.3 不同特征臨床護士的死亡態度各維度均分比較結果顯示,年齡及臨床工作年限組間護士死亡恐懼、死亡逃避及逃離接受維度均分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為了便于分析工作場所對護士死亡態度的影響,將29 個臨床科室分為兩類,患者死亡率相對較高的科室分為群A(主要包括急診科、腫瘤科、重癥監護室、血液內科、呼吸內科、神經外科等),其余科室分為群B。結果顯示,在死亡率較低科室工作的護士死亡恐懼、死亡逃避維度均分更高,對死亡的態度更趨向于趨近接受(P<0.05)。擁有宗教信仰護士的趨近接受維度均分高于沒有宗教信仰的護士(P<0.05),而婚姻狀況對護士的死亡恐懼、死亡逃避有影響(P<0.05),以往是否接觸過死亡教育課程對護士的死亡恐懼存在影響(P<0.05)。此外,性別及其以往是否有照護臨終患者的經歷對臨床護士的死亡態度各維度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詳見表2。
表2 不同特征臨床護士的死亡態度維度均分比較 (分,)

表2 不同特征臨床護士的死亡態度維度均分比較 (分,)
項目性別男性女性t值P值年齡(歲)≤25 26~30 31~35 36~40≥41 F值P值工作年限(年)1~5 6~10≥11 F值P值工作科室科室群A科室群B t值P值宗教信仰例數(構成比)[n(%)]死亡恐懼 死亡逃避 中性接受 趨近接受 逃離接受26(3.24)777(96.76)180(22.42)225(28.02)164(20.42)106(13.20)128(15.94)256(31.88)193(24.03)354(44.09)301(39.35)502(60.65)3.05±0.72 3.08±0.69-0.240 0.810 2.90±0.63 3.18±0.69 3.06±0.76 3.17±0.73 3.11±0.62 4.803 0.001 2.95±0.64 3.22±0.73 3.09±0.70 8.650<0.001 2.98±0.71 3.14±0.68-3.229 0.001 3.25±0.70 3.22±0.74 0.187 0.852 3.08±0.68 3.25±0.77 3.25±0.79 3.27±0.74 3.33±0.69 2.731 0.028 3.12±0.69 3.28±0.77 3.28±0.74 4.192 0.015 3.15±0.74 3.27±0.73-2.212 0.027 3.95±0.77 3.92±0.51 0.297 0.766 3.96±0.52 3.94±0.58 3.96±0.49 3.89±0.55 3.82±0.41 1.749 0.137 3.95±0.53 3.93±0.58 3.90±0.48 0.821 0.440 3.95±0.49 3.90±0.54 1.215 0.225 3.16±0.83 3.05±0.61 0.870 0.384 3.00±0.62 3.08±0.64 3.06±0.68 3.08±0.58 3.05±0.55 0.477 0.753 3.00±0.61 3.12±0.66 3.06±0.61 2.065 0.127 2.98±0.60 3.10±0.62-2.677 0.008 3.21±1.04 2.99±0.80 1.400 0.162 2.84±0.74 3.02±0.87 3.09±0.85 3.05±0.82 3.02±0.68 2.381 0.050 2.85±0.78 3.09±0.85 3.05±0.80 6.142 0.002 2.93±0.78 3.03±0.82-1.714 0.087無有t值759(94.52)44(5.48)P值婚姻狀況已婚未婚離異F值P值關于死亡的過往教育情況從未接觸過沒有專門學習,其他課程有涉及專門學習過相關課程F值P值以往照護臨終患者的經歷3.07±0.69 3.18±0.74-0.984 0.325 3.22±0.73 3.41±0.81-1.681 0.093 3.93±0.52 3.89±0.58 0.494 0.621 3.04±0.61 3.29±0.71-2.623 0.009 2.99±0.81 3.15±0.82-1.290 0.197 521(64.88)261(32.50)21(2.62)3.13±0.71 2.96±0.64 3.41±0.71 7.631 0.001 3.29±0.74 3.08±0.72 3.44±0.79 7.755<0.001 3.91±0.51 3.94±0.55 3.97±0.43 0.330 0.719 3.07±0.64 3.02±0.59 3.16±0.65 0.787 0.456 3.03±0.81 2.91±0.79 3.21±0.99 2.607 0.074 68(8.47)523(65.13)212(26.40)無有t值290(36.11)513(63.89)P值3.27±0.77 3.07±0.69 3.02±0.68 3.388 0.034 3.11±0.68 3.06±0.70 0.941 0.347 3.32±0.75 3.22±0.74 3.20±0.73 0.778 0.460 3.27±0.69 3.21±0.77 1.126 0.260 3.82±0.58 3.94±0.52 3.93±0.51 1.479 0.229 3.90±0.55 3.94±0.50-0.844 0.399 3.16±0.63 3.08±0.61 2.98±0.63 2.973 0.052 3.10±0.66 3.03±0.60 1.626 0.104 3.14±0.89 3.00±0.80 2.93±0.81 1.794 0.167 3.02±0.83 2.98±0.79 0.690 0.490
2.4 臨床護士死亡態度影響因素的多元線性回歸分析以臨床護士死亡態度各維度均分為因變量,將單因素分析中有統計學意義的變量為自變量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α入=0.05,α出=0.10)。啞變量設置:婚姻狀況以“未婚”為參照,婚姻_1為已婚VS 未婚,婚姻_2為離異VS 未婚;以往相關教育情況以“從未接觸過”為參照,教育_1 為“沒有專門學習,其他課程有涉及”VS“從未接觸過”,教育_2 為“專門學習過相關課程”VS“從未接觸過”。多元線性回歸分析顯示,有5 個變量對死亡恐懼得分解釋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2個變量對趨近接受得分解釋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此外,死亡逃避、逃離接受各只有1 個可能的預測變量,分別為婚姻狀況:已婚VS 未婚及工作年限。

表3 臨床護士死亡態度影響因素的多元線性回歸分析(N=803)
3 討論
3.1 臨床護士死亡態度現狀DAP-R 量表主要用于測量人群對死亡的恐懼、逃避及不同的接受態度,各個維度分別反映了被測者在面對死亡時的態度,這種內在心理結構的不同層面,無法以總分來表述人群所持態度。本次調查的三級醫院護士死亡態度各個維度均分在3~4 分之間,提示其各個維度均為中等水平,其中臨床護士死亡態度最趨向于中性接受,得分為(3.92±0.52)分,但低于韓舒等[7]在同類型醫院所做調查中性接受得分(4.31±0.33)分;死亡恐懼、死亡逃避得分則略高于之前國內其他地區醫院調查結果[8-9]。這可能與本研究樣本數量遠多于上述研究有一定相關性,同時也反映了臨床護士面對死亡時尚無法視死亡為生命中自然的一部份,存在害怕、恐懼等負性心理情緒,也逃避思考及討論與死亡有關的事物,對死亡有忌諱回避心理[10]。肖旋等[11]通過訪談了解到面臨死亡對護士來說尤其困難和苛刻,缺乏良好的應對機制會增加其焦慮感。恐懼和逃避可能導致對死亡的否認,這可以解釋為一種防御機制,以對抗接觸死亡過程的影響,使護士能夠正常面對后續的工作。
3.2 臨床護士死亡態度的主要影響因素
3.2.1 年齡和工作年限表2 的數據顯示,年齡較大的護士和臨床工作時間較長的護士更不愿意思考及討論與死亡有關的事物(P<0.05),而且死亡態度趨向于逃離接受。這與國內進行的類似調查結果趨勢一致[12-13],但與陳蓄等[14]的調查結果相反。陳蓄等[14]的調查認為隨著護士年齡以及工作年限的增長,其對死亡持有更為積極的態度。這可能與年齡的增長并不是死亡恐懼的直接原因有關,多元回歸分析的結果初步證實了這一點。對死亡的理解和解釋決定了每個人對死亡的態度,而文化差異導致這種認知的不同。Cicirelli[15]通過分析指出,美國人認為死亡將意味著一個人的成就獲得蓋棺定論,意味著達到了完滿的目標,在這種認識下,可以認為隨著年齡和工作時間的增長,一個人的成就越多,他/她對死亡的恐懼就會越低。中國人因為死亡意味著“遺憾”“不確定性”,面對死亡具有集體回避性[16]。而且隨著年齡的增長,國人往往在家庭以及工作中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活著”本身才能帶來的責任感、滿足感促使人們重生避死,以求超越死亡、尋得人生價值。
3.2.2 婚姻根據表2、表3 結果顯示,擁有過婚姻的護士(包括已婚和離異)相對于未婚護士,其死亡恐懼、死亡逃避兩個維度得分較高(P<0.05)。研究者認為,這初步表明中國現有文化對護理人群總體死亡觀的影響:中國人對死亡“敬而遠之”的擱置回避態度,使得盡情享受當下的年輕人和未婚者用眼前的美好生活沖淡了對死亡的思考,而隨著年齡增長及婚姻帶來的生命延續,人們不得不面臨必將到來的死亡時,反而更容易由于之前對世俗感性生活的沉迷而對死亡產生更為深沉的焦慮[17]。
3.2.3 工作科室與死亡教育表2、表3的分析結果提示,工作經驗是對上述負面死亡態度的保護因素,那些在死亡率較高科室工作的護士其死亡恐懼和死亡逃避的分值較低(P<0.05)。Zheng 等[18]通過系統評價也得出了類似的結果,隨著接觸死亡患者的增加,護士對死亡的焦慮也有所減輕,能夠更好地應對患者的死亡。表2 同樣顯示,以往接受過死亡教育課程是死亡恐懼的另一個重要保護性因素(P<0.05),相關文獻研究結果也初步證實了科學的死亡教育可促使護士的死亡恐懼等負性態度正向化發展[19-20]。
3.2.4 宗教信仰有些研究認為宗教信仰可以降低護士的死亡恐懼[21-22],但本研究提示僅死亡的趨近接受受宗教信仰的影響(P<0.05),考慮因為趨近導向的死亡接受意味著相信有幸福的來生,死亡是通往來生之門,而這通常與宗教信仰有關。但趨近接受并不意味著能減輕死亡恐懼和死亡逃避。表3 顯示,那些擁有宗教信仰的人群其死亡恐懼和死亡逃避得分更高(P<0.05)。本次調查中有宗教信仰者僅為44 名(5.48%),提示宗教信仰在我國國情下很難成為護士死亡態度的保護因素。
3.3 靈性教育或能為改善臨床護士死亡態度創造可能
3.3.1 傳統死亡教育對多年期護士的死亡態度支持作用較弱本次調查結果并不樂觀,這提示必須思考如何針對臨床護士開展真正有價值的、能夠切實幫助護士應對患者死亡對其產生的沖擊及蓄積效應的相關教育。質性研究表明臨床護士尤其是高年資的臨床護士在死亡態度和需求方面更希望獲得心理支持和社會支持,這與在校護生所需要的死亡教育重點是不一致的,前者對死亡相關的習俗、喪親者的反應、臨終以及死亡后相關護理措施已經了解得較為充分[11,23]。我國近些年來對死亡教育課程的構建多以死亡概念、臨終患者及其家屬的護理以及相關倫理法律問題為主,較適用于護理學生或初入職的護理人員,面向因長期面對患者死亡而產生的相關死亡心態或者哲學觀的教育所占比例則較少[24-25]。而護士自身心理體驗表明當其經常遭遇患者死亡,可能會出現強烈的情緒波動和心理影響,包括焦慮、痛苦、應激反應、無助感、挫敗感以及工作疲潰感,并在應對患者死亡時表現出缺乏信心[4,11],這可以歸納為護士的靈性痛苦,而與之相對應的概念是靈性健康[26]。后者可以被界定為個人對生命意義的肯定狀態,了解和肯定自身、他人與環境的價值,與他人和環境和諧相處的能力;擁有內在的資源和力量,以及適應逆境的能力[27]。因此,那些擁有靈性健康的臨床護士將可能對死亡持有更為正向的態度,并最終影響到護士在長期臨床工作中的態度和照護質量。目前尚缺乏專門針對改善護士負性死亡態度的靈性教育,但研究者認為可從目前較為熱門的面向學生的靈性教育和面向護理人員的靈性照護教育(主要用于教育護士如何為臨終患者和孤寡老人提供靈性照護)中分別吸納部分內容,結合護理人員本身的需求,構成獨特的靈性教育模式。
3.3.2 關于改善護士死亡態度的靈性教育的思考靈性作為一種意識能夠促成生命活性,引導自我反思,開啟精神超越,是人生而蘊含的生命潛能和精神傾向[28]。因此,通過靈性教育促進靈性覺醒,進而激發人生而蘊含的生命潛能和精神傾向,將有效幫助護士進一步理解生命的價值和生存的意義,從而改善其死亡觀和死亡態度。靈性教育應有自己獨特的教學目標、教學內容及教學模式。首先,在確定教育目標時一定要去宗教化。許多學者認為靈性與宗教并不等同,也不一定有直接聯系[29],本次的調查研究也證實了宗教信仰并未成為保護性因素。因此,靈性教育的主要目標應該是幫助護士在了解靈性以及靈性覺醒相關概念的基礎上,通過自我覺察,提升靈性,從而能從較高角度思考生命的意義與圓滿,反思死亡對自身的沖擊,并最終尋找到合適的應對策略。其次,教育內容主要包括:靈性的定義與內涵(這將幫助護理人員了解什么是靈與靈性,靈性健康在維持身心健康方面的重要作用);靈性需求及評估方法(幫助護士評估和了解面對死亡時對個人產生的靈性困擾);人文知識的學習(特別是人文經典的學習);死亡意識的覺醒(即以死觀生的學習);靈性自我覺察(通過策略學習,反思自身內在的正性和負性變化);壓力與應對的哲學觀和相關理論(系統學習他人經驗和策略);構建自身應對策略等[27,30]。最后,教學方法應以基于案例分享的團體討論、臨床研討會為主。此外,通過書寫反思日記的自我反省練習、角色模擬以及影視或文學、藝術作品教學,可以提高學習者對生命的了解程度,反思自身對生死的心態,有助于幫助臨床護士培養出切合自身的應對策略。
4 小結
三級醫院護士的死亡態度受到多重因素影響,但目前缺乏行之有效的干預措施。本研究通過對調查結果的深入分析,認為靈性教育有望幫助臨床護士應對遭遇患者死亡時可能出現的負性態度,促進其正向轉化,并最終改善護理人員長期從事臨床工作的積極心態。本研究僅選取無錫市1 所醫院的護理人員進行調查,樣本量較單一,研究結果有待進一步佐證;且受時間限制,靈性教育尚未在臨床護理繼續教育中開展,后續研究可在拓寬研究對象的基礎上,進行干預前后對比,以充分探討護士死亡態度的有效改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