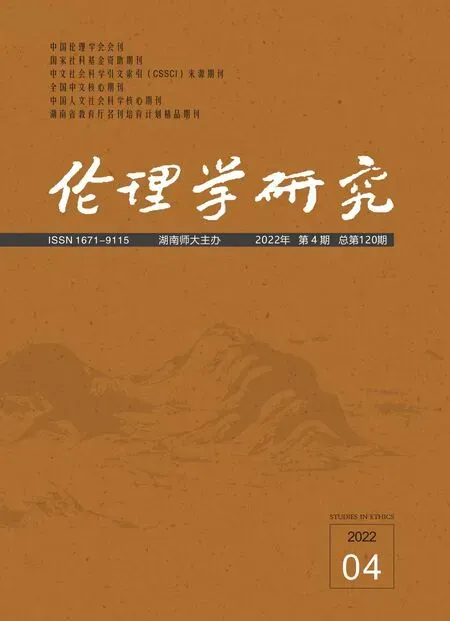康德的道德規范性理論探析
文賢慶
毫無疑問,規范性問題是道德哲學中的核心話題之一。然而,圍繞規范性存在很多爭論,康德主義與休謨主義是這些爭論中的兩種主流思潮。兩種思潮的核心爭論點是我們有什么理由采取某個行動。休謨主義認為,如果說一個行動者有一個理由做某事,就是說一個行動者處在一種可以解釋他所采取行動的狀態中,我們可以稱之為動機性理由;與之不同,康德主義者認為,如果說一個行動者有一個理由做某事,就是說一個行動者被某種要求規定著,這種要求為行動提供了理由辯護,我們可以稱之為辯護性理由。在這兩種關于理由的說明中,休謨主義已經得到了專門的分析①參見WILLIAMS B,Moral Luc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p.114-123;SMITH M,“The Humean Theory of Motivation,”Mind,1987,96(381),pp.36-61;MILLGRAM E,“Was Hume a Humean?”Hume Studies,1995,XXI(1),pp.75-93.。但是對于康德主義②參見KORSGAARD C,The Constitution of Agenc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27-68;DARWALL S,The Second-Person Standpoint:Morality,Respect,and Accountabilit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pp.213-242.,不同的康德主義者只是在某種程度上借助康德的不同思想進行說明,以致出現了很多分歧。基于此,本文試圖深入分析康德本人有關規范性的思想,以期更好地理解康德主義者之間的爭論,我們進而也希望能更好地理解康德主義和休謨主義之間的爭論以及有關道德規范性爭論的實質。通過分析,我們可以發現,不同的康德主義者有關康德規范性思想的爭論源自康德規范性思想的豐富性,然而,康德自身就已經為規范性問題提供了一個整全的解釋。
一、有關自由意志的挑戰
按照康德的思想,人類作為理性存在者,總是共同生活在某種規范性之下。然而,這是如何可能的呢?康德認為,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有賴于我們對普遍必然的道德規則的尋求和建立。事實上,為人類行動尋求一個道德基礎也就是有關人類生活的規范性問題。因此,我們可以說康德有關道德哲學所做的工作就是試圖為人類行動的道德規范性提供一個說明。
康德認為,規范性的主張之所以能夠影響我們是因為我們的理性本質。在《道德形而上學的奠基》的第三部分,康德說道:“意志是有生命的存在者就其有理性而言的一種因果性,而自由則是這種因果性在能夠不依賴于外來的規定它的原因而起作用時的那種屬性。”[1](446)①對康德著作的引用都將以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 的頁碼為標準。對康德有關實踐哲學著作的引用源自以下版本:KANT I,Practical Philosophy(The Cambridge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Immanuel Kant),trans.&ed.by GREGOR M J,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在本文的引用上,Ground work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使用縮寫G,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使用縮寫Cr。在這里,康德表明意志是自由的,它通過自身就可以采取一個行動。而且,康德進一步說道:“既然一種因果性的概念帶有法則的概念,按照法則,由于我們稱為原因的某種東西,另一種東西亦即結果必然被設定,所以,自由盡管不是意志依照自然法則的一種屬性,但卻并不因此而是根本無法則的,反而必須是一種依照不變法則的因果性,但這是些不同種類的法則;因為若不然,一種自由意志就是胡說八道。”[1](446)盡管自由意志能夠獨立于外在原因而采取一個行動,然而它也必須遵守某種法則。那么,這種自由意志的法則是什么呢?
作為獨立于外在原因的自由意志,它意味著意志自身就是自己的原因。因此,自由意志能夠為自己給出法則。至于法則的內容,我們將在下節討論。就目前的分析而言,我們需要確定的是,康德想要表達:一種規范性的主張源于我們的自由意志。按照康德的觀點,“意志不是僅僅服從法則,而是這樣來服從法則,即它也必須被視為自己立法的,并且正是因此緣故才能服從法則(它可以把自己看作其創作者)”[1](431)。相比于意志為自己給出法則,其他東西都是意志的他律,在這個意義上,意志是不自由的。康德說:“如果意志……在它的某個客體的性狀中,尋找應當規定它的法則,那么,在任何時候都將出現他律。在這種情況下,就不是意志為它自己立法,而是客體通過其與意志的關系為意志立法。”[1](441)按照康德的這種觀點,規范性的法則只能因為意志的自律而給出法則,而任何其他的意志他律都不能給出規范性的法則。科斯嘉說道:“自由意志面臨的問題是,意志必須有一個法則,但因為意志是自由的,這個法則必須是它自身的法則。沒有什么東西能夠決定這個法則必須是什么。它不得不是的所有一切就是一條法則。”[2](98)這也就是說,對康德而言,自由意志的法則就是自律的法則。在這個意義上,規范性的權威只能來源于我們的自由意志強加給我們自身的法則②關于康德的自律概念,學界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解釋。以平卡德為代表的研究者認為,自律提及的“自我立法”會導致自律概念陷入難以解決的悖論(參見PINKARD T,German Philosophy 1760-1860:The Legacy of Ideali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226);以科斯嘉為代表的研究者認為,自律提及的“自我立法”實際指的是道德主體的“自我構成”,并不會產生悖論(參見KORSGAARD C,The Sources of Normativi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100)。在這里,筆者重在揭示康德本人通過自律概念對行為者作為行動主體的強調,強調人因為擁有自由意志而能夠自己立法并且守法的能力。基于此,我更愿意接受科斯嘉的觀點。。在這里,康德其實表達的是,任何能夠作為我們行動規范性的東西都必須通過我們意志的自律才能夠成為行動者的東西。
但是,僅僅因為自由意志是自我強加的,我們就說它是道德規范性的來源是很奇怪的。在這個意義上,自由意志僅僅表示我們人類作為自由的行動者能夠作出自由的選擇。在選擇行動中,我們作為行動主體可以選擇不同的規則作為我們的行動原則。例如,如果我通過撒謊可以獲得錢,那么我就會撒謊。很顯然,認為撒謊作為一個原則具有規范性的權威是十分荒謬的。如果這種情形發生了,那么根本就不存在道德與否的區別了。因此,十分明顯,我們不能僅僅因為我們擁有了自由意志就說我們具有了道德規范性的權威,我們必須進一步考慮自由意志法則所包含的內容。康德認為這種對內容的考慮就是有關道德法則的可普遍化,在康德看來,正是這種可普遍化性造就了道德規范性的權威。
二、絕對命令的實踐使用
然而,因為道德法則是關于意志或實踐理性的一條原則,那么當道德法則在關聯于主觀欲求表象為一個命令時,它具有什么樣的形式呢?按照福特的看法,“如果我們發現在行動和目的之間并不存在著正確的關聯——要么是無法取得他想要的(或做他想要的),要么不是在所有可能的方法之中最為合適的”[3](159),那么關于行動的這個命令就只能是一種假言命令。福特認為行動者的主觀欲求決定了命令的形式。然而,康德認為這個命令必然是一個定言命令,而不可能是假言的。在康德看來,意志關聯于行動給出的命令是通過人的理性本質給出的,因此意志不可能關聯于對某個目的的實現或對某種欲求的滿足而通過某種外在的東西被決定,道德的法則只能是基于自由意志自身而被給出,這樣的道德法則因此必然是定言的、無條件的,這個無條件的命令的唯一形式只能是“要只按照你同時能夠意愿它成為一個普遍法則的那個準則去行動”[1](421)。在這里,定言命令是一個形式結構上的可測試性原則。按照康德的看法,定言命令可以排除出于主觀欲求的那些行動準則,從而在可允許的行動上遭受確定的限制。然而,定言命令是怎樣應用于我們行動的實際經驗的呢?
康德詳細地解釋了定言命令的應用。“由于結果的發生所遵循的法則的普遍性構成了真正說來在最普遍的意義上叫作自然的東西”[1](421),所以康德說定言命令也可以被表述為:“要這樣行動,就好像你的行動的準則應當通過你的意志成為普遍的自然法則似的。”[1](421)我們可以把它稱為“自然法則公式”(下文縮寫為FLN)。康德試圖表明,定言命令給行動強制性地賦予了一種具有規范性權威的普遍性。康德是怎樣給出這種論證的呢?我們可以通過《實踐理性批判》中“論純粹實踐判斷的類型”這一節把握其中的要點[4](67-71):
(1)一個規則控制下的行動要求實踐判斷。
(2)作為自由意志的法則,純粹理性的實踐規則可以不依賴于任何經驗的東西而被確定;相反,所有處在實踐法則檢測之下的可能行動都僅僅是偶然經驗的。
(3)不像理論理性的自然法則通過想象力可以為圖型給出感性直覺,純粹理性的實踐規則不能為純粹的知性概念給出感性直覺。
(4)在感性世界中,一個處在純粹實踐法則之下的可能行動并不關注這個行動能夠作為感性世界中的一個事件之可能性。
以“2.3.2”項下擬合模型為目標函數,使用Matlab 2014b軟件的GADS工具箱,采用遺傳算法求解指標成分的最優提取工藝條件。遺傳算法工具GUI參數設置見表5;隨機搜索10次,結果見表6。由表6可知,10次隨機搜索結果的變異范圍較小,對目標函數最佳值的逼近程度較好。因此,取10次隨機搜索的平均水平即60.872 000%乙醇提取3.105 564 h、液料比15.719 832∶1(mL/g),預測綜合評分為2.895 433。
(5)盡管實踐判斷是屬于理性的理論應用,即評估按照因果性法則而行動的可能性;但是通過法則自身作為圖型對意志的確定聯結著關于條件的因果性概念。
(6)道德法則(實踐規則)應用于自然對象的唯一方式就是通過知性。
(7)實踐規則只有通過表現為自然法則的形式才能夠把感性直覺表現為一條自然法則。定言命令通過轉化為FLN 能夠證實在經驗世界中發生的特殊的行動準則。
綜上所述,康德認為定言命令通過FLN 能夠檢測直接發生在經驗世界中的行動準則。通過表明自由意志的自律所具有的自我強制和FLN 的可檢測性,康德賦予了道德法則對經驗行動所具有的普遍規范性權威。
三、絕對命令的可檢測性來源于自相矛盾的邏輯形式嗎?
現在,我們已經確定道德法則作為普遍法則具有了規范性權威。然而,道德法則加諸經驗行動的普遍規范性權威到底意味著什么呢?按照康德的觀點,出于理性本質的緣故,理性強加給自己的規范性權威的唯一限制就是任何理性規則都不能自相矛盾。需要注意的是,理論理性和實踐理性之間存在著一個比較大的差異:作為理論理性,形式邏輯的一致性是判斷理性唯一重要的元素,然而,作為實踐理性,形式邏輯的一致性和經驗元素一起對理性進行評價①盡管康德意識到我們不能總是在不自相矛盾的前提下使得一個準則成為普遍自然法則,但是他拒絕直接承認我們應當把這種檢測和某些經驗條件相聯結。這是因為康德拒不接受經驗條件是道德的基礎。因為只有邏輯一致性和經驗條件一起才能夠解釋道德的規范性,所以十分清楚的是,對康德而言,對規范性問題的回答不能依賴于純粹的邏輯一致性。。因此,形式邏輯的一致性不可能是自由意志行動唯一的規范性來源②在科斯嘉看來,絕對命令只是提供了普遍的法則,但并沒有解決自由意志法則在什么范圍有效的問題,通過絕對命令檢測的法則既可能依據欲求而行動,也可能依據理性而行動。因此,從經驗內容的角度來看,道德法則還需絕對命令依據普遍理性而行動,才能為自由意志給出確定的范圍,這要求把人性作為經驗內容考慮進去,所以科斯嘉認為需要“實踐同一性”的概念(參見KORSGAARD C,The Sources of Normativi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p.99-100)。但在康德本人看來,人因為是理性的存在者而天生就是能夠自律的存在者,這其實是一個理性的事實。因此,對康德而言,絕對命令就是道德法則,自由意志讓我們受制于絕對命令,也就是讓我們受制于道德法則。。
康德表達得十分清楚,意欲某種主觀準則成為普遍法則將會導致自相矛盾。康德描述了四種不同的義務,它們“劃分為對我們自己的義務和他人的義務,劃分為完全的義務和不完全的義務”[1](421)。
(1)第一種情形是關于某人自己的完全義務:一個行動者即使在他的生命遭受病痛折磨時也不能自殺。康德認為“如果一個自然的法則是憑借以敦促人增益生命為使命的同一種情感來毀滅生命本身,則這個自然就與自身矛盾,從而就不會作為自然存在”[1](422)。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并非理性的一致性,至少不僅僅是理性的一致性,而是同時包括了自然目的,二者一起構成了檢測矛盾的標準。
(2)第二種情形是關于他人的完全義務:明知自己無法償還卻仍然向他人借錢并承諾說償還。按照康德的觀點,“因為一個法則,即每一個人在認為自己處于困境時都可以承諾所想到的東西,卻蓄意不信守之,其普遍性就會使承諾和人們在承諾時可能懷有的目的本身成為不可能,因為沒有人會相信對自己承諾的東西,而是會把所有這樣的表示當作空洞的借口而加以嘲笑”[1](422)。這也就是說,在這種情形中,實踐行動的準則就會被取消,因此它就會是自我否認的。
(3)第三種情形是關于某人自己的不完全義務:即使一個行動者有能力發揮和增長自己的才干,他卻不作為而放任享樂。在這里,康德說,“作為一個理性存在者,他必然愿意自己里面的所有能力都得到發展,因為它們畢竟是為了各種各樣的意圖而對他有用,并被賦予他的”[1](423)。很明顯,康德認為某些自然目的是評價性的標準。
(4)第四種情形是關于他人的不完全義務:一個行動者若自己事事如意,無須求助別人,就認為自己不需要幫助別人。在這種情形中,康德考慮說,“一個決定這樣做的意志就會與自己抵觸,因為畢竟有可能會發生不少這樣的情況:他需要別人的愛和同情,而由于這樣一個出自他自己的意志的自然法則,他會剝奪自己得到他所期望的協助的一切希望”[1](423)。在這里,這個準則是否自相矛盾則取決于特殊的經驗或環境。
綜上所述,康德試圖證明實踐理性必須且能夠通過定言命令的檢測,這也就是說,理性能夠給出絕不自相矛盾的法則。然而,這種對自相矛盾的評價不僅源自理性的形式邏輯的一致性,而且總是聯結著基于自然或經驗世界的某種目的。因為實際的義務總是聯結于某種目的,對我們來說,十分重要的是,我們能夠把一條行動的準則意欲為一條普遍法則。為了檢測一條準則是否能夠成為一條不自相矛盾的普遍法則,我們需要滿足這樣一個前提,即“如果不能潛在地把一條準則意欲為一條普遍法則,那么一個人就不能意欲它”[5](538)。然而,通過對上述案例的分析,康德表明,某些行動的準則不能沒有矛盾地被思想為一條自然的普遍法則,“愿意它們的準則被提升到一個自然的普遍法則,這畢竟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樣一個意志就會與自己矛盾”[1](424)。因此,當康德宣稱意愿一條準則成為一條普遍的法則會導致自相矛盾時,這并不會讓我們有理由相信,他認為一個人由于自相矛盾的緣故而必須是道德的,對自相矛盾的檢測并不完全證成道德規范性。
四、道德法則的意識
很明顯,當康德說道德法則是合理性的命令時,這表明他試圖基于人的理性給出有關道德規范性現象的解釋。然而,到目前為止,康德通過訴諸自相矛盾的形式的不一致性作為道德規范性的標準并沒有成功。那么,就康德的思想來說,我們還能不能進一步回答有關道德規范性的問題呢?
當我們在討論上面四個案例時,康德承認說如果我們通過理性法則來衡量這些案例,那么我們將會發現意愿中的矛盾。然而,我們知道必須添加相關的自然目的。那也就是說,一方面,一個意愿行動不僅應該被看作是受理性原則主導的;另一方面,它也應該受到自然目的的檢測。現在,十分清楚的是,矛盾并不是因為理性的形式邏輯的不一致性,而是來源于一個意志的主觀準則對意志的普遍法則的對抗。
在這里,看到以下一點是十分重要的,即矛盾并不是因為把一條不道德的準則意愿成一條普遍法則會自相矛盾,相反,這個矛盾是因為“偏好對理性規范的對抗”[1](424)。很明顯,康德用理性規范來描述道德法則的絕對必然性,道德法則是理性的真正使命。對人類而言,理性作為一種能力是我們的本質,我們能夠且必須出于理性規范而遵守道德法則。不過,我們也擁有感性的本質去欲求一個特殊的或偶然的目的。一種自相矛盾或不合理性來自我們意志行動的選擇,它不僅受到我們理性本質的引導,而且也受到我們感性偏好的影響。盡管意志的實踐原則應當遵循道德法則,但它也總是受偏好的影響,基于偏好而意愿一條不道德的準則雖然并不一定是一致的但卻是可能的。
現在,我們發現道德法則具有理性強加給自己的規范性權威并不是來源于任何的推理規則都不能自相矛盾這一思想。那么,道德法則擁有規范性權威到底來源于哪里呢?康德宣稱我們通過常識就可以知道道德法則,他說,“(一旦我們為自己擬定了意志的準則),道德法則是我們直接意識到的”[4](29)。這也就是說,道德法則是一個理性事實。按照這種觀點,理性應當產生這樣一種道德法則,即作為確定意志行動基礎的一種絕對必然性,道德法則是“不讓任何感性條件占上風的、確實完全獨立于它們的決定根據,所以道德法則就徑直導致自由概念”[4](30)。
道德法則的規范性來源于自由意志能夠選擇反對欲求準則的道德法則的能力。在這個意義上,規范性取決于被欲求影響的自由意志行動采取原則的客觀必然性。現在,理解康德規范性思想的關鍵轉化為以下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自由意志行動采取原則的客觀必然性”是什么意思;第二個問題則是如何理解客觀必然性和欲求影響之間的關系。接下來我們將回答這兩個問題。
五、尊重道德法則
康德認為只有遵循道德法則的行動才具有內在價值。這意味著只有在主觀準則同時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前提下,意志行動才能夠具有道德價值。如果道德法則直接確定意志,那么就存在著對情感的一個主觀的消極影響。這也就是說,有一種拒絕感性的沖動或者阻止主觀準則與道德法則相沖突的性情。在這個意義上,道德法則直接確定意志的事實是一種道德情感,但它僅僅是一種消極的情感,我們可以稱之為道德謙卑。不過,在另一方面,因為道德法則能夠遵循我們心靈中的自我控制,所以它也具有一種積極的力量。道德法則因為這種積極的力量而變成了一個尊重的對象。因此,對道德法則的尊重為遵循道德法則提供了一種興趣,這種興趣不是某種對于道德的動因,而是道德自身因為被看作純粹實踐理性而在主觀上被看作是一種動因。簡而言之,康德宣稱道德情感與道德法則的意識是一起被認識的。
出于對道德法則的尊重,我們擁有了遵循道德法則的一種實踐興趣。這種興趣拒絕偏好,并把道德法則確定為自律意志行動的基礎。因此,對道德法則的尊重使得我們處在某種責任之下,與此同時,它向我們展示了人類理性本質的“尊嚴”和“崇高”。作為一種消極的力量,道德法則直接決定意志的事實是擊敗自欺欺人的情感的結果。意志行動由于遵循道德法則的緣故而是實踐的,并且排除了偏好的決定性基礎。在這里,有一點值得注意,對一個意志行動而言,它總是“有一種以任何方式被推動而至活動的需要,因為一種內在的障礙遏止這個活動”[4](79)。這也就是說,一個意志行動的動因來源于自發性和我們心靈中的規則之間的關系。作為人類,在本質上我們既是感性的,也是理性的,“存在者意愿的主觀性質并非自發地符合實踐理性的客觀法則”[4](79)。它總是加諸遵循道德法則的意志行動之上的一種強制性。
作為一種積極的力量,道德法則直覺決定意志就像尊重道德法則作為純粹的理性法則把偏好限制在道德法則之下一樣。作為有理性的生命存在者,自由是其因果性屬性,這種因果性只能通過純粹的法則形式而被決定。自由意志具有成為自己的法則的屬性。因此,意志自由就是遵循道德法則的意志行動。人類因為理性具有遵循道德法則的能力而具有內在價值,那么,自由意志就因為它自身而具有內在價值。現在,十分清楚的是,尊重道德法則的意志行動同時也是來源于人類理性本質的意志自律,人性因為為自己給出道德法則并且尊重它而具有尊嚴。
基于上述分析,自由意志的自律就是遵循道德法則的意志行動。一方面,因為消極情感,一個自由意志把自己安置在某種必然性下面;另一方面,因為積極力量,一個自由意志擁有了一種內在價值。這也就意味著,自由意志的自律或遵循道德法則的意志行動回答了為什么某些人必須是道德的這個規范性問題。作為人類,任何實踐行動只有通過自由才是可能的。通過自由,我們出于理性本質而能夠遵循道德法則,而只有遵循道德法則的意志行動才具有內在價值。但是,因為我們在內心中也總是受偏好影響的,所以這種遵循對于人類而言就總是一種強制性。
六、基于自由意志的道德規范性
康德說:“道德性是行動與意志自律的關系。”[1](439)人類心靈中的意志自律是通過意志行動的準則可能給出普遍法則的。從主觀的角度來說,盡管自由意志總是受到偏好的影響,但它對意志自律原則的依賴性就是責任。從客觀的角度來說,自由意志普遍法則因為理性而是必然的。因為這種客觀必然性,意志的普遍法則擁有了內在價值,同時,我們人類在人性中表現了某種崇高與尊嚴。所以,普遍法則擁有了道德規范性權威,我們人類應該遵循道德法則。
現在,回顧我們的分析:按照康德的觀點,作為一種理性存在者,我們人類通過自由意志擁有某種道德能動性,我們通過直覺就可以意識到道德法則。然而,盡管自由意志是自律的,但它卻僅僅是一種純粹形式并因而具有一種可檢測性。實踐理性只能通過理解理性的理論使用來評估遵循因果性法則的可能性。因此,通過訴諸邏輯形式的自相矛盾的檢測并不能使絕對命令成為引導行動有效的道德規范性主張。康德認為我們能夠因為理性本質而意識到道德法則,這就意味著道德法則可以直接決定意志。因為只有遵循道德法則的意志行動才具有內在價值,所以對道德法則的興趣為我們給出了尊重道德法則的情感。這也就是說,自我立法的能力通過自由意志而具有內在價值;自由,作為人類理性本質的一種屬性,使得人性有了內在價值。
關于“我們為什么應當是道德的”這個規范性問題的回答,康德認為并不是因為絕對命令的可普遍化的檢測性,而是因為通過尊重道德法則的情感對內在價值的認可,我們應當是道德的。就康德的立場而言,對自由作為有理性的人類的基本屬性的認可是回答規范性問題的起點,然而,康德承認,我們確實不知道自由作為一個先天綜合概念在我們的實踐領域是如何可能的。但是,只要我們能夠從一種自然主義的觀點認識到自由的能力,我們就可以拒絕他的先驗限制。我們可以接受康德有關規范性問題的回答源于我們人類具有的某種崇高和尊嚴。當然,也許這并非我們規范性的唯一來源,但它卻必然是最本質的一個來源。
很顯然,就康德的理論而言,絕對命令或道德法則作為一種可檢驗程序表現的是一種邏輯結構的規范性。如果絕對命令或道德法則沒有能夠關聯我們的人性而表現出一種尊重的情感,那么它就不可能解釋規范性所需要的實踐性動機。只有當絕對命令或道德法則關聯人性的情感時,這種邏輯結構的規范性才被賦予了一種價值和興趣,才相關于我們的生活意義并給出了規范性的辯護。然而,我們不得不承認,康德為道德規范性提供的辯護十分有限。盡管康德可以通過把意志和理性相關聯而為行動者的行動理由提供客觀規范性的來源說明,但是這種客觀性只是在結構上辯護了客觀性。一旦它試圖為行動者給出實際生活中的道德規范性,就無能為力了。因為從根本上來說,實際生活中的道德規范性需要我們討論具有理性和自律的主體如何從應然走向實然,這要求我們必須考慮主體間性的問題,而這也就是為什么黑格爾及稍后的一些哲學家都會從單純對人的理性和自律的強調中走向主體間的承認和社會規范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