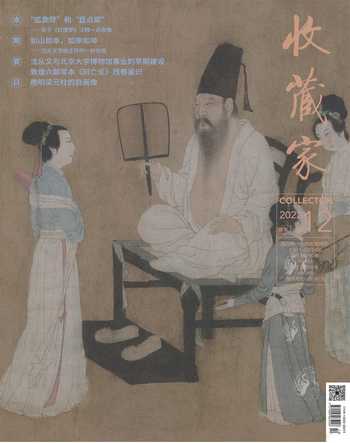沈從文四十七年前的書法饋贈

2022年10月19日,我忽然接到沈從文先生于1975年書贈我的草書條幅,已時隔四十七年。
釋文如下:
郁郁澗底松,離離山上苗。
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
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
地位使之然,由來非一朝。
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
馮公豈不偉,白首徒見招。
郁郁園中柳
青青河畔草,郁郁園中柳。
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
娥娥紅粉妝,纖纖出素手。
昔為倡家女,今為蕩子婦。
蕩子行不歸,空床難獨守。
試擬雅宜山人體書古詩二章,筆拙手生難達意,畫虎類犬,勢所必然!上官碧,時年七十進四。作書待及格,似尚遙遙無期也。贈楊璐弟。乙卯深秋,同在北京。(圖1)
所書古詩是左思的《詠史》及古詩十九首中的《青青河畔草》,詩中“地勢使之然”,沈先生寫為“地位使之然”;“白首不見招”寫為“白首徒見招”。沈先生素愛這兩首詩,曾在明代故紙上用草書小字抄錄送我。題跋中“雅宜山人”是元代書法家王寵,最善章草;上官碧,是先生三十年代的筆名;乙卯,就是四十七年前的1975年。先生章草極有功力,作家荒蕪稱贊“沈老章草為當世第一”,書跋中先生的自謙之語,令我警策。先生書此條幅時,是在相慶書稿的完成?是對我前路的喟嘆和希冀?抑或是對世事的比擬?……四十七年的風云已過,今人或不得而知。那畢竟是在國家動蕩的“文革”期間,無論倚勢平步的金日?、張安世,還是懷才不遇的馮唐,今天都是歷史陳跡。
沈從文先生于1972年從丹江五七干校回京,住在東堂子胡同51號一間小屋,仍號“窄而霉齋”。次年先生教我簪筆抄書:將其草書手稿《中國古代服飾資料》(當時書名)用毛筆謄錄為行楷,先生稱作“司書生”。先生對書稿精益求精,在謄抄件上屢次增刪勾乙,以致滿紙字如蜂聚蟻斗,寫滿了就在稿紙邊貼紙再寫;我便再次謄抄,循環往復。有時見到先生的孫女沈紅來送飯,先生便會留我共餐。略有閑暇時,沈先生也會談及書法,他說:“我們‘出身相同,都是(學)《草訣歌》《十七帖》《急就章》出身,所以我們草書是一個路子。”當時我們書面交流全用草書。一次,沈先生竟背出《續草訣》的一串句子,我聞所未聞,甚為驚訝,他說是明代大內刻本。四十年后,我在故宮遍查無果,最后居然在海外找到了《續草訣》《后草訣》,是萬歷皇帝朱翊鈞所書,確為明代大內刻本,遂印入《草書歌訣匯編》一書中。這是后話了。“司書生”工作雖在1974年初因社會情況暫有停頓,1975年終于完成。沈先生此時書寫兩首古詩條幅贈我,也許是一種紀念吧?只是造化弄人,四十七年后收到,令人感動,回憶往昔,渾如一夢。
寄贈珍貴條幅的是沈先生親戚――蘇州張先生,他告訴我,是沈紅告訴他我的住址,寄出條幅的同時用手機微信發來此書法照片,當時我正和徐俊、趙珩等幾位出版社社長、總編飲茶小聚,《收藏家》力約稿件,盛情難卻,故贅述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