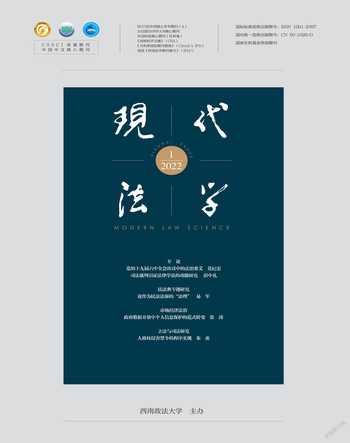論未辦理抵押登記時不動產抵押合同的效力
摘 要:當事人訂立抵押合同的目的在于設立抵押權,未辦理抵押登記的抵押合同無法在當事人之間產生設立保證或者其他非典型擔保的效力。抵押人未按照約定辦理抵押登記時的違約損害賠償責任采用嚴格責任原則,其違約損害賠償的范圍限于債權人未從債務人處獲得清償的債權數額,同時,該責任受到當事人約定的擔保范圍、抵押權能夠設立時抵押人應當承擔的責任范圍以及違約責任減輕規則的限制。抵押人未辦理抵押登記的,債權人有權選擇請求抵押人承擔繼續履行的責任與違約損害賠償責任,并有權選擇請求債務人或者抵押人承擔責任。
關鍵詞:抵押權;抵押合同;抵押登記;違約責任
中圖分類號:DF521? 文獻標志碼: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22.01.08
一、問題的提出
依據《民法典》第402條的規定,不動產抵押權的設立“應當辦理抵押登記”①,否則,即便抵押合同已經生效②,也無法設立抵押權。但問題在于,在當事人未辦理抵押登記的情形下,當事人所訂立的抵押合同具有何種效力?《民法典》第215條規定:“當事人之間訂立有關設立、變更、轉讓和消滅不動產物權合同,除法律另有規定或者當事人另有約定外;合同自成立時生效;未辦理物權登記的,不影響該合同效力。”該規則也當然適用于不動產抵押的情形。也就是說,未辦理抵押登記并不影響抵押合同的效力。③進一步而言,在當事人訂立的抵押合同生效后,如果抵押人未按照約定辦理抵押登記,則債權人有權請求抵押人按照約定辦理抵押登記(及繼續履行抵押合同)[《〈民法典〉擔保司法解釋》第46條第1款。],從而取得抵押權。在抵押人無正當理由拒絕辦理抵押登記時,債權人也有權依法請求抵押人承擔其他違約責任。[劉貴祥:《擔保制度一般規則的新發展及其適用——以民法典擔保制度解釋為中心》,載《比較法研究》2021年第5期,第57頁。]
可見,關于未辦理抵押登記時不動產抵押合同的有效性,并不存在很大的爭議。《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有關擔保制度的解釋》(以下簡稱《〈民法典〉擔保司法解釋》)第46條進一步對該合同的效力作出了規定,該條第1款規定了債權人請求抵押人繼續履行合同的規則,該條第2、3款區分不能辦理抵押登記的不同情形,分別規定了抵押人的責任。該條規定為解決實踐中出現的不動產抵押合同糾紛提供了法律依據,但從理論和實踐層面看,對于未辦理抵押登記時,不動產抵押合同的效力,仍有如下問題需要進一步探討:一是未辦理抵押登記時,抵押合同能否在當事人之間產生設定擔保的效力?換言之,在抵押人未辦理抵押登記的情形下,雖然無法有效設立抵押權,但當事人訂立抵押合同時有設定擔保的意愿,此時,能否認定在當事人之間成立擔保關系?二是在抵押人未按照約定辦理抵押登記時,如何認定其對債權人的違約損害賠償責任?例如,抵押人的違約責任采取何種歸責原則?如何界定抵押人違約損害賠償的范圍?抵押人承擔違約損害賠償責任的前提是造成債權人損失,如何認定債權人的損失?在債權人的損失大于抵押財產的價值時,抵押人承擔違約損害賠償責任的范圍是否以抵押財產的價值為限?等。三是抵押人違約損害賠償責任規則應當如何具體適用?在抵押人未按照約定辦理抵押登記時,債權人請求抵押人承擔違約損害賠償責任與繼續履行責任是否存在順序限制?抵押人違約損害賠償責任與債務人責任之間的關系如何?在債務人未履行到期債務時,抵押人所承擔的違約損害賠償責任究竟是一種補充責任,還是連帶責任?本文擬從《〈民法典〉擔保司法解釋》第46條規定出發,對上述問題進行探討。
二、抵押人未辦理抵押登記需承擔擔保責任之質疑
關于未辦理抵押登記的不動產抵押合同是否具有設定擔保的效力,有學者主張,對不動產抵押而言,未辦理抵押登記雖然不能有效設立不動產抵押權,但當事人訂立抵押合同的合意之中包含了雙方設定擔保的合意時,應當在當事人之間成立擔保關系,抵押人應當在抵押物價值的范圍內承擔保證責任。[石冠彬:《民法典應明確未登記不動產抵押合同的雙重債法效力——“特定財產保證論”的證成及展開》,載《當代法學》2020年第1期,第35-36頁。]還有學者主張,對未辦理抵押登記的不動產抵押合同而言,債權人除享有登記請求權外,還享有擔保權,此種擔保權在性質上屬于債權,是介于保證與抵押權之間的非典型擔保。[劉延杰、王明華:《未辦理抵押權登記時抵押人應承擔何種責任》,載《人民司法》2013年第3期,第56頁。]
在我國司法實踐中,也有一些人民法院認為,未辦理抵押登記的抵押合同具有設立擔保的效力。依據所設立的擔保方式的不同,其具體又可以分為如下幾種做法:一是認定該合同具有設立非典型擔保的效力,即未辦理抵押登記的不動產抵押合同將在抵押人與債權人之間成立非典型擔保。債權人雖然不享有優先受償權,但抵押人仍應當以抵押物的價值為限對債務人的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張家港市金源世紀家居市場有限公司、張家港金茂名置業有限公司與何陽房屋租賃合同糾紛案”,江蘇省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8)蘇05民終9376號《民事判決書》;“葉紅陽訴杜朋、華福明等追償權糾紛案”,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2016)浙民終228號《民事判決書》;“武梅枝與榮成市豫中實業有限公司等民間借貸糾紛上訴案”,山東省威海市中級人民法院(2017)魯10民終965號《民事判決書》。]二是認定該合同具有設立保證的效力。例如,有的人民法院認為,從鼓勵交易、節約交易成本出發,應當將未辦理抵押登記的抵押合同解釋為有效的擔保行為,并且該擔保在性質上應當屬于連帶責任保證。例如,在“黨某某與李某某、高某文等民間借貸糾紛案”中,二審人民法院即認為,未辦理抵押登記的抵押合同雖然無法有效設立抵押權,但抵押人仍應當在約定的擔保財產價值范圍內對債務人的債務承擔連帶責任保證責任。[江蘇省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21)蘇04民終862號《民事判決書》。類似立場可參見“周興起與樊華民間借貸糾紛上訴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一終字第76號《民事判決書》;“楊崢訴張艦等民間借貸糾紛案”,河北省廊坊市中級人民法院(2018)冀10民終1267號民《事判決書》;“劉峻瑞等訴新疆石河子農村合作銀行借款合同糾紛案”,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2354號《民事裁定書》。]當然,也有人民法院認為,此種保證在性質不應當屬于連帶責任保證,而應當屬于一般保證。[“湖北通環混凝土實業有限公司、許裕典民間借貸糾紛案”,湖北省咸寧市中級人民法院(2020)鄂12民終72號《民事判決書》。]
從《〈民法典〉擔保司法解釋》第46條規定來看,該條第2、第3款區分了不能辦理抵押登記是否可歸責于抵押人,并分別規定了抵押人的責任:如果因不可歸責于抵押人的原因導致不能辦理抵押登記,抵押人獲得了代位物,則其需要在代位物的范圍內承擔責任,該規定參照適用《民法典》第390條的規定,承認了抵押人賠償責任的物上代位性[林文學:《不動產抵押制度法律適用的新發展——以民法典〈擔保制度司法解釋〉為中心》,載《法律適用》2021年第5期,第22頁。];如果因可歸責于抵押人的原因導致不能辦理抵押登記,則抵押人需要在約定的擔保范圍內承擔責任。該條雖然沒有明確將抵押人的責任規定為擔保責任,但從該條的行文表述來看,其對抵押人的責任似乎也采取了擔保責任的立場。
可見,理論界與司法實務界均有觀點主張,未辦理抵押登記的抵押合同具有設立擔保的效力,只是該擔保在性質上究竟屬于非典型擔保還是保證,屬于一般保證還是連帶責任保證,存在一定的爭議。筆者認為,上述基本立場值得商榷,未辦理抵押登記的不動產抵押合同無法在當事人之間產生設立保證或者非典型擔保的效力,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抵押屬于法定的擔保類型,而不屬于非典型擔保,無法適用非典型擔保的規則認定抵押合同的效力。主張未辦理抵押登記的抵押合同具有設立擔保效力的重要理由在于,未辦理抵押登記的不動產抵押合同雖然無法成立抵押權,但可以成立非典型擔保。所謂非典型擔保,顧名思義,就是法定擔保類型之外的擔保。[崔建遠:《對非典型擔保司法解釋的解讀》,載《法治研究》2021年第4期,第3-4頁。]依據《民法典》第388條的規定:“設立擔保物權,應當依照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規定訂立擔保合同。擔保合同包括抵押合同、質押合同和其他具有擔保功能的合同。”該條中的“其他具有擔保功能的合同”就包含了設定非典型擔保的合同[中國審判理論研究會民事審判理論專業委員會編著:《民法典物權編條文理解與司法適用》,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415頁。],這實際上是承認了非典型擔保的效力。對不動產抵押合同而言,當事人在設定抵押合同時,顯然也具有設定擔保的意愿,如果將未辦理抵押登記的不動產抵押合同認定為設立非典型擔保的合同,則其將產生設立擔保的效力。
但事實上,不動產抵押合同不屬于《民法典》第388條所規定的“其他具有擔保功能的合同”,其也無法產生設立非典型擔保的效力,主要理由在于:一方面,從《民法典》第388條規定來看,“其他具有擔保功能的合同”是指抵押合同、質押合同之外的合同,如融資租賃合同、保理合同、所有權保留買賣合同以及其他擔保合同。[王晨:《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草案)〉的說明——2020年5月22日在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附草案說明)》,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262頁。]而抵押并不屬于非典型擔保,而是《民法典》物權編所規定的典型擔保類型,在文義上應當將抵押合同排除在“其他具有擔保功能的合同”的范疇之外。另一方面,依據《民法典》第388條規定,抵押合同、質押合同和其他具有擔保功能的合同雖然均具有設立擔保物權的功能,但設立典型擔保的合同(即抵押合同、質押合同)與設立非典型擔保的合同(即其他具有擔保功能的合同)在功能上仍存在一定的區別。如果認定未辦理抵押登記的抵押合同具有設立擔保物權的效力,這不僅不當擴張了抵押合同的效力,導致這兩類合同關系難以區分,而且可能導致不同類型擔保物權的混淆。
第二,認定未辦理抵押登記的抵押合同具有設立擔保的效力,不僅是不尊重當事人的意愿,反而是對當事人意愿的一種背離。前述觀點主張,由于當事人在訂立抵押合同時具有設立擔保的目的,在未辦理抵押登記、無法設立抵押權的情形下,承認抵押合同具有設立擔保的效力,是對當事人設立擔保意愿的尊重。[石冠彬:《民法典應明確未登記不動產抵押合同的雙重債法效力——“特定財產保證論”的證成及展開》,載《當代法學》2020年第1期,第35-36頁。]在司法實踐中,有的人民法院也持此種立場。例如,在“武梅枝與榮成市豫中實業有限公司等民間借貸糾紛上訴案”中,人民法院認為,對不動產抵押而言,未辦理抵押登記不影響合同效力,當事人所訂立的抵押合同仍然依法有效。同時,應當尊重當事人以抵押物提供擔保的意思表示,債權人有權請求抵押人在抵押物的價值范圍內對債務人的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山東省威海市中級人民法院(2017)魯10民終965號《民事判決書》。]
上述觀點值得商榷,在設立不動產抵押權的過程中,當事人的擔保意愿包含如下兩個層次:一是一方提供擔保而另一方接受擔保的意思,即雙方有設定擔保的合意;二是當事人設定抵押這一擔保方式的意思。在認定當事人的擔保意愿時,需要同時考慮當事人上述兩個層次的意愿。前述觀點只是看到了當事人訂立抵押合同時設立擔保的意愿,而忽視了當事人設立抵押這一擔保方式的意愿,在當事人訂立抵押合同的情形下,如果當事人既沒有設立抵押之外其他擔保的意愿,也沒有就設立其他擔保達成合意,此時,強行將未辦理抵押登記的抵押合同解釋為在當事人之間成立保證或者非典型擔保,并不是對當事人意愿的尊重,而是對當事人設立抵押意愿的一種背離。[當然,如果當事人明確約定,在未辦理抵押登記或者抵押權因未辦理抵押登記而無法有效設立的情形下,抵押人仍然以抵押財產對債權人負擔擔保義務,則此時當事人之間就設定非典型擔保已經達成了合意,此時可以認定在當事人之間成立了非典型擔保。范小華:《未辦抵押登記的不動產抵押合同中抵押人責任研究》,載《法律適用》2015年第4期,第114頁。]尤其應當看到的是,擔保的類型不同,擔保人所需要承擔的擔保責任也存在差異。[紀力瑋:《以登記為生效要件的抵押權未為登記時的責任劃分》,載《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2期,第104頁。]在認定未辦理抵押登記的不動產抵押合同的效力時,應當充分尊重當事人對擔保類型的選擇,而不得違背當事人的意愿,在當事人沒有設立保證或者其他非典型擔保意愿的情形下,不宜認定未辦理抵押登記的不動產抵押合同具有設立保證或者其他非典型擔保的效力。[正如有人民法院在裁判文書中所指出的,當事人約定的擔保方式為抵押,在未辦理抵押登記的情形下,無法設立抵押權。債權人主張抵押人承擔保證責任的,與當事人約定的抵押屬于不同的擔保方式,因此,對債權人的請求不予支持。參見“山河建設集團有限公司與夏彬銀、季沖、新疆東城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民間借貸糾紛案”,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奎屯墾區人民法院(2020)兵0701民初438號《民事判決書》。]此外,即便否定未辦理抵押登記的抵押合同具有設立擔保的效力,也不意味著不尊重當事人設立擔保的意愿,因為當事人仍然可以通過辦理抵押登記的方式設立抵押權。而在當事人無法辦理抵押登記時,如抵押財產被征收,或者毀損滅失,當事人訂立抵押合同設立擔保的目的已經無法實現,此時,仍然課以抵押人承擔擔保責任,顯然是對當事人意愿的一種背離。
第三,認定未辦理抵押登記的不動產抵押合同具有設立擔保的效力,將在一定程度上架空設立不動產抵押權的公示要件。按照我國《民法典》物權編的規定,一般而言,不動產抵押權的設立既需要當事人就設立抵押權達成合意,也需要當事人完成設立抵押權的公示,即辦理抵押登記,否則無法設立抵押權。而認定未辦理抵押登記的不動產抵押合同具有設立擔保的效力,將會在某種程度上架空設立不動產抵押權的公示要件要求。因為就抵押人的責任而言,在抵押權有效設立的情形下,其僅需要在約定的擔保范圍內承擔擔保責任,而如果認定未辦理抵押登記的抵押合同具有設立擔保的效力,則意味著抵押人仍需要在約定的擔保范圍內承擔擔保責任。此種擔保責任雖然不同于抵押權有效設立時的擔保責任,債權人可能無法就抵押財產享有優先受償權[“中國青旅實業發展有限責任公司與錦銀金融租賃有限責任公司等融資租賃合同糾紛上訴案”,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終222號《民事判決書》。],但就抵押人的責任而言,此種擔保責任在責任范圍上與抵押權有效設立時無異,這就在一定程度上架空了不動產抵押權設立所需要的公示要件。
第四,認定未辦理抵押登記的不動產抵押合同具有設立擔保的效力,將會不當加重抵押人的責任。按照《〈民法典〉擔保司法解釋》第46條的規定,對不動產抵押而言,在未辦理抵押登記的情形下,該條第2、3款區分了不能辦理抵押登記的原因,分別規定了其法律后果。從該條第2款規定來看,如果因不可歸責于抵押人自身的原因導致不能辦理抵押登記的,則債權人無權請求抵押人在約定的擔保范圍內承擔責任。即在此種情形下,抵押人原則上無須對債權人承擔責任,即便抵押人獲得了一定的代位物,其也僅需要在代位物的范圍內對債權人承擔責任。而按照前述觀點,即便抵押人對無法辦理抵押登記不具有可歸責性,抵押人也需要對債權人承擔擔保責任,即抵押人承擔擔保責任“與未登記原因無關”[石冠彬:《民法典應明確未登記不動產抵押合同的雙重債法效力——“特定財產保證論”的證成及展開》,載《當代法學》2020年第1期,第37頁。],這顯然會不當加重抵押人的責任。
第五,未辦理抵押登記的不動產抵押合同一般屬于有效合同,認定其效力不需要借助無效法律行為轉換制度。前述觀點主張未辦理抵押登記的抵押合同能夠設立擔保的理由之一在于,未辦理抵押登記的抵押合同無法產生設立抵押權這一當事人追求的法律效果,因此,需借助法律行為轉換制度,將其認定為具有在當事人之間設立擔保的效力。[在我國司法實踐中,也有人民法院持此種立場。例如,在“劉峻瑞等訴新疆石河子農村合作銀行借款合同糾紛案”中,當事人簽訂了抵押房屋抵押合同,但并未辦理抵押登記,人民法院認為,如果當事人在訂立擔保合同之時,知道擔保合同不能發生效力,而且在不辦理抵押登記以節約登記費用的情況下,雙方會選擇由擔保人提供保證這一擔保方式,以保證貸款合同的順利履行,則可以將當事人所簽訂的抵押合同轉換為連帶責任保證合同。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2354號《民事裁定書》。]無效法律行為轉換是指某一無效法律行為符合其他替代行為的要件,而且當事人如果知道原有行為不生效力或者無效將希望替代行為生效的,則該替代行為有效,從而使無效法律行為被轉換為有效法律行為。[殷秋實:《無效行為轉換與法律行為解釋——兼論轉換制度的必要性與正當性》,載《法學》2018年第2期,第106頁。]一般而言,無效法律行為轉換需要具備如下幾個條件,即法律行為無效,該無效法律行為具備另一法律行為的生效要件,無效法律行為轉換符合當事人的意思。[
王利明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詳解》(下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671頁。]
從我國《民法典》的規定來看,其并沒有對無效法律行為轉換制度作出規定,因此,基于無效法律行為轉換制度認定未辦理抵押登記的不動產抵押合同的效力,欠缺法律依據。即便從學理層面看,也無法依據無效法律行為轉換制度認定未辦理抵押登記的不動產抵押合同的效力。無效法律行為轉換制度的前提是當事人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無效,需要通過轉換使之生效。[冉克平:《論未登記不動產抵押合同的效力》,載《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20年第1期,第129頁。]如前所述,抵押合同一旦成立,原則上就可發生效力,未辦理抵押登記并不影響抵押合同的效力,并不存在適用無效法律行為轉換制度的必要。正如有觀點所指出的,按照文義解釋的方法,在當事人就抵押事項達成合意時,已經足以認定當事人之間所訂立的合同為抵押合同,而沒有必要越過文義解釋的方法,將該合同解釋為保證合同或者其他擔保合同。[劉春梅、孫兆暉:《未辦理不動產抵押登記時金融債權的保護問題研究——以不動產抵押權設立和轉讓交易中的爭議問題為重點》,載《中國應用法學》2019年第6期,第166-180頁。]同時,如前所述,無效法律行為轉換應當符合當事人的意思,而對抵押合同而言,如果當事人沒有設定其他擔保方式的意愿,則借助無效法律行為轉換制度認定抵押合同的效力也難謂符合當事人的意思。此外,就未辦理抵押登記的不動產抵押合同而言,從《〈民法典〉擔保司法解釋》第46條第1款規定來看,債權人有權依據該合同請求抵押人繼續辦理抵押登記,這實際上是肯定了該合同的效力,在此情形下,如果仍然適用無效法律行為轉化制度,則會產生如下后果:即一方面允許當事人依法主張履行該合同,承認該合同的效力;而另一方面又主張通過無效法律行為轉換制度認定其效力,這實際上是否定了該抵押合同的效力,這顯然會帶來法律評價上的沖突和矛盾。
第六,認定未辦理抵押登記的抵押合同具有設立保證的效力,也會違反保證的形式要求,有違法律保護保證人的立法目的。在保證中,保證人通常是無償為債務人的債務提供擔保,而且一般情形下,保證人需要以其全部責任財產為債務人的債務提供擔保,因此,法律為了保護保證人的利益,對保證合同的形式和內容作出了嚴格要求。從域外法的規定看,有些國家對保證合同的形式作出了明確規定,即要求保證合同必須采用書面形式。例如,《德國民法典》第766條規定:“為使保證合同有效,必須以書面作出保證的表示。不得以電子形式作出保證的表示。”[《德國民法典》(第5版),陳衛佐譯著,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368頁。]有的國家雖然沒有要求保證必須采用書面形式,但也要求當事人必須有明確地提供保證的意思。例如,《法國民法典》第2015條規定:“保證不得推定,應當明示之;且不得將保證擴大至超過保證契約所定的限度。”[《法國民法典》,羅結珍譯,中國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460頁。]《意大利民法典》第1937條也規定:“提供保證的意思表示,應當是明示的。”[《意大利民法典》,費安玲等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457頁。]我國《民法典》也采取此種立場,依據《民法典》第685條規定,保證合同原則上也需要采取書面形式。[關于《民法典》第685條規定是否要求保證合同必須采用書面形式,有觀點認為,依據該條規定,保證合同具有要式性,必須采用書面形式。黃薇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合同編解讀》(上冊),中國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749頁;謝鴻飛、朱廣新主編:《民法典評注·合同編 典型合同與準合同》(2),中國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39頁。但事實上,從《民法典》第685條第1款規定來看,保證合同可以是單獨訂立的書面合同,此時,保證合同具有要式性,但保證合同也可以是主債權債務合同中的保證條款,此時,保證條款并不當然需要是書面形式,但一般而言,保證合同應當采用書面形式。]法律上要求保證合同采用書面形式,一方面是為了以書面形式固定當事人提供擔保的合意,另一方面也是為了確定保證人有提供保證的意愿。[
謝鴻飛、朱廣新主編:《民法典評注·合同編、典型合同與準合同》(2),中國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39頁。]而就未辦理抵押登記的不動產抵押合同而言,其并不符合保證合同的上述形式要求,不宜認定其具有設立保證的效力,因為當事人訂立的抵押合同雖然也具有書面形式,但當事人在該合同中并沒有提供保證的意愿。因此,不能將抵押合同的書面形式解釋為保證合同的書面形式,而且當事人也沒有就設定保證達成合意,書面形式的抵押合同也無法發揮固定當事人保證意愿的作用。因此,認定未辦理抵押登記的抵押合同具有設立保證的效力,將會違反保證的形式要件要求,也會不當增加抵押人承擔擔保責任的風險。[
有觀點主張,此種情形下抵押人僅需要在抵押財產價值范圍內承擔保證責任,即所謂“特定財產保證”。石冠彬:《民法典應明確未登記不動產抵押合同的雙重債法效力——“特定財產保證論”的證成及展開》,載《當代法學》2020年第1期,第36頁。此種觀點雖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抵押人的擔保風險,但其仍然無法有效解釋前述抵押人設定此種保證的意愿以及保證合同書面形式要件等問題。]
三、抵押人未辦理抵押登記時違約損害賠償責任的認定
(一)抵押人違約損害賠償責任的歸責原則
依據《民法典》第577條規定,違約損害賠償責任原則上采用嚴格責任原則。就抵押合同而言,我國《民法典》合同編并未就其歸責原則作出特別規定,物權編雖然就抵押合同作出了規定,但其也沒有專門規定抵押合同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因此,依據《民法典》的規定,抵押合同的違約責任應當采用嚴格責任原則。如前所述,將未辦理抵押登記時抵押人的責任解釋為擔保責任并不妥當,而從違約責任的視角觀察《〈民法典〉擔保司法解釋》第46條,則其與《民法典》的規定也存在不符之處:
一方面,抵押人承擔違約責任并不需要其具有過錯。如前所述,依據《民法典》的規定,抵押合同的違約責任采用嚴格責任原則,在抵押人未按照約定辦理抵押登記時,不論其是否具有過錯,都應當就因此給債權人造成的損失承擔違約損害賠償責任。而從《〈民法典〉擔保司法解釋》第46條規定來看,在無法辦理抵押登記的情形下,如果抵押人不具有可歸責性,則其原則上無須對債權人承擔責任;而如果抵押人對不能辦理抵押登記具有可歸責性,則其應當承擔賠償責任。此處“可歸責于抵押人自身的原因”應當是指抵押人對無法辦理抵押登記具有過錯。[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二庭:《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擔保制度司法解釋理解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年版,第413頁。]可見,《〈民法典〉擔保司法解釋》第46條就抵押人責任規定的是過錯責任原則,這與《民法典》的規定并不一致。
另一方面,我國《民法典》雖然就違約責任采用嚴格責任原則,但在存在免責事由的情形下,違約方也不需要承擔違約責任。例如,依據《民法典》第590條的規定,在發生不可抗力的情形下,應當根據不可抗力的影響,部分或者全部免除違約方的責任。而從《〈民法典〉擔保司法解釋》第46條第2款規定來看,在因征收等不可歸責于抵押人自身的原因導致不能辦理抵押登記時,如果抵押人已經獲得保險金、賠償金或者補償金等代位物,則仍然需要其在該代位物價值的范圍內承擔賠償責任。該條中的征收行為屬于當事人訂立抵押合同時不可預見、無法避免且無法克服的客觀情況,應當屬于不可抗力,該款在規定不可歸責于抵押人自身的原因導致無法辦理抵押登記的事由時,還使用了“等”這一兜底性表述,其在解釋上也包含其他不可抗力。在因征收等不可抗力導致抵押人無法辦理抵押登記的情形下,此類原因構成抵押人違約責任的免責事由,即抵押人無須對未辦理抵押登記承擔違約責任,而從《〈民法典〉擔保司法解釋》第46條第2款規定來看,即便出現此類事由,如果抵押人因征收等原因而獲得了一定的代位物的,則其仍然需要在該代位物價值的范圍內承擔賠償責任,這顯然不符合違約責任的一般原理。
因此,依據《民法典》的規定,在抵押人未按照約定辦理抵押登記的情形下,抵押人的違約責任應當采用嚴格責任原則,不論抵押人是否具有過錯,其都需要依法對債權人承擔違約損害賠償責任;如果存在不可抗力等免責事由,則抵押人有權主張不承擔違約損害賠償責任。《〈民法典〉擔保司法解釋》第46條關于抵押人違約責任的規定仍存在需要完善之處。
(二)抵押人違約損害賠償范圍的確定
在因抵押人未按照約定辦理抵押登記造成債權人損失的情形下,如何認定債權人損失的范圍,并進而確定抵押人違約損害賠償的范圍,存在一定爭議。
1.債權人損失的確定
關于未辦理抵押登記情形下債權人損失的認定,存在不同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債權人的損失應當是指債權人的債權未受清償的部分,即在主債務履行期限屆滿后,債務人未履行或者未完全履行債務時,債權人債權未受清償的部分即為債權人的損失,抵押人應當對該損害承擔賠償責任。[
高燕竹、王晶晶:《不動產未辦理抵押登記情形下抵押人責任的裁判路徑分析——以再審申請人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東莞分行與被申請人陳某1、陳某2、梁某某等金融借款合同糾紛案為例》,載《法律適用》2020年第12期,第52頁;范小華:《未辦抵押登記的不動產抵押合同中抵押人責任研究》,載《法律適用》2015年第4期,第116頁。]在司法實踐中,也有人民法院持此種立場。例如,在“福建省新威電子工業有限公司、黃振彬買賣合同糾紛案”中,人民法院認為,對房地產抵押而言,辦理抵押登記的義務主要由房地產權利人負擔,抵押人未按照約定辦理抵押登記的,應當對因此給債權人造成的實際損失在抵押物價值的范圍內承擔連帶賠償責任。[福建省莆田市中級人民法院(2020)閩03民終1020號《民事判決書》。]在該案中,人民法院在認定抵押人的賠償責任時,并沒有將債權人無法從債務人處獲得清償作為抵押人承擔賠償責任的條件,而是認定抵押人與債務人對債權人承擔連帶責任。因此,在債務履行期限屆滿后,債權人無須向債務人主張權利,只要債務人未履行到期債務,即可認定債權人因此遭受損失,債權人可直接請求抵押人承擔賠償責任。[類似裁判立場可參見“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滿洲里分行與滿洲里中歐化工有限公司、北京伊爾庫科貿有限公司信用證糾紛案”,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二終字第112號《民事判決書》;“徐振國訴董相福等民間借貸糾紛案”,黑龍江省雞西市中級人民法院(2015)雞商終字第80號《民事判決書》;“孟企平與湖南芒果雅苑酒店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湖南北山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房屋租賃合同糾紛案”,湖南省長沙市雨花區人民法院(2018)湘0111民初403號《民事判決書》。]另一種觀點認為,此處債權人的損失應當是指其債權不能從債務人處獲得清償的部分,因為在主債務人未清償債務時,債權人的損失并未實際發生,僅存在發生的可能性。[孫超:《未登記不動產抵押人的責任探析——從強制執行的視角切入》,載《人民司法》2020年第25期,第51頁。]按照此種觀點,在債務履行期限屆滿后,在債務人未按照約定履行債務時,還不能直接認定債權人遭受了損失,債權人還應當積極向債務人主張債權,只有通過強制執行債務人的責任財產無法實現其債權時,其債權未受清償的部分才能視為債權人的損失。例如,在“中新聯進出口公司訴遼寧墨林書藝文化傳媒有限公司、上海泰甌物資供應有限公司抵押合同糾紛案”中,在未辦理抵押登記的情形下,關于抵押人對債權人承擔的違約損害賠償責任,人民法院認為,抵押人僅在債務人履行不能的范圍內承擔違約損害賠償責任,在債權人未明確以訴訟方式向債務人提供請求的情況下,人民法院無法確定債務人不能履行的范圍,也無法據此確定抵押人承擔的損害賠償責任的范圍,因此,人民法院駁回了債權人對抵押人的請求。[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16)京02民終7780號《民事判決書》。]有觀點認為,之所以應當將債務人不能清償的部分視為債權人的損失,是因為在抵押人未按照約定辦理抵押登記的情形下,主要法律后果是使債權人喪失對抵押財產的優先受償權。在認定債權人的損失時,可類推適用擔保合同無效時的規則,即依據《〈民法典〉擔保司法解釋》第17條的規定,在擔保合同無效時,債權人的損失是“債務人不能清償部分”,類推適用該法律效果,在抵押人未按照約定辦理抵押登記時,債權人的損失也應當是其債權不能從債務人處獲得清償的部分。[高圣平:《民法典擔保制度及其配套司法解釋理解與適用》(下),中國法制出版社2021年版,第541頁。]
筆者認為,在未辦理抵押登記的情形下,在認定債權人的損失時,不宜類推適用擔保合同無效時的規則。因為一方面,類推適用屬于法律漏洞填補規則,只有在存在法律漏洞的情形下,才能適用該方法;而就未辦理抵押登記情形下抵押人的違約損害賠償責任而言,我國《民法典》合同編已經就違約損害賠償的一般規則作出了規定,即便法律未專門就抵押人的違約損害賠償責任作出規定,也可以直接依據該規則認定抵押人的責任,而不存在法律漏洞,并無適用類推方法的必要。另一方面,未辦理抵押登記情形下抵押人的責任與擔保合同無效情形下擔保人的責任性質不同,不宜類推適用。雖然無論是未辦理抵押登記的情形,還是擔保合同無效的情形,都是使債權人喪失就抵押財產的優先受償權[高圣平:《民法典擔保制度及其配套司法解釋理解與適用》(下),中國法制出版社2021年版,第541頁。],但這兩種情形下抵押人的責任性質不同,前者屬于違約責任,后者屬于締約過失責任。二者性質不同,責任的認定規則與責任范圍的確定規則也存在差異,并不符合類推適用的條件。
相比較前述兩種觀點,筆者認為,前一種觀點更為合理,即在未辦理抵押登記的情形下,債權人的損失體現為其債權未受清償部分;換言之,在債務履行期限屆滿后,債務人未履行或者未完全履行債務的,債權人債權因此未獲得清償的部分即為其所遭受的損失。之所以采取此種立場,主要理由在于,依據《民法典》第584條的規定,“損失賠償額應當相當于因違約所造成的損失”。對不動產抵押而言,如果抵押人按照約定辦理抵押登記,則可以有效設立抵押權,因此,債權人因抵押人未辦理抵押登記而遭受的損失體現為其無法取得抵押權。[“現代(邯鄲)物流港開發有限公司等與中國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票據追索權及合同糾紛案”,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終718號《民事判決書》。]進一步而言,在債權人取得抵押權的情形下,其有權依法行使抵押權,以實現其債權,因此,債權人因抵押人未辦理抵押登記而遭受的損失即為債權人無法行使抵押權而遭受的損失。關于抵押權的行使,《民法典》第394條第1款規定:“為擔保債務的履行,債務人或者第三人不轉移財產的占有,將該財產抵押給債權人的,債務人不履行到期債務或者發生當事人約定的實現抵押權的情形,債權人有權就該財產優先受償。”依據該規定,在能夠設立抵押權的情形下,只要債務人不履行到期債務,債權人即可依法行使抵押權,債權人在向抵押人提出請求時,并不以就債務人責任財產強制執行無法完全實現債權為條件,甚至并不需要債權人先向債務人提出請求。可見,在責任承擔順序上,抵押人的責任與連帶責任保證中保證人的責任具有相似性。而在抵押人未按照約定辦理抵押登記的情形下,在債務人未履行或者未完全履行到期債務時,債權人喪失了直接請求抵押人承擔擔保責任的權利,這即構成債權人的損失。試舉一例加以說明:債務人對債權人負擔1000萬元債務,抵押人將其房屋抵押給債權人,以擔保債務人債務的履行,在抵押權有效設立的情形下,在債務履行期限屆滿后,如果債務人未履行債務,則債權人可以直接行使抵押權,請求抵押人承擔擔保責任;而在抵押權未有效設立的情形下,在債務人未履行到期債務時,債權人即無法直接請求抵押人承擔擔保責任,這本身就是債權人所遭受的損失。因此,將債權人的損失界定為債權人債權未獲得清償的部分,與前述抵押權實現的規則具有內在契合性。
2.抵押人違約損害賠償范圍的限制
雖然債權人在清償期屆滿時未獲得清償的債權均屬于其所遭受的損失,但這并不意味著抵押人對債權人的損失均需要承擔損害賠償責任。從《〈民法典〉擔保司法解釋》第46條第3款規定來看,在因可歸責于抵押人自身的原因導致不能辦理抵押登記時,債權人有權請求抵押人在約定的擔保范圍內承擔責任,但是不得超過抵押權能夠設立時抵押人應當承擔的責任范圍。該條確立了抵押人違約損害賠償責任的兩項限制規則,即:當事人約定的擔保范圍與抵押權能夠設立時抵押人應當承擔的責任范圍。當然,就抵押人的違約損害賠償責任而言,上述規則不僅適用于因可歸責于抵押人自身的原因導致不能辦理抵押登記的情形,也應當適用于其他抵押人應當承擔違約損害賠償責任的情形。此外,抵押人的違約損害賠償范圍還應當受到《民法典》合同編通則中違約損害賠償責任減輕規則的限制。
(1)當事人約定的擔保范圍
按照私法自治原則,當事人可以對抵押人擔保的債權范圍作出約定,即當事人既可以約定抵押人對債權人的主債權及其利息、違約金、損害賠償金等提供擔保,也可以約定對其中部分債權的實現提供擔保。如果當事人明確約定了擔保范圍,則抵押人僅在約定擔保范圍內承擔違約損害賠償責任。換言之,如果債權人的損失小于當事人約定的擔保范圍,則主要依據債權人的損失確定抵押人違約損害賠償的范圍;反之,則主要依據當事人約定的擔保范圍確定抵押人的違約損害賠償范圍。
司法解釋將當事人約定擔保范圍作為確定抵押人違約損害賠償范圍的限制條件是合理的,因為抵押人不同于債務人,其僅對抵押權無法有效設立而給債權人造成的損失承擔賠償責任。換言之,抵押人所承擔的違約損害賠償的范圍不應當大于抵押權有效設立時債權人所能獲得的利益。而在抵押權有效設立的情形下,即便債權人依法行使抵押權,其也僅能請求抵押人在約定的擔保范圍內承擔擔保責任。因此,應當將當事人約定的擔保范圍作為抵押人違約損害賠償責任的限制條件。
(2)抵押權能夠有效設立時抵押人應當承擔的責任范圍
與當事人約定的擔保范圍類似,抵押人違約損害賠償的范圍還應當受抵押權能夠設立時抵押人應當承擔的責任范圍的限制。因為在抵押權有效設立的情形下,債權人有權依法請求抵押人承擔擔保責任,這也是抵押合同有效履行時債權人所能獲得的履行利益,其也應當成為確定抵押人違約損害賠償責任范圍的限制條件。
一般而言,在抵押權能夠設立的情形下,當事人約定的擔保范圍應當是確定抵押人擔保責任范圍的依據。但在特殊情形下,如果抵押財產的價值減少,小于當事人約定的擔保范圍,由于抵押人僅在抵押財產價值的范圍內承擔擔保責任,此時,就不再根據當事人約定的擔保范圍確定抵押人的擔保責任,而應當根據抵押財產的價值予以確定。例如,抵押人以其價值1000萬元的房屋為債權人提供擔保,雙方約定的擔保責任范圍為1000萬元,后該房屋的價值下跌至500萬元且債權人沒有依法請求抵押人增加擔保。在此情形下,抵押人也僅應當在該房屋的價值范圍內(即500萬元)對債權人承擔擔保責任。因此,《〈民法典〉擔保司法解釋》第46條第3款雖然將當事人約定的擔保范圍與抵押權能夠設立時抵押人應當承擔的責任范圍均作為抵押人違約損害賠償范圍的限制條件,但二者的作用存在一定的區別,即在依據當事人約定的擔保范圍確定抵押人的違約損害賠償范圍時,不得超過抵押權能夠設立時抵押人應當承擔的責任范圍。
但問題在于,如何確定抵押權能夠設立時抵押人應當承擔的責任范圍?其是否等同于抵押財產的價值?對此,有觀點認為,在未能辦理抵押登記的情形下,抵押人應當在抵押財產的價值范圍內承擔責任[高圣平:《未登記不動產抵押權的法律后果——基于裁判分歧的展開與分析》,載《政法論壇》2019年第6期,第167頁;紀力瑋:《以登記為生效要件的抵押權未為登記時的責任劃分》,載《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2期,第107頁。],而且此處的抵押財產價值應當是抵押權能夠實現時抵押財產的價值。[冉克平:《論未登記不動產抵押合同的效力》,載《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20年第1期,第129頁。]從司法實踐層面看,多數人民法院也持此種立場。此種觀點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為一般而言,債權人在實現抵押權時,是就抵押財產進行變價,并就該變價優先受償。對抵押人而言,也僅在抵押財產價值的范圍內對債權人承擔擔保責任。但筆者認為,將抵押權能夠設立時抵押人應當承擔責任的范圍界定為抵押財產的價值,在某些情形下并不合理,尤其是抵押財產的價值在抵押合同訂立后發生變化時,不宜完全將抵押權能夠設立時抵押人應當承擔的責任范圍界定為抵押財產的價值之內,具體而言:
第一,抵押財產價值增加。在抵押合同訂立后,抵押財產價值增加的,如抵押財產為房屋,而房屋價值因為市場等因素的變化而增加的,此時,如果抵押人按照約定辦理抵押登記,則債權人可以就價值增加后的抵押財產實現抵押權。因此,在此情形下,抵押權能夠設立時抵押人應當承擔的責任范圍應當是抵押財產價值增加后的價值。
第二,抵押財產價值減少。在抵押合同訂立后,抵押財產價值減少可能基于如下兩方面原因:一是因抵押人的原因導致抵押財產價值減少。如果因抵押人的原因導致抵押財產價值減少,在抵押權能夠有效設立的情形下,依據《民法典》第408條的規定,債權人有權請求抵押人增加擔保,而在因抵押人未辦理抵押登記導致抵押權無法有效設立時,債權人并不享有請求抵押人增加擔保的權利,這也應當構成債權人的損失。因此,在此種情形下,抵押權能夠設立時抵押人應當承擔的責任范圍既包括抵押財產價值減少后的價值,也應當包括抵押財產因抵押人行為不當減少的價值。二是因抵押人之外的原因導致抵押財產價值減少。從《民法典》第408條規定來看,其調整的是因抵押人的行為導致抵押財產價值減少的情形,即因抵押人的原因造成抵押財產價值減少時,抵押權人才有權請求抵押人增加擔保,至于因抵押人之外的原因造成抵押財產價值減少時,抵押權人能否請求增加擔保,《民法典》并未作出明確規定。一般認為,此種情形下,抵押權人并不享有要求抵押人增加擔保的權利。[黃薇:《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物權編解讀》,中國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687-688頁。]因此,在此情形下,即便抵押權能夠設立,債權人也只能請求抵押人在抵押財產價值減少后的范圍內承擔擔保責任。換言之,在因抵押人違約導致抵押權并未設立的情形下,抵押財產減少的價值不宜被認定為債權人的損失。此時,抵押權能夠設立時抵押人應當承擔的責任范圍是抵押財產價值減少后的價值,債權人原則上無權請求抵押人在抵押財產原價值范圍內承擔違約損害賠償責任。當然,依據《民法典》第390條規定,如果抵押人因抵押財產價值的減少而獲得了一定的保險金、賠償金、補償金等代位物的,該代位物也應當屬于抵押權的客體,成為債權人債權實現的保障。因此,在因抵押人未辦理抵押登記導致抵押權無法有效設立的情形下,債權人應當有權請求抵押人在抵押財產減少后的價值與代位物價值總和的范圍內承擔違約損害賠償責任。
第三,抵押財產完全毀損、滅失。如前所述,如果抵押財產毀損、滅失是因不可抗力而導致的,則抵押人有權主張免責。此時,抵押人無須對債權人承擔違約損害賠償責任。[當然,依據《民法典》第590條的規定,在抵押人遲延履行辦理抵押登記義務的情形下發生不可抗力、導致抵押財產毀損、滅失的,不因此免除抵押人的違約責任。]但抵押財產毀損、滅失并不都是由不可抗力所導致,也可能由意外事件、第三人原因等所導致,此時,如何確定抵押人違約損害賠償責任的范圍?筆者認為,在此情形下,在抵押權能夠設立時,如果抵押人因抵押財產毀損、滅失而獲得了一定的代位物,則按照抵押權物上代位的規則,抵押權人有權主張在代位物的范圍內優先受償。此時,該代位物的價值即為抵押權能夠設立時抵押人應當承擔的責任范圍。當然,如果抵押人沒有因抵押財產的毀損、滅失獲得代位物,也沒有因此對第三人取得請求權,則即便抵押權有效設立,債權人的抵押權也會因此消滅,此時,債權人應當無權請求抵押人承擔違約損害賠償責任。
(3)違約損害賠償責任的減輕規則
抵押人的違約損害賠償責任還應當受違約損害賠償責任減輕規則的限制[需要指出的是,抵押權人不協助辦理抵押登記并不會給抵押人帶來何種損失,因此,在未辦理抵押登記的情形下,通常沒有雙方違約規則適用的空間。高圣平:《未登記不動產抵押權的法律后果——基于裁判分歧的展開與分析》,載《政法論壇》2019年第6期,第164頁。],具體而言:一是合理預見規則。依據《民法典》第584條的規定,違約損害賠償責任受到合理預見規則的限制,即違約方的違約損害賠償責任“不得超過違約一方訂立合同時預見到或者應當預見到的因違約可能造成的損失”。就不動產抵押合同而言,抵押人違約損害賠償的范圍也不得超過抵押人訂立合同時預見或者應當預見到的因違約而給債權人造成的損失。一般而言,在抵押合同訂立時,抵押人能夠預見到的其違約行為給債權人造成的損失是使債權人的債權失去抵押權的保障。因此,此處抵押人預見的范圍應當是抵押權能夠設立時抵押人應當承擔的擔保責任的范圍。如前所述,其通常是指債務人不履行到期債務時抵押財產的價值。二是減輕損失規則。依據《民法典》第591條的規定,在一方違約后,如果另一方沒有采取適當措施導致自身損失擴大的,則違約方無須對該損失擴大的部分承擔責任,該規則同樣適用于債權人對抵押人的違約損害賠償請求權。三是與有過失規則。依據《民法典》第592條第2款規定,如果非違約方對損失的發生也有過錯的,則應當減輕違約方的違約損害賠償責任,該規則也適用于不動產抵押合同。例如,最高人民法院近期發布了第30批指導性案例,其中指導性案例第168號即涉及不動產抵押合同的效力問題。在該案中,人民法院認為,抵押權人對未能辦理抵押登記有過錯的,相應減輕抵押人的賠償責任[“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東莞分行訴陳志華等金融借款合同糾紛”,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再155號《民事判決書》。],這顯然也是采取了此種立場。
四、抵押人未辦理抵押登記時違約損害賠償責任的適用
(一)抵押人違約損害賠償責任與繼續履行責任之間的關系
在抵押人未按照約定辦理抵押登記的情形下,抵押人的行為構成違約,債權人有權依法請求抵押人承擔違約責任,關于抵押人承擔違約責任的方式,除法律另有規定的情形外,《民法典》合同編通則關于違約責任承擔方式的規定原則上都可適用于抵押合同。從《〈民法典〉擔保司法解釋》第46條的規定來看,該條專門規定了繼續履行(第1款)與違約損害賠償(第2、3款)兩種違約責任承擔方式,問題在于,在抵押人違約的情形下,繼續履行與違約損害賠償之間是否有適用順序的限制?換言之,債權人在請求抵押人承擔違約損害賠償責任之前,是否需要首先請求抵押人承擔繼續履行的責任(即辦理抵押登記)?
從《〈民法典〉擔保司法解釋》第46條規定來看,雖然沒有明確限定繼續履行與違約損害賠償的適用順序,但從該條的文義來看,二者仍然存在適用順序上的限制:該條第2、3款在規定抵押人的違約損害賠償責任時,將其適用條件限定為“不能辦理抵押登記”。也就是說,不論是否可歸責于抵押人,只有在“不能辦理抵押登記”的情形下,債權人才能請求抵押人承擔違約損害賠償責任。據此,在可以辦理抵押登記的情形下,債權人原則上無權請求抵押人承擔違約損害賠償責任,而只能主張繼續履行責任。這就明確限定了二者的適用順序:即在抵押人違約的情形下,債權人首先應當請求抵押人繼續辦理抵押登記,只有在無法辦理抵押登記的情形下,債權人才能請求抵押人承擔違約損害賠償責任。
筆者認為,在抵押人違約的情形下,嚴格限制繼續履行與違約損害賠償適用順序的做法并不合理,主要理由在于:
第一,此種做法與《民法典》的規定存在不符之處。從《民法典》合同編的規定來看,并沒有對繼續履行與違約損害賠償這兩種違約責任承擔方式的適用順序作出限制,當事人對二者的適用享有選擇權。事實上,當事人享有選擇違約責任承擔方式的自由是其選擇違約補救方式自由的體現,本質上體現的是對當事人合同自由的保護。[
王利明:《回顧與展望:中國民法立法四十年》,載《法學》2018年第6期,第40頁。]對不動產抵押合同而言,在抵押人違約的情形下,對違約責任承擔方式的適用進行嚴格排序,既與《民法典》的規定存在不符之處,也構成對當事人合同自由的不當限制。因此,在抵押人未按照約定辦理抵押登記的情形下,債權人既有權選擇請求抵押人繼續履行合同、辦理抵押登記,從而取得抵押權;也有權選擇請求抵押人承擔違約損害賠償責任。
第二,此種做法不符合違約損害賠償責任的適用條件。就違約損害賠償責任而言,只要因一方當事人的違約行為造成另一方損失,另一方當事人即有權依法主張違約損害賠償責任。《〈民法典〉擔保司法解釋》第46條將債權人主張繼續履行責任作為違約損害賠償責任的適用前提條件,實質上是對債權人違約損害賠償請求權的行使額外附加了條件,此種做法值得商榷。
第三,此種做法不利于保護債權人的利益。從《〈民法典〉擔保司法解釋》第46條規定來看,似乎只有在無法辦理抵押登記時,債權人才能請求抵押人承擔賠償責任,這可能不利于保護債權人的利益。因為在抵押人未按照約定辦理抵押登記時,債權人可能已經因抵押人的行為遭受一定的損失,此時,應當有權依法請求抵押人承擔違約損害賠償責任,而不是僅在無法辦理抵押登記的情形下才能向抵押人提出請求。尤其是在抵押財產價值已經發生貶損的情形下,如果抵押財產價值減少是因抵押人的行為造成的,或者抵押人在抵押財產價值貶損的同時獲得了一定的代位物,與請求抵押人辦理抵押登記、取得抵押權相比,主張違約損害賠償責任更有利于保護債權人的利益。
因此,在抵押人未按照約定辦理抵押登記的情形下,債權人既有權請求抵押人承擔繼續履行的責任(即辦理抵押登記),也有權依法請求抵押人承擔違約損害賠償責任,兩種違約責任承擔方式的適用不應當有嚴格的順序限制。當然,如果抵押人客觀上已經無法辦理抵押登記,如抵押財產已經被征收,或者已經毀損、滅失,則抵押人即不再承擔繼續履行的責任。
(二)抵押人違約損害賠償責任與債務人責任的關系
在抵押人未按照約定辦理抵押登記、造成債權人損失的情形下,債權人能否直接請求抵押人承擔違約損害賠償責任?抑或只能先請求債務人承擔責任,而只有在債務人不能履行債務時,才能請求抵押人承擔違約損害賠償責任?這就涉及抵押人違約損害賠償責任與債務人責任之間的關系,對此,無論是理論層面還是實踐層面,均存在較大爭議。
一種觀點認為,抵押人的違約損害賠償責任與債務人的責任之間并不存在順位關系,但關于抵押人不享有順位利益的原因,則存在不同主張。例如,有學者認為,抵押人的違約損害賠償責任與債務人的責任屬于同一順位,二者不分先后。因為在抵押權能夠設立的情形下,在債務人逾期不履行債務時,債權人可以直接行使抵押權,而無須先向債務人提出請求,在因抵押人未辦理抵押登記導致抵押權無法設立時,為了充分保護債權人的利益,也應當認定抵押人的違約損害賠償責任與債務人的責任處于同一順位。[
楊代雄:《抵押合同作為負擔行為的雙重效果》,載《中外法學》2019年第3期,第768頁。]也有學者主張,抵押人的違約損害賠償責任與債務人的責任之間構成不真正連帶責任,只不過是抵押人在承擔責任之后,有權向債務人追償。[冉克平:《論未登記不動產抵押合同的效力》,載《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20年第1期,第129頁。]按照此種觀點,抵押人的違約損害賠償責任與債務人的責任也處于同一順位。在我國司法實踐中,一些人民法院認定,在未辦理抵押登記的情形下,抵押人應當與債務人一起共同對債權人承擔連帶責任。例如,在“福建省新威電子工業有限公司、黃振彬買賣合同糾紛案”中,人民法院認為,在未辦理抵押登記的情形下,抵押人應當以抵押財產的價值為限對債務人的債務承擔連帶賠償責任。[福建省莆田市中級人民法院(2020)閩03民終1020號《民事判決書》。類似立場可參見“陳柏羽與營口弘逸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糾紛案”,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申1189號《民事裁定書》;“徐振國訴董相福等民間借貸糾紛案”,黑龍江省雞西市中級人民法院(2015)雞商終字第80號《民事判決書》;“尤亞蘭訴李洪冰等民間借貸糾紛案”,四川省三臺縣人民法院(2018)川0722民初468號《民事判決書》;“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滿洲里分行與滿洲里中歐化工有限公司、北京伊爾庫科貿有限公司信用證糾紛案”,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二終字第112號《民事判決書》。]按照上述觀點,在責任承擔方面,抵押人并不享有順序利益,在抵押人違約的情形下,債權人可以直接請求其承擔違約損害賠償責任,而不需要先向債務人提出請求。
另一種觀點認為,抵押人的違約損害賠償責任與債務人的責任之間存在順位關系,抵押人只是在抵押財產價值范圍內承擔補充責任。其理由主要在于:在抵押人違約的情形下,給債權人所造成的損失是債務人不能清償的債務部分,從這種意義上說,債權人首先應當向債務人提出請求,只有債務人無法完全履行債務時,債權人才能向抵押人提出請求。因此,在責任承擔方面,抵押人享有順序利益,只承擔補充責任。[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二庭:《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擔保制度司法解釋理解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年版,第414頁;林文學:《不動產抵押制度法律適用的新發展——以民法典〈擔保制度司法解釋〉為中心》,載《法律適用》2021年第5期,第23頁;高圣平:《民法典擔保制度及其配套司法解釋理解與適用》(下),中國法制出版社2021年版,第542頁。]抵押人就未辦理抵押登記對債權人所承擔的違約責任在性質上屬于“補充債務”。因為抵押人承擔賠償責任以債權人存在實際損失為前提,在債務人未清償債務的情形下,債權人只存在發生損失的可能性,而沒有實際遭受損失,只有債權人就債務人的責任財產強制執行而仍未獲得清償時,債權人的損失才確定發生。因此,抵押人的賠償責任在性質上屬于有先訴抗辯權的補充債務。[
劉延杰、王明華:《未辦理抵押權登記時抵押人應承擔何種責任》,載《人民司法》2013年第3期,第57頁。]在我國司法實踐中,有的人民法院也持此種立場。例如,在“姚某某、馬某某民間借貸糾紛案”中,人民法院認為,在未辦理不動產抵押登記的情形下,法律并未對抵押人應當承擔的責任形態作出規定,在當事人未約定承擔連帶責任的情形下,認定抵押人承擔連帶責任缺乏法律依據。因此,抵押人僅在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時承擔補充責任。[河南省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21)豫01民終5774號《民事判決書》。類似立場可參見“梅州市梅港實業有限公司訴劉安云等民間借貸糾紛案”,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16)粵民再32號《民事判決書》;“金國強訴錢虎興等民間借貸糾紛案”,浙江省海寧市人民法院(2017)浙0481民初6686號《民事判決書》;“丁衛訴楊志耘等民間借貸糾紛案”,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2017)云民再12號《民事判決書》。]
從《〈民法典〉擔保司法解釋》第46條的規定來看,只規定了抵押人對債權人承擔賠償責任的條件,而沒有對抵押人責任與債務人責任之間的關系作出規定,因此,無法從該規則中得出抵押人責任與債務人責任之間的順位關系。筆者認為,抵押人違約損害賠償責任與債務人責任之間的關系與前述債權人損失的認定之間存在直接關系。換言之,如果將債權人的損失界定為債務人無法履行的債務,則債權人首先應當請求債務人履行債務,以確定債務人無法履行的債務數額,然后才能向抵押人主張違約損害賠償責任。此時,抵押人所承擔的是一種補充責任,其責任具有次位性;反之,如果將債權人的損失界定為債務人未履行的債務,則意味著,債權人并不需要首先向債務人提出請求,而可以直接請求抵押人承擔責任。此時,抵押人的責任與債務人的責任處于同一順位。如前所述,在抵押人未按照約定辦理抵押登記的情形下,債權人的損失為債務人未履行的債務。因此,只要債務人未按照約定履行債務,債權人就可以直接請求抵押人承擔違約損害賠償責任,而不需要首先向債務人提出請求。據此,抵押人的違約損害賠償責任應當與債務人的責任處于同一順位,其責任并不具有次位性。
五、結語
不動產抵押作為一種重要的擔保方式,在保障資金融通、促進交易發展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依據我國《民法典》的規定,不動產抵押權的設立原則上既需要有效的抵押合同,也需要辦理抵押登記,但在未辦理抵押登記的情形下,不動產抵押合同究竟具有何種效力,在學理和司法實踐層面均存在較大爭議。《〈民法典〉擔保司法解釋》第46條對不動產抵押合同的效力作出規定,一定程度上回應了上述爭議,也為解決不動產抵押合同糾紛提供了法律依據。對不動產抵押合同而言,雖然當事人在訂立合同時有設定擔保的意愿,但當事人的訂約目的在于設定抵押權,因此,在未辦理抵押登記的情形下,不宜認定在當事人之間成立保證或者其他非典型擔保。抵押人未按照約定辦理抵押登記的,債權人有權依法請求抵押人承擔違約責任。抵押人違約損害賠償責任的認定需要與《民法典》合同編通則中的違約責任規則以及物權編中抵押權的效力規則相協調,抵押人的違約損害賠償責任應采用嚴格責任原則,抵押人違約損害賠償的范圍以債權人的損失為限,并受到當事人約定擔保范圍、抵押權能夠設立時抵押人應當承擔的責任范圍以及違約損害賠償責任減輕規則的限制。在抵押人未按照約定辦理抵押登記時,債權人有權選擇請求抵押人承擔繼續履行的責任與違約損害賠償責任,而不需要先行請求抵押人辦理抵押登記;與債務人責任相比,抵押人的違約損害賠償責任并不是補充責任,其責任也不具有次位性。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Real Estate Mortgage Contract
without Mortgage Registration
WANG Ye-gang
(School of law,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The purpose of the parties to conclude a mortgage contract is to establish a mortgage. A mortgage contract without mortgage registration cannot produce the effect of setting suretyship or other atypical guarantee between the parties. The principle of strict liability should be adopted when the mortgagor fails to register the mortgage according to the agreement. The scope of the mortgagor’s liability for damage of breaching contract is limited to the amount of creditor’s rights that has not gotten paid off from the debtor. At the same time, this liability is limited by the scope of guarantee agreed among the parties, the required liability of mortgagor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mortgage was validly established, and the general rule of liability for breach of contract. If the mortgagor fails to register the mortgage, the creditor has the right to choose to request the mortgagor to bear the liability of continuing to perform the contract and the liability for damages for breach of contract, and has the right to choose to request the debtor or the mortgagor to bear the liability.
Key Words:mortgage; mortgage contract; mortgage registration; liability for breach of contract
本文責任編輯:林士平
青年學術編輯:孫 瑩
收稿日期:2021-12-01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個人信息收集、處理行為合法性研究”(20CFX015)
作者簡介:王葉剛(1987),男,安徽阜陽人,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