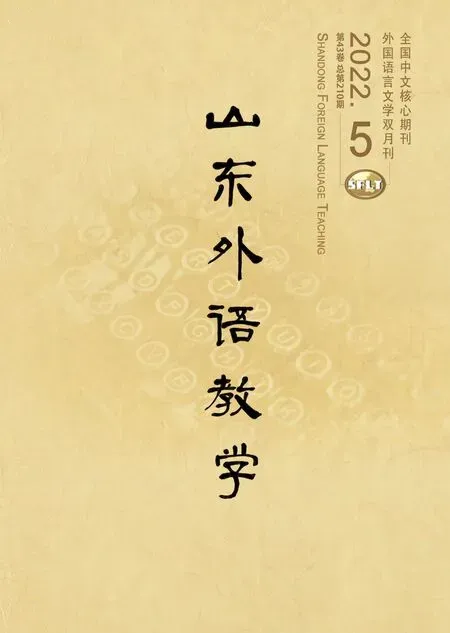挪用“彈震癥”:《士兵的回歸》中的失憶、懷舊與共同體難題
程匯涓
(上海外國語大學 國際工商管理學院,上海 201600)
1.引言
彈震癥(shell shock)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出現的對新型機械化戰爭所造成的創傷性神經官能癥的描述。在有關一戰的文學表現中,彈震癥占據了極為顯著的位置,小說家“提供了豐富多樣的關于彈震癥及其后果的文學呈現”(Dodman,2015:12)。歷史學家特蕾西·洛克倫(Tracey Loughran)認為,“自一戰停戰以來,彈震癥就被包含進戰爭想象”,從彼時到當代,有關一戰的小說都表現出“對創傷的徹底的現代迷戀”(2012:97)。
麗貝卡·韋斯特(Rebecca West, 1892-1983)在一戰尾聲時出版的小說《士兵的回歸》(TheReturnoftheSoldier, 1918)常被視為最早將罹患彈震癥的士兵形象引入虛構創作的嘗試之一(Baldick,2004:338;O’Malley,2015:92)。受到有關彈震癥經典話語的影響,以及戰后審美意識形態的浸染,當代批評家傾向于將這本小說中的“彈震癥”與戰爭創傷表征關聯起來(Kavka,1998;Bonikowski,2005;Pinkerton,2008;Pividori,2010;Pulsifer,2013),小說男主人公克里斯仿佛與伍爾夫筆下標志性的彈震癥受害者“賽普蒂默斯”一樣,受困于機械化戰爭所造成的創傷后應激障礙。
然而細讀之下,《士兵的回歸》對克里斯罹患彈震癥后狀態的表現,存在違背常理之處。小說的核心事件是克里斯因彈震癥失去了十五年的記憶,他忘記已婚的事實,也不記得早夭的兒子,只牽掛十五年前的舊情人瑪格麗特,并強烈地渴望與后者重修舊好。盡管失憶在有關彈震癥癥狀最早的醫學記錄里就占據一席之地(Myers,1915:316;Rivers,1918:173),但它無疑是與失眠、焦慮、聽嗅味視覺受損等情況并發的(Smith,1917:4-6)。相較之下,克里斯的彈震癥有兩點違背醫學經驗:一是其癥狀僅限于失憶,其余可能造成負面情緒的并發癥均不存在,失憶反倒使他在情緒上走到醫學病例的反面,表現出積極、幸福的狀態;二是他記憶缺失的時段(十五年)過于特殊,事實上,由彈震癥誘發的逆行性失憶主要表現為兩種形態:一種是與意識喪失并發的完全失憶,另一種是失去受傷前后不久形成的記憶(Mott,1919:84-91)。也就是說,由彈震癥誘發的失憶具有明顯的創傷屬性和事件關聯性。
那么,為何《士兵的回歸》中的彈震癥表現得如此遠離真實?韋斯特對它做的去現實化的處理蘊含了怎樣的批評眼光?本文認為,若僅在戰爭創傷表征的邏輯上理解這種錯位,就可能忽略小說對特定時代情緒的回應,也會錯過深入探究失憶所誘發的田園懷舊以及共同體問題。
2.被挪用的“彈震癥”與嫁接的失憶
《士兵的回歸》是最早將彈震癥作為主要情節的小說之一,它與20世紀20年代之后出版且在接受史中被經典化的文本不同。它誕生于彈震癥醫學觀念和大眾觀念形成的早期,生動地反映出共識達成之前流動不居的形式自由。在學術研究、評論文章和文學教育的共同作用下,對英語國家當下的閱讀群體來說,表現彈震癥的經典文本是被不斷篩選出來的,它們逐漸在審美意識形態上走向統一,繼而影響后繼的創作。凱特·麥克唐納德(Kate Macdonald)曾就1914至1918年戰爭持續期間英國出版的長篇小說和雜志刊登的短篇小說,做了一整套基于文本庫的研究(2017:43-44),并雄辯地指出,當代讀者對一戰經驗,特別是“彈震癥”作為其核心要素的理解,“更多來自戰后文學”(2017:38)。從伍爾夫的《達洛維夫人》(Mrs.Dalloway, 1925)到福特·馬多克斯·福特(Ford Madox Ford, 1873-1939)的《隊列之末》四部曲(Parade’sEnd, 1924-1928),再到帕特·巴克(Pat Barker, 1943-)的《重生》(Regeneration, 1991-1995)三部曲,有關彈震癥的文學表現在不斷深化的同時,也自發地與看上去不夠真實或者說不夠“痛苦”的寫法拉開距離。
《士兵的回歸》創作于書寫范式達成之前。在這個階段,從作者到讀者,遠離前線和戰地醫院的公眾對彈震癥只有模糊的認識,由此也給彈震癥在文本中的挪用和拼接創造了條件。彈震癥的源頭敘事通常被追溯至英國皇家陸軍醫生查爾斯·邁爾斯(Charles Myers, 1873-1946)于1915年2月13日在《柳葉刀》上發表的文章《一篇關于彈震癥研究的文稿》(“A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Shell Shock”),但邁爾斯并不是第一個使用“shell shock”來描繪這類癥狀的醫生,吉爾伯特·巴林(Gilbert Barling, 1855-1940)比他早一個月在《英國醫學雜志》(BritishMedicalJournal)上已使用該說法。軍隊醫生在學術刊物上專文探討這一病理現象,反映出患病士兵的表現和人數對軍方來說已不能忽視。然而,前方的醫學觀察傳播至后方公眾,不僅會有必然的時間差,也存在信息的過濾和擇選。從“英國報紙檔案庫”(The British Newspaper Archive)的檢索結果來看,有關彈震癥的報道在1916年呈明顯上升趨勢,但它主要出現在傷亡將士名冊的簡短說明中,或是以樂觀主義精神報道的個別士兵康復案例里。事實上,身處大后方的公眾即便能夠從報紙雜志中窺見一鱗半爪,在戰爭尚未結束時,其認識往往停留在紙面上,因為“重癥患者通常被直接送進戰地醫院,公眾在后方的正常生活里遇見患者的機會有限”(Macdonald,2017:48)。在《士兵的回歸》中,克里斯·鮑德里的舊情人瑪格麗特前往他的宅邸,告知其妻克里斯的狀況,但她琢磨半晌卻不知如何描述,“我不知該怎么說……他不能嚴格說是受傷了……炮彈爆炸了”,她的說法仿佛是在“提供一個她長期以來苦苦思索卻無法理解的術語”,最終她口中蹦出了一個詞“彈震癥”,但克里斯的妻子和堂妹對這個詞并未產生任何恍然大悟的反應(West, 2010:55)①。此處韋斯特用后方女性聽聞彈震癥的困惑,模仿了彼時大眾對彈震癥一知半解的狀態。
在這樣的話語關系網中,彈震癥成了一個文本楔子,它與新型戰爭方式和當下士兵境況的關聯,自然能夠激發讀者的閱讀關切,但同時后方公眾與它的距離又使作者享有部分挪用的自由,免除了情感和道德壓力之下的表征趨同。正是在這一條件下,小說將克里斯的彈震癥癥狀壓縮至單純的失憶,剔除了創傷性神經官能癥的其他表現:他從醫院被送回家后,熱情地與人打招呼,高興地哼歌(64);待人有禮,情緒平穩(70);得知自己失去十五年的記憶后,也并不在意——只要能找回瑪格麗特,他就能沉浸于幸福的過去(79)。事實上,克里斯的“失憶”確實源自其他故事靈感。卡爾·羅利森(Carl Rollyson)在《麗貝卡·韋斯特傳》(RebeccaWest:ALife, 1996)中披露,小說受到醫學雜志上一篇文章的啟發,“該文描寫了一位上年紀的工廠雇員從樓梯上摔下來,頭部著地,醒來后認為自己是個二十歲的年輕人,他拒絕痛苦的妻子,一心要找曾經的情人”(1996:69)。這個病例幾乎被原封不動地嫁接到了克里斯的彈震癥失憶上,只是將病因做了替換。
從文本效果的角度來看,病因的替換無疑解釋了《士兵的回歸》中彈震癥那種不合時宜的純粹表現,但更重要的是,其嫁接的“失憶”悄然轉變了小說聚焦的核心議題。它將士兵可能受到的傷害擱置,轉而以“失憶”喚醒人物和同時代讀者對記憶斷裂前時代的懷舊。小說中克里斯“人生大事”的相關年份都具有強烈的象征意味:他在戰場受傷的時間是1916年,失去十五年的記憶,則記憶倒退至1901年——對英國人來說,這個年份是維多利亞女王去世、愛德華七世繼位的節點,是回憶中更令人驕傲、值得懷念的歷史時段的終結處。塞繆爾·海因斯(Samuel Hynes)就指出這部小說“部分帶有愛德華時代的特性”,那是“英國歷史上的動蕩時期,是維多利亞主義與現代主義浪潮遭遇的狹窄通道”,彼時“工人問題、婦女問題和愛爾蘭問題同時存在;政治與社會權力轉移;緊接著就是戰爭的大麻煩”(1998:ix)。因此,克里斯的“失憶”很容易喚起身處一戰之中的英國讀者的懷舊共情——若能瞬間就擺脫十幾年動蕩不安的記憶和憑借后見之明已知的戰爭后果,這何嘗不是彼時英國社會的共同情感向往?
來自有產階級的克里斯與美貌妻子基蒂于1906年結婚,他們的兒子奧利弗于1911年夭折,孩子的夭折自然隱喻著婚姻的無果,而這兩件人生要事以五年為間隔,標記了克里斯因彈震癥失去的記憶與愛德華時代近乎完整的重合。從心理分析的角度來看,失憶是對不愉快經歷的主動壓抑,事實上《士兵的回歸》也是“最早描寫精神科醫生的英語小說之一”(O’Malley,2015:92),文本后半段引入的弗洛伊德式精神分析師吉爾伯特·安德森這樣評估克里斯的失憶:“他的無意識自我,拒絕讓他恢復與正常生活的關系,因此就造成了現下的失憶”(108)。該點評不僅適用于克里斯這位從戰場上回來的士兵,也同樣呼應了戰時動蕩不安的環境下英國人的某種共同情感傾向——重返過去、重返田園,正如斯維特蘭娜·博伊姆(Svetlana Boym)在分析“懷舊”出現的時機時指出的,“在一個生活節奏和歷史變遷節奏加速的時代里,懷舊不可避免地就會以某種防衛機制的面目再現”(2021:7)。對彼時的英國人來說,懷舊是一個極具誘惑力的選擇,而《士兵的回歸》恰以“失憶”誘導出克里斯和瑪格麗特十五年前在猴島(Monkey Island)上的一段帶有黃金時代色彩的回憶,復現了“懷舊”的運作機制,傳遞出一種渴望用純真替換物來消除“麻煩”的共同意識。
3.猴島:召喚田園懷舊
在小說中,猴島是屬于克里斯和瑪格麗特的共同回憶,也是被彈震癥失憶所召喚的懷舊想象,有關它的描述均帶有強烈的田園牧歌特點(O’Malley, 2015:95-105)。失去十五年記憶的克里斯返回家宅,在堂妹珍妮眼中,他的一舉一動均顯得與現實脫節,然而克里斯只強調“猴島是真的,你不知道老猴島,我來告訴你”(72)。通過想象和敘述的運作,“懷舊”將懷舊客體帶至當下,置換真實感。從克里斯的講述中,一處理想的、孤立的田園烏托邦出現了——這個位于泰晤士河畔的小島綠樹成蔭,風景秀美,瑪格麗特和她的父親在猴島上經營著一家遠離塵囂的旅店。對克里斯來說,少女瑪格麗特身上有著屬于田園的寧靜氣質,在他的記憶中,猴島上最重要的景觀是“白山楂樹”(72,76)。“山楂樹”作為愛情的象征符號,從中世紀起就在西方文學中占據顯著位置,它是“愛情寓言的常量之一”,沒有山楂樹的園地就仿佛“熟睡且感覺安心的宮廷情人一樣不可思議”(Eberly,1989:41)。小說里每當克里斯對“白山楂樹”的回憶出現時,少女時代的瑪格麗特也必然身著“白色的裙子”(72,76)以最純美的模樣浮現于記憶之中,用克里斯的話來說,“她就是慈善和愛本身”(72)。將過去時空中的具體意象與抽象道德和高尚情感聯系起來的做法,是懷舊邏輯中普遍且必要的一環。
正是借助“白山楂樹”在克里斯和瑪格麗特心中獨特的地位和不可磨滅的印記,象征時空中的標記物對懷舊主體的價值被揭示出來——它是召喚共同情感依附的符號,隔離令人不安的現實。在小說中,堂妹珍妮代表在后方受到前線戰況報道影響的大眾,她時常做“近期英國婦女常做的噩夢”,將戰爭宣傳電影里的情景投射到夢中,夢見克里斯穿過西線戰場的“無人區”(No Man’s Land),四處是被炸得血肉橫飛的士兵(48-49)。而當她聽聞克里斯和瑪格麗特對白山楂樹以及猴島記憶的描繪時,也產生了一種與現實隔絕的夢幻感,“真奇怪,他們倆都那樣細致地描繪渡口邊楊樹林里的一棵白山楂樹”;“真奇怪,克里斯和她講起那里,仿佛那不是一個地方,而是一種魔法狀態”(84)。這種隔絕感正是懷舊在認知層面為心理需求所建構的舒適區。“環境斷裂或劇烈沖突會否定人類維護自我連續性和統一性的根本需求”(戚濤,2020:96),而懷舊情感正是主體應對連續性危機的產物。在空前殘酷的戰爭環境下,不論對克里斯這樣的遣返士兵,還是瑪格麗特和珍妮這樣的后方平民,猴島空間都成為理想化的隔絕地。他們為猴島和白山楂樹賦予的光暈不僅將自身置換進沒有痛苦的田園世界,也用施魅的話語把聽者帶入其中,從這個意義上說,作為敘述者的珍妮摹仿了每一個聽到田園詩般講述的讀者,而講述的過程則應和了彼時英國社會和群體意識中愈發清晰的重返田園的呼聲。
事實上,重返田園的鄉村懷舊貫穿于英國文學的發展歷程,只不過每一次促使呼聲走向嘹亮的動因有所差別。在一戰爆發前的愛德華時代,已有相當數量的作品立足于“英國狀況”且以田園作為“他處的神話”(Mackenzie,2013:108),提供有關秩序的暗示。福特·馬多克斯·福特的《鄉村的心臟》(TheHeartoftheCountry, 1906)和E. M. 福斯特(E. M. Forster, 1879-1970)的《霍華德莊園》(HowardsEnd, 1910)都在這條道路上做了嘗試。而愛德華時代的關鍵文本之一,肯尼斯·格雷厄姆(Kenneth Grahame, 1859-1932)的《柳林風聲》(TheWindintheWillows, 1908)更是將河濱田園生活作為動物故事的框架結構,以“懷舊的筆調構建了一個傳統紳士共同體”(陳兵,2022:24)。這些文本的共同特點是面對轉型期的困頓以某種知識分子的人道主義懷舊,尋求解決工業和城鄉問題的可能性。如果說愛德華時代的英國問題是復雜糾纏的(工人問題、婦女問題、愛爾蘭問題和政治與社會權力轉移等),那么隨著一戰的爆發,這些問題上又疊加了新型機械化戰爭的暴力。對戰爭作出反應的“田園懷舊”也成為戰爭爆發后不久文學創作,特別是詩歌中的顯性聲音。保羅·福塞爾(Paul Fussell)在其一戰文學批評經典《大戰與現代記憶》(TheGreatWarandtheModernMemory, 1975)中指出,薩松(Siegfried Sassoon)和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等人作品中的田園理想是“夾在暴力與恐怖之間的時刻”,它們作為“插曲”或“綠洲”在戰爭回憶中“短暫重現”(1975:236-237),這種模式為敘述的推進提供了情緒動力,通過并置誘使讀者譴責現代世界的混亂與苦難,向往阿卡迪亞式的世外桃源。
從文本的章節安排上來看,《士兵的回歸》似乎也使用了類似的敘述模式,涉及猴島的兩章被夾在整個文本六章的中間部分(三、四章),其前后分別以患彈震癥士兵回歸后方和治愈返回戰場為主要事件,這就使田園懷舊成為名副其實的綠洲,夾在暴力的背景和前景之間。田園作為退守之處所蘊含的逃避和隔絕意義,同樣嵌套于文本設計之中:猴島是田園的象征符號,其與小說人物最早的瓜葛就始于逃避和療愈,瑪格麗特和父親之所以搬去猴島經營旅店恰是因為母親的逝世,那里與外界的“斷然差別是種療愈”,他們“在綠色的寂靜中安頓了下來”(85)。十五年前克里斯與瑪格麗特在猴島的夢幻相戀,同樣起始于克里斯因躲避家族生意的散心(86-87),十五年后,猴島的再次出現又與壓抑戰爭不愉快經歷的失憶和逃避重合。小說有一處關于瑪格麗特在猴島房間陳設的描寫,她的“小房間暮色沉沉,只有桌子上的縫紉機和壁爐架上她母親那放大了的照片,以及用紅色毛絨相框擺設起來的丁登寺之景”(77),封閉房間里封閉相框中被當作心靈幽居所觀賞的景色,其田園懷舊的隔絕意味呼之欲出。隱居、退守的安全感是這種風景和懷舊背后的倫理,它往往為經歷危機和懷疑的群體提供某種基于共同審美取向和情感需求的認同,讓人產生歸屬感的快樂。
4.田園懷舊的美學與共同體難題
共同的審美取向確實能夠制造出精神上的共識,但對20世紀初至一戰這一特定歷史語境下的英國人來說,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是:田園懷舊背后有著怎樣的心理訴求,其美學表象下的倫理暗語為何,它是否能夠成為共同體所必須的“共識”的紐帶?事實上,田園風光在文學書寫中早已不是單純的自然反映,它是被反復編碼的風景,其美學既受到時代思想和情感結構的影響,也在風景與人的關系中透露出書寫者的搖擺。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鄉村與城市》(TheCountryandtheCity, 1973)中追溯了歷史沿線上的數個時期,指出人們面對舊秩序的破壞時所自發求助的習慣,即“把過去,把那些‘過去的好日子’當作一種手杖,來敲打現在”,但不斷后退的歷史(懷舊)和田園書寫的結合“其實是一種更為復雜的運動”,“對于每一種回顧……都需要進行準確的分析”(威廉斯,2013:15)。在對田園詩傳統中“精心挑選的意象”之流變的考察下,威廉斯發現“不受干擾的鄉村快樂和安寧”以及“黃金時代的回復”都是選擇性的建構,是建立在“關鍵張力被刪除”的基礎上的,其結果就是“詩中不再有真相”,“田園詩變成一種極其造作和抽象的形式”(同上:24-27)。
韋斯特在《士兵的回歸》中借由彈震癥失憶所插入的猴島片段,模仿了這種抽象造作的形式,但經由士兵被弗洛伊德式心理暗示所刺激恢復的現實記憶,小說又對田園懷舊擺出了反叛姿態。克里斯究竟應該沉浸于失憶的后果,還是應該被喚醒、正視現實,這實際上是從愛德華時代到一戰的英國社會在面對現代性問題和戰爭暴力的“麻煩”時,所感到困擾的選擇。伯納德·施韋策(Bernard Schweizer)認為,小說中三個女性人物關于是否應喚醒克里斯記憶的爭論讓“這部小說在主題和結構上都被設定為對整個懷舊觀念的公投”(2013:30)。當精神分析醫師與她們探討恢復克里斯記憶的方法時,瑪格麗特認為“談話療法有什么用呢?你無法治愈他……我的意思是說,你沒法讓他快樂,你只能讓他變得普通”(110)。她們的爭論再現了愉悅與真相之間的艱難選擇,小說最終給出的答案是“真相就是真相……他必須知道”(116)。盡管這本小說從出版伊始,就不斷受到責難,人們認為其結局提供的解決太過倉促,似乎把弗洛伊德式的精神治療推到了荒誕的極致——瑪格麗特用克里斯夭折兒子的遺物喚醒了他對現實的記憶,而這個過程僅用了一個自然段的篇幅。但這一不夠精巧的安排隱含了某種針對田園懷舊的道德判斷——它的美好代替不了殘酷卻必要的真相。
實際上,盡管瑪格麗特和克里斯擁有共同的猴島記憶,但兩人回顧的細節卻有所不同,這些微妙卻重要的差別破壞了田園懷舊作為共同體歸屬感的基礎。對克里斯來說,田園懷舊從最開始就被當作審美消費品。真正在猴島上定居并從事養殖生產的是瑪格麗特和她的父親,他們豢養家禽和兔子(74,76),訪客因這番辛勤的養殖勞作得以享用白鴨蛋等食物(85)。相較之下,克里斯的來訪是富裕階層到田園尋訪野趣的消遣活動,其游覽的性質與猴島在現實中的歷史亦頗有關聯。猴島并非韋斯特生造的世外桃源,它原本和丁登寺一樣為僧侶使用,后于1723年被第三代馬爾伯勒公爵查爾斯·斯賓塞(Charles Spencer, 1706-1758)購買,經建筑改造后用作貴族享樂(Over,2012)。韋斯特熟諳猴島歷史,小說亦將猴島旅店的修建史概括如下:“第三代馬爾伯勒公爵把它建成‘大而無用的怪異建筑’……它有一種屬于18世紀的優雅和愚蠢”(73)。對韋斯特時代的作家來說,愛德華七世和亞歷山大王后時常到猴島度假的傳聞也并不陌生(Over,2012)。可以說,貴族按照自己的品味對田園做出美學加工并消費調適后風景的傳統一直流傳下來,只是隨著時代的發展,田園風景的消費者從貴族擴展到了有產有閑階級,但不變的是他們外在于土地的關系。
與依賴田園土地而生存的“內部人士”相比,這些生活在田園外部卻希望間歇尋訪野趣的人所采用的是“外部人士”的視角(Relph,1976:49),這種視角差異決定了以田園懷舊作為共同體情感基礎的可疑性。克里斯來自有產階層,不僅擁有偌大的宅邸,還有相當規模的與英帝國海外利益密切相關的家族生意。他與瑪格麗特的相戀不是田園內牧羊人與牧羊女的愛情,而是外部的風景觀賞者與想象中牧羊女的關系。堂妹珍妮分別傾聽了克里斯和瑪格麗特講述對猴島的記憶,我們可以發現,在前者的故事中,田園懷舊就像猴島上的希臘神龕那樣遙遠神秘,“只有美”,就像他的愛一樣“永恒不變”(78);但從瑪格麗特的講述中,我們才知道兩人分手的原因是克里斯目睹瑪格麗特同他眼中的“俗人”嬉笑——盡管此人是瑪格麗特從小的玩伴,那一刻瑪格麗特才意識到“他不像信任同階級的女孩那樣信任我”(86)。他們爭吵的當晚,克里斯與父親聊到很晚,“第二天早晨就動身前往墨西哥,保證他們的礦業在當地革命中不受影響”(87)。可見,對于尋訪田園野趣的“外部人士”來說,即便其審美欣賞并非出于獵奇,但當現實秩序受到威脅時,作為娛樂對象的田園風景是可以割舍的。而瑪格麗特后來的人生軌跡顯然證明田園“景框”中的內部人士,并不像游客那樣“享有從景色中離開的自由”(Cosgrove,1998:19)。借由兩人猴島記憶敘述的微妙差別,內在于田園懷舊美學的斷裂被揭示出來,被忽略或刪除的“關鍵張力”重新進入文學文本。
從這個意義上說,《士兵的回歸》反思的是現代場景下基于懷舊的情感團結和共同體沖動。盡管田園懷舊作為一種普遍的情感,可能出現于任何時間和空間,但對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英國來說,它無疑形成了一種熱潮,并在戰爭的“大麻煩”下被推向了高峰。在這一時期,各行各業似乎都涌動著“往回看”的暗流,“市場營銷者、建筑師和作家都在小說、廣告、住房和社區設計中喚起懷舊欲望,販賣懷舊形象”(Outka,2013:255)。鄉村懷舊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營銷也大致始于此時,創刊于1897年的《鄉村生活》(CountryLife)雜志一躍成為英國最受人歡迎的讀物之一——《士兵的回歸》甚至靈巧地抓住了這個細節,讓鮑德里莊園的女人在日常生活中如饑似渴地閱讀《鄉村生活》(95)。戰爭爆發后,塹壕與后方之間頻繁傳遞的明信片和書信更將田園懷舊在“兩條戰線”上一并推進(Roper,2011:421-432)。不論對前方士兵,還是對后方平民來說,個體在危機下尋求田園懷舊作為情感慰藉并不新奇,但倘若其美學基于消解真實性的想象,且無法在共同生活中實踐,那么它曲折隱含的道德引導對共同體而言是不可靠乃至危險的。
5.結語
《士兵的回歸》對“彈震癥”的挪用具有歷史的特異性,其創作時間恰處于“彈震癥”開始從前線軍醫的研究進入后方報道的過渡期,公眾對其既有耳聞,又缺乏實感。對當時的創作者和讀者來說,“彈震癥”包含真切的當下性,但同時仍未成為顯性的文學主題,不至誘發陳陳相因的心理習慣。因此,當代讀者擺脫后見,再審視這部作品中的“彈震癥”時就會注意到,小說悄然將前線的危機與社會深層的情感結構和共同意識聯系了起來。韋斯特借用“彈震癥”內含的休克元素,把它與“失憶”故事的素材嫁接,使田園懷舊這一凸顯的共同情感傾向進入小說圖景。而文本中不和諧的細節暴露出田園懷舊美學所隱含的共同體難題:它若脫離客觀性,僅提供看似美妙、可消費的共同體驗,那就難免遮蔽復雜的現實,倒退著將過去的秩序理想化為被情緒裹挾的共識。
注釋:
① 本文對《士兵的回歸》的引用均出自West(2010),以下出自該著引文僅標注頁碼,不再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