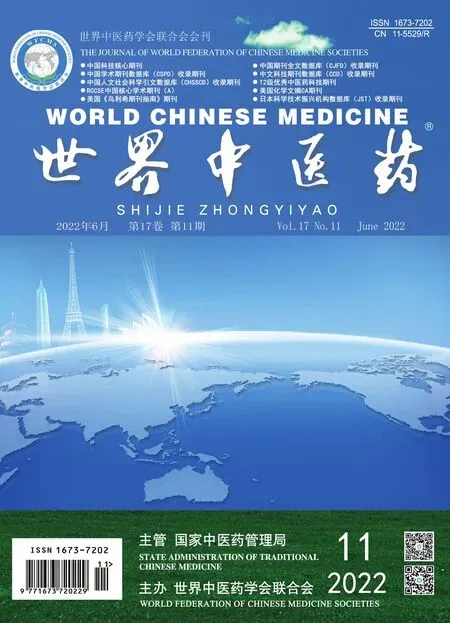疏肝健脾法在潰瘍性結(jié)腸炎治療中的應(yīng)用
陶麗芬 彭卓崳 李桂賢 蔡林坤 藍(lán)斯瑩
(1 廣西中醫(yī)藥大學(xué),南寧,530001; 2 廣西中醫(yī)藥大學(xué)第一附屬醫(yī)院消化內(nèi)科,南寧,530023)
潰瘍性結(jié)腸炎(Ulcerative Colitis,UC)屬中醫(yī)“痢疾”“久痢”“泄瀉”及“腸澼”等范疇,臨床以黏液膿血便或血性腹瀉、里急后重為主要表現(xiàn)[1]。關(guān)于該病病因病機(jī),張介賓在《景岳全書(shū)》中言:“凡遇怒氣便作泄瀉者,必先以怒挾食,致傷脾胃……此肝脾二臟之病也,蓋以肝木克土,脾氣受傷而然。”《醫(yī)方考》中亦有“瀉責(zé)之脾,痛責(zé)之肝;肝責(zé)之實(shí),脾責(zé)之虛,脾虛肝實(shí),故令痛瀉”之論。可見(jiàn)UC雖病位在大腸,但肝脾功能的失調(diào)在UC發(fā)病過(guò)程中起重要作用。肝郁脾虛是臨床上UC發(fā)生的關(guān)鍵病機(jī)之一,相關(guān)研究也證實(shí)了肝郁脾虛證在UC中的多發(fā)性[2]。因此疏肝健脾法的研究對(duì)于中醫(yī)治療UC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shí)意義。
1 肝郁脾虛是UC發(fā)生發(fā)展的重要病機(jī)
1.1 肝脾在生理上相互為用,維持正常消化功能 肝主疏泄,喜調(diào)達(dá)而惡抑郁,脾主運(yùn)化,宜健運(yùn)而惡壅滯,肝疏脾運(yùn)是維持正常消化功能的重要基礎(chǔ),兩臟生理功能上相互影響、密不可分。首先,脾的運(yùn)化有賴(lài)于肝的疏泄。《血證論》曰:木之性主于疏泄,食氣入胃,全賴(lài)肝木之氣以疏泄之,而水谷乃化。”可見(jiàn)木能疏土而脾滯以行,土得木而達(dá)。脾得肝之疏泄、分泌膽汁才能升降相宜、運(yùn)化功能健旺,從而為脾胃受納腐熟、運(yùn)化水谷、通利三焦氣機(jī)升降提供保障。其次,肝的疏泄有賴(lài)于脾的滋榮,《醫(yī)宗金鑒》曰:“肝為木氣,全賴(lài)土以滋培。”脾胃健運(yùn)、升降有序則水谷精微輸布有序于肝,肝木得陰血滋濡則剛?cè)嵯酀?jì),肝氣沖和條達(dá)、疏泄有常,即土旺木榮之意。由此可知,肝脾兩臟在生理上相互為用、相得益彰,共同維持著水谷精微的消化吸收,誠(chéng)如《醫(yī)學(xué)衷中參西錄》所言:“肝脾者,相助為理之臟也。”
1.2 肝郁脾虛發(fā)為UC,影響疾病預(yù)后及轉(zhuǎn)歸 正常情況下機(jī)體內(nèi)肝木脾土的關(guān)系以承平為度,承乃制,“肝木疏土,脾土營(yíng)木,土得木而達(dá)之,木賴(lài)土以培之”。肝疏脾運(yùn)協(xié)同作用,以維持體內(nèi)水谷精微消化、吸收、輸布功能的正常,是保證機(jī)體氣血津液平衡的重要環(huán)節(jié),但當(dāng)木太過(guò)或土不及,這種平衡就會(huì)遭到破壞。在快節(jié)奏的現(xiàn)代生活中,思慮過(guò)度、焦躁緊張等精神心理因素普遍存在,不良情緒刺激易導(dǎo)致肝失疏泄之職,氣機(jī)失調(diào)、肝氣郁結(jié)為患。因肝受氣于心,傳之于脾,且肝脾兩臟為疏泄與運(yùn)化相互為用的關(guān)系,肝木一郁,疏泄不及,則先克脾胃之土,導(dǎo)致脾土陰凝板滯,久壅不運(yùn)而成虛,形成肝郁脾虛之證。肝脾同損則氣血生化不足,引起腸絡(luò)黏膜失養(yǎng),腸黏膜屏障功能下降而易受濕、熱、瘀、毒等病理因素侵襲。此外,木壅土虛、運(yùn)化失常則水反為濕、谷反為滯,濕滯壅滯腸間,日久濕從熱化,濕熱熏蒸,搏結(jié)氣血,腸道傳導(dǎo)失司,脂絡(luò)受損,氣凝血滯,腐敗成瘍,化為赤白膿血而下。加之肝氣郁結(jié)阻滯,血?dú)饽郎⒏瓪獠煌ǎ蔝C患者常有腹痛、里急后重頻發(fā)。并且UC具有纏綿難愈、病程漫長(zhǎng)的特點(diǎn),臨床UC患者多合并有不同程度的情志不舒癥狀,使得氣滯郁結(jié),木壅土滯,脾虛更甚,脾虛難復(fù),可見(jiàn)肝郁脾虛因素始終貫穿在UC整個(gè)病理過(guò)程之中,是關(guān)系到疾病發(fā)作和愈合的關(guān)鍵環(huán)節(jié)。現(xiàn)代研究發(fā)現(xiàn),肝主疏泄與調(diào)節(jié)下丘腦-垂體軸有關(guān),脾主運(yùn)化主要與胃腸功能有關(guān)[3]。肝氣郁結(jié)后出現(xiàn)的焦慮、抑郁等癥狀可直接作用于支配胃腸運(yùn)動(dòng)的迷走神經(jīng),使膽堿能神經(jīng)興奮性減弱,從而抑制胃腸運(yùn)動(dòng)功能,胃腸道動(dòng)力不足而引起分泌、消化、吸收障礙[4-5],導(dǎo)致出現(xiàn)納差、腹痛、腹脹、腹瀉等UC相關(guān)胃腸道癥狀。此外,肝郁、脾虛均可對(duì)胃腸道黏膜屏障具有一定的損害作用。肝郁可通過(guò)改變胃腸黏膜的局部微循環(huán)、免疫微環(huán)境,以及黏膜上皮細(xì)胞增殖與凋亡等來(lái)影響炎癥的發(fā)展和潰瘍的愈合[6]。另有研究表明,焦慮、抑郁通過(guò)影響神經(jīng)內(nèi)分泌介質(zhì)的主要效應(yīng)物如乙酰膽堿、腎上腺素、去甲腎上腺素、皮質(zhì)醇促使抗炎反應(yīng)失衡,可能是UC復(fù)發(fā)、轉(zhuǎn)化的潛在機(jī)制[7]。脾虛引起腸黏膜損傷的機(jī)制可能與胃腸運(yùn)動(dòng)的異常、胃電節(jié)律的紊亂、胃腸黏膜細(xì)胞的凋亡、胃腸激素分泌的異常等有關(guān)[8-9]。這些研究思路和成果從現(xiàn)代分子生物學(xué)角度支持了肝郁脾虛病機(jī)從心理、神經(jīng)、免疫系統(tǒng)等交互作用,影響著UC的發(fā)生發(fā)展及預(yù)后轉(zhuǎn)歸,為中醫(yī)臨床從肝郁脾虛論治UC和疏肝健脾法的確立提供了一定的科學(xué)依據(jù)。
2 疏肝健脾法在UC治療中的應(yīng)用研究
肝郁脾虛是UC發(fā)生、發(fā)展的關(guān)鍵病機(jī),臨床上亦發(fā)現(xiàn)UC患者普遍存在身心癥狀[10-11]。契合該病肝郁脾虛的病機(jī)特點(diǎn),治療當(dāng)以調(diào)和肝脾為切入點(diǎn),正如葉天士所言:“治痢之大法,不過(guò)通塞二義,肝脾并重。”UC治療當(dāng)以疏肝健脾為治療要旨,疏肝理氣、調(diào)暢氣機(jī)為先,益氣健脾、扶正祛邪并重。使肝氣調(diào)達(dá)則情志得舒,胸脅脹滿(mǎn)竄痛自消,脾胃健運(yùn)、統(tǒng)攝有常則脹除食復(fù),氣化濕去,黏液膿血便自止,腹痛后重可除。
臨床上已有不少醫(yī)家采用疏肝健脾法取得了較好療效,所用方劑從柴芍六君子、痛瀉要方、逍遙散等經(jīng)方到各種自創(chuàng)方,涉面較廣。如吳春江和趙雙梅[12]認(rèn)為本病多與情志失調(diào)有關(guān),辨證多為肝郁脾虛,以痛瀉要方加減治療,總有效率為94%,而宋小莉[13]的研究結(jié)果也證實(shí)了痛瀉要方的有效性。全國(guó)名老中醫(yī)李桂賢教授認(rèn)為UC為本虛標(biāo)實(shí)之疾,以肝郁脾虛為本,濕熱內(nèi)蘊(yùn)為標(biāo),臨證運(yùn)用經(jīng)驗(yàn)方加味柴芍六君子湯治療肝郁脾虛型的UC患者,療效頗好[14]。李帥軍等[15]認(rèn)為UC病機(jī)基礎(chǔ)為肝氣郁滯,橫逆犯脾,脾胃運(yùn)化失常,并給予痛瀉要方化裁而成的腸舒顆粒治療肝郁脾虛證患者,結(jié)果顯示腸舒顆粒可顯著減輕患者臨床癥狀,改善腸黏膜病變,并且下調(diào)患者血清一氧化氮水平及白細(xì)胞介素-8、白細(xì)胞介素-6、腫瘤壞死因子-α的水平。彭志紅等.[16]、楊樺和鄧金鳳[17]認(rèn)為本病與肝郁脾虛關(guān)系密切,將肝郁脾虛型UC患者隨機(jī)分為2組,分別予以逍遙散化裁方、柳氮磺胺吡啶治療,結(jié)果顯示逍遙散化裁方在治療本病上具有療效顯著、復(fù)發(fā)率低的優(yōu)點(diǎn)。陳旭[18]認(rèn)為肝郁脾虛證是UC臨床常見(jiàn)證型,并采用疏肝健脾顆粒治療29例肝郁脾虛證型UC患者,以柳氮磺吡啶腸溶片作對(duì)照,結(jié)果表明疏肝健脾顆粒組臨床總有效率明顯高于柳氮磺吡啶腸溶片組。李淑英等[19]認(rèn)為UC主要病機(jī)為情志因素致肝氣郁結(jié),橫犯脾胃,脾運(yùn)失常,傳導(dǎo)失司,日久濕濁內(nèi)蘊(yùn),氣血凝滯,腸絡(luò)失和,血敗肉腐成瘍。并將142例患者分為觀察組(柳氮磺吡啶片+健脾疏肝煎)和對(duì)照組(柳氮磺吡啶片+中藥安慰劑)進(jìn)行干預(yù)觀察,結(jié)果表明健脾疏肝煎可顯著減輕肝郁脾虛型UC患者的臨床癥狀并改善腸黏膜病變。
現(xiàn)代醫(yī)學(xué)認(rèn)為UC的發(fā)病機(jī)制涉及免疫、腸黏膜屏障、腸道微生態(tài)、凝血等多種因素,中醫(yī)藥對(duì)本病的干預(yù)作用機(jī)制相應(yīng)地也多從以上幾個(gè)方面研究[20-21]。目前疏肝理脾法治療UC的機(jī)制研究報(bào)道不少,但研究尚未深入全面,大多集中于神經(jīng)-內(nèi)分泌-免疫、胃腸道免疫、腸黏膜屏障、腸道微生態(tài)機(jī)制的研究。如秦震聲和張燕生[22]研究發(fā)現(xiàn),疏肝理脾法可能是通過(guò)作用于調(diào)節(jié)神經(jīng)-內(nèi)分泌-免疫網(wǎng)絡(luò),促進(jìn)抗炎因子的產(chǎn)生而發(fā)揮治療作用的。顧立剛等[23]的研究結(jié)果表明,疏肝健脾方藥可使結(jié)腸黏膜組織一氧化氮含量和髓過(guò)氧化物酶活性下降,從而減少腸黏膜組織炎癥細(xì)胞浸潤(rùn),促進(jìn)炎癥修復(fù)。肖永峰[24]、蔣志濱等[25]的研究結(jié)果顯示,痛瀉要方可通過(guò)調(diào)控肝臟硬脂酰輔酶A去飽和酶1與腸道5-羥色胺的平衡,下調(diào)腫瘤壞死因子-α等炎癥介質(zhì)途徑,或通過(guò)提高結(jié)腸黏膜中過(guò)氧化物酶體增殖物激活受體γ基因和蛋白表達(dá)途徑,調(diào)節(jié)腸黏膜免疫抗炎機(jī)制而對(duì)肝郁脾虛型UC大鼠起到治療效果。李哮天等[26]的研究證實(shí)加味柴芍六君子湯可能是通過(guò)調(diào)整腸道菌群,以及促使體內(nèi)炎癥介質(zhì)如白細(xì)胞介素-1β、白細(xì)胞介素-10的分泌增加,抑制抗炎因子如腫瘤壞死因子-α和γ干擾素等水平的下降而有效治療UC。牛躍輝[27]的研究也表明了加味柴芍顆粒可通過(guò)降低UC患者血清中白細(xì)胞介素-6、腫瘤壞死因子-α和C反應(yīng)蛋白等水平改善UC患者炎癥狀態(tài),改善病情。這些臨床觀察及實(shí)驗(yàn)藥理學(xué)研究成果為疏肝健脾法治療UC提供了一定的理論依據(jù),也為中醫(yī)藥治療UC的機(jī)制和靶點(diǎn)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
3 研究不足和展望
但是,中醫(yī)對(duì)UC的研究多側(cè)重于臨床觀察,且臨證用方繁雜不一,療效評(píng)價(jià)機(jī)制尚未完善,也存在著研究樣本量較小,可重復(fù)性差的不足。對(duì)于實(shí)驗(yàn)研究方面的研究,僅提示了疏肝解郁方治療前后某些指標(biāo)的變化,并且特異度靈敏度高的檢測(cè)指標(biāo)尚未確定,目前的實(shí)驗(yàn)研究也尚未能充分反映UC慢性病理過(guò)程中相關(guān)指標(biāo)的復(fù)雜性、動(dòng)態(tài)性變化。此外,實(shí)驗(yàn)研究多集中于免疫機(jī)制研究,對(duì)于其他如腸道微生態(tài)、神經(jīng)-免疫-內(nèi)分泌機(jī)制的研究相對(duì)較少,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成果。因此,未來(lái)的研究方向:1)在臨床研究中應(yīng)增大樣本量,完善療效評(píng)價(jià)機(jī)制。2)實(shí)驗(yàn)研究上應(yīng)深入全面探究疏肝健脾治法與現(xiàn)代分子生物學(xué)的內(nèi)在聯(lián)系,并加強(qiáng)特異度靈敏度高指標(biāo)的研究;結(jié)合中醫(yī)整體觀,從遺傳基因、通路等多角度、多機(jī)制研究疏肝健脾法治療UC的作用機(jī)制和靶點(diǎn),為基于此治法研發(fā)出治療UC更有效的藥方提供依據(jù)。
4 小結(jié)
辨證論治是中醫(yī)臨證醫(yī)學(xué)體系的核心,而治法上貫理、下統(tǒng)方藥,在辨證論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對(duì)于治法的研究是中醫(yī)取效的關(guān)鍵環(huán)節(jié)之一。肝郁脾虛證是UC臨床多見(jiàn)的證型,針對(duì)肝郁脾虛的病因病機(jī)所確立的疏肝健脾法在UC治療中的應(yīng)用已日趨成熟。并且證實(shí)基于疏肝健脾法選用的疏肝健脾方對(duì)于緩解患者癥狀、改善黏膜損傷等確有療效,在實(shí)驗(yàn)學(xué)指標(biāo)如血清炎癥指標(biāo)、腸道菌群的調(diào)節(jié)方面也有一定的效果,不良反應(yīng)少,遠(yuǎn)期療效可觀,與西醫(yī)治療比較,確有其優(yōu)勢(sh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