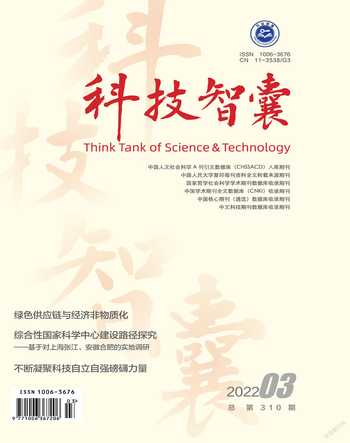綠色供應鏈與經濟非物質化
盧風
摘? 要:綠色供應鏈是“生態經濟體系”的“內在環節”或子系統。從生態文明建設的角度看,綠色產業鏈的形成依賴于文明各維度的聯動變革,從屬于由“黑色發展”轉向“綠色發展”的根本需要。從工業文明的“黑色發展”轉向生態文明的“綠色發展”必然要求經濟增長的非物質化。非物質經濟就是生產和消費非物質價值的經濟。物質經濟增長是有極限的,但非物質經濟增長沒有極限。非物質需要是人的本真需要。大力發展非物質經濟,既可以保持經濟的持續增長和人民生活的幸福,又可以卓有成效地節能減排、保護環境、維護生態健康。綠色供應鏈應成為激勵非物質經濟增長的商業機制。
關鍵詞:綠色供應鏈;非物質價值;非物質經濟
中圖分類號:X32;F27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881/j.cnki.1006-3676.2022.03.01
自從1972年羅馬俱樂部發表《增長的極限》以后,經濟增長有沒有極限的問題就成了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增長的極限》一書的基本結論之一是:“如果在世界人口、工業化、污染、糧食生產和資源消耗方面現在的趨勢繼續下去,這個行星上增長的極限有朝一日將在今后100年中發生。最可能的結果將是人口和工業生產力雙方有相當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衰退。”[1]在“發展”是最強音的現時代,在增長被理解為發展的必要條件的情況下,持存在增長的極限的觀點必然會大受質疑。1981年出版的朱利安·林肯·西蒙著的《終極資源》一書,便是對這種觀點的系統反駁。在西蒙看來,關于增長存在極限的悲觀論調忽視了一個最重要的事實:人類知識增長是沒有極限的,人類在謀求發展的過程中總會遭受挫折,遇到困難,但隨著知識的增長和技術的進步,挫折會被超越,困難會被克服。一種資源枯竭了,總能找到替代的資源,環境被污染了,但總能重新使之清潔。西蒙說:“我們加速進步的主要動力就是知識儲備,而減速的剎車就是想象力不足。終極資源(the ultimate resource)是人——有技術、有精神且滿懷希望的人,他們為自身利益而實現其意愿,發揮其想象力,且最終必讓所有人都受益。”[2]直至今天,仍有很多人不能接受存在增長的極限的判斷。如今,“供應鏈”是一個被頻繁使用的術語。在新冠疫情長時間持續的今天,許多人在擔憂供應鏈的斷裂。筆者結合建構綠色供應鏈的必要性和非物質經濟發展趨勢,探討是否存在增長極限的問題。
一、綠色供應鏈是生態經濟體系的子系統
古代社會的供應鏈簡單,百姓必需品(如糧食)的大部分是百姓自己生產的,需要買賣的東西也多半是當地生產的。西方研究者認為,物流和供應鏈管理概念在古代已被應用。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亞歷山大大帝,他的杰出才能并不僅是軍事才能,他最突出的才能是有效運用供應鏈管理方法。例如,他的軍隊通常駐扎在河邊或海港,這樣就便于從其帝國的其他地區運送物資。歷史學家已指出,亞歷山大大帝常常利用其強大的軍需供應鏈,制定其軍隊的行動計劃并管理軍隊。[3]中國古語“兵馬未動,糧草先行”,足見中國古人早已明白物資供應是打勝仗的必要條件。不難推斷,中國古代的杰出軍事家必然重視供應鏈管理(當然,他們未必用了“供應鏈”這個概念)。現代社會的勞動分工越來越細,交通和通信越來越發達,供需關系越來越復雜,供應鏈必然越來越受重視。今天的供應鏈已是全球化的,一個國家某種重要生產原料或商品的短缺會影響很多國家的經濟運行。
隨著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的加劇以及生態危機和氣候變化的凸顯,西方管理學界首先提出了“高效低耗供應鏈”(lean supply chain,縮寫為LSC)。“高效低耗供應鏈”被界定為“在合適時間和地點,為終端客戶制造合適產品時使供應鏈下游產生的廢物最小化”的供應鏈。LSC是一種基于成本降低和成本彈性的戰略,它通過減少或消除整個供應鏈中與過多時間、勞動力、設備、空間以及庫存相關的無附加值操作而改善供應過程。通過LSC,公司可以節約資本,提高效率和競爭力。[4]
隨著環境保護政策制定和立法的推進,企業降低“環境足跡”(environmental footprint)的壓力增大。作為一種哲學的綠色范式(green paradigm)應運而生。從此,供應鏈中的綠色實踐既受到實業界的重視,也受到了學術界的重視。各種利益相關者,包括客戶、政府以及執法部門都提出了降低供應鏈環境影響的要求。“綠色供應鏈”(green supply chain 縮寫為GSC)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提出來的。不同研究者給出了不同的“綠色供應鏈”定義。有人從形式的角度定義綠色供應鏈,綠色供應鏈是以整合環境保護與組織間活動的形式而形成的協調的供應鏈;也有人把綠色供應鏈界定為結合了環境保護的供應鏈,包括產品設計、原料采購和選擇、制造過程、向客戶提供的最終產品,以及產品使用期結束之后的全生命周期管理[5]。結合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的最新發展和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現實需要,趙建軍等研究者對“綠色供應鏈”進行了新的界定,認為完善的綠色供應鏈應該以產品的全生命周期為邏輯主線,全面考慮整個過程中企業、消費者、政府、社會公眾、自然等利益相關者的權益;要形成包含供應端—物流端—消費端—回收端—數據端在內的“五端”閉合鏈條,將各方資源整合成一盤棋,聯成一張網,統一規劃,整體布局,上下聯通,形成全產業鏈的協調配合,形成合力,促進企業之間以及社會各種角色之間實現產品和信息最大程度上的互動。[6]
打造綠色供應鏈顯然是建設“以產業生態化和生態產業化為主體的生態經濟體系”[7]的必然要求,而生態經濟體系是生態文明建設的基礎。在生態文明視域中,才能全面透徹地理解打造綠色供應鏈的必要性和復雜性。
從生態文明建設的角度看,打造綠色供應鏈,不僅是生產、運輸和通信和企業界的事,也不僅是經濟領域的事。為打造綠色供應鏈,必須改變能源結構,改變產業結構,淘汰重污染、低效能的產業,發展低碳高效產業,提高運輸效率,降低運輸排放,等等。如果生產和運輸主要依靠燃燒化石燃料,那么產量和運輸量增大必然增加排放、污染環境。為改變這種情況,必須逐漸降低對煤、石油等化石燃料的依賴,大力發展太陽能、風能、氫能等可再生能源。簡言之,綠色供應鏈的打造從屬于生態經濟體系的建構,有了成熟的生態經濟體系才可能有完整的綠色供應鏈,而建構生態經濟體系要獲得公共政策和法律的支持。供應鏈連接著大眾消費,不改變大眾消費模式,供應鏈就不可能從污染轉變為綠色,綠色供應鏈的形成需要大眾綠色消費的支持。由“大量拋棄”或“大量排放”的消費到綠色消費的轉變是一種文化的轉變。總之,作為生態經濟體系之子系統的綠色供應鏈的形成依賴于文明各維度的聯動變革。
對于企業來講,采用綠色供應鏈管理模式是為了既能履行法律賦予的環境保護責任,又能提高企業效率和競爭力。從生態文明建設的高度看,打造綠色供應鏈是為了謀求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可持續發展。只有綠色發展才是真正可持續的,打造綠色供應鏈歸根結底是為了實現文明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由工業文明的“黑色發展”轉向生態文明的“綠色發展”。
二、經濟非物質化是綠色發展的必然要求
工業文明的“黑色發展”既與大量使用化石能源直接相關,也與物質主義發展觀密切相關。在人們相信化石能源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時代,人們也認為,發展的根本標志就是物質財富數量的增長。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增長就主要體現為物質經濟的增長。正如美國經濟學家霍肯(Paul Hawken)所分析的,工業文明的經濟主要是物質經濟(mass economy)。工業文明物質經濟的發展自1880年到20世紀80年代,歷時100多年。在這段時間內,人們發現了石油,發明了內燃機,逐漸普遍使用電力,逐漸建構了工業化、消費導向的社會。之所以用“物質”(mass)一詞,是因為這段歷史的主要經濟動力是以化石燃料取代人力來為大眾生產物質產品。[8]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人承認地球生物圈或生態系統的承載力是有限的。在這種情況下,對“綠色發展”的界定必須考慮經濟的非物質化趨勢。物質經濟的增長是有極限的。習近平總書記說:“生態環境問題歸根結底是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問題,要從根本上解決生態環境問題,必須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加快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空間格局、產業結構、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把經濟活動、人的行為限制在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能夠承受的限度內,給自然生態留下休養生息的時間和空間。要加快劃定并嚴守生態保護紅線、環境質量底線、資源利用上線三條紅線。對突破三條紅線、仍然沿用粗放增長模式、吃祖宗飯砸子孫碗的事,絕對不能再干,絕對不允許再干。”[7]這段話說得很明確,必須把“經濟活動、人的行為限制在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能夠承受的限度內”。這就是說,物質經濟增長是有極限的,“三條紅線”就是物質經濟增長的極限。
那么,物質經濟增長的極限就是經濟增長的極限嗎?不是!物質經濟不增長了,非物質經濟可以不斷增長。謀求綠色發展必須促進經濟的非物質化增長,經濟非物質化是綠色發展的必然要求。
非物質經濟活動是生產和消費(對應著供給與需求)非物質價值的經濟活動。在20世紀90年代,已有西方經濟學家開始分析物質價值和非物質價值之間的區別,并開始探討這兩種價值之間的關系。
對客觀真理的追求有力推動著精確科學(exact science)的進步,有西方經濟學家認為,這種追求就是供給側的對非物質價值(nonmaterial value)的根本追求。科學家共同體為人們提供客觀知識,就是在供給側創造非物質價值。西方經濟學家用“非物質的”(nonmaterial)代替意義含糊的“精神的”(spiritual)或“心靈的”(mental),“非物質的”一詞的外延更廣。他們傾向于認為,非物質價值就是那些深深植根于人性(human nature)之中且不同于可用貨幣購買的貨物或服務的價值。對客觀真理的追求無疑是對非物質價值的追求,但人性中還有一種更強的非物質價值追求,那就是自我表現(self-expression)。自我表現是每一個健康人的內在需要,這種需要遠遠超過追求客觀真理的需要。正是這種強烈需要創造了藝術和評論性科學(the commenting sciences),它們遠比精確科學更能讓眾多人著迷。需求側的非物質價值可被定義為對自我表現的追求,它滿足人類評論世界和自我情感的需要,對這種價值的追求是藝術創造、評論性科學研究乃至人們一部分日常行為的動力。[9]已有西方經濟學家認為,物質價值和非物質價值的相互作用既是經濟增長的原初動力,又是促進產業循環的動力,而產業循環是經濟增長的自然機制。[10]
非物質價值并非不可以通過貨幣買賣。自古以來,人的許多非物質需要都是可以通過貨幣購買的,創造非物質價值的人也可以通過出售自己的作品而獲得經濟收益。例如,中國古代書畫家也賣書畫,喜歡書畫的人也買書畫。如今,正蓬勃發展的文化產業正是典型的生產非物質價值的產業。同時,也并非只有科學研究和自我表現才創造非物質價值,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像中醫按摩這樣的行業所“生產”的價值也屬于非物質價值。消費者從這個行業購買的是身體的舒適感,而不是物質產品。這樣的行業如果能夠健康發展,也有助于保護環境和節能減排。如果越來越多消費者的消費偏好由買大排量的車轉變為享受中醫按摩的舒適,那么就能有效地實現節能減排。
謀求綠色發展之所以必須發展非物質經濟,是因為非物質價值的創造是沒有極限的。當然,非物質價值必須有物質載體。例如,一本小說的價值主要在于其非物質價值,但一本小說必須有個版本——紙質或電子版。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是,非物質產品的量值比(即單位質量的價值)可以遠遠大于物質產品的量值比。例如,汽車的量值比大約是200元∕kg,水泥的量值比更低,而電腦軟件(包括音樂、影視劇、游戲等)的量值比也許可達100000元∕kg。像梵高那樣的藝術大師創作一幅畫的能耗微乎其微,所需的物質材料數量也微不足道,但其作品的量值比或許可達10000000元/kg以上。隨著數字化技術的發展,將來文化產品的物質形態可能完全隱而不見。例如,紙質書將來可能趨于消亡,只有研究版本學的學者才需要去找紙質書;有個閱讀器,就可以閱讀任何書,無須像今天的人文學者那樣,書房里滿是紙質書。將來買一本書就是買電子文本的使用權,這樣一來暢銷書的量值比就更大了。正因為非物質產品(可能是無形的)的量值比比物質產品的量值比高得多,且非物質產品有很大的提高量值比的空間。所以,促進非物質經濟增長而控制物質經濟增長,可以在有效節能減排、保護環境、維護生態健康的同時,繼續保持經濟增長。
早在20世紀30年代,美國哲學家、建筑設計師、作家和發明家富勒(Buckminster Fuller)就曾預言,隨著技術的進步,人類將有能力用越來越少的材料做越來越多的事情,直至不用任何東西而做任何事情。[11]這在當時聽起來像神話。但隨著數字化和人工智能技術的迅猛發展,這一發展趨勢已在某種程度上成為現實。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尼古拉·尼葛洛龐帝(Nicholas Negroponte)說:“從原子到比特的飛躍已是勢不可擋、無法逆轉。”[12]“傳統的世界貿易由原子之間的交換組成。以愛維養礦泉水為例,我們用緩慢、辛苦而昂貴的方式,耗費很長時間,把大量笨重而缺乏生氣的‘質量’(mass)——也就是‘原子’——運送到千里之外。經過海關的時候,你需要申報的是原子而不是比特。即使是采用數字錄音方式制作的音樂,都以塑料光盤(CD,compact disc)的形式發行,無論在包裝、運送還是庫存上的成本,都相當可觀。這一切都在發生急劇的變化。過去,大部分的信息都經過人的緩慢處理,以書籍、雜志、報紙和錄像帶的形式呈現;而這,很快將被即時而廉價的電子數據傳輸所取代。這種傳輸將以光速來進行。”[13]
“從原子到比特的飛躍”是經濟非物質化的一個側面(信息是非物質的)。美國企業家羅伯特·特賽克(Robert Tercek)在2015年出版的《蒸發:在去物質化世界中獲得成功的可靠策略》一書中,比較夸張地描述了這一側面。特賽克說:隨著智能手機功能的擴展和改進,對其他各種單一功能的數字化設備的分別使用正趨于消失。在過去的8年中,伴隨著智能手機的銷售浪潮,錄像機、錄音機、照相機、便攜式音樂播放器、DVD播放器、掌上游戲機的銷量暴跌。一句話,它們都蒸發了。當可觸摸的物質產品被不可見的軟件所取代時,物質產品就蒸發了,軟件可在數字化設備上立即下載。當附近的商店被網絡連鎖店所取代時,商店就蒸發了。網店并不存在于任何一個特定地點,卻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候都可以光顧,只需要用手機去連接數據。當制造、海運、倉儲、零售業的全球供應鏈被分解且被軟件和數字化網絡重組時,那些舊業態就蒸發了。真實事物被數字化隱喻所取代的過程就是蒸發,按一下按鈕數字化隱喻即可得以復制、升級、分配、刪除。[14]
因為非物質價值需要物質載體,所以發展非物質經濟必然耗能,發展非物質經濟必須堅持“產業生態化”的發展方向。如果拍一部影片就砍掉一片樹林,那么非物質經濟增長同樣會導致生態破壞。迅猛發展的信息技術本可以有力支持非物質經濟的發展。在2020年“十一黃金周”期間,黃山等旅游勝地人山人海,擁擠不堪,行走困難,許多人說“我后悔來XX了”。如果虛擬技術高度發達,在虛擬空間游黃山與實地游根本沒有區別,那么旅游業就可以大大節能減排,還可以避免“黃金周”的擁擠。但是,這取決于網絡技術的能耗。就目前情況看,信息和通信技術(ICT)部門的能耗隨著互聯網流量的增長而迅速增加,對環境和氣候的影響也在增加。[15]欲使信息技術為經濟非物質化和綠色發展作貢獻,必須通過技術創新大幅降低互聯網的能耗。
三、非物質需要是人的本真需要
非物質需要是人類的本真需要。人與非人動物的區別何在?著名美國人類學家格爾茲(Clifford Geertz)說:“我與馬克斯·韋伯一樣,認為人是懸掛在由他們自己編織的意義之網上的動物。”[16]如果用“動物”做定義項,就可以把人定義為:追求意義的文化動物。格爾茲說:“在文化起源和我們今天所熟悉的人的出現之間,存在大大超過一百萬年的重合。準確的日期……并不關鍵;關鍵的是存在時間的重合,而且是非常持久的重合。人類種系發生史的最后一些階段……與人類文化史的一些初始階段,都發生在同樣一個偉大的地質時代——所謂的冰川期。”[17]所以,“文化不是被附加在完善的或實際上完善的動物身上,而是那個動物本身的生產過程的構成要素,是核心構成要素”[17]。換言之,文化是人超越于非人動物的根本標志。
人與非人動物都有物質需要,但文化使人的物質需要超越了非人動物的物質需要。人的物質需要經文化的放大而表現得不知饜足。非人動物吃飽了就滿足了,但人對食物的需求不止于吃飽而食不厭精,人創造了食文化,土豪甚至一頓飯可花去幾萬乃至十幾萬元。非人動物有個巢穴就滿足了,但人對居所的需求不止于遮風避雨而力求豪華,正因為如此,土豪們裝修豪宅可花費上千萬元甚至上億元。但人的真實物質需求量與非人動物并沒有區別。例如,每個人每天都只能吃那么多食物,每個人行住坐臥只能占那么大的空間。土豪們在吃飯、裝修別墅等方面一擲千金,并非為了滿足自己的真實物質需要,而是為了滿足自己的非物質需要——讓別人羨慕。說到底,他們是在“表現自我”,想讓別人羨慕,也就是想得到別人的承認。所以,人之物質需求的不知足源自對非物質價值的追求。
意義追求才是人的本真需要。意義追求源自人之超越于非人動物的本真特征——文化性,而物質需要源自人的動物性,即人與非人動物共同的特征。“意義”是非物質形態的,必須在文化體系中才能得以標識或體現。文化體系由器物、制度和觀念構成。在特定文化中,一個人如何向其他人表明自己的人生是有意義的?似乎必須通過自己所擁有的物質財富和在社會中所處的等級或階層而表明自己存在的意義。古代文明用不同數量、形制和質料的器物去標識人間的尊卑貴賤,但不容許廣大勞動人民擁有“難得之貨”。現代工業文明的制度和主流意識形態激勵所有人都參與創造、獲取、占有物質財富的競爭,過分突顯了器物(即商品)的符號功能,這使多數人認為,物質財富是最重要的人生意義標識。這是對人類價值追求的嚴重誤導。實際上,物質財富不是人生意義的唯一標識,甚至不是必要的標識,一個人完全可以通過自己的德行和智慧而獲得他人的承認,從而實現自我價值。
當然,不能指望多數人都能像蘇格拉底、梭羅、顏回等人那樣重視德行、智慧遠甚于重視身外之物。多數人都需要用貨幣的刺激才能持久地勤奮勞作,許多聰明人也需要用貨幣刺激才能保持不衰的創新沖動。正因為如此,在市場經濟的社會條件下大力發展非物質經濟既是重要的,又是必要的。文明的發展源自人的無限追求。追求無限就是追求意義。各行各業的創新就源自各行各業精英對意義或無限的追求。保護私人財產權和知識產權的市場經濟制度能激勵各行各業的創新。但是,工業文明的市場經濟制度過分激勵了物質價值的創造和創新,它激勵人們無限追求物質經濟的增長。由于物質經濟增長是有極限的,所以經濟增長必然被虛擬化。一個地區汽車、廠房、住房等物質財富存量的增長是有極限的,但政府可以通過貨幣政策制造經濟增長的假象,地方政府可以通過不必要的“折騰”——例如,拆掉一條大街兩旁的房子,重新建房并拓寬街道——而制造經濟增長的假象。各種金融機構可以通過包裝、推銷各種金融產品而刺激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交易,從而制造經濟增長的假象。但虛擬經濟的泡沫遲早會破滅,建設生態文明必須促進市場經濟的制度創新。我國不僅要培育碳交易或污染權交易的市場,以激勵企業和個人積極從事節能減排的創新,而且要培育激勵非物質經濟增長的市場,以激勵企業和個人積極從事非物質價值的創造。
大力發展非虛擬的非物質經濟既可以在保持經濟增長的同時有效地節能減排,又能提高人們的幸福感。有鑒于此,打造綠色供應鏈,不能只考慮物質產品供應,還必須充分考慮非物質產品供應。綠色供應鏈應成為促進非物質經濟增長的商業機制。
參考文獻:
[1] 丹尼斯·米都斯,等.增長的極限[M].李寶恒,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7.
[2] Julian L. Simon. The Ultimate Resource [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1:348.
[3] Charisios Achillas,Dionysis D. Bochtis,Dimitrios Aidonis,Dimitris Folinas. Gree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M].New York:Routledge,2019:5-6.
[4] Turan Paksoy, Gerhard-Wilhelm Weber,Sandra Huber. Lean and Gree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Optimization Models and Algorithms[M].Cham, Switzerland:Springer,2019:2-3.
[5] Turan Paksoy,Gerhard-Wilhelm Weber,Sandra Huber. Lean and Gree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Optimization Models and Algorithms[M].Cham, Switzerland: Springer,2019:3-4.
[6] 中國社科院大學新時代生態文明研究中心,21世紀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生態文明研究中心,綠色發展智庫研究院.“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與綠色供應鏈專家座談會資料匯編[Z].2020:21-22.
[7] 習近平.推動我國生態文明建設邁上新臺階[J].求是,2019(03):4-19.
[8] Paul Hawken.The Next Economy[M].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83:8.
[9] Arvid AuIin.The Origins of Economic Growth: The Fundamental Interaction between Material and Nonmaterial Values[M].Verlag Berlin:Springer,1997:18.
[10] Arvid AuIin. The Origins of Economic Growth:The Fundamental Interaction between Material and Nonmaterial Values[M].Verlag Berlin:Springer,1997:V.
[11] Robert Tercek. Vaporized:Solid Strategies for Success in a Dematerialized World[M].Los Angeles:Life Tree Media,2015:12.
[12] 尼葛洛龐帝.數字化生存[M].胡冰,范海燕,譯.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13.
[13] 尼葛洛龐帝.數字化生存[M].胡冰,范海燕,譯.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12.
[14] Robert Tercek.Vaporized: Solid Strategies for Success in a Dematerialized World[M].Los Angeles:Life Tree Media,2015:34.
[15] 趙杰文,王明.數據中心的輔助矩陣啟發式最小能耗綠色服務遷移[J].現代電子技術[J].2020(08):32-35,40.
[16] 克利福德·格爾茲.文化的解釋[M].納日碧力戈,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5.
[17] 克利福德·格爾茲.文化的解釋[M].納日碧力戈,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