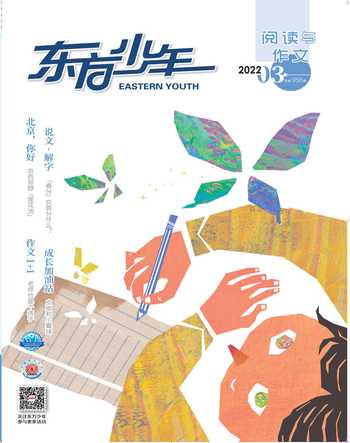童年記憶瑞蚨祥
許福元

許? 福? 元
筆名星白,北京順義人,中國作協會員。主要作品有個人專集《早春》《半夏》《仲秋》《瑞冬》《驚蟄》《印象美國三十天》六部。在《北京文學》《大家》《星火》《飛天》等文學期刊發表小說多篇。短篇小說曾獲“浩然文學獎”一等獎。
我七歲那年秋天,爺爺帶我去了一趟北京城里大柵欄的瑞蚨祥綢緞莊。
“吁!”驢車停在了一座高高的門洞口,兩邊各蹲著一頭大白石獅子。
“來了,您哪!”招呼聲帶著露水,潮乎乎地撲了過來,“您老早,您老早!怕是起冒五更了吧!”一個高個子、頭戴筒形氈帽、身著青布長衫的人邁過門檻,邊下臺階邊笑著拱手相迎。
不等爺爺搭話,他又點手招呼伙計:“柱子,和往年一樣,把小車子趕到老地方,讓大青驢先在井槽子飲飲水,打打滾兒,落落汗兒;再給喂上,加點兒黑豆。”
爺爺忙擺手:“不用,不用。草料都帶著呢。”然后,爺爺把鞭子遞給那個叫柱子的半大小子,口中連說:“勞駕、勞駕,受累、受累。”
可是,柱子一聲未吭,甩一聲響鞭就把車趕走了。
大高個兒在前邊走,爺爺在后面跟,我貼在爺爺的身后。那個人上臺階進了屋,爺爺卻停住了腳,立在了門口。我還要往前邁一步,爺爺往后拽了我一下,示意我像他那樣,直直地戳著。他還小聲跟我說:“那可是二掌柜!”
二掌柜出得門來,兩只手的袖口里都順著一把布條撣子,布條花花綠綠的。這時,柱子也剛好過來,麻利地從二掌柜手里接過一把撣子。于是,二掌柜用撣子抽打爺爺身上的土星兒,柱子用撣子抽打我身上的土屑。先是兩肩后背,接著胳膊前胸、屁股膝蓋、褲腳鞋幫。我總覺得柱子這小子有點兒壞——他讓我抬起兩臂,平端伸直,然后撣子帶著風聲,就像鞭子一樣抽了過來。我的頭躲向左,他的撣子也向左;我的頭躲向右,他的撣子也向右。雖抽不著我的臉,卻抽得我胸脯子生疼,可我不敢也不好意思喊疼。
身上被抽打得麻麻酥酥,清清爽爽,我們就被請進了屋里。一張方桌,兩邊是栗子色的方椅子,椅子上鋪軟墊。二掌柜往爺爺的銅煙鍋里摁上煙末,就和爺爺分坐在了兩邊。柱子端來茶水,白碟子上坐一個茶色小蓋碗。我坐在一條寬春凳上,凳面很光很硬。二掌柜讓柱子給我端來一盤糖耳朵。
我一邊吃甜甜的糖耳朵,一邊聽二掌柜和爺爺說話。
爺爺緊吧嗒了幾口煙,又呷一口茶,眉開眼笑說起了收成:“今年風調雨順,大白瓷的棒子,甩出一尺多長;花朵兒似的黃豆,豆莢一嘟嚕一嘟嚕的;上坡地的白薯,小孩腦袋似的;落花生,一窩猴兒。吃穿量家當,咱莊稼人,完秋賣了糧,心里才有譜兒進城來瑞蚨祥買上一年穿的。”
二掌柜這時從容站起,又招呼柱子過來:“老爺子煙也抽了,水也喝了,快帶他到柜臺上走走轉轉,時興的、實用的、價錢不貴耐用的,都摸摸看看,明碼標價別打眼。六七十里地,一年進一趟城不容易。有錢得花在刀刃兒上,有粉得搽在臉蛋兒上。”
這時,已不時有三五成群的顧客進來,二掌柜又拱手對爺爺說:“先讓柱子伙計帶您過過眼,我去去就來。有什么事兒,讓小學生喊我一聲。”說完,他還用大手摸了一下我的禿腦殼。噢,我就是那小學生啊!
柜臺后架子上那一豎排一豎排的綾羅綢緞,讓人眼花繚亂;柜臺案子上那一匹匹挨肩疊背的布料,使人不知所措。就連一向穩重老練的爺爺竟也像小孩子一樣局促不安起來。
柱子此時神氣起來,連聲問爺爺:“您要這個?不要。您要那個?也不要。那是要那個?還不要。”問了幾回,柱子的話里就帶了點嘲笑的意思:“您這也不要,那也不要,您干嗎來了?要不,您看看海龍水獺大氅領袖,哈喇回絨西服絲呢?”
爺爺的臉,此時紅布一樣。一路趕車沒有出汗,現在汗珠子卻如蟲子一樣,爬上了額頭。
二掌柜畢竟是二掌柜,看到這個情形及時趕來“救駕”。他對柱子說:“你去看看大青驢吃飽了沒。再飲飲水,戴好了糞兜兒。剩下的草料,給裝在麻袋里。把小車兒里邊歸置歸置,一會兒好碼布匹。”而后,他又對我爺爺說:“老爺子,您把心里的譜兒亮給我,我給您參謀參謀。薄的厚的,春秋換季的,您想周全點兒。買布先從上往下買,高堂高壽,做一件換季棉袍,面子用青士布,里子用豆包布,柔軟隨身;女眷時興小碎花,面子寬;斜紋布,出門入戶;平紋布,下地干活兒。本店還新進了一批白布,便宜,當被里兒、褥里兒、套褲里兒、棉褲腰都合適。您拿回去在順義南門外染房店一染,要青灰有青灰,要瓦灰有瓦灰,要藏藍有藏藍。等您洗幾過兒,藏藍變瓦灰,瓦灰變青灰,青灰變月白,像您的孫男弟女,穿著都合適。還有,街坊四鄰、親親故故,托您捎捎帶帶,還不一勺兒燴了?反正一只羊也轟著,兩只羊也趕著。”
二掌柜的一番話,說得爺爺連連點頭。他又將爺爺引到柜臺前,“啪啪啪”一字排開一匹匹布料,“嘣嘣嘣”用雙手左右抻著、上下抖著,讓布面展開,斜繃在他胸前。“老爺子,您光點頭兒不行,您聽聽這是什么聲兒,彈老弦子似的,銅音兒。我再告訴您,您買得多,還照老規矩,老尺加一,還外送一副青腿帶、一條唐布手巾。”
爺爺笑瞇瞇地說:“掌柜的,我就愛聽您說話兒。”說著,他從懷里掏出皺皺巴巴的一大把紙條兒,上面寫著自己家及本家族親屬及街坊四鄰拜托采買的品種、規格、數量。二掌柜將紙條兒攤在柜臺上,一一撫平、辨認清楚;然后端起茶杯,仰脖一飲而盡;又將兩袖高挽過肘,撩起長衫下擺掖于腰間,顯得精神抖擻、干凈利落;最后他高喊一聲:“柱子,放布。”
柱子雙手徐徐放布于前,二掌柜持木尺測量于后。他眼中瞄完紙條,盯著木尺,口中高喊:“青士布,一尺、二尺、三尺……九尺,一丈,老尺加一!”“老尺加一”四個字的聲音拔高拉長,在整個商鋪里回蕩,引得堂內顧客引頸觀看。多加的尺寸,二掌柜定要讓爺爺看一眼。爺爺看過,二掌柜木尺的一端(似乎有一缺口,鑲有刀片)輕輕一硌,接著俯下身去,用剪刀沖開一小口,然后雙手扯開……只聽“哧”的一聲,布在空中一撕到底,豁然斷開。斷口處的布絲如蛛絲般飄浮,他用手當空一抓,好像沒抓到什么,其實那布絲已被他三繞兩繞,纏在了布上。沒多久,斜紋布、平紋布也都照樣子扯好了,二掌柜最后喊了一聲:“上等好漂白布,四匹!”
臨別的時候,二掌柜又拱手送至門外:“您老順便就過來坐坐,落落腳兒。喝點兒水,歇歇腿兒。”
在回來的路上,我靠在晃悠悠的布垛上,挺舒服。大青驢也是奔家心切,打著響鼻兒、撒著歡兒、撂著蹦兒、撅起尾巴往回跑。可即便這樣,回到家的時候,南天上的星星也已經歪了。
一進門,就見一屋的人還在等我們歸來。爺爺把給鄉鄰帶的各種布一份一份連同找回的零錢,悉數交到他們手中。莊稼人不會說“謝”,只是憨憨地笑。
一連多半個月,我家就像辦喜事兒似的——街坊四鄰一撥兒一撥兒有事沒事都想到我家坐坐。因為我和爺爺去了一趟北京城,在眾鄉鄰眼里,就如同捉了逆賊、擒了反叛,掛印封侯了一般。爺爺和我一遍又一遍地回答鄉親們提出的在我看來都十分簡單的問題。我們嘴里永遠得念叨著八仙桌、太師椅、春凳、蓋碗兒、高末兒茶、關東煙、糖耳朵、青腿帶、唐布手巾、二掌柜、老尺加一、東來順、內聯升、同仁堂……爺爺說膩了,我卻一直沒煩,因為有幾個老人總夸我:“七歲看大,八歲看老!這孩子一瞧就有福氣,剛七八歲,就能和二掌柜那么大的人物平起平坐……”
有幾個老莊稼人還神神秘秘地問爺爺:“聽說北京城的錢厚了去了,是嗎?”
爺爺得意地一捋山羊胡:“那是!一進前門,那錢哪,就沒了腳面子;一邁進大柵欄,那錢哪,就到了膝蓋骨,得蹚著往前走!”
“那北京人一個個怎么個打扮呢?”
爺爺又一捋山羊胡,連說帶比畫:“頭戴‘馬聚源’,腳踩‘內聯升’,身穿‘瑞蚨祥’,腰纏‘四大恒’。”
直到冬天曬暖,幾個老人挎著糞箕子,貼墻根兒聊古話兒,爺爺還兩眼半睜半合,嘴里嘟囔著:“瑞蚨祥二掌柜那么大的人物,也把咱莊稼人當人哪!”
爺爺笑瞇瞇的,陶醉在被人尊重的快樂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