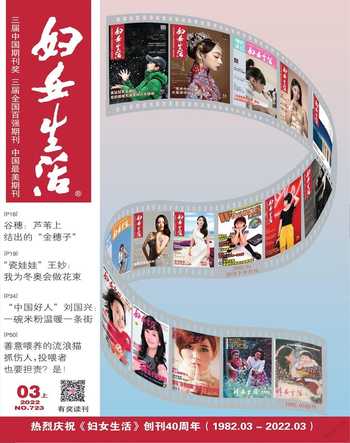“瓷娃娃”王妙:我為冬奧會做花束
李瑞輝


出生14天,她被確診患有成骨不全癥,醫生預言她活不過15歲。如今,她30歲了,家庭美滿,事業有成……
2022年2月6日晚上8點08分,中國短道速滑隊站上最高領獎臺。隊員們揮舞著“永不凋謝的冬奧之花”向世界微笑。
同一時刻,距離北京800公里的河南省周口市鹿邑縣東大王村,“瓷娃娃”王妙守在電視機前,緊盯屏幕,熱淚盈眶。
王妙告訴記者,看著自己編織的花束出現在奧運會的領獎臺上,她仿佛覺得自己和奧運冠軍們一起站在領獎臺上,向世界揮手致意。那一刻,她不再是身高只有1.2米的殘疾人,不再是“瓷娃娃”,不再是人們眼中的弱者……
“給你們說句實話,像她這種情況的病人我見過不少。以她的身體狀況,估計活不過15歲。別太折騰她了,好好照顧,保守治療吧。”
1992年6月的一天,王妙出生在周口市鹿邑縣一個普通農民家中。父母文化程度不高,為孩子取名“妙”字,寄托了對女兒的所有希冀與寵愛。
可很快,他們發現這個孩子好像有點不一樣,經常大哭。夫妻倆帶王妙去當地醫院檢查,被告知孩子患有“成骨不全癥”(患這種病的人常被稱為“瓷娃娃”)。
被確診的時候,王妙才出生14天。夫妻倆從醫生口中得知,這個病要伴隨孩子一生,磕碰甚至打個噴嚏都能使她骨折。
之后,夫妻倆到處尋醫問藥。按摩、扎針、喝煙灰……他們試了各種偏方,就希望能遇到一個管用的。可不管他們怎么努力,王妙的身體情況都沒有好轉,經常骨折。
在一次求醫的過程中,看著疲憊不堪的夫妻倆,醫生說:“給你們說句實話,像她這種情況的病人我見過不少。以她的身體狀況,估計活不過15歲。別太折騰她了,好好照顧,保守治療吧。”
醫生的話打破了夫妻倆的幻想,但他們還是悉心地照顧王妙。
“我雖然不能上學,但每天都在家里學習。我能把課本倒背如流,課后的生字,哪一個在第幾頁我都記得清清楚楚。”
小時候,王妙病情嚴重,動輒骨折,日常生活全靠母親照顧。母親不在的時候,一米寬的小床就是她的世界。大多數時候,王妙就在床上躺著不動,這樣能緩解骨折處的疼痛。但躺得久了,背上又會生褥瘡,王妙只好靠著被子枕頭坐一會兒,可坐得久了腿又會疼起來。
“為了打發躺在床上的時間,四五歲的時候,我就和奶奶一起‘掐辮子(把麥稈編成長辮形),然后讓奶奶拿到集市上去賣。有時候我還會和奶奶比賽,看誰掐得又快又好。剛開始我總是輸,但后來每次都是我贏。”
除了“掐辮子”,5歲的王妙還學會了很多手藝活兒,縫沙包、做布擋子都是她的強項。“我縫的沙包好看又結實,送人很受歡迎。”
在王妙的印象中,從小到大,家人對她寵愛有加,家里有了好吃的好玩的,永遠都先給她,跟她說話也都是夸贊:“你看看妙妙嘴多甜。”“妙妙真是心靈手巧,做的這些東西真好看。”“看我們王妙,長得多好看,這么白凈,眼睛還大。”
雖然被家人的愛包圍著,但看著同齡的孩子去上學,放學了還可以瘋玩,她也渴望小床以外的世界。她開始嘗試下床,但都以失敗告終,只要稍一用力,腿就會骨折。
直到8歲,她才靠雙手的支撐,連托帶拉地“走”出家門。“與其說是走,不如說是拉。我比家里的門檻高不了多少,出去的時候我會用手撐著門檻,把一條腿抬上去,等坐穩了,再把另一條腿抬上去。”跨出家里的那個門檻,需要耗費十幾分鐘甚至更長的時間,但能夠有片刻時間離開那個待了8年的小床,就足以讓王妙感到高興了。
弟弟已經開始上學,王妙每天最期待的事情就是等弟弟放學回來,給她講學校的事情,教她學拼音和漢字。“我雖然不能上學,但每天都在家里學習。我能把課本倒背如流,課后的生字,哪一個在第幾頁我都記得清清楚楚。”
不能去學校,王妙更珍惜學習的機會,除了跟著弟弟學習學校的課程外,她還愛上了讀書:“我小時候最喜歡讀《七色花》,常想象自己有一朵七色花,把我的身體變得和正常人一樣,然后走出去,實現自己好多好多的愿望。”
后來隨著年齡漸長,王妙又讀了史鐵生的《我與地壇》《合歡樹》和路遙的《平凡的世界》等書。無論是作者還是書里的主人公,都給了她莫大的鼓舞。她越來越渴望自己有一天能好起來,去成就一番事業。
“這么多年,和很多優秀的病友在一起,我的思路完全打開了。腿不好怕什么?拄著雙拐又怎樣?我還有頭腦和雙手啊,一樣可以活得熱烈、活得精彩。”
姐姐上大學以后,開始接觸電腦和網絡,她告訴王妙,像她這樣得這個病的人并不少,有些是可以治療的。聽姐姐這樣說,王妙很開心,她開始幻想自己被治愈以后的生活。
聽說山東有個醫生很善于治療這種病,20歲的姐姐帶著十幾歲的王妙幾經周折跑了過去。“那是我第一次出遠門,在那之前,我幾乎連村子都沒出去過。姐姐和我都是第一次坐火車,路上的艱難可想而知。”
姐妹倆坐大巴到火車站,由于是第一次坐火車,她們并不知道要提前檢票進站,眼看火車要開了,姐姐抱起王妙,背著、提著大包小包的行李朝火車車廂飛奔過去。“因為跑得太快,姐姐一個踉蹌差點把我摔到地上。旁邊有個好心的年輕人看到了,幫我們拿著行李,姐姐抱著我,一路飛奔才趕上火車。”
滿懷希望的姐妹倆,到了山東卻被潑了一盆冷水。醫生看完王妙的病情之后,說像她這樣的做不了手術。這意味著她不能站起來、不能走路、不能像正常人一樣生活了。
那一刻,王妙的所有希望都破滅了,一向樂觀的她掩面痛哭。“我覺得一切都完了,我的所有夢想都實現不了了。那么多像我一樣的病友都可以做手術,為什么我卻不能做?老天爺對我太不公平了!”
懷著失望的心情,姐妹倆回了家。王妙說自己那個時候失去了方向,很絕望。但家人都不放棄,姐姐勤工儉學,用掙來的錢給她買了一個二手手機。“我記得很清楚,那個手機50塊錢。姐姐上大學以后就沒問家里要過一分錢,那個錢她攢了好久。”
這個手機,讓王妙建立起了跟外界的聯系。她加入“瓷娃娃罕見病關愛中心”,結識了更多的專家,終于有一個專家說可以為她做手術。
2015年,王妙先后去天津做了兩次手術,也在那里認識了很多病友和志愿者。因為治療時間比較長,空閑時,她就自學編中國結和手鏈,然后把這些東西送給其他病友。
“有個病友收到我的中國結,說要送一朵針織玫瑰花給我。我看她那個玫瑰花織得很好看,就跟她學著織。我教她編中國結,她教我織玫瑰花。”隨著手藝的精進,王妙開始外出擺攤,賣自己做的手工藝品。
“那時候,做出來一個東西需要大半天時間,做一星期拿出去賣,有收獲,但效果不怎么理想,因為別人認為太貴了,覺得我是仗著自己有殘疾變相乞討。”
這激起了王妙的好勝心,她開始去圖書館看各種編織的書,還報了網上的編織課,經常從早上學到深夜。她說她那時候心里只有一個想法,就是要讓別人覺得買她的東西值。慢慢地,她會織的東西越來越多,作品也越來越精巧。終于,王妙接了一個“私人定制”的活兒,一個小東西賺了100元。對方特別滿意,一個勁兒地夸王妙手巧。
經過兩次手術治療,王妙的身體有了很大好轉,已經能拄著雙拐走路,骨折的頻率也越來越低。
出院后,王妙回老家鹿邑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接一些編織品的訂單,有了比較穩定的收入。
隨后,王妙在網絡平臺上開設了自己的編織課程,教留守婦女、殘疾人學習。對一些生活困難的殘疾人,她還會轉給他們一些訂單,幫他們創收。
事業之外,王妙還遇到了愛情,如今,她已經有了自己的孩子。采訪過程中,她老公和婆婆對她贊不絕口。
說起自己,王妙很樂觀:“醫生說我活不過15歲,如今我已經30歲了。我15歲生日那天,我們全家都很開心。從那天之后,每一天我都覺得是從死神手里賺來的。這么多年,和很多優秀的病友在一起,我的思路完全打開了。腿不好怕什么?拄著雙拐又怎樣?我還有頭腦和雙手啊,一樣可以活得熱烈、活得精彩。”
王妙的作品做工精細,構思巧妙,多次獲得國內大型手工展獎項。2018年,她還成功申請了縣里的非遺項目,成了遠近聞名的“鹿邑巧姑娘”。
“天哪!你怎么不早告訴我。我竟然能給奧運會做訂單,真不敢相信啊!”
2021年10月中旬,天津市潮汐公益服務中心與王妙聯系,請她制作一批標準要求非常高的花束。王妙將樣品寄過去通過檢驗后,對方給了她5000朵繡球花和1300片月桂葉子的訂單。
“這一批花和之前我們做的編織花很不一樣,它的材料是絨線,而且特別細,勾起來很困難。針法也特別復雜,一個小小的花瓣都要用到長針、短針、狗牙針、辮子針等7種針法。組裝的時候要求也很嚴格,比如上邊的兩粒小米珠,串的位置要有固定角度,不能摞起來,做起來實在不容易。”
王妙告訴記者,因為做工困難,耗時又費力,失敗率還特別高,稍微弄錯一點就需要拆了重新做,所以很多織女都不愿意接這個單子。“我剛開始找了80個人,最后愿意做的只有不到20個。”
為了能及時完成訂單,王妙跑到愿意做的女工家教學,經常跑來跑去,飯都顧不上吃。外出參加活動,她也要把材料帶在身上,一有時間就見縫插針地織一點。
一支繡球花有20朵小花,一個熟手全部做出來需要100分鐘左右。枝條纏線、安裝花心、組裝花束又要近100分鐘。這樣算下來,一支繡球花的制作時間就需要200分鐘。“這還是我這樣的熟手才能做到的,有些女工做得慢,一枝花需要1天甚至更長的時間。還有些女工年紀大了,根本織不了很精細的小花瓣,我就讓她們組裝,讓其他人織。”
“月桂的葉子難度也不小,它的絨線顏色太深,不好穿針眼兒,只有在光線特別好的白天才能做。”王妙說,訂單的要求很苛刻,繡球花瓣的誤差不能超過2毫米,月桂葉子的誤差不能超過5毫米,她和其他十幾個織女加班加點,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終于在兩個多月后完成了這筆訂單。
“接到這筆訂單的時候,我并不知道它的用途,就覺得客戶信任我,我一定要認真把它做好。”訂單完成后,對方向王妙透露,這批訂單是給北京冬奧會用的。那一刻,王妙興奮地喊了出來:“天哪!你怎么不早告訴我。我竟然能給奧運會做訂單,真不敢相信啊!”
按照保密協議,王妙和其他織女嚴格遵守保密規定,不發照片、錄視頻到朋友圈,不向外界透露任何信息。北京冬奧會開幕后,王妙每天都守在電視機前。看著奧運冠軍站在領獎臺上,揮舞著“永不凋謝的奧運之花”,她覺得自己和那些花一起,也站在了冬奧會的領獎臺上,和冠軍們一樣朝著世界揮手微笑。
【編輯:潘金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