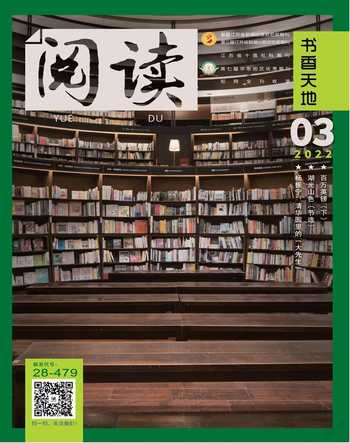人類“躺平”小史
貝恩德·布倫納


“躺著”,就是放棄與地球引力的對抗,就是身體在水平方向上散步。米開朗基羅,躺著悟出來西斯廷教堂天頂的驚人畫作;普魯斯特,躺在自己的鋼絲床上完成了浩瀚巨著《追憶似水年華》……有時, “躺平”并非消極懈怠的代名詞,只不過是換種姿勢更好地生活。
躺下相當于水平方向上的散步
你要是正躺著,就應該理直氣壯。我們每個人都會做這件事,我們經常躺著,并總是躺得很開心。躺下時我們很放松,這是身體受阻最小、最不費勁的姿勢。
我們躺著做這些事:睡覺、做夢、思考、沉浸于憂傷的情緒、打盹兒、忍受病痛。只有一件事我們幾乎不會躺著做:運動。當我們水平伸展躺下時,我們與那種被莫名其妙地稱為“靜止”的狀態非常接近。
在這個充斥著可快速量化指標的社會,人們企圖用快速的行動顯示自己的決斷力,有時候還會在辦公桌和電腦前久坐以證明自己的勤奮,因此躺下可真不是一件值得贊賞的事情。更糟的是,躺下會給人以懶散的印象,是對劇烈變化的世界感到無能為力的標志。躺臥的人不能進步,也就是說,他很差勁,不能好好利用自己那點寶貴的時間。
盡管如此,躺臥對我們來說卻有如在濃霧中散步一般的效果,經過這番“散步”,我們的思維總是比之前更清晰。有意識地躺臥則是一種精打細算的實踐,能幫我們擺脫無所不在的時間壓力和效率考量,它不花一文,卻價值非凡。
躺下相當于水平方向上的散步,就像多愁善感的浪子那夢游般的漫步一樣,雖在行走,眼下卻沒有特定的目標。躺臥的人從那些市鎮與風光中穿行而過時更需要想象力,因為見不到能使他發散思維的真實面孔和地標。
當我們仰頭躺下、睜著眼睛看向天花板或外面的天空時,我們的身體對周圍的事物失去了感應,我們的思緒肆意飛揚,整個心境都隨著姿勢的改變而改變。我們再也不能以剛才直立時采用的方式來應對世界。剛才還讓人撓頭的問題,從水平的角度去看,立刻顯現出不同的面貌。各種聲音——甚至包括電話鈴,聽起來都不再那么讓人緊張了。處于水平狀態時,信念比在任何其他狀態下都更容易動搖。當人躺倒時,可能會產生一種被淹沒的感覺,因而肩上的重擔就會掉落下來。
躺臥的意義,關乎生理、心理、藝術等多個方面,同時也與當代經濟和我們的生活節奏息息相關。美國心理學家羅伯特·萊文曾敏銳地將這種生活節奏描述為“一段華彩的韻律,一段不斷變化的節拍和序列,一段由音符和休止符、循環和新的沖動構成的混亂隊列”。就通常的看法而言,躺臥是否合適,以及何時躺臥才合適,與我們的時間觀念息息相關——我們據此判斷該如何行動,它像無聲的語言一樣決定我們的日程。
在這種催人不斷行動、使人內心不得安寧并侵占一切生活領域的時代與文化之中,我們沒法不擰緊時間的螺絲,跟緊別人的節拍。在時間走得似乎比我們慢的地方,日程由偶然發生的事件決定,人們很少事先規劃。我們能從這樣的地方知道,按照別的時間規則來生活意味著什么。一段乍看起來無所事事的時間,在另一個社會中并不會被認為是浪費——或許他們根本就沒有“浪費時間”這種概念——反而被當成生活中愜意而重要的部分。正因如此,我們更有必要在躺平的世界中一探究竟。
向重力屈服的誘惑往往更強烈
我們的身體是為很多其他需求而生的,而不只是為了我們今天要求它做的那些有限的動作。與幾代以前的祖先相比,我們坐得更久,動得更少。就我們的基因編排和身體構造而言,我們生來就處于不斷變化的運動形式之中:行走、躺臥、坐下、站立……在水平方向稍作停留只是其中的一種。當然,向重力屈服的誘惑往往更加強烈,它把我們引向地面。我們會發現自己一直處在與這種力量較勁的狀態之中。即便我們完全意識不到這種行為——我們生而如此,會下意識地這樣做——我們也在消耗大量的體能以對抗重力。
躺臥與行走是相輔相成的,它們在某些方面互為因果:只有行走、漫步、快走、奔跑或劃槳到筋疲力盡的人,才能體會到躺臥所帶來的無窮的放松之感,否則便得不到這種體驗。對有些人來說,躺臥還有另一重意義:當身體過于疲乏時,躺臥就成了一種“避難”。它使身體短暫休眠,重歸于零。
我們以地球表面為參考系,從兩個方向衡量自己:垂直和水平。行走時,我們與大地的聯系只在腳掌,而躺臥時,這種聯系則擴張到整個身體。地平線,這條把天空與大地分隔開來的線,在遠方清晰可見,它召喚我們超越已知的一切,將目光投向更遠處,同時又描畫了邊界。它是一種暫時的構想,當人們奮力追逐它時,它又總是退到遠方。它是一個無法抵達的終點。
躺臥在許多地方都能實踐,不必以臥榻或床的存在為先決條件。不過,穩固的底面還是必要的。如果我們躺得不舒服,還得操心安全問題——如果有對跌落的擔憂,就沒法真正放松。為躺臥而做的準備工作會影響我們躺下的體驗,決定我們在水平方向上的存在方式。我們采用的躺臥方式要適應所處的位置。躺得越舒服,身體的負重就越多地由底面承擔,我們也就能休息得越好。
想給“躺”下定義一點也不容易。一個建議:躺就是指身體的絕大部分處于或接近水平狀態,且負擔轉移到底面。我們可以仰臥、側臥、俯臥;可以躺在另一個人旁邊,也可以躺在另一個人的上方或下方,至少躺一小會兒沒問題;還可以在身體躺平時抬起腿。你可以在勒·柯布西耶設計的躺椅上體會到類似的感覺,使用這把躺椅時,上身與地面大約呈四十五度角。躺臥與坐下有所不同,坐在椅子上的人仍須對身體保持一定的控制,躺臥則完全不費勁。躺臥或許是最古老的姿勢,它讓我們想起更早以前的存在方式,而站起來總是需要一些自制力,尤其在時間并不緊迫的時候。不過躺臥也是一件有風險的事,因為很容易沉睡過去,進入無意識狀態。
躺臥時什么都有可能發生,它涵括了我們所有的狀態:從徹頭徹尾的被動到熱情洋溢的主動。沒錯,人的生命自躺臥而始,至躺臥而終——作家所要竭力描述的事情,多半也是躺著發生的。
躺著成了浪費時間的標志
躺著的人常常被視為消極、遲鈍、遜于他人。顯然,這與躺下的真正動機往往毫不相干。躺下也許是為了休息、放松,也許是為了凝神思索下一步的妙招。對伺機而動的人來說,躺臥則是英明決策的一部分。當“快閃”隊列里的許多人同時倒地、阻擋人流與車流并表達抗議的時候,躺臥就成了一種反抗。躺臥也是懶人最喜歡的姿勢。德國作家漢斯·費舍爾曾經寫道:
徹底的懶惰之人什么也不追求,不求快樂,不求更舒適,連最低限度的自我滿足都不要。只要不撞到墻,他就任由身體沉下去,在力學定律的作用下,獲得趨近水平的位置。他最愛的地方是沙發,因為那里著實舒服。僅存的那點意識警告他小心又平又硬的地板,畢竟摔下去是很疼的,但他又不打算到床上去,因為上床意味著要脫衣服,簡直太麻煩了。不過他也并不想在沙發上睡覺或舒展身軀,不,他只想為身體的重量找個支撐,否則這重量像是要把他拉入地心。
通常來說,疲倦是躺下唯一可被接受的理由。為什么躺下總是被看成不太好的事情?我們聽到太多警告:要時刻處于行動之中,其他任何做法都是缺乏自律、力量和雄心的表現。在當下,積極進取、時間優化受到極致的推崇,深夜還在辦公室加班是一種榮耀,而躺下則成了浪費時間的標志。在我們的文化里,躺著只是一個用來恢復精力的、越短越好的片刻。
在床上也能夠實現一切
為了獲得靈感,讓·雅克·盧梭需要進行長時間的散步。湖光山色就是他的工作室。哪怕只是看到一張書桌,他都會感到不快,更別提“躺著工作”的設想了。他與那些躺著的藝術家截然相反。躺著工作的人往往不愿承認這一點,因為他們深知,這會給他們招來懶惰的名聲。躺臥通常與疲勞、倦怠、缺乏動力、遲疑、懶惰以及消極、松懈聯系在一起,還會讓人想起《浮士德》里的“懶床”。
暫且拋開偶爾午休這種可能的情況不談,我們應該只在夜里躺下嗎?也不盡然,因為對有些人來說,躺下顯然能為提升創造力和高度集中的注意力提供最佳的先決條件。躺臥如何對專注力產生影響?會不會存在某種有待實驗證實的原理,能證明躺臥在提升創造力與注意力方面不亞于坐著?了解這些事兒很有意思。
或許創造力就是要完全從日常事務中抽離出來才能獲得?藝術家是否必須經歷消極的階段,才能真正做出具有創造性的東西?許多人都對此表示認同。馬塞爾·普魯斯特在自己的書信中提到,他在那張傳說中的鋼絲床上躺著寫作,尤其是在生命的最后幾年,他因病臥床,為了完成《追憶似水年華》,他用軟木蓋住臥室的墻面,與世隔絕。在床上可以實現一切,從情色的產生到毀滅性的死亡。
在床上工作的思想巨擘不只馬塞爾·普魯斯特,馬克·吐溫和因描寫英國怪人而聞名的詩人伊迪絲·西特韋爾也屬此列。水平方向的躺臥似乎能使思維異常凝練。據傳,威廉·華茲華斯最愛在一片黑暗中躺在床上寫詩,一旦紙張不見,就又從頭寫起,因為在黑暗中摸索尋找實在太費勁了。
瓦爾特·本雅明回憶說,法國象征主義詩人圣波爾·魯為了不被打擾,會在臥室的門上寫上“詩人在工作”。海因里希·海涅在巴黎度過了生命的最后幾年,受疾病所迫,只能在床上寫作。在這個被他稱作“床墓”的地方,他把自己最后的文學作品帶給了世界。
逃到床上工作,使《純真年代》的作者伊迪絲·華頓得以躲避女性要衣著整肅的鐵律。在床上,她不必再穿束身胸衣,這對她放飛思想也大有裨益。就連八十歲壽辰,她也在床上慶賀——插滿蠟燭的蛋糕本為助興,卻引起了火災……
有的人躺著的時候會望向遠方,聽收音機、聽音樂,另一些人則選擇閱讀。躺臥時人們愛讀哪些書?在水平狀態下閱讀什么作品,才能給人帶來特殊的、在其他狀態下很難達成的閱讀體驗?我們在躺臥時會不會對書籍產生不同的理解?會不會對特定的情緒更加敏感?
如果加拿大小說家阿爾維托·曼古埃爾的論點是正確的,那么,當人們在書中發現一個與自己此刻作為讀者所在的現實世界相類似的世界時,他們就需要調整一種“冗余感”。這時候,他們最可能做的,就是在躺臥于床榻的孤寂中閱讀那些情節緊湊、內容豐富的書籍。
有趣的是,對曼古埃爾來說,閱讀偵探故事和恐怖小說能使他安然入睡;而對另外的許多人來說,這種讀物肯定會讓他們睡意全無。當然,適合在躺椅上讀的書通常是那些輕松易讀的,人們擔心太過擾人心神的情節會攪亂周末或假期。真是奇特的邏輯。
陷落到沙發或床上,懶得管別人怎么想
躺著的人情緒各異,其屬性也就不同,它可以是消極的,也可以是積極的。我們的工作方式對我們如何度過剩下的時間有種反作用力:那些大多數時間都坐著——比如長時間坐在電腦屏幕前的人,會在業余時間用運動求取平衡,也只有在運動之后才能享受到躺下帶來的放松效果。相反,那些每天從事體力勞動、甚至為此筋疲力盡的人,在業余時間則更愿意閑著什么也不做。躺下對他們而言有著完全不同的性質。
今日職場的劇變,對工作與休閑的關系產生了什么影響?對“什么也不做”的時光和躺著的時光,以及對我們的睡眠時間又有怎樣的影響?如果工作更具彈性,我們會有更多“什么也不做”的機會、更多休閑愉悅的時光(也就是積極的、合人心意的懶惰)以及一種不僅是為了恢復體力的躺法嗎?當前進失去了動力或方向時,躺臥可以教人考慮得更周全,使人以舒適的方式擺脫“沒有進步便是退步”這種非黑即白的霸道邏輯。
我們是否忘掉了該怎樣躺著,就像我們因為總是去吃快餐而忘掉了怎樣烹飪一樣?也許吧。就像吃飯不僅是繼續工作和身體運作的前提一樣,躺著也不僅僅是為坐在書桌前做準備。躺著確實不常帶來立竿見影的效果或經濟收益,但也遠不止讓我們養精蓄銳那么簡單,就像業余活動存在的意義不僅是為了讓我們有事可忙一樣。
有跡象表明,我們當下的社會對躺臥所持的態度正處于變革之中。近年來在法國出現了“癱倒的一代”,指的是那些一屁股坐下去、堅決不肯坐直的年輕一代。他們不愿意好好坐著,而是陷落到沙發或床上,再將自己調整到舒適的姿勢,根本懶得管別人會怎么想。這真讓人羨慕。人們可以從中窺見對靜坐與直立的異議,以及對或許仍執迷于立規矩的父母的無聲反抗。
對這種發展趨勢,專科醫生倒是泰然視之,事實上他們認為通常的坐姿(坐在椅子上)與人體的生理要求并不相符。相反,成一百二十七度角的半躺半坐的姿勢顯然更加合適,它能夠消除人們坐直時脊椎承受的壓力。
人們還喜歡把這種態度的轉變納入“慢生活”的領域之中。就像“慢食倡議”一樣,這種藝術也發源于意大利。與之相關的是一股減速與暫停的風潮,這股風潮不再追求用最短的時間和最小的投入達到特定的目標,而著重于充分體驗過程,正如其宣言所示:道路即目標。
(摘編自南海出版公司《躺平》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