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平凹:若可能,快將那些“豪言壯語”從作品中抹去
一根羽毛,一根羽毛,或許太平常了,但組合起來,是孔雀的艷麗彩屏;一縷絲線,一縷絲線,或許太普通了,但經緯起來,是一匹光華的綢緞;一部好作品,使多少人笑之忘我,悲之落淚,究其竟,不過是一堆互不相連的方塊字呢。然而,這么些方塊字,湊起來,有的是至情至美,有的卻味同嚼蠟:這是什么樣的魔術啊?
妙齡人大概都有這么個感覺吧:外表美,心靈不美,當然不是好對象;心靈美,外表不美,卻不能不是一種遺憾了。語言是作品的眉眼兒,縱然有著純潔善良的靈魂,那何不就去修飾打扮,使天下的讀者“一見鐘情”呢?
鳥兒都喜歡自己的羽毛,作家更想把自己的語言寫好。然而,孩子們的憨是一種可愛,大人們的憨,卻是一種滯呆;少女們插花會添幾分嫵媚,老嫗們插花則是十分的妖怪了。
這是為什么呢?
騙子靠裝腔作勢混世,花里胡哨是浪子的形象。文學是真情實感的藝術,這里沒有做作,沒有扭捏:是酒,就表現它的醇香;是茶,就表現它的清淡;即便是水吧,也只能去表現它的無色無味。如此而已!
可惜,我們的學生,或者說,我們在學生的時候,那是多么醉心于成語啊!華詞艷辭以為才氣,情泄其盡為之得意。寫起春天,總是“風和日暖”“春光明媚”,殊不知何和何暖的風日,何明何媚的春光?寫起秋天,總是“天高云淡”“氣象萬千”,殊不知又怎么個高淡的天云,怎么個萬千的氣象?單純、樸素,這實在是一張藝術與概念、激情和口號之間的薄紙,而令我們幾年、十幾年地徘徘徊徊,欲進不能。
如果可能的話,快將那些“豪言壯語”從作品中抹去,亂用高尚、美麗的成語,會使這些詞匯深刻、真切的含意貶值。
……一道溪水,流,是它的出路和前途。它必然有過飛珠濺沫的歷程。而總是飛珠濺沫,它便永遠是小溪,而不是大河啊!
那么,就將土語統統用上吧,那油腔滑調,那歇后語,那順口溜……
錯了!
難道坩子土里有鋁,能說鋁就是坩子土嗎?金在沙中,浪淘盡,方顯金的本色;點石如果真能成金,那也僅僅是鉆進了蛤蚌體內,久年摩擦、侵蝕而成的一顆珍珠。如果以為是現實里發生過的,就從此有了生活氣息,以為是有人曾說過的,就從此有了地方色彩,那流氓潑婦就該是語言大師了?!藝術,首先是美好;美好是“冶煉”出來的。
什么是好語言呢?
理論家們可能有一套一套的學說,老師們可能有一條一條的規范;我,卻只有一點兒偏見,又那么地含糊,似乎也只是有意會而苦不能言說呢。
之一:充分地表現情緒。
“窗外有兩棵樹,一棵是棗樹,另一棵還是棗樹。”魯迅表現的是蒼涼、寂寞的情緒。“我送你一個名字,我從此叫你‘女兒綠’,好么?”朱自清表現的是欣喜、激贊的情緒。陶潛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是一種遁世的閑適。李白的“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是一種懷親的哀愁。這些字眼是多么平淡無奇喲。但是,發纖秾于簡古,寄至味于淡泊;不寫的地方,正是作者要寫出的地方。
月有情而憐愛,竹蓄氣而清爽。這一道理,該是我們從寫第一篇作品到最后一篇作品,都不要忘記的。
之二:和諧地搭配虛詞。
一首歌曲,是那么優美,慢慢聽,慢慢聽,原來有了節拍的2/4,3/4,原來有了節奏的長與短,力度的強與弱,速度的快與慢,結構的整與散,色彩的濃與淡,織體的簡與繁,唱法的放與收……噢,奧妙原來如此!而文學呢?刻畫的形象若要細致逼真,精妙入微,就應在其意境中貫穿充盈脈脈的隱隱的情思,奧妙也該是如此了。為著情緒,選擇自己的旋律,旋律的形成,而達到表現情緒的目的,正是朱自清散文情長意美,正是孫犁小說神清韻遠的緣由。以此推論下去,我們終于明白了老舍寫文章為什么要對旁人反復吟詠,柳青的文章為什么有些句式顛三倒四。
每一個藝術大師,無不是在作品里極力強調自己的感覺,而這一切又是那么追求著氣韻、意境、含蓄和心靈內在的諧和呢。
之三:多用新鮮、準確的動詞。
人們樂道王安石的“綠”字,李清照的“瘦”字,李煜的“愁”字,杜甫的“過”字……所謂錘句煉字,竟然都是在動詞上了。生動,生動,活的才能動,動了方能活呢。杜甫的“牽衣頓足攔道哭”,七個字里四個動詞,形象能不凸現嗎?試想,如果要描寫兩山之間有一道細水,“流”亦可,“漫”亦可,“竄”亦可,但若用個“夾”字,兩山便有了“窄”的形象,水便有了“細”的注腳。
當然了,嚼別人嚼過的饃沒有味道,隨心所欲更是荒唐。你必須是你自己的,你說出的必須是別人都意會的又都未道出的。于是乎,你征服了讀者,迫使著他們感而就染,將各自的經歷體會的色彩涂給了你的文章。你,也便成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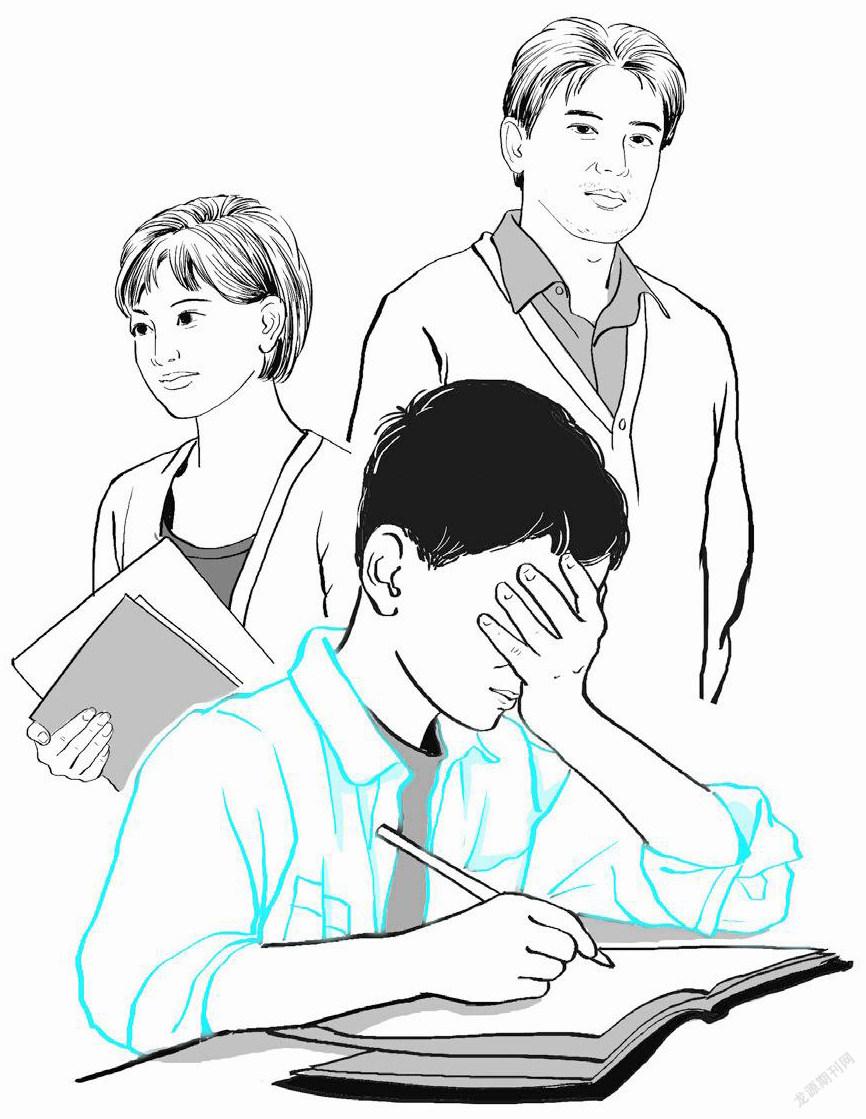
語言探索是迷人的,探索語言是受罪的;只要在生活里挖掘,向大師們借鑒,藝術綠樹長青,語言永遠不死。
(嘉林秀摘自《賈平凹文集》陜西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