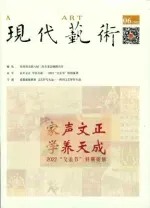寫意音畫的和合相生
配樂是電影重要的組成部分,細膩而精巧的配樂能使電影“先聲奪人”。一般來說,電影配樂多被用以幫助電影渲染情緒、營造環境氛圍、襯托人物心理或形象、過渡或推動故事情節發展、調整敘事節奏、引發聯想和想象、升華主題等。而電影配樂的這些功能在《九零后》中幾乎均得到充分的實現。
紀錄電影《九零后》以西南聯大為題材,旨在對這所傳奇大學獨特而永恒的魅力進行集中展現、對其富有震撼力量的精神特質加以深入解讀和傳承弘揚。法國馬克思主義批評家皮埃爾·馬舍雷曾主張在進行文藝批評時,不應采用經驗主義的批評方式,也不應采用形式主義/結構主義的批評方式,而應采用科學的文藝批評方式。在他看來,文藝作品“怎么說”比“說什么”更為重要,批評者要更多關注文藝作品是如何產生的,要更多分析其故事的講述方式和敘述策略,因為在這之中往往隱藏著某些有待發現的真理性內容。
結合馬舍雷在方法論層面所給予的啟發,對《九零后》的敘述視角、素材選擇、結構組織及視聽呈現等方面作綜合分析即會發現,本片遵循電影藝術規律、巧妙運用視聽修辭講好了“聯大”故事、中國故事;同時在思想層面上,又以高度的藝術使命感和召喚意識,對青春精神、理想主義、家國情懷等共通價值進行深情召喚,從而使影片達成了可聽、好看、“耐嚼”的審美效果,而這也正是其能取得良好反響和藝術成功的重要原因。就目前已有評論而言,評論者多從影片視覺呈現層面的“好看”和思想價值層面的“耐嚼”對本片進行評論,卻鮮少對影片視聽修辭層面的配樂作深入分析。
配樂是電影重要的組成部分,細膩而精巧的配樂能使電影“先聲奪人”。該片制作團隊對音樂的創造性使用,有效幫助了電影內容的組織與結構,擴展了電影敘事的空間和容量,增強了電影的藝術感染力,加深了電影思想表達的深度。應該說,這部電影的音樂是會講故事的,這是一部“可聽”的電影。
首先一個顯著的特征是,本片創作者非常注重對同一段音樂、同一首歌曲的穿插和反復使用,以此形成結構上的呼應和審美上的一唱三嘆的復沓效果,并且從內容上強化了思想主題的表達,使音樂真正成為“有意味的形式”。典型者即是抗戰歌曲《松花江上》和英文老歌《當我們年輕時》(《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在影片中被多次穿插運用。
《松花江上》在影片中的三次出現,形式都隨著情境的需要做了恰切的變化,同中有變,錯落有致,在內容串聯、情緒烘托和思想表達等方面都起到了奇效。其次,創作者善于借助音樂完成敘事段落之間的巧妙過渡。全片以西南聯大作為故事講述的聚合點,每個人物的敘述也都基本按照如何進入“聯大”學習、在“聯大”的生活與學習記憶、畢業離開“聯大”后的作為這樣三個階段展開;而就整體而言,影片又可按照從“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爆發到西南聯大成立,西南聯大開始辦學招生到解散及其解散之后這樣三個階段,分為三個篇章。時間線和節點都很清晰,每個篇章之間,則選擇了恰切的音樂起到自然過渡的作用。譬如臨近篇末,影片由許淵沖先生埋頭“貼屏”堅持翻譯的畫面,過渡到楊苡先生聽歌的畫面,導演意圖很明顯,既以楊先生開篇,便再以她作總結,形成一種首尾呼應的、渾然一體的結構。這段過渡設計得非常精彩。當鏡頭從許老的背影拂過,他話音剛落,《你是我的陽光》 (《You Are My Sunshine》)的配樂和歌聲便響起來。這是一首創作于20世紀40年代的英文歌曲,在當時特別流行,可以說是那個時代青年的青春記憶。隨著音樂聲,楊先生家的院墻、院門、小院、門上的風鈴,這些影片開篇出現的畫面,又一一出現,然后便自然引入楊先生正用收錄機聽歌的場景。此時方知,歌聲原來是從楊先生的收錄機中傳出來的。當楊先生按下按鍵,《你是我的陽光》這首歌曲停止,《當我們年輕時》(《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唱響,這一停一起既起到節奏調整的作用,又將影片內容講述轉至尾聲。兩首歌曲不僅起到結構形式上的過渡作用,而且其旋律、歌詞又符合人物心境、可起到替人物言明心聲的作用;加之歌曲風格復古懷舊,歌詞直抵人心,營造出使人追懷往昔美好的意境,讓觀者不由帶入自身情感體驗,與之共鳴。如此,創作者、人物、觀者便實現共情,這足見出導演之高妙匠心。
除講究使用音樂的時機與情境,講求音樂呈現的形式變化之外,該片創作者還非常注重音樂的地域性和文化意蘊。用導演自己的話說就是,“選擇什么樣的音樂,一定要與這個時代的背景或者地域的特點有非常緊密的聯系”。在巫寧坤先生回憶自己家鄉揚州的段落里,先是聽得雨聲淅淅瀝瀝,銅鈴悠悠然然;其后,背景音樂便漸漸響起,是范宗沛所作的《水色》,在悠遠而靈動的琵琶聲中,一段蘇州評彈翩然而起:“伶俐聰明寇宮人,她奉主命且向御園行……”江南女聲,吳儂軟語,清麗高逸,若隱若現,更添了幾分飄渺。又間以潺潺水聲,簌簌風聲,好鳥相鳴,嚶嚶成韻。轉軸撥弦,輕攏慢捻,三兩聲中,古老揚州悠久的歷史、厚重的底蘊、才氣淋漓的人文風貌、柔婉優雅的江南意韻,還有那種可洗盡鉛華的安寧、平和與美好,款款顯影。由這些種種富有江南特色的音樂元素所氤氳的美好,與巫寧坤先生講述的被迫離家的現實,與他講述時的悲愴情緒,形成強烈的錯位沖突,便愈顯家鄉之美、去國懷鄉之痛,也即更顯侵略者之可憎。尤其當巫老哽咽難言之時,背景音樂里隱隱傳來幾聲女子清唱的評彈,低回,渺遠,讓老人的無言,勝過萬語千言。地域性特征鮮明的音樂往往本身便具有厚重的歷史文化底蘊,它們是群落特有歷史、文化、心理和情感的凝結與表達載體,因而具有不可取代的情緒激發和情感喚醒功能。《九零后》的音樂運用充分發揮了地域性音樂的功能,有效擴展了鏡頭語言的容量,增強了情感表現的立體感。
作家格非在其題為《重返時間的河流》的演講中說,電影膠片上沒有時間,占據其一個個空格的都是空間性的照片,電影的原理即是,那些圖和畫面通過攝影放映機的運動組接在一起,造成“一種時間在流動的假象”。圖和畫面畢竟是二維或三維的短暫定格瞬間,必然造成信息和時間性意味的損耗與散失,而音樂則能以其時間性的特質對圖畫進行一定程度的彌補與挽救。從這個角度看,寫意音畫的契合配搭與和合相生才是《九零后》配樂成功的關鍵所在。
影片在講述聯大學子青春愛情的段落里,插入了一段頗具現代感的校園民謠《未央歌》,“九零后”們與畫面中的當代青年學子構成一種時空對話:雖星移物換,但那對于美好愛情的熾熱憧憬與純真幻想,那獨屬于青春時代的怦然心動,卻穿越時空,心靈相通。可以說,音樂銘記了“九零后”一代人共同的往日時光,亦喚醒了如今這一時代人們的共同的往日時光,更昭示了所有時代奮進而美好的人們的共同的往日時光。
“當我們還年輕/唱起了春之歌/那音樂是多么動人……”
音樂停止,電影落幕,而“九零后”們的青春懷想及其奮斗人生所引發的思索則蔓延開來。
鐘良鳴?四川師范大學文學院在讀博士生,“四川藝術基金獻禮建黨百年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青年評論人才培養”項目學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