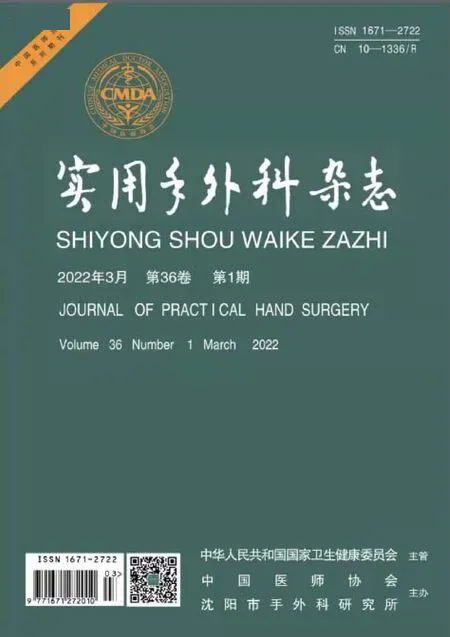改良脛骨橫向骨搬移術治療糖尿病足潰瘍及脈管炎潰瘍
劉應良
(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醫院 骨二科,云南 楚雄 675000)
糖尿病足潰瘍是糖尿病常見的嚴重并發癥,也是糖尿病的主要并發癥之一[1],是臨床上較為棘手的難題,通常難以治愈,呈高發病率、高截肢率,治療費用高昂,病死率比惡性腫瘤還高11%[2]。天津地區調查發現糖尿病足患者5年病死率為32.7%[3]。截肢是最常見的治療方法,Wagner 3級或以上的病例,截肢率高達90%,很多人認為截肢是最好的選擇,但截肢后的5年病死率仍然高達25%~50%[4-5]。通過常規顯微外科手術行皮瓣移植重建糖尿病足潰瘍創面通常是不成功的,往往出現皮瓣壞死等并發癥[6]。脈管炎導致的足潰瘍亦讓臨床醫生望而卻步。近年來,我國學者采用脛骨橫向骨搬移技術進行治療,取得了較好的效果[1],臨床有普及開展的趨勢。但該方法仍在發展階段,術后容易存在細菌污染而導致感染、切口皮瓣壞死、傷口不愈合、醫源性骨折等并發癥,嚴重者骨折后可能并發血栓導致死亡。我們針對其缺點進行研究并采用改良脛骨橫向骨搬移術,應用于臨床,現報道如下,供臨床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2019年6月-2020年9月我科收治的糖尿病足潰瘍8例、類風濕性脈管炎潰瘍1例。男6例,女3例;年齡47~71歲,平均56.5歲。8例糖尿病足潰瘍Wagner分級3級2例,4級4例,5級2例;按糖尿病足綜合分型Ⅰ型1例,Ⅱ型5例,Ⅲ型2例。本組1例冠心病術后心功能嚴重不全;1例腎功能不全;1例趾血管炎性潰瘍為趾遠、近節全干性壞疽,第1跖骨頭殘端約3 cm×3 cm創面不愈,伴有類風濕、高血壓。
1.2 納入與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糖尿病足潰瘍Wagner分級3級及以上;慢性傷口,經常規清創、換藥等方法治療2個月無改善或愈合傾向。
排除標準:一般情況難以耐受或不宜外科手術者;患者存在精神障礙無法配合手術或知情選擇不愿意手術者。
1.3 手術方法
采用大型骨搬移架7例、小型微創骨搬移架2例。
大型骨搬移架手術:行神經阻滯麻醉或腰硬聯合麻醉生效后,患者取仰臥位,消毒,鋪巾。消毒范圍上達大腿上段、下達踝部,小腿下段及以下無菌敷料包扎后再行護皮膜包扎徹底封閉隔絕。設計骨瓣切取區域,以脛骨中上段寬闊內側面為宜,盡量靠近端但不影響骨搬移架安裝及妨礙膝關節活動。向腓側行約15 cm弧形切口,直達骨膜,以1號線縫合骨膜及皮膚,無張力打結懸吊以防二者分離,以骨剝輕柔向脛側掀起皮瓣,顯露脛骨面。于脛骨面設計長約12 cm、寬2 cm骨瓣,骨瓣兩端采用“拱門”狀弧形設計,以電刀標記。先在骨瓣上定位2枚牽引針位置并鉆孔備用,再于骨瓣周圍鉆孔、截骨,盡量保護內骨膜及骨髓,形成可微動的骨瓣。助手保護骨瓣,皮瓣行2處約5 mm橫行切口,手動置入2枚牽引針,安裝牽引架,遠、近端各置入2枚固定針,旋轉牽引螺母調整牽引架至適宜位置,擰緊各固定螺母。試行旋轉牽引螺母,確認骨瓣可按要求提升或下沉移位。沖洗,細致縫合骨膜,再縫合皮下組織及皮膚。干燥敷料、無菌繃帶包扎,并以護皮膜包扎粘貼徹底封閉隔絕,再行足部清創術,清創常規包扎結束后再撤去護皮膜。
小型微創骨搬移架手術:于脛骨上段內側面行3~5 cm切口,切開皮膚及皮下組織,不切開骨膜,保護淺筋膜;于骨膜淺面向脛側掀起皮瓣,設計長5 cm、寬2 cm骨瓣,骨瓣兩端設計呈弧形;骨瓣上定位并鉆2孔,置入牽引針。骨瓣四周鉆孔、骨刀截骨,截骨時可保留骨瓣兩側骨膜完好。安裝固定架,遠、近側各置入1枚固定針。其余同大型骨搬移架手術。
1.4 術后治療
術后胰島素規范控制血糖,并采用高糖、胰島素、氯化鉀配伍支持防治低血糖、低鉀及高能量供給等,密切監測調控血糖,根據創面感染及細菌學情況使用抗生素抗感染,換藥,較大創面聯合VSD治療。3 d后開始旋轉牽引螺母行骨瓣搬移,先向外提升移位,1 mm/d,分4~6次完成(根據不同牽引架刻度設計),14 d后休息3 d,再反向旋轉搬移。創面愈合或接近愈合可停止搬移。如殘留創面仍較大,可繼續搬移骨瓣,7 d或14 d后可據情況開始反方向移位。移位停止后,留置骨搬移架繼續固定6周,去除骨搬移架。期間觀察并記錄肢端感覺、血運情況及全身其他改變,定期攝片復查,扶拐保護,治療內科疾病,防治血栓、肺炎等并發癥。
1.5 療效評價
通過創面愈合傾向及愈合情況、最終愈合時間、足血運及感覺恢復情況、胰島素使用情況及頭發改變、全身其他合并疾病情況、表現等進行綜合評估。
2 結果
本組9例手術順利完成,術后順利出院。均獲得8~23個月的隨訪,平均13個月。8例潰瘍術后出現良好愈合傾向并順利愈合,1例出現繼發感染、壞死,再次行清創術后出現愈合傾向,換藥后緩慢愈合。骨搬移時間4~12周,平均6周,潰瘍愈合時間1~26周,平均12周。足趾感覺、血運均較術前獲得改善,無皮瓣壞死、骨折、血栓等并發癥。1例術后1年出現另外一側肢體足底潰瘍,為肥胖患者,訴無法控制飲食,血糖控制差,平素空腹血糖波動于9~15 mmol/L。1例愈合5個月后同足其他部位出現潰瘍,為肥胖患者,訴無法控制飲食,血糖控制差,平素空腹血糖波動于19~24 mmol/L。本組糖尿病足潰瘍患者中,5例術后出現頭發、胡須變黑現象,發生率為62.5%;2例胰島素使用量較前減少;1例合并嚴重心臟病,術前心功能Ⅲ級,術后13個月隨訪心功能達Ⅱ級,一般情況明顯改善;1例術前出現白內障、視力下降,術后創面愈合,視力持續下降,無好轉或穩定趨勢,平素空腹血糖控制于12~13 mmol/L(圖1-16)。

圖1 皮膚壞死

圖2 廣泛膿腫侵及深層組織

圖3 肌腱外露

圖4 向脛側掀起皮瓣、截骨

圖5 皮瓣無壞死,愈合良好

圖6 術后25 d,創面愈合中

圖7 術后37 d,未植皮

圖8 術后80 d創面已完全愈合

圖9,10 術前

圖11 術前足趾

圖12 向脛側掀起皮瓣、截骨

圖13,14 術后皮瓣無壞死,愈合良好;術后23 d,足趾成活,血運改善,足背皮膚壞死潰瘍仍存在

圖15,16 術后4個月,足趾成活,潰瘍愈合,足血運良好
3 討論
糖尿病足潰瘍為糖尿病的嚴重并發癥,其高病死率、高截肢率導致糖尿病足潰瘍成為了很多糖尿病患者的終末期并發癥。脈管炎導致的潰瘍也是臨床上的棘手問題,截肢后殘端創面的不愈合導致不得不多次向上提高平面進行反復截肢,讓臨床醫生望而卻步。
中國醫生在世界上首先采用脛骨橫向骨搬移術來治療糖尿病足潰瘍、脈管炎潰瘍,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且復發率較低。很多患者完全保肢成功并最終治愈,且該技術仍在不斷地發展、進步和完善中,但也有諸多問題亟待解決,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技術機制和原理尚不明確;作用效果不穩定,有效率高低不齊;存在皮瓣壞死、醫源性骨折,甚至死亡等嚴重并發癥。因為糖尿病足患者老年人居多,部分老年人骨折后長期臥床,在治療骨折過程中并發血栓、肺部感染等并發癥而死亡。筆者對該手術中存在的諸多不足進行了研究和改良,并應用于臨床,獲得了較高的愈合率,無并發癥發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筆者在手術技術上的改良,主要集中在以下幾點:在切開皮膚的時候,采用了皮瓣外科的理念(一般將其稱之為“脛骨瓣移位術”),即對皮膚血液供應的研究和手術操作技術的改良。脛骨內側面的皮膚、皮下組織、骨膜主要血供來自于脛后動脈發出的穿支,采用脛側切口無疑切斷了皮瓣的主要血供,增加了皮瓣壞死的發生率,故全部采用弧形凸向腓側的切口,將脛側留作皮瓣的蒂部,并采用筋膜縫合懸吊等皮瓣操作,慎用電刀,術中可以看到多個由脛側發出的穿支或血管網,均應細心保留。在本組病例中,所有患者的切口均順利愈合,未發生缺血壞死,且具有良好的骨膜血供,也是手術成功率較高的原因,現已有骨膜牽張治療糖尿病足潰瘍的報道[7],如果骨膜的血供受到損害,一塊自身活力都難以保障的骨膜,其牽張效果也無從談起。在截骨設計上,我們將傳統矩形的截骨進行了改良,兩端采用“拱門”狀的弧形截骨,矩形截骨產生的直角較銳,在骨科力學中屬于典型的應力集中模型,應該為早期設計的誤區,筆者采用“拱門”狀的圓弧形設計,將應力平均分散,有效地降低了醫源性骨折的風險,本組病例中,所有病例均未出現骨折及移位等情況。
傳統理論依據和理念為Ilizarov創立張力-應力法則及其“組織牽拉再生”的生物學原理[8],主要應用于肢體延長和骨缺損的重建,其原理是生物組織被緩慢牽拉時會產生一定的張力,可刺激組織再生和生長,張應力的機械刺激、牽拉,促進了血管網的形成、創面愈合。Ilizarov技術在骨或骨-軟組織段復合缺損的修復中發揮了直觀的作用,其使用原理和軟組織擴張器有相通之處。很多學者觀察到,該技術在創面修復尤其對糖尿病足潰瘍的修復具有非常好的效果,并在組織再生領域進行了研究和解釋,這就是中國學者將該技術應用于糖尿病足等慢性傷口取得的卓越成就。而在組織再生領域,筆者研究認為其再生原理無法用單純的張應力法則來解釋,如果這樣采用一些運動比如引體向上,也可以起到皮膚、骨骼牽引的效果,也可以對組織包括骨骼產生張應力,但顯然該方法無法用于潰瘍的治療,所以該理論解釋不排除存在歧誤的可能,中國學者發現的現象、并且用于臨床的技術可能不適用于或不完全適用于Ilizarov技術原理的解釋。
筆者認為,該手術的本質是創傷刺激[9],主要技術機制是提供了一種可控、可調的創傷刺激,人體存在“創傷-修復與再生-重建系統”,當機體受到創傷時,必然會產生對創傷的修復應答,這種創傷-修復應答反應,主要目的在于修復創傷,其過程主要是由分子水平的細胞因子來實現的,其可能的因子包括但不僅限于多種炎癥因子、生長因子、骨形態發生蛋白、干細胞動員等。炎癥因子可以擴張血管,帶來豐富的血管再生,這在各種炎性組織的豐富血管再生中就可以見到。炎癥因子等反應可以擴張血管、改善血管通透性和物質交換,這解釋了術后即可見到血管、血供明顯改善的現象。而由這種創傷-修復應答帶來的因子反應隨之啟動了機體的再生-重建系統,帶來的不僅僅是血管再生,還包括識別損傷修復區的細胞,使其重新獲得生長修復的能力,這種細胞生長愈合能力使得本來已經喪失愈合傾向的慢性傷口開始愈合,達到修復重建的目的。而“創傷-修復與再生-重建”之間的一系列過程,可能包含了一系列的信息物質和信號傳遞,形成了一個統一的系統。創傷可能給機體帶來有害的一面,同時也能帶來有益的一面,骨瓣移位作為一個微截骨手術,選擇對肢體和功能無明顯影響、可逆的供區或者操作,其有害的一面可調可控,每次旋轉螺母帶來骨瓣的微移,正好符合這個需求,類似疫苗(減毒或者滅活),而我們利用的正是其啟動機體修復系統中有用的一面,適宜的創傷刺激帶來了積極有利的一面,骨的愈合反應時間漫長,在骨上進行創傷刺激也正好符合該手術的需求。現在已經證實,創傷的愈合需要多種因子的參與,而一些生長因子的半衰期較短,如廣普細胞分裂素bFGF是體內已知促進血管生長最強的因子,可有效促進皮膚、血管、肌、神經、骨等多種組織生長,但其在體內極易水解,半衰期僅3~10 min[10-12],半衰期實在太短,外界給藥往往無法達到要求,需要源源不斷提供。而骨搬移技術每次移位均可造成新鮮的微損傷(創傷),每日數次,長期進行,則提供了長期的創傷刺激誘發出創傷-修復應答反應,獲得源源不斷的修復因子,這種創傷反應在一個相對健康的區域進行,其獲得的創傷反應可靠,其獲得的生化因子位于組織體液系統,通過血液循環到達全身、潰瘍創面,對需要修復的損傷進行識別并啟動其修復愈合能力。遠離手術部位的足部出現愈合傾向、細胞生長能力改善、潰瘍愈合、各部位的血管出現再生反應,只有通過血液系統傳播的細胞因子可以系統解釋。血液循環系統遍布全身,同時也實現了各部位組織細胞的再生和修復重建,也能帶來與相關因子相應的全身效應,可以解釋多個器官系統出現“好轉”現象的原因。
以上理論對治療的指導非常重要,是改良技術的核心。在該理論體系下,對治療提出了明確的指導和改良。首先骨瓣的供區選擇不是一定的,在一側肢體進行手術,對側肢體也可獲得改善,雙側糖尿病足無需雙側手術,因為其效果是全身性的。其次,不僅向外搬移牽拉時產生的張應力有效,回搬時的壓應力也是有效的。一句話,只要是引起微創傷,都可能產生效果,臨床上不一定過度牽拉數周導致皮膚張力過高、壞死,也無需受搬移幾周的時間限制,搬移時間可以根據潰瘍嚴重程度、創面大小、愈合需要的時間靈活調整,必要時完全可以延長搬移時間。其次,在藥物使用方面,我們停止了對創傷炎癥反應有明顯影響的藥物如術后常用的非甾體類抗炎類藥物、激素,對細胞分裂再生有影響的藥物比如奎諾酮類藥物也應盡量避免使用。1例術后療效差的患者,患有嚴重冠心病,長期服用阿司匹林,后改用低分子肝素鈣,這給筆者提供很多思考和啟發。最后,無論是糖尿病足潰瘍,還是脈管炎潰瘍等其他慢性傷口,筆者認為該治療方法都有效,如果傳統方法嘗試都無效、無法獲得愈合傾向,該手術可作為一種考慮。
這些理念和技術改良,是術后患者潰瘍獲得較高愈合率的可能原因,也可能正是沒有對這些因素進行統一控制,臨床上開展該手術有效率高低不一。人體衰老是由基因系統調控的,術后多個患者出現頭發、胡須變黑等情況,也可以佐證該手術不是單純使血管網形成、血供改善(即使老年人的頭皮也有非常旺盛的血供),而是對機體全身性系統的反應,細胞因子修復過程影響了機體再生能力、衰老重建的意外啟動。其中1例患者為冠心病患者,術前心功能Ⅲ級,術后隨訪Ⅱ級,一般情況明顯改善,不排除冠狀動脈是否也存在血管內皮細胞再生、血管網重建改善的情況,雖然由于冠狀動脈造影的風險及費用,未貿然進行造影檢查和對比,單例的對比也不一定存在統計學意義,但這些現象值得深入研究。1例脈管炎并趾壞疽潰爛不愈的患者,我們也采用該手術進行治療,獲得了良好的愈合,故也納入到觀察組中。部分患者出現胰島素用量下降,這些都提示該手術可能帶來多器官系統性的再生和重建。
值得關注的是,本組中療效差、再次出現其他部位潰瘍的患者,都同時有依從性差、血糖控制差的情況,提示了長期的血糖管理是維持療效的核心因素,對患者的健康教育、監督、鼓勵,在術后護理中至關重要[13],在考慮進行該手術前,患者的依從性、血糖控制條件等也應納入考慮。
綜上所述,改良脛骨橫向骨搬移術對糖尿病足潰瘍、脈管炎潰瘍等慢性傷口的修復有良好的效果,可以降低皮膚壞死、骨折的風險,為如何提高有效率、規避并發癥提供了新的方法。“創傷-修復與再生-重建系統”理論可以很好地解釋其手術機制和作用原理,為各種炎癥因子、再生因子、干細胞動員、信息傳遞等分子水平領域對創面的修復提出了新的思路,尋找或排外相關因子可以作為未來尋找相關證據的研究方向,無論證實和證偽,都有進一步積極探索的廣闊空間和研究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