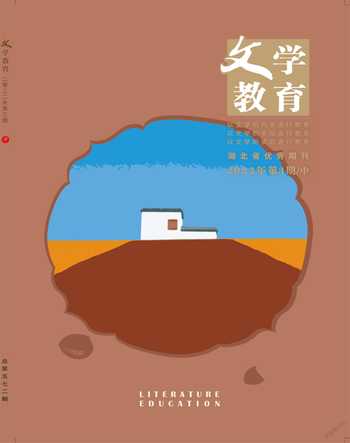基于跨媒介的《悲慘世界》敘事視角探析
范文一
內容摘要:經典小說《悲慘世界》的歷史背景宏闊,人物形象近百,敘事方式新穎獨特,思想內容啟人深思。本文從敘事視角入手,通過對小說《悲慘世界》改編的同名影視作品《悲慘世界》的敘事分析,探索《悲慘世界》跨媒介敘事成功的緣由,主張運用敘事技巧對經典作品的翻拍來推動影視化改編的跨媒介敘事創新。
關鍵詞:《悲慘世界》 跨媒介 敘事視角
“跨媒介敘事”是亨利·詹金斯于2003年在《文化融合》中提出的新敘事概念,“跨媒介敘事代表著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作品中的構成元素被系統地分散到多個渠道上,以創造統一和協調的娛樂體驗。在理想的情況下,每一種媒介都會對故事的展開做出自己獨特的貢獻。”(詹金斯,2003)也就是說,一個故事通過借助多種媒介的共同參與,展現故事文本的敘事新模式,每個新媒介都對故事的呈現產生新的影響。卡爾維諾、馬爾克斯等作家認為,視覺形象在敘事活動中具有優先地位。電影敘事憑借其特有的“視聽語言”,更適合當下快餐式獲取知識的途徑。電影語言是燈光、對白、攝像等多種因素共同呈現的結果,是用音像傳遞信息的一種模式。但是電影語言對經典文學作品的表達也有一定局限性。在信息碎片化、圖像化的時代,經典文學作品仍然經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文字敘述的不確定性能夠帶來無限幻想,正如“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這樣的情感體驗是具體的圖像難以賦予我們的。經典名著如何滿足電影敘事的要求,而電影敘事如何表現經典名著的宏大世界觀,成為了經典文學作品影視化改編的難題。
新媒介時代,基于經典文學作品改編的影視作品越來越少,并且由此改編的影視作品的收視率遠不及由“耽美文學”、網絡文學改編的網劇。許多導演寧愿高價購買網絡文學作品的版權,也不愿利用現成的經典文學作品作為影視腳本。文學經典改編的影視劇日漸式微,究其根本,是因為改編經典文學的難度較大、成本較高。為了還原讀者心中的“名場面”,演員選擇與“服化道”盡力貼合原著。即便如此,仍然存在眾口難調的情況。為了兼顧電影情節的進程和文學作品內容的完整性,難免會對原作進行刪改,此行為常遭到忠實讀者的批評。經典文學作品影視化改編成了一項“吃力不討好”的苦差。如何拯救日漸式微的經典文學作品改編?文字與電影媒介之間的矛盾又應如何調和呢?
本文以《悲慘世界》小說、音樂劇、音樂劇主導的電影為例,分析跨媒介敘事成功運用于經典文學作品傳播的原因,主要從《悲慘世界》中的經典人物形象——沙威入手,探究三種媒介在塑造人物形象時采用的不同敘事視角,以及它們帶給觀眾的獨特審美體驗。所以,本文認為《悲慘世界》的經典傳承,對中國經典文學作品的影視化改編具有借鑒和推廣作用,有助于突破現有的經典作品敘事媒介單一的障礙。
一.跨媒介敘事的視角理論
小說的敘事視角源于熱奈特的“聚焦”理論,熱奈特在《敘事話語》中將敘事視角分為三大類:非聚焦型、內聚焦型和外聚焦型。學者胡亞敏對此進行了較詳細的闡釋,“非聚焦型即零度聚焦,指敘述者或人物可以從所有的角度觀察被敘述的事,無所不知;內聚焦型則是每件事情都嚴格按照一個人或幾個人物的感受和意識來呈現。而在外聚焦型視角中,敘述者只提供人物的行動、外表及客觀環境。”(胡亞敏,2004)由此可見,“聚焦”理論將小說文本從視覺的角度進行了描述,那么,當小說文本跨越原有的單一媒介,轉化為可視可聽的音樂劇或音樂劇主導的電影等多種媒介的大眾影視作品,“聚焦”仍然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聚焦”在跨媒介敘事中仍是一個關鍵因素,詹金斯在《文化融合》中指出,小說敘事不應局限于這部小說,而應將它放在整個媒體環境中,跨媒介協同對其進行藝術再創作,最終成為一個新的故事。經典小說《悲慘世界》及由此改編的影視作品中擁有豐富多樣的跨媒介敘事研究資源,表明不同的敘事視角可以通過多種藝術形式來展現,成功地迎合了大眾的審美需求。
由此可見,如果突破經典作品敘事媒介單一的障礙,實現多媒介融合,對中國經典文學作品影視化改編具有借鑒和推廣作用,滿足中國大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當代戲劇、電影、文學要通過跨媒介敘事,傳承中國文化,講好中國故事,培養優秀的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實現中華民族從“文化救國”到“文化強國”的偉大復興。
二.《悲慘世界》跨媒介的三種視角
《悲慘世界》的跨媒介研究主要呈現三種視角,原媒介小說文本多采用零聚焦視角展現宏闊歷史背景下的故事,音樂劇文本(著重分析歌詞)運用內聚焦視角凸顯音樂劇中的人物形象,音樂劇主導的電影文本多借助混合視角展呈一部科技與藝術融合的優秀影視作品。
1.小說《悲慘世界》的零度視角
小說《悲慘世界》的敘事特點鮮明,正如法國文學家朗松評價道:“這部小說是個大千世界,大雜燴,里面充斥著借題發揮、節處生枝和沉思冥想。最偉大的美與最乏味的嚕蘇話在書中相映成趣……他把各種各樣的筆調、主題和體裁混雜在一起。”(應舒悅,2018)換句話說,這是一部內容豐富、情節跌宕的鴻篇巨作,就敘事視角而言,主要采用了非聚焦視角。
在小說中,作者以零度視角清晰地描述了沙威的身世:即使從小生活在監獄,后來卻神奇地成為一名警官。他的父母都是可憐的底層人,母親終日流浪,以占卜為生;父親則是他最痛恨的一類人——苦役犯。苦難的生活使沙威的心逐漸變得冰冷,他痛恨罪犯,認為罪犯均是無可救藥之人,他只需要將他們送進監獄,就完成了自己神圣的使命。沙威并不是傳統意義上“偉光正”的人物,也不是一個嫉惡如仇的英雄。驅使他追捕逃犯的動力并不是源自內心的正義感,而是對法律、國家、權勢的絕對服從。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他與人民站在對立面,但絕不能說他是一個壞人。最終,一個視法律為信條的人,卻被自己多年來追捕的逃犯——冉阿讓救贖了。冉阿讓喚醒了沙威內心深處的“神性因子”,使他內心的信仰大廈崩塌,最終以極端的方式走向了生命的盡頭。
由上而知,小說將沙威的一生清晰地呈現在讀者眼前,即使他最終的命運使部分讀者大為驚愕,但結局既在情理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回顧前文對沙威的描述,能夠預測到他悲慘的結局。值得一提的是,小說《悲慘世界》中存在大量游離于主干故事之外的插入成分,是作者針對某一社會現象和社會問題發表的評論(如滑鐵盧戰役),屬于敘述者干預。敘事因此被割裂,使主線劇情的展開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響。這也成為了許多讀者被這部作品“勸退”的主要原因。
2.音樂劇《悲慘世界》的內聚焦視角
1978年,法國藝術家阿蘭·鮑勃利和克勞德·米歇爾勛伯格協作的音樂劇《悲慘世界》收獲了出乎意料的熱烈反響。兩位創作者為了多面立體地還原人物形象,采用了以話題視角統領全劇的敘事方式,以便主要人物評述自身的情節,從而引出與之相關的多種社會問題,表達各自的聲音。這種內聚焦視角的敘事方式,用歌曲充分表現了人物的內心世界。
音樂劇《悲慘世界》中,許多曲目廣為傳唱,影響深遠。例如,孩童時期的珂賽特身處泥淖,身心均受到酒店老板夫婦的殘害,卻依然擁有天馬行空的想象力。在她的歌聲里,云上會有一座城堡為她而建,會有愛她的天使和伙伴……讓人不由得為之心痛。少婦芳汀的一曲“I Dreamed A Dream”恍如杜鵑啼血,唱出了棄婦難言的悲苦。值得一提的是,劇中的相同旋律常常出現在不同的場景里,為渲染同一種氛圍,頗有“復調”之感。例如,冉阿讓受到主教的救贖后,與沙威受到冉阿讓的感化后,用同一段旋律演唱了不同內容的內心獨白。急促的音樂暗示著兩位角色內心激蕩著強烈的情感,但是兩人選擇的道路大相徑庭。創作者巧妙地“求同存異”,凸顯了兩個角色觀念與命運的迥異。由此可見,以話題視角統領音樂劇的方式,抒發情感毫不呆板,觀賞價值很高,兼具內聚焦敘事的生動性與歌曲的藝術性。
筆者認為,在音樂劇中,沙威的主題曲一定是沉郁頓挫、極具個人特色的《Stars》。由于沙威的疏忽,冉阿讓又一次逃脫。他沮喪地來到一段激流前,面對滿天的繁星,傾吐了自己的苦悶:
“看/黑夜之中/有逃犯在亡命/逃離了上帝/自正道墮落/上帝是我的見證/我絕不退縮/直到我再次找到他/直到我與他面對面/他熟知黑暗中的路數/我行走于天主的正道/那些追隨正途的人/終會得到獎賞/假使有人/如路西法一般隕落/他將落入烈焰/經受劍雨/閃爍的繁星/無法數清數目/充滿了夜空/帶來秩序與光明/你們是衛士/沉默而堅實/在深夜中守望/守護著黑夜/你知道你在空中的位置/你深知你的軌跡目標/季節更換/周而復始/你從未改變/那些動搖者和墮落之人/必須付出代價/主啊/讓我找到他/讓我再見到他/將他擲于牢中/在那之前我絕不停下/我在此起誓/以繁星之名起誓!”(譯文來自音樂劇《悲慘世界》曲目《stars》)
常常引人遐思的星空,在沙威的眼中,卻由無數“循規蹈矩”的星星構成,倘若某人成為冉阿讓那樣的“路西法”,便只能隕落。這段歌詞巧妙地對應了小說“在塞納河的一段急流處沙威陷入沉思”的部分,從沙威的視角出發,敘述他體驗的世界,尤其是當時社會對人物心靈的摧殘和迫害,向我們充分展示了沙威的世界觀的巨大變化。
3.音樂劇電影《悲慘世界》的混合視角
《悲慘世界》曾十九次被翻拍成電影,但是各個版本均反響平平。所以,音樂劇的成功無疑為《悲慘世界》的新型影視化改編提供了另一思路。2012年,湯姆.霍伯基于音樂劇改編的《悲慘世界》音樂劇電影上映,在全球獲得了巨大票房。這部音樂劇電影的表現手法與一般音樂劇相比,更為豐富多樣,比如在“服化道”方面更為精致等,尤其是鏡頭語言,能夠更加有效地向受眾傳遞情緒。
沙威投身激流的場景是小說中最為經典的一幕。多個版本的音樂劇演繹這一幕時,由于空間受制于舞臺,僅僅借助光影的變幻,整體效果較為扁平,未讀過原著的觀眾可能會看得一頭霧水。而2012音樂劇電影版《悲慘世界》中,沙威投身激流的鏡頭給觀眾帶來了極大的震撼,俯拍特寫長鏡頭下,沙威縱身跳入冰冷的塞納河,消失在深藍的河水中,宛如一顆流星隕落天際,經過剪輯處理,整個過程十分連貫。這一幕的視角設置十分合理,觀眾似乎站在云端,親自目睹了這場壯烈的悲劇。相較于在舞臺上演繹的音樂劇,視覺張力十足。《悲慘世界》的歷史背景是宏闊的,集體合唱“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的部分時采用全景CGI 鏡頭,營造了零度視角下的宏大場景。集體合唱曲目“One Day More”時,鏡頭在各個演唱者之間來回切換。閣樓上的青年、身居陋巷的艾潘妮、坐上逃亡馬車的冉阿讓父女,他們在不同地點、不同境遇下唱著同一支歌,暴風雨來臨之際,沒人知道未來將會怎樣。盡管“明天”對每個人的意義不盡相同,但是無論如何,明天都是新的一天,身處時代洪流,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除了較為常見的零聚焦視角,內聚焦視角在本片也較為多見。馬呂斯同摯友們在閣樓上共同討論起義大計,主要使用了跟鏡頭,此處的跟鏡頭表現的是馬呂斯目光的移動,形成了由他出發的內聚焦視角,介紹了這一組織的每個青年領袖。毫無疑問,混合視角的優勢在音樂劇電影中體現得極為明顯,觀眾更容易獲得沉浸式體驗。
由此,采用混合敘事視角的音樂劇電影受到世界各地觀眾的青睞,許多人因此加深了對音樂劇的認知。然而,即使票房可觀,2012版的音樂劇電影《悲慘世界》也被不少音樂劇迷詬病:演員在表演時加入了過多“自戲”,沉迷于表演,而非專注于演唱,導致歌曲質量遜色于十周年紀念版的音樂劇,很多觀眾因此失望。因此,兩種藝術手段交融產生的碰撞,難免存在媒介融合引致的矛盾,如何實現二者的平衡有待學界探索。
經典文學作品經過歷史的沉淀和時間的檢驗,是不可多得的優秀影視腳本。選擇翻拍經典文本,不僅保證了影視作品的內涵,在科技與藝術的結合中,也能夠賦予文學作品更長久的生命力和新的價值。國內影視行業發展蒸蒸日上,電影、音樂劇已被大眾接受和喜愛。近年來,中國音樂劇事業發展迅速,音樂劇由小眾愛好逐漸轉變為大眾文化。許多優秀的音樂劇作品也陸續在中國各地巡演,《悲慘世界》便是其中之一。更多中國影視人應致力于文學作品的影視化改編,借助多種媒介手段,使用大眾喜聞樂見的多種藝術形式,傳播經典文學作品的人文價值。在改編的過程中,我們不僅要深入考慮觀眾的審美體驗,更要融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
參考文獻
[1][美]亨利·詹金斯.融合文化[M].杜永明譯,商務印書館,2012.
[2]胡亞敏.敘事學[M].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3]應舒悅.小說與音樂劇電影的審美體驗比較——以《悲慘世界》為例[D].浙江大學碩士論文,2018.
[4]維克多·雨果.悲慘世界[M].李玉民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
本文屬2021年湖北文理學院大學生創新創業項目(XJ2021112)的成果。在寫作中得到指導老師鄭曉鋒博士的悉心指點,在此表示衷心感謝!
(作者單位:湖北文理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