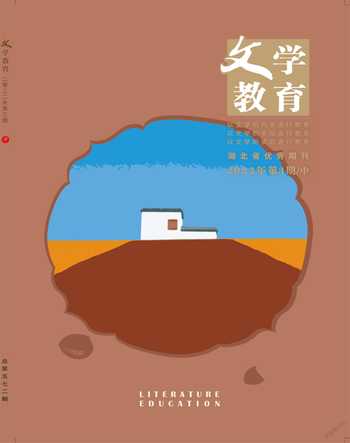“華南聯大”教育活動史研究芻議
鄢祥鋒
內容摘要:將抗日戰爭時期,以中山大學為代表的內遷粵北的華南地區高等院校團體,稱為“華南聯大”。“華南聯大”先師們在民族危機下堅守教育,以教育抗戰救國,為廣東高等教育和學術的延續發展積蓄力量。采用微觀史學、心理史學、教育人類學等研究方法梳理教育史料,考察“華南聯大”的教學、管理、科研、社會活動和師生精神狀態等教育歷史,拓展民國高等教育史和廣東地方教育史、抗戰史研究范疇,加深歷史體悟,為教育歷史研究提供借鑒。
關鍵詞:高校內遷 教育史 “華南聯大”
“大學是民族的靈魂,大學的興衰,反映著國家文化的臧否。”[1]抗日戰爭時期,大批高等學校內遷辦學。在華南地區,以國立中山大學為代表的華南地區高等院校遷址粵北堅持辦學、教書育人。據統計,抗日戰爭時期內遷高校124所[2],遷到韶關辦學的有8所,加上抗戰時期在韶關創建的有3所[3],共11所高校在韶關烽火育人、教育興邦。
一.“華南聯大”概念闡述
“華南聯大”,是指抗戰時期以中山大學為代表的內遷粵北的華南地區高等院校團體。它是高等教育史領域一個研究概念,主要基于地理位置、內遷粵北高校團體共同性、與已有高校團體名稱對比以及內遷粵北高校巨大成就等凝練而成。
一是地理位置屬性,一方面“廣義的華南地區除廣東、廣西外,包括福建中南部、臺灣、海南和南海諸島,以及江西省、湖南省部分位于五嶺以南的州縣。”[4]粵北即廣東省北部,屬于華南地區。另一方面,國立中山大學、廣東省立文理學院、私立嶺南大學等高校均來自華南地區(廣州),它們集中遷址粵北堅持辦學。
二是內遷粵北高校團體共同性。抗日救亡和教育追求的一致性,以及高校團體間開展的聯動。抗日救亡一致性體現在高校一致抵御外敵,共同抗戰,師生組織街頭演說、戲劇話劇等方式宣傳抗戰救國等方面。教育追求一致性體現在各校秉承既著眼于當前教育形勢,開展戰時課程教育和戰時研究,也著眼未來培養戰后建設人才。“華南聯大”的聯動體現在內遷粵北高校在教育資源方面的聯動,如校際借讀和圖書資源共享等。
三是與已有高校團體名稱對比。既區別于由國民政府組建的西南聯大、西北聯大,也區別于學術界研究豐富的學術概念“西南聯大”、“西北聯大”。
四是內遷粵北高校取得的巨大成就。廣州淪陷后,韶關成為戰時省會,大批文化團體組織和高校到此開展抗日救亡運動,形成獨具特色的抗戰文化,加上高校云集,當時任教的名師有哲學家朱謙之、經濟學家王亞南、劇作家洪深、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李達、音樂家馬思聰、圖書館學家杜定友、文獻學家冼玉清等,文化大師聚集。“韶關從山城一躍成為與昆明、成都、桂林齊名的文化據點和廣東戰時文化中心”[5],不僅培養了原子光譜分析家黃本立、人類學家梁釗韜、文藝理論家徐中玉、地理學家曾昭璇等卓越人才,還培養了國家急需青年人才,當時坪石有“粵北文化城”之說,創造了輝煌燦爛的教育成就。
“華南聯大”這段教育歷史,在民國史、文化史、抗日戰爭史、地方史、文史資料中粗略提及,多為史料性和概括性描述,無深入系統研究。但是“華南聯大”師生為規避戰爭烽火,秉著教育救國、興學抗戰的理想,創造了民國時期廣東教育史上的奇跡。它作為地方歷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華南高等教育史乃至中國高等教育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二.研究意義:重溫興學救國歷史、續寫教育國家記憶
一般而言,華南教育歷史是包含華南地區的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基礎教育及社會教育等教育活動的歷史。“華南聯大”教育歷史與華南教育歷史有一定聯系又區別明顯。“華南聯大”教育歷史是特指抗戰時期,華南地區以國立中山大學為代表的內遷粵北的高等院校的教育歷史,它是華南教育歷史的一部分,也是極其特殊和重要的一部分。“華南聯大”興學救國,在廣東高等教育史上寫下濃墨重彩一筆。正如余一心在《教育雜志》的“抗戰以來的高等教育專號”中講到“中山大學在千萬人期許之下果敢地回到炮火中的粵北坪石……這種回到前線的勇邁的壯舉將在中國大學教育史寫上最光榮的一頁……”[6]
1.一定程度上拓寬高等教育研究范疇。“華南聯大”在韶關粵北踐行學術理想、教育救國,培養了大批杰出人才,他們也是日后中山大學、華南理工大學、華南師范大學等廣東高等教育的根脈。“華南聯大”教育史研究,可以更明確從歷史脈絡展示“華南聯大”甚至廣東地區高等教育發展、延續的演變進程,拓寬廣東高等教育史研究范疇,是豐富華南地區內遷高校教育史研究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基礎性研究。
2.一定程度上深化和豐富區域抗戰史和教育史的研究。“華南聯大”在戰亂中堅守教育興邦的理想信念和以身許國的民族氣節,保存了華南高等教育的根脈,是廣東教育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一環,推動了華南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中國對日本的抗戰,是反侵略拒絕侵略的戰爭……勝利的保證,都在于人力與物力的運用,智慧與科學的貢獻,大學教育和學術機關正是戰勝的有力支柱,它們本著民主的精神、科學的方法,為真理與和平服務,以求贏得戰爭獲取和平。”[7]“華南聯大”教育史研究,可以豐富民國時期華南抗戰史和高等教育史研究。
3.加深歷史理解,有助于從歷史角度深刻把握教育歷史及內在聯系,加深理解大學教育教學的規律。通過研究“華南聯大”在戰爭年代承擔的獨特社會責任:培養技術知識人才,開設專修科、實用學科,科研研究和成果、社會教育、文明開化活動等。可以加深對于大學與社會,教育與國家、教育與社會之間關系的認識。
三.研究內容:真實生動的“華南聯大”教育歷史豐碑
“華南聯大”教育史立足于歷史上微觀的、現實的、具體的教育事實。它以抗日戰爭為時代背景,以韶關為地域中心,把內遷到粵北的以中山大學為代表的華南地區高等院校的教育歷史作為研究內容。
1.研究內容來源的多樣性與特殊性。一方面要立足文本,深入挖掘書籍、報刊、師友、師生、親友信件、日記、傳記、紀念文集、特刊等,另一方面要關照非文本,分析證件、聘書、繪畫、書法、器物、教具、教材、文具、圖片、建筑等實物資料,將文本與非文本有機結合。
2.研究內容在宏觀與微觀層面的結合。一是研究“華南聯大”的概念界定、特點、數量;內遷原因、內遷的歷程、意義;院系設置、教職員情況,辦學概況和發展,師生學習和生活狀況,教學、管理、服務等活動。以及“華南聯大”參與粵北經濟發展、人才培養、社會服務的活動。二是研究“華南聯大”各高校在教育活動過程中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學科(專業、課程)設置,教學考察和校外調查、實習活動,教育行政管理活動,招生與考試,學生社團活動,民眾教育,以及師生所從事的抗日宣傳活動、學生服務軍需征調、參軍支持抗戰活動。三是研究“華南聯大”師生創作的《文學生活》《春蕾》等壁報,各校出版的《中山學報》《文理月刊》《嶺南大學校報》等刊物,學術大家出版的《中國經濟論叢》《人類科學論集》《重原子核內之潛能及其利用》等著作及《舞臺技術》《經濟科學論》等經典論文成果。以及“華南聯大”各校的學術研究、討論、演講、座談活動。“關于學習研究,也不覺沉寂,每系設有學會經常邀請名流學者的學術的演講,或舉行座談會討論會等活動,每當討論會舉行之際,全院同學大半參加,到會者不甘寂寞,必辯至面紅耳赤才至,這是法學院的特色。”[8]如1941年6月26日,中山大學法學院蘇德戰爭座談會。1941年11月25日,中山大學師范學院舉行的時事座談會:美日談判與太平洋現勢。1944年4月11日-12日英國都倫大學雷威克來中山大學講學。四是研究“華南聯大”各師生讀書報國和抗日救亡并重所體現的精神、心理狀態等。“廣東文理學院的學生,在大體上說起來,對于精神的糧食與物質的糧食,都是相當注重的。如果我們可以用這兩點來作為分類的標準,那么只注意于精神的糧食而忘記物質的糧食,和注意于物質的糧食而忘記了精神的各占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的比數;一面注意精神的糧食,一面又注重物質的糧食,卻占百分之七十以上……”[9]以及“華南聯大”學人知識分子群體所展現出來的獨立思考、知行統一等大學精神和艱辛辦學、潛心學術的教育理想。內遷粵北的私立嶺南大學,“本校教育政策向以研究高深學術,培植專門人材為目的。抗戰以來,為適應需要實施戰時教育,增設有關抗戰建國科目。尤其注重提高民族意識,養成學生強固之愛國觀念。一方面本著政府維持高等教育之方針,從事于經常工作;一方面負起時代之使命,盡量充實各院系教學與研究內容,提高教育效率,訓練人才參加抗戰工作及為將來戰后建國之用。”[10]內遷粵北的私立廣州大學,“知行合一教育,本校除注重高深學術之研究外,并著重教學合一,務使即知即行,免落空虛之弊,于法律系則設有假設法庭,于銀行學系則設有銀行實習,于工程則有星期踏勘等,又如農村服務,前線慰勞,后方籌募,一切抗建工作,均鼓勵學生參加,務求養成學生立己立人,達己達人之最高原則。”[11]
四.研究方法:多維視野、融合貫通、史論結合
研究方法多元化、多維視野是深化教育史研究的有效途徑,要“通過現代各種學科的最新成果和時代的眼觀來‘疏通’史實與史實之間的關系。”[12]“華南聯大”教育活動史研究主要應用以下幾種研究方法,且幾種方法是綜合運用。
1.微觀史學。微觀史學更關注的是歷史上那些具體的、易于觀察的、個別的事物,更多的是關注個體的人的情感、心態、日常生活、思想等各個方面。它講究小中見大,要把小點的研究與大的意義相聯系,個案分析和結構、過程的結合。
以運用微觀史學以研究“華南聯大”教師活動為例,不僅研究教師的教學活動,還得研究與教師有關的家庭、吃穿、人際交往等因素,關注教師校內外活動的關聯,以達成整體還原教師的教育活動。
2.教育人類學。教育人類學要求研究者吸收和融合人類學的田野調查、訪談等方法,深入“華南聯大”辦學實地,回歸真實的教育活動場景,與教育歷史參與者融為一體,實現教育活動“在場性”還原,深刻把握當下來更好理解和研究過去的教育活動。
3.心理史學。各類教育主體的心理狀態,是我們感知教育歷史的途徑之一,心理史學要求研究者要善于從“華南聯大”教師、學生和教育管理者等的日記等帶有私人性質的史料載體中尋找心理痕跡,深入教育歷史,從客觀世界走進人的內心世界,感知教育歷史。
4.教育口述研究。教育口述研究從“‘活動主體的聲音’這一側面入手,通過與主體面對面交流、接觸,既補充了原有材料的不足,更通過主體聲音凸顯了真實性和在場性。”[13]要搜集“華南聯大”各類教育歷史參與者、知情者的口述資料。
5.教育圖像史學。教育圖像史學要求研究者將視線由文字資料轉到各種可視化的圖像資料上,如“華南聯大”在粵北辦學處留下的各類有關教育歷史的照片、圖像等,應用圖像再現教育歷史。
6.計量史學。教育史研究主要在教育規模、程度和范圍;有關教育結構的分析研究;各教育現象與教育因素的相關性研究應用計量史學方法。比如“華南聯大”各高校師生數量規模、師資結構、生源,專業和課程結構等,可以運用計量史學,通過數據資料的統計分析和對比,可以使有關“華南聯大”的教育事實呈現得更為清晰、準確,在此基礎上進行的定性分析也更有理有據。
7.史論結合研究。“史論結合”即充分分析歸納“華南聯大”教育歷史資料,同時全面掌握科學的教育基本理論、高等教育理論。要把研究“華南聯大”教育發展、演進的歷史和對此進行指導的教育理論研究有機結合、辯證統一起來,以達到論從史出,以史帶論,史論結合。
參考文獻
[1]歐元懷.抗戰十年來中國的大學教育,中華教育界,1(1):7.
[2]徐國利.關于“抗戰時期高校內遷”的幾個問題[J].抗日戰爭研究,1998(2):123.
[3]韶關市政協文史委員會編印.韶關文史資料第20輯[M].韶關:韶關市政協文史委員會,1989:129.
[4]桑兵.“華南”概念的生成演化與區域研究的檢討[J].學術研究,2015(7):95.
[5]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廣東地方史·第一卷[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472.
[6]余一心.抗戰以來的中山大學,教育雜志,1941,31(1):5.
[7]歐元懷.抗戰十年來中國的大學教育,中華教育界,1947,1(1):7.
[8]握籌.學校生活素描特輯:中山大學在坪石,學生之友,1942,4(4-5):21.
[9]許幕齋.戰時的廣東省立文理學院,民意周刊,1940(159):10.
[10]佚名抗戰以來的嶺南大學,教育雜志,1941,31(1):41.
[11]王志遠.抗戰八年之廣州大學,廣大學報廣州大學十九周年紀念特刊,1946:5.
[12]康樂,彭明輝.史學方法與歷史解釋[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3.
[13]周洪宇.論教育活動史多維視野的實現途徑[J].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2):77.
基金項目: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2020年度青年項目-“華南聯大”教育活動史研究-以抗戰時期內遷韶關高校為例(課題編號:GD20YJY05);2020年度韶關學院校級人文社科科研項目重點項目-民族危機下的華南高等教育研究-以抗戰時期內遷粵北高校為例(課題編號:SZ2020SK04)階段性成果。2021年度韶關學院黨建與思想政治研究課題“抗戰時期的大學精神對我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啟示研究-以華南高校內遷粵北群體為例”,編號SY2021SZ07;
2022年度廣東省教育科學規劃課題(黨建研究專項):黨的高等教育方針百年歷程啟示研究
(作者單位:韶關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