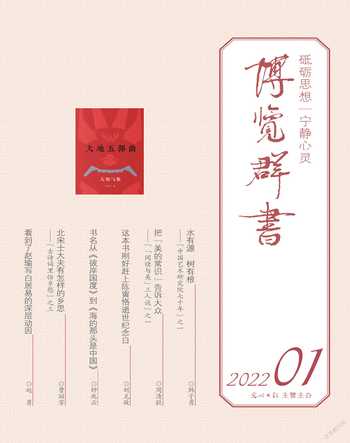歷史編撰學是神話嗎
譚佳
所謂歷史編撰學,其實就是如何寫史的學問。世界文明史上產生于西亞兩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北非尼羅河流域的埃及圣書字,中國黃河流域的漢字是公認的三大代表性的古典文字,對世界文明的產生發生了巨大的影響。不過,除了漢字一直傳承使用至今,楔形文字和埃及圣書字都早已于公元一世紀和五世紀前后退出歷史舞臺,唯獨漢字持續傳承發展,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成為三大文字體系中唯一傳承至今的符號系統。因此之故,作為四大古文明中唯一不曾間斷,有著最為持續和壯觀的文獻傳統的中華文明,同樣有著世界文明發展中最壯觀發達的史學體系,比如眾人皆知的“二十四史”。相應,中國的歷史編撰學也最為持久壯大、枝繁葉茂。
在傳統中國,官方的歷史編撰學是不容置疑的,比如經朝廷編撰修訂的正史享有絕對權威,是歷史敘事典范的標準所在。晚清革故鼎新之際,梁任公便是從“史學革命”入手,希望革除傳統史學編撰之弊,迎接新學問新思想。自此,傳統歷史編撰學的合法性受到質疑。百余年來地不藏寶,現代考古學不斷用新材料推翻古史記載或空白。“夏商周斷代工程”以多學科相結合的方法,推出了一份夏商周三代文明史的科學年表。不妨對比,兩千多年前的司馬遷在《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里將中國的歷史紀年追溯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前841年,再往上的《三代世表》便有世無年。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最直接作用在于,將公元前841年向前推進了1200多年。其實,考古學拉長歷史記載的根本目的,仍與傳統史學有重疊之處,即印證中華文明的起始和來源。張光直先生曾疑惑:“為什么中國學者對文明起源僅僅限制在‘中國文明是從什么地方來的’這個問題上來理解?為什么不討論產生文明的社會內部動力問題?”(《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序》,陳星燦《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三聯書店1997年版)。
“文明的社會內部動力問題”當然很復雜。考古學家們要面臨諸多理論范式和材料問題,一般情況,他們少有涉及歷史編纂學——這門悄然深刻主導著中華文明敘事的學問。擅長史前研究的神話學者;擅長即敘事研究的文學研究者往往因被冠名為“文人”之名,而不太能介入以實證為訴求的考古界。換個角度,放眼世界學林,歷史編撰學問題,恰恰可以由文學和神話學者來完成。意大利學者馬里奧·利維拉尼的論文集《古代近東歷史編撰學中的神話與政治》,就是這方面的成功代表。這本書雖然是論文集,卻具有非常完整的組織結構:以古代近東歷史編撰的反思為核心,側重以跨學科的方法研究古代近東的文明史。
馬里奧·利維拉尼(Mario Liverani)是意大利著名古代近東研究專家,羅馬大學教授,意大利西林學院院士。在這部論文集中,利維拉尼顯然帶著批判的眼光重新審視了過往古代近東的歷史材料和歷史編撰成果。他認為,古代近東歷史書寫中存在著對文獻材料采取表面化與比附的弊端,往往輕易將文獻檔案等材料視作信史來源而缺少深度分析。因此,利維拉尼注意采用人類學、文學、神話學等方法,重新解讀古代近東神話敘事,并將其具體分析,進而建構出不一樣的古代近東政治文化史。在閱讀中,讀者朋友一定要用心體會作者如何揭示了歷史學家究竟如何賦予古代文獻以意義。大致而言,作者認為,研究者必須分析編撰者的意識形態,即那些政治的、道德的、神學的觀念形態,才能更加接近文本和歷史真實的原初意圖;必須通過文學敘事、文學修辭的視角揭示文本表象之下的深層動機。該書為我們反思古代近東的歷史編撰問題帶來全新啟發,并有效地彌合了文學與歷史學科之間研究目的的對立。
國內和國際學界并不缺專攻近東考古、近東歷史或近東神話的優秀學者。然而,在利維拉尼的研究中,神話學、考古學、歷史學、文學被并置兼容,他成功告訴讀者近東古代的歷史編撰學與神話一樣,是一種敘事和修辭,是一種不斷受變化的政治需求、宗教和意識形態的形塑結果。這也是他帶給今日中國學界的最大啟迪所在。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