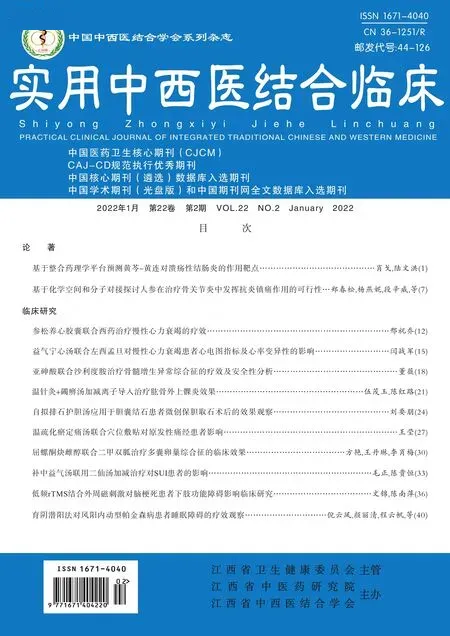溫疏化瘀定痛湯聯合穴位敷貼對原發性痛經患者影響
王瑩
(河南科技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婦科 洛陽 471003)
原發性痛經多于經期前或經期時發生,主要表現為下腹部伴痙攣性疼痛及腹脹感、四肢厥冷[1]。引發痛經常見因素為日常生活中不良的生活習慣、心理壓力、情緒不穩、內分泌失調等,是最常見的婦科疾病之一,嚴重影響女性生活質量及社會活動[2]。臨床治療主要以布洛芬鎮痛為主,可有效緩解患者疼痛,但無法根治,且長期服用會損傷神經系統[3]。中醫學將原發性痛經歸屬“經行腹痛”范疇,主要為寒氣稽留、氣血運行不暢所致,治療應溫經散寒、化瘀止痛[4]。溫疏化瘀定痛湯及穴位敷貼中所含配方均有溫經散寒、活血化瘀之功效。本研究分析溫疏化瘀定痛湯聯合穴位敷貼對原發性痛經患者的影響。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8年4月至2020年4月醫院收治的原發性痛經患者92例為研究對象,按入院順序分為觀察組和對照組,各46例。兩組一般資料對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本研究經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核批準。見表1。

表1 兩組一般資料比較(x±s)
1.2 入組標準 (1)診斷標準:西醫符合《婦產科學》[5]中原發性痛經相關診斷標準,婦女在經前及經后數小時出現下腹疼痛、伴腹瀉、惡心、嘔吐等癥狀,婦科檢查排除生殖系統器質性病變。中醫符合《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6]中相關辨證標準,主癥:小腹冷痛,得熱減痛;次癥:月經量少、經色紫黯、手足欠溫;舌、脈象:舌黯苔白,脈沉緊。(2)納入標準:符合上述西醫與中醫診斷標準;年齡16~35歲;月經周期28~35 d;自愿參加本研究,并簽署知情同意書;病程在6個月以上。(3)排除標準:因子宮腺肌癥導致繼發性痛經者;患嚴重惡性腫瘤、傳染病者;患嚴重心、腎、肝等重要臟器功能障礙者;備孕或妊娠期婦女;1周內服用過激素藥物或預防疼痛性藥物者。1.3 治療方法 對照組采用穴位敷貼:取子宮雙側、氣海、天樞雙側5個穴位,將細辛3 g、生附子6 g、延胡索9 g、川牛膝9 g上述藥物細研為粉,麥芽糖調成糊狀直接外敷,呈藥餅狀,厚度0.5 cm,直徑2 cm,每周2~3次,每次0.5 h,經期停止治療,同時采用TDP神燈照射于患者腹部上方30 cm處加熱,以患者感到溫熱為宜,照射時長為0.5 h,1個月為一個療程,共治療3個療程。觀察組采用溫疏化瘀定痛湯聯合穴位敷貼治療,穴位敷貼方法同對照組,溫疏化瘀定痛湯,方劑組成:當歸12 g、川芎12 g、五靈脂12 g、小茴香6 g、白術6 g、赤芍12 g、香附12 g、生姜3 g,水煎服,早晚2次服用。連續服用6 d,連續治療12周。
1.4 觀察指標 (1)臨床治療效果[7],痊愈:腹痛及癥狀完全消失,且連續3個月經周期無復發;顯效:腹痛及癥狀明顯減輕,3個月經周期未加重;有效:腹痛及癥狀較治療前減輕,但反復發作;無效:腹痛及癥狀均未好轉或加重。總有效=痊愈+顯效+有效。(2)中醫癥候積分[8]:治療前后對患者相關癥狀進行評估,包括小腹冷痛、月經量少、經色紫黯等,按照病情嚴重程度分為無癥狀、輕度、中度與重度等,分別計0、2、4、6分,得分越高,說明病情越嚴重。(3)疼痛程度:采用視覺模擬評分(VAS)[9]對兩組患者治療前后痛經程度進行評估,總分10分,0分為無疼痛,1~3分為輕微疼痛,4~6分為疼痛明顯,7~10分為疼痛劇烈。(4)激素水平:兩組患者治療前后采集清晨空腹靜脈血5 ml,離心后用免疫吸附法檢測患者雌激素(E2)、孕激素(P)、前列腺素E2(PGE2),試劑由上海恪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5)疼痛相關因子:治療前后采集清晨空腹靜脈血5 ml,離心后用,分別采用雙抗體夾心法、免疫吸附法檢測血漿β-內啡肽(β-EP)、內皮素(ET-1)、超敏C反應蛋白(hs-CRP),由中國上海藍基公司提供試劑盒。
1.5 統計學方法 本研究采用SPSS22.0統計學軟件分析處理數據,計量數據行正態性檢驗,符合正態分布數據以(x±s)表示,組間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以%表示,采用χ2檢驗。P<0.05表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臨床治療效果比較 觀察組臨床治療總有效率為95.65%,高于對照組的82.61%(P<0.05)。見表2。

表2 兩組臨床治療效果比較[例(%)]
2.2 兩組中醫癥候積分比較 治療前兩組中醫癥候積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觀察組中醫癥候積分低于對照組(P<0.05)。見表3。

表3 兩組中醫癥候積分比較(分,x±s)
2.3 兩組性激素水平比較 治療前兩組性激素水平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觀察組PGE2、P水平均高于對照組,E2水平低于對照組(P<0.05)。見表4。2.4 兩組疼痛相關因子水平比較 治療前兩組患者疼痛相關因子比較(P>0.05);治療后觀察組β-EP水平明顯高于對照組,ET-1、hs-CRP水平均明顯低于對照組(P<0.05)。見表5。

表4 兩組性激素水平比較(x±s)

表5 兩組疼痛相關因子水平比較(x±s)
2.5 兩組VAS評分比較 治療前兩組VAS評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觀察組VAS評分低于對照組(P<0.05)。見表6。

表6 兩組VAS評分比較(分,x±s)
3 討論
痛經可分為繼發性痛經與原發性痛經,其中繼發性痛經是指盆腔發生器質性病變所致,如子宮畸形、慢性盆腔炎、子宮肌瘤等,常在初潮數年后發生;原發性痛經多由子宮結構異常、神經-內分泌異常所致[3]。中醫根據原發性痛經癥狀與病因歸為“腹痛”范疇,認為寒濕凝滯、瘀血阻滯導致沖任、胞宮氣血阻滯,無法得之濡養,出現“不通則痛”,從而出現痛經。在《金匱要略》記錄中“婦人之病……經絡凝堅”[10]。認為病機與寒邪侵襲體內,陽氣被阻遏,經脈氣血不通暢,阻滯不通,瘀血內生,導致其惡性循環而發本病,因此在治療上需以溫經散寒、活血化瘀為治療原則。
本研究結果顯示,觀察組治療總有效率高于對照組,表明溫疏化瘀定痛湯聯合穴位敷貼對原發性痛經治療效果更好[11]。分析其原因為溫疏化瘀定痛湯,當歸味甘辛性溫,為君藥,歸肝、心、脾經,有極顯著的生血作用。川芎、五靈脂、小茴香為臣藥,川芎味甘辛性溫,歸肝、膽、心包經,具有活血行氣、祛風止痛之功效;五靈脂味甘辛性溫,歸肝經,具有活血散瘀之功效;小茴香味甘辛性溫,歸肝、腎經,具有行氣止痛、溫通筋脈之功效。白術、赤芍、香附、生姜均為佐藥,白術具有益氣健脾之功效,赤芍具有散瘀止痛之功效,香附具有調經止痛之功效,生姜具有溫胃降逆而散寒之功效。諸藥聯用可養血溫經、祛瘀散寒,通則不痛,臨床效果顯著。治療后觀察組中醫癥候積分、VAS評分均低于對照組,表明溫疏化瘀定痛湯聯合穴位敷貼可有效改善原發性痛經患者臨床癥狀及緩解疼痛。可能為溫疏化瘀定痛湯方五靈脂可行氣止痛、活血化瘀;現代醫學發現香附可以調節中樞神經系統功能,刺激雌激素分泌,抑制子宮收縮,鎮痛作用顯著。全方通過改善子宮血供,起到活血止痛之功效。此外,通過藥物穴位敷貼,將藥糊直接置于相應的穴位之上,可循經絡運行,到達臟腑經氣,充分發揮藥物功效,敷貼中細辛、生附子、延胡索、川牛膝等藥方成分均具有溫經散寒、理氣解郁、活血止痛的效果[12]。
原發性痛經一般無明顯器質性病變,與患者體內激素異常變化有關,PGE2能刺激子宮平滑肌收縮,當濃度降低時,子宮平滑肌會出現痙攣性收縮而致痛經[13];E2參與痛經的病理變化,能夠與P協同增強子宮收縮力,因此也與原發性痛經有著密切的關系,當子宮E2表達增高時,會使子宮平滑肌痙攣、缺血進而產生疼痛[14]。原發性痛經發病過程也是炎癥反應過程,發作時,患者體內炎癥介質、內皮素水平均呈異常增高狀態。臨床試驗證實[15],ET-1、hs-CRP均參與疾病發生發展,ET-1是子宮血管強烈收縮劑,是引起原發性痛經的重要因素;hs-CRP是炎癥介質反應標志物,其升高說明促炎性反應增加[16];β-EP是與疼痛有密切關系的神經激素,與疼痛發生及疼痛程度呈負相關[17]。本研究結果還顯示,治療后觀察組β-EP、hs-CRP、ET-1、E2、P、PGE2改善效果均優于對照組,說明溫疏化瘀定痛湯聯合穴位敷貼治療,能明顯改善調節患者性激素及疼痛相關因子水平,這是因為溫疏化瘀定痛湯內含香附與生姜,發揮了兩者的最大功效,生姜性溫,有助陽散寒功效,且為輔助藥物,能增強整體藥物的治療效果,調整患者體內激素水平;香附能夠雙向調節子宮平滑肌,內含類雌激素物質,通過松弛子宮平滑肌調節局部血流量,改變機體血液流變學,起到解熱鎮痛、抑菌抗炎的作用。
綜上所述,溫疏化瘀定痛湯聯合穴位敷貼治療原發性痛經,有利于提高臨床療效,緩解患者痛經程度,降低中醫癥候積分,調節患者性激素水平及疼痛相關因子水平,值得臨床推廣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