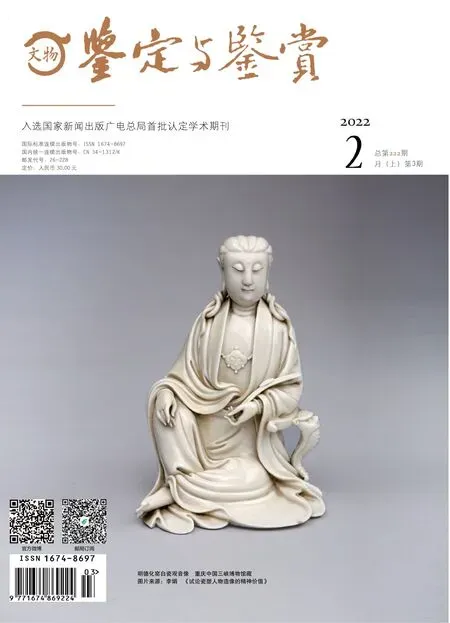元代“四愛”題材繪畫研究
李優鑫


摘 要:元代虞集在《四愛題詠序》中指出“四愛”為“陶淵明愛菊,周敦頤愛蓮,林逋愛梅,黃庭堅愛蘭”。作者此文以“四愛”文化為討論基點,對元代“四愛”題材的出現與發展、內容和文化內涵以及元代具有代表性的“四愛”題材繪畫作品進行研究,闡述“四愛”題材繪畫作品在元代輕視南方士人的背景下蓬勃發展,分析該題材反映出的內涵與意蘊,描述元代文人畫風尚。
關鍵詞:元代;“四愛”繪畫;文人畫
DOI:10.20005/j.cnki.issn.1674-8697.2022.03.006
1 “四愛”題材內容概述
關于“四愛”的說法有兩種:其一是根據元虞集的《四愛題詠序》,將“陶淵明愛菊、周敦頤愛蓮、林逋愛梅、黃庭堅愛蘭”稱為“四愛”;其二是根據歷史文獻以及元明清三代的畫家作品,最終在《中國大百科全書·文物與博物館卷》書中詞條“元代青花瓷器”里,把“王羲之愛鵝、陶淵明愛菊、周敦頤愛蓮、林逋愛梅”定為“四愛”。而對于其他說法,如蘇東坡愛硯、米芾愛石、李白愛酒等,雖然歷史上確有其事,但在繪畫作品中極少有表現,除個別現代作品如北京牙雕作品《四愛》表現“陶淵明愛菊、王羲之愛鵝、蘇東坡愛硯、米芾愛石”這種說法外,缺乏歷史依據和其他作品佐證。
關于陶淵明愛菊的詩和繪畫作品很多,董源、馬遠、錢選、董其昌、石濤、吳昌碩等人都畫過關于陶淵明愛菊的作品。史籍上有這樣一段對王羲之愛鵝的描述:性好鵝……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舉群相送耳。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甚以為樂。”①這段描述可見王羲之對鵝的喜愛。黃庭堅曾說:“蘭之香蓋一國,則曰國香。”他年少從師孫覺,孫家有女聰慧賢淑,擅繡蘭花,倆人識曲知音,蘭結伉儷。中年貶居涪州時,在寓所東邊植蘭,西邊樹蕙,終日以蘭、蕙為伴,“讀書、賦詩、蒔蘭樹蕙”②。林逋愛梅、愛鶴,所以有“梅妻鶴子”這一說法,也留下“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斷魂”的名句。“暗香”“霜禽”分別指代梅與鶴。至于周敦頤“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此處不再贅述。這四位都是立德立言的君子大儒和隱逸高士,他們的風尚雅趣是后世文人士大夫推崇和模仿的對象,后人借他們的事跡和各自所愛之物表達自己清高、隱逸的情懷與追求。
元代《皇元風雅·后集》卷四中收錄了《四愛題詠》,在這一篇文章中,元人首次明確地提出了“四愛”這一說法—“所謂四愛者:陶淵明愛菊、周茂叔愛蓮,又附益以林逋仙愛梅,黃魯直之愛蘭者也”,葉凱翁在遷居江西樂平后,將自己住所命名為“四愛堂”,也證明“四愛”在元朝興起并被世人接受。湖北省博物館館藏元青花“四愛圖”梅瓶(圖1)和武漢市博物館館藏傳世元青花“四愛圖”梅瓶是極少數將“四愛”中的內容全部表現出來的作品③。
2 元代文人畫中的“四愛”
元代是“四愛”文化的育成期,也是“四愛”題材繪畫的第一個高峰期。現存《四愛題詠》的詩文中多有“君子、隱逸、遠世俗、絕世累”等詞匯。
元朝早期的畫家劉貫道曾在《紈扇六幀冊》中畫有一幅《林和靖灌梅圖》,內容取材于“四愛”中的林逋愛梅,圖中林逋立于松下,后有婦人坐在亭中,侍童斜首回望,手上端著灌壺,向生長在假山石后的梅樹潑水。整個畫面細膩豐滿,人物也生動傳神,“畫人物眉睫鼻孔皆動,真神筆也”。六幀冊除這幅《林和靖灌梅圖》外,其余幾幅多與政治人物有關,如《韓熙載夜宴》《李景游醉歸》等。④
趙孟頫畫有一幅與“四愛”中陶淵明愛菊有關的作品《陶淵明賞菊圖》,圖中陶淵明席地而坐,頭戴綸巾,肩披茅蓋,空白紙卷攤開放在兩膝蓋上,腳邊放有杯盞與一盆菊花,童子持酒而立,畫上方有趙孟頫本人題詩“解帶歸來鬢未華,首巾蕭散勝烏紗。緣知榮辱都忘卻,畫把閑情付菊花”。趙孟頫作為前宋宗室仕元,內心苦悶壓抑。魯迅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酒之關系》一文中評價陶淵明:“陶潛總不能超于塵世,而且于朝政還是留心……”這與趙孟頫的心境極為符合,兩人內心都充滿無可奈何,陶潛題材也成為他繪畫作品中的一大類。
錢選和趙孟頫以及其他六位畫家被世人稱為“吳興八俊”,錢選與趙孟頫不同的是他一生都不為元朝服務,在得知趙孟頫北上做官之后就和他斷絕了來往,潛心作畫賦詩。“四愛”中的陶淵明愛菊、王羲之愛鵝、林逋愛梅,他都畫過。《王羲之觀鵝圖》(圖2)是取自“王羲之愛鵝”的故事,茂林修竹間有一亭,羲之立于亭中,注視水面上的兩只鵝。畫面左上方有錢選的題記和印章。在這幅畫中我們其實可以看出業余文人畫家引領元代文人畫發展的蛛絲馬跡,與職業畫家劉貫道和趙孟頫的畫中人物相比,這幅作品在寫實性上“遜色”了不少,人物的五官表情寥寥數筆就勾畫完成,鵝的刻畫也有些板拙,亭子的屋頂向后延伸顯得突兀,在畫面中并不和諧。
在錢選的另外一幅“四愛”題材繪畫作品《西湖吟趣圖》中,這樣的風格表現就更加明顯了。林逋愛梅是這幅作品的中心思想,畫上林逋伏案遠觀梅花,神情專注,若有所思。案旁小童正手腳并用地烤火,一只白鶴棲于小童身后。二人和仙鶴的目光都似乎集中在遠處的梅樹上。這幅畫人物的刻畫更加簡練,愈發不加修飾,與上述所有作品不同的是這幅畫在卷首有字數較多的題跋,卷尾有錢選自題詩文“粲粲梅花冰玉姿,一童一鶴夜相隨。月香水影驚人句,正是沉吟入思時”,詩中的“月香水影驚人句”是指林逋《山園小梅》中的“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一句。
“周敦頤愛蓮”這一題材在元代屬于較為流行性的題材,但是傳世的作品并不多。現藏于遼寧省博物館的《蓮舟新月圖》是其中最為有名的一幅,傳言其為南宋趙伯駒的作品,后證實為元代作品,其作者已不可考。畫中周敦頤與友人泛舟在蓮葉深處,江渚之上細風拂柳,左上方寫有題記。這幅畫設青綠色,人物和景色用筆精細,色彩清麗,筆致清勁,明顯受唐代人物畫尤其是道釋人物畫和青綠山水的影響,但是人物和景色的描繪卻不像唐宋那樣復雜具體,很明顯融入了個人風格,將這幅作品和錢選的《王羲之觀鵝圖》對比,會發現它們在風格上有很多相似之處,尚意之氣蓋過了“尚形”,繪畫作品的故事性加強,雖然也有設色,但摒棄了南宋的絢爛,作品中藝術形象也重精神氣質而輕形貌,元代文人繪畫發展到此,這些已經成為它的總的特征。gzslib202204051210王冕畫梅在元代最負盛名,他的《南枝早春圖》是一幅與“四愛”中“林逋愛梅”有關的繪畫,畫中墨梅老干新枝,盡顯勁峭冷香、豐韻傲骨,以“飛白法”畫枝干,兼有書法筆意,運筆風神峭拔,挺勁瀟灑,自下而上,一氣呵成。畫粗干勁健挺拔,畫細梢又如鐵鞭鶴。王冕一改北宋揚咎之等畫家的畫梅之法,以枝多花繁為一大特色,但繁而不亂,疏密有序,圈花點蕊,別出新意。這幅作品雖然題材選自“林逋愛梅”,但是畫中并未出現林逋的形象,而是通過畫卷一邊的詩交代出來的—“和靖門前雪作堆,多年積得滿身苔。疏花個個團冰玉,羌笛吹他不下來”。詩文和圖畫的結合使這幅畫的象征意義遠遠超過裝飾效果。
和《南枝早春圖》這幅畫類似的有元末僧人畫家普明的《光風轉蕙圖》,這幅圖取材于“四愛”題材中的“黃庭堅愛蘭”,畫中并未出現黃庭堅的形象,但作者在圖上寫下了黃庭堅詠蘭的詩句“采蘭秋蓬深,汲井短綆凍”⑤。
3 從“四愛”繪畫管窺元文人畫家意趣
元朝歧視南宋遺民和文人儒生,文人不得志,或做小吏、或干脆歸隱。中期以后各地反元勢力接踵而起,國家再次陷入不安定的境地,文人但求自保,歸隱幾乎成了唯一的途徑。“藝術起源于求共鳴”⑥,不論陶淵明、林逋這樣的隱士,還是王羲之、周敦頤、黃庭堅這樣人生路并不平坦的大賢,元代文人都能夠從他們身上找到符合自己的特點,錢選將自己和陶淵明相比,作為南宋遺民的他終身隱居山林,創作了不少陶淵明題材的繪畫,如《柴桑翁像》《歸去來辭圖》《扶醉圖》等。王冕也把林逋作為自己的楷模,他被認為是繼林逋之后愛梅成癖的第二人,在他的《墨梅》詩中用“不要人夸顏色好,只留清香滿乾坤”來詠梅,他與妻兒隱居山林,自稱“梅花屋主”,并在墻上寫下“轉身西泠隔煙霧,欲問逋仙杳無所”,“逋仙”就是林逋。隱士文化和隱士題材的繪畫在每個朝代都有,但元朝是其全盛期,“四愛”這一文化的形成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趙孟頫提倡取法北宋以上的傳統,主張文人畫應“士氣”“隸體”⑦,從蘇軾、米芾風格中學習筆墨和尚意之風是元代文人畫的一種風尚。而王冕《南枝早春圖》中梅花樹干的刻畫吸取董源披麻皴畫樹木主干的方法⑧。即使景致不多,林逋歸隱后賞梅閑適愉悅依然撲面而來,寫意的效果明顯超過了摹寫刻畫的裝飾效果。
何澄的《歸莊圖》、錢選的《歸去來辭圖》等都是對“董巨”樣式和風格的發揚與創新。若把北宋畫家李公麟的《陶淵明歸隱圖》和趙孟頫《陶淵明賞菊圖》中的陶淵明進行對比,會發現在線描手法上比較相似。另外趙孟頫提出“作畫貴有古意”的以詩入畫,李公麟這幅畫以陶淵明的名篇作畫,趣味相似,都可以看出元代畫家有意選取南宋以前的風格來繼承發揚,繼承的是董巨的筆法、蘇、米的意氣,發揚的是蘊含自己“趙體”書法意趣的繪畫風格。
南宋畫家馬遠的《王羲之玩鵝圖》與錢選的《王羲之觀鵝圖》同屬“王羲之愛鵝”這一題材,但后者在人物刻畫、畫面布局方面都更舒展,作品的文學性和寫意性勝于馬遠作品。
元代的文人畫家取法自唐至宋諸家風格,畫中江南景象、詩文和個人內心情感為主要的表達對象,完成文學性極高的作品。賢臣帝王畫在元朝走向沒落,文人畫家們不再需要畫這樣的題材來激勵自身做官,教化世人報國,畫隱士和江南風景才是他們抒發心情的方式,繪畫作品的教化作用便越來越小。同時元代統治階級和貴族階級藝術修養普遍不高,元代文人畫家不受重視和干涉,他們創作和取材的自由性得到了保障,可引發“美感”的萬物幾乎均可入畫。
4 結語
“四愛”文化在元代形成,并成為一種流行的繪畫題材,學界的兩種主流看法就是對“四愛”內容的梳理。元代“四愛”題材繪畫不是把相關故事畫出來教化世人,而是通過它們自娛,表達自己內心情感,即對隱逸生活的向往,對國破家亡的無奈,這和南宋隱逸題材繪畫體現的畫家樂趣和向往自由賞玩的閑適是截然不同的。通過對元代“四愛”繪畫的描述,我們得出了元代文人畫風尚的獨特內容:首先,元代文人畫繼承南宋前的傳統,同時加入新意。其次,詩、書、畫的有機結合以及“畫有古意”的提倡,使元代文人畫的文學性和趣味性達到了巔峰,是中國畫的一次創造性發展。再次,元代文人畫突破并摒棄了南宋求工求似的院體“作家氣”和濃墨重彩,將“形”放在了“神”之后,主張“以神求貌”“以逸為上”,重視畫家主觀意興和情感的抒發。“四愛”文化的形成,也增加了中國畫題材選擇的廣泛性。
注釋
①房玄齡.晉書:王羲之傳[M].北京:中華書局,1996:443.
②黃寶華.黃庭堅評傳[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7.
③崔鵬,周浩.元青花四愛圖梅瓶紋飾研究[J].江漢考古,2016(3):95-101.
④陳文璟.元代繪畫十講[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26.
⑤引自黃庭堅《山谷集中·次韻吳宣義三徑懷友》。
⑥吳冠中.文心獨白[M].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6:202.
⑦李鑄晉.鵲華秋色:趙孟頫的生平與畫藝[M].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