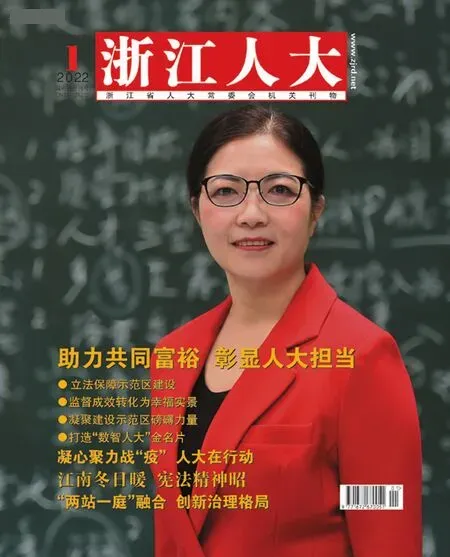“兩站一庭”融合 創新治理格局
施紫楠

湖州市南潯區在浙江范圍內首次嘗試“兩站一庭”村級治理模式,這是對新時代“楓橋經驗”的一次實踐探索。
據悉,該模式由社會治理聯動工作站和人大代表聯絡站衍生發展而來,即在“兩站”的基礎上融入“共享法庭”,旨在以一體化的服務模式打通基層治理服務的“最后一公里”,形成多部門聯動的“四治融合”基層治理新格局。
日前,浙江省湖州市南潯區東遷街道創新利用“兩站一庭”治理模式成功化解一起涉及人數64人、金額195萬元的欠薪糾紛。至此,這場持續11年之久的“揪薪拉鋸戰”落下帷幕。
多方聯動? 矛盾不出村
2021年4月份,東遷街道潯北社會治理聯動工作站收到同心村村民小方的一封感謝信:“本來只是抱著試試看的心理來工作站求助,沒想到在調解員的幫助下,不到一個禮拜就解決了這個事情,這筆補助金是我們全家的救命金。”
2020年12月,小方的父親老方上班過程中突發中風,后經搶救脫離危險,但高額的醫藥費壓得全家喘不過氣來。小方及其家人多次上門要求公司給予相應賠償卻徒勞無功,便找到了家門口的工作站尋求幫助。
調解員陳平新組織雙方談判,歷經多天的“拉鋸戰”,老方獲得了5萬元的賠償補助金。
有著十幾年村務工作經驗的陳平新,是當地頗有威望與人緣的鄉賢。隨著基層治理工作的日趨精細化,他結合自身經驗建立“平心調解工作室”。
“經常想一想老百姓最盼望什么、關心什么、怨恨什么,要從老百姓不幸福、不快樂、不滿意的地方入手。”這是陳平新掛在嘴邊的話。據悉,工作室成立1個月就成功化解民眾反映的各類問題58起,不到1年就調處矛盾糾紛238起。
人大代表駐站? 為民解憂
在一些進展較慢的案件中,陳平新發現“單打獨斗”的調解方式效率低,也容易造成案件遲滯不前。當人大代表聯絡站完成和社會治理聯動工作站的融合后,事情發生了轉機。
前段時間,英雄村村民老徐因一筆“陳年舊賬”找上了陳平新。2019年,該村在開展美麗鄉村建設時,因土地流轉補償金額與老徐發生分歧。案件時間久遠,雙方各執一詞,加上缺乏信任感,陳平新在雙方面紅耳赤的爭吵中犯了難。
“問題還沒解決,雙方情緒又很激動,為了避免矛盾的進一步激化,我想到了老吳。”陳平新口中的“老吳”,便是當地的人大代表吳國平。
由鄉里鄉親選舉出來的人大代表吳國平熟悉群眾和基層工作情況,更容易獲得當事雙方的信任。在這起案件中,吳國平將人大代表熟悉民情、反映民意的獨特優勢發揮出來。
“但是,土地流轉補償糾紛,涉及很多法律法規,我們又不太懂。”“不怕,我們還有‘王牌’沈律師。”沈琪勤是民盟南潯區總支副主委、浙江理直律師事務所律師、湖州市人大代表,她也是老百姓的學法解憂名師。
最后,雙方在陳平新、吳國平的勸解下,以及沈琪勤的釋法說理中,短短幾天內便握手言和,簽下了調解協議書。“為此,我和老陳還收到了一面‘為民所急,為民解憂’的錦旗,可把我樂壞了。”談及該案件,吳國平很是自豪。
“兩站一庭”構建基層治理格局
2021年9月,南潯區人民法院邱劍鋒庭長收到兩起同一被告的案件,查詢發現張某作為被告的案件從2014年至今已有14起,最長債權前后達11年之久。同時,調解員沈俊杰也找到邱劍鋒咨詢近期糾紛中的法律問題,糾紛的一方當事人也是張某。
在該起群體性債務糾紛中,由于債務人張某去向不明、名下無任何財產,有人因1萬元貨款向法院起訴,有人因3萬元裝修款到社會治理聯動工作站申請調解,還有人因10萬元勞務費用向當地人大代表反映。
“案件持續時間長,涉及人員眾多,民眾反映強烈。”人大代表莫國祥意識到,該起矛盾化解必須要有全程的法律服務來支撐。于是,他向人民法院申請了“共享法庭”的介入。
社情民意的實際需要促成了“兩站一庭”的深度融合,社會治理聯動工作站作為“調解為主”的支點,“共享法庭”作為“訴訟斷后”的重點,形成了“三方會談”。
前后歷時三個月,該群體性糾紛最終得到妥善化解。
“集社會治理聯動工作站精細化排摸能力、人大代表聯絡站民聲暢通渠道、共享法庭高效司法服務之所長,‘兩站一庭’以此來完善村一級關于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的共融機制,營造出同頻共振的治理氛圍。”東遷街道辦事處副主任朱建國說。
眼下,“兩站一庭”的基層治理新模式迅速在南潯區落地生根,讓基層在社會治理現代化的路上有了取之不盡的創新動力,也將打造出更多智慧、高效、可持續的社會治理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