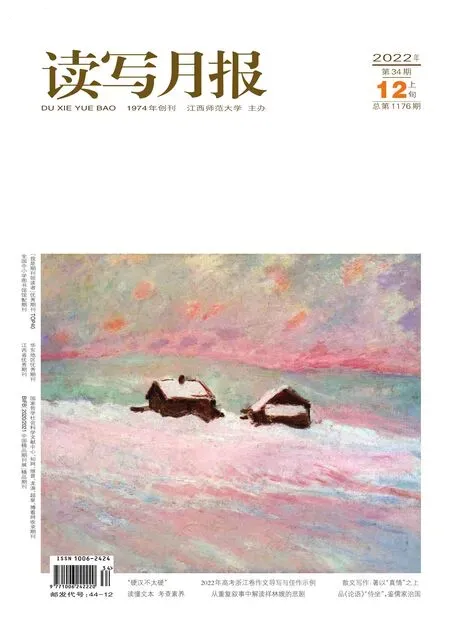“硬漢不太硬”:譜系溯源與文本還原視域下的《老人與海》
梅振鐸
截至目前,國內對海明威《老人與海》的解讀大多局限在“硬漢的抗爭美學”“人的靈魂與英雄的尊嚴”“尚力與永不言敗的精神”“失敗的強者與人生抉擇”等方面,即便出現新的爭論,也很少超出上述議題的范疇。這些解讀的批評原點,往往離不開海明威在《午后之死》中提及的“冰山原則”。筆者認為,“冰山原則”作為海明威“極簡主義”敘事風格的集中體現,固然是打開《老人與海》的一把密鑰;但切入文本不同的“審美假定”,會使論者對“露在水面上的八分之一”以及“藏在水面下的八分之七”產生截然不同的審美解讀。有鑒于此,筆者做了一個大膽的“闡釋假定”:《老人與海》或許隱藏著尚未被眾多論者關注到的微觀意旨——“硬漢”也許是被懸浮在“冰山”之上的“原型表象”,“不太硬”才是潛藏在“冰山”之下的“形象內核”,“硬漢不太硬”抑或就是“冰山原則”背后隱喻的一種藝術辯證法。
一、“硬漢”的譜系溯源:“冰山”之上的原型表象
桑地亞哥的“硬漢”形象濫觴于“海明威式英雄”的塑造,是文本懸浮于“冰山”之上的原型表象。顯然,老人“打不敗的精神”潛藏著人在“自然絕對力量”面前的激越抗爭;同時,老人超拔的勇氣和強力的意志是讀者常常能觸摸到的“冰山露在水面上的八分之一”,故而成為悲劇英雄最好的哲學注腳。如果僅僅停留在這個既定“審美事實”的層面,那么就無法觸碰到老人這位終極生存者背后濃重的西方文化淵藪。卡洛斯?貝克指出,在文本的世界里,真正把海明威與“硬漢”嵌套在一起的,是西方文化的精神內核——“英雄的神話譜系”[1]。彌漫在《老人與海》字里行間的神話原型,或許可以推開重讀桑地亞哥的另一扇窗。
桑地亞哥的“硬漢”原型,指向古希臘文化的神靈與天空。老人作為一個長期被艱難與不幸裹挾的老漁夫,因遭受衰老和命運的捉弄,連續八十四天一條魚也沒捕到。所以在周遭世界里,他的能力成了問題,生存成了問題,職業成了問題,甚至連自我的價值和尊嚴也成了問題。當他歷盡艱辛捕獲大馬林魚后,這場冒險似乎配得上老人付出的尊嚴和代價。事實上,老人這場暫時勝利的冒險的審美原型恰好見諸《荷馬史詩》的《奧德修斯》。詩人荷馬把奧德修斯海上十年的歷險,以時空倒置的方式放在他臨到家前四十多天的時間里來描述。奧德修斯憑借個體的終極生存意念,在茫茫大海中與未知的命運進行不間斷的抗爭:戰勝圓目巨人、智斗塞壬海妖、闖關卡律布狄斯……在原型視角的燭照下,奧德修斯歷經終極力量的重重考驗和桑地亞哥克服自身極限捕獲碩大無比的馬林魚,是一種敘事藝術上的“異質同構”:它們共同支撐起“人與命運”“人與自然”的抗爭母題;無論是“奧德修斯式”的歷險環境,還是“桑地亞哥式”的斗爭方式,都把“個體超越現實的桎梏”上升到苦難哲學本體論的高度。
“硬漢”原型的神話圖騰,寄寓在桑地亞哥試圖用小船把大馬林魚從蒼茫的大海拉回港的“受難歷程”中。這是一場驚心動魄的“人魚大戰”:攻擊老人的鯊魚數量越來越多,搶奪大馬林魚的鯊魚的種類越來越兇殘,攻擊間隔的時間越來越短,而老人打擊鯊魚的作戰工具越來越少——他一次又一次被殘酷的攻擊打出命運的常軌,最終在自然的極限困境面前失去了自己捍衛尊嚴的戰利品“大馬林魚”。實際上,這種證明“強大的阻撓”與“自我價值實現”的沖突原型,源于古希臘神話西西弗斯所推的無休止的滾石。西西弗斯因藐視俄林波斯諸神而被懲罰不斷重復、永無休止地做同一件事:把巨石推上山頂,但每當將要到頂時巨石就會脫落滾下。這種既荒誕無效又孤獨無望的勞作,被哲學家加繆視為最嚴厲卻最美妙的懲罰,因為西西弗斯在絕望中發現了新的意義:他與巨石的較量所碰撞出來的堅毅力量,像“戰斗的舞蹈”一樣優美[2]。當西西弗斯不再因為荒謬而抱怨,他就成了“神話時代的桑地亞哥”。只不過桑地亞哥面對的“諸神”變成了大海與鯊魚群,他同樣無法避免無休無止的搏斗,受到難以名狀的非人折磨。所以,桑地亞哥用努力抗爭去捍衛自我的尊嚴時,他就比“西西弗斯的巨石”更強大,硬是從一種沒有效果的事業中尋找出存在的價值。
“硬漢”原型的譜系溯源,更脫離不了基督教的自然宗教圖景。在西班牙語的言語系統中,“桑地亞哥”指涉“救主”和“受難者”。一方面,基督教所宣揚的耶穌受難環境跟老人所處的苦難環境高度吻合,老人苦行僧般的生命歷程幾乎再現了基督受難的痛苦經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桑地亞哥本人并不信仰宗教,不過當他的肉身被苦難壓得異常沉重且超越自身極限的時候,他以圣徒彼得的名義,用虔誠的宗教儀式多次向上帝禱告,祈求獲得挺下去的力量。另一方面,桑地亞哥在捕獲大馬林魚時,充滿了溢美之詞,甚至特意指出它的眼睛“像宗教隊伍中圣徒塑像的眼睛”。有鑒于此,老人出海捕魚儼然成為一場“朝圣”的精神之旅:鯊魚的攻擊就成了“受難者”的必須,老人的煎熬就好比向“拯救者”的贖罪。所以,海明威對桑地亞哥形象的建構鮮明地體現了兩面性:“受難者桑地亞哥”是對“拯救者耶穌”的一種精神皈依,“硬漢桑地亞哥”是對“受難者耶穌”的價值投影。實際上,老人的宗教原型已經囊括一種源于崇高的悲劇美,即分有上帝形象的桑地亞哥能夠承受并超越一切現世痛苦里的孤獨、失敗甚至死亡,卻永遠也不會衰敗。
基于上述對《老人與海》“硬漢”形象的文化譜系溯源,不難看出老人“硬漢神話原型”潛藏的“本相”:宗教式“孤勇者”的苦難生存哲學。這種哲學氤氳的西方文化內核,正如美國藝術史家伯納德·貝瑞孫所言,指向“老人身上的上帝形象”,凸顯“人作為分有神性的存在擁有超越苦難的永恒精神”[3]。
二、“不太硬”的文本還原:“冰山”之下的形象內核
宗教式“孤勇者”桑地亞哥的身上所寄寓的苦難生存哲學,固然可以解釋“硬漢”顯露于西方文化“冰山”之上的“原型表象”。但是,在固有闡釋的視域之內,苦難生存哲學的另一面往往容易被忽略,即老人作為弱小的個體在無限重復的苦難面前同樣“畏葸不前”:懷揣極端懷疑的本能恐懼,不愿直面絕對困境的退縮,不斷陷入否定自我的消極,無法掌握命運的深層焦慮……這些人性的本能,顯然不是“硬漢”的“硬”可以完全解釋的。
桑地亞哥的“不太硬”,始見于他作為“獨力的個體”在絕對困境面前的猶豫退縮。人本能的心理體驗、精神境況最能反映內在自我在現實面前的純粹狀態。面對大馬林魚被兇殘貪婪的鯊魚不斷蠶食的窘況,桑地亞哥一度陷入“夢的囈語”中:
1.看見鯊魚越來越近的時候,他向那條死了的大魚望了一眼。他想:這也許是一場夢。
2.“它們準是把它吃掉四分之一了,而且吃的凈是好肉。”他大聲說,“我真盼望這是一場夢,但愿我根本沒有把它釣上來。”
3.他想:能夠撐下去就太好啦。這要是一場夢多好,但愿我沒有釣到這條魚,仍然獨自躺在床上的報紙上面。[4]
從“也許”“真盼望”到“要是”,桑地亞哥的意識流不斷陷進“一場夢”的反復迷惘中。此時,他的自我獨白透露出其隱秘的心理位格:不愿直面外在的殘酷,借助夢來有意回避現實。因為“夢”作為潛意識最直接的表征,它暗示著老人跟“普通人的性情”并無二致——在絕對強力的壓迫下,他本能地退回到事件發生的現實之外。此時的老人嘗試“自己跟自己”對話,通過反復激勵自我,試圖把自己從怯懦中拉回來,以緩解他對戰利品不斷喪失、外在世界難以把握的深深焦慮。這就表明:老人作為終極生存者的“硬”,并不是一種“天性的必然”,反而更像一種“挺住的選擇”。他并沒有特別的辦法完全超越主體的自我弱點,也沒有辦法在外在環境的極限進逼下完全坦然面對艱難和不幸。
桑地亞哥的“不太硬”,彰顯于他釋放內心深處的孤獨壓抑時“搖擺式的自我否定”。老人在捕獲到大馬林魚時,內心充滿了把自己作為萬物尺度的激情。但當鯊魚群一直糾纏自己、折磨自己時,他開始將自己放在“懷疑的天平上”,他的自我由“最初的堅定”滑向“反復的搖擺”:
“別想啦,老家伙,”他又放開嗓子說,“還是把船朝這條航線上開去,有了事兒就擔當下來。”不過還是得琢磨琢磨,他想。可是我一定要想,因為我剩下的只有想想了。除了那個,我還要想想壘球。……他想:不抱著希望真蠢。此外我還覺得這樣做是一樁罪過,他想:別想罪過了吧。不想罪過,事情已經夠多啦,何況我也不懂得這種事。……“你想得太多啦,老頭兒。”他高聲說。[5]
當老人開始重新追問這次出海捕魚的必要性后,他就不斷陷于“想太多”和“別想啦”的自我矛盾中。老人的內心不再堅實,雖然他不斷安慰自己要擔當,但擔當的合理性卻被隱隱的罪過心理沖刷,因而在保衛大馬林魚和痛擊鯊魚群兩個極端中不斷搖擺。老人變成了自己的“懷疑論者”:反復質問自我、否定自我、重估自我,心中堅定的價值尺度開始動搖。可見,“失望者”和“希望者”這種“二律背反”的角色已經深入到老人意識的深處。這個“不太硬”的老人,恰恰才是“海明威式的英雄審美”隱秘卻動人的地方。這樣的桑地亞哥才是一個活潑潑的人,才是一個“既見得天地、又見得眾生”的人。因此,老人身上的堅韌超拔,更多的是他在不間斷的自我否定中一次次找回自我的結果。
桑地亞哥的“不太硬”,還表現在他放下優雅風度對魚“躬親自省”的“應激獨白”里。老人在捕獲到大馬林魚時,毫不掩飾自己對它的愛,甚至把它上升到力量美學和意志美學的高度。當大馬林魚被鯊魚咬住時,他將其看成“自己身受的一樣”,甚至希望自己沒有釣到它。可見,老人不僅在大馬林魚身上獲得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職業成就感,還直接維護了他作為漁夫的尊嚴。甚至在大馬林魚遭受群鯊的圍攻時,他脫口而出:
1.“魚啊,我不應該把船劃到這么遠的地方去,”他說,“既不是為了你,也不是為了我。我很不好受,魚啊。”
2.“你原來是條整魚。我過意不去的是我走得太遠,這把你和我都給毀啦。”[6]
這些“應激獨白”反映出桑地亞哥既有無法掌控大馬林魚前途與命運的矛盾與懊悔,也有對自己出海太遠的反省與批判——或許由于自己無節制與非理性的索取,遭到了來自大海群鯊、自然嚴厲的報復。憑借大馬林魚,他本可緩解經濟和生存的壓力,但現在一切都可能歸零。他與大馬林魚必須同時面對被追擊、被包圍的困窘,自覺聯結成“命運共同體”,以致他開始懺悔自己為什么要捕殺大馬林魚。可見,老人不但“不硬”,甚至還覺得殺大馬林魚和鯊魚都是自己的罪過:
我不懂得這種事,我也不怎么相信。把一條魚弄死也許是一樁罪過。我猜想一定是罪過,雖然我把魚弄死是為了養活自己也為了養活許多人。不過,那樣一來什么都是罪過了。不想罪過了吧。[7]
在桑地亞哥的潛意識里,殺戮本身有罪。只要被摧毀的是崇高、有力的生命,那么這種恥感就伴生于老人的世界觀里。這種對位思考,修改了人在自然面前的優先尺度,甚至消弭了罪惡有形的邊界:魚和人各為生存,在自然的法則面前不得不走向對立甚至成為生存的敵人。老人對作為敵人的“魚”,非但沒有半點“硬氣”,更為重要的是他承認了自己的有限——必須通過消滅敵對客體(魚)的肉身才能獲得更多的生存空間。面對這一情狀,他的內心滿是無可奈何,那份與“魚”惺惺相惜的“柔情”在無意識間肆意噴涌。
不難看到,桑地亞哥這個“硬漢”“不太硬”。只是老人在與自然世界的對抗中了悟“挺住意味著一切”,從而完成了自我救贖,成為自己的英雄。
三、“硬漢不太硬”:“冰山”背后隱喻的藝術辯證法
經過譜系溯源以及文本還原,桑地亞哥也許是海明威藝術世界里最富隱喻性的藝術形象。“冰山”之上的老人,是祛除西方文化蔭蔽的宗教式“孤勇者”;“冰山”之下的老人,是兼具人性本能弱點的“普通人”。或許,這個“硬漢不太硬”是海明威創作中最為隱秘卻富有傳奇色彩的藝術辯證關系,它為打開《老人與海》新的“審美之維”提供了一個微觀視角。
“硬漢”作為“孤勇式英雄”的審美形象,揭示了海明威藝術世界里“崇高美”的深刻性。桑地亞哥雖遭受失敗,但絕不屈從于命運,甚至淡然面對自己的一無所獲,對于失敗沒有一絲一毫的感傷。他用生命、靈魂、信仰的力量重新點燃了自己,成為自己的英雄,鑄就了一種決不妥協的“堅韌之美”。恰恰是這種“不幸”而“錯位的美”,最終成就了顯露在海明威藝術“冰山”之上的崇高與莊嚴。當然,這種源于古希臘偉大而靜穆的美學傳統,一直是西方藝術審美的主旋律:《復活》中的聶赫留朵夫,不屈從于自身的傲慢與偏見,毅然決然去拯救瑪絲洛娃墮落的靈魂而獲得自我良知的救贖,最終使兩人的靈魂獲得了“復活”;《百年孤獨》里,因為麗貝卡的到來,失眠癥、失憶癥襲擊了馬孔多全鎮的居民,但奧雷里亞諾不屈從于現實的枷鎖,最后闖出對抗失憶的生存之路;《大衛·科波菲爾》中的大衛,小小年紀就在謀生之路上不斷被歧視、被虐待,但他并沒有被不幸裹挾和打倒,最終因抗爭而獲得成長……而海明威筆下的桑地亞哥,只是旗幟鮮明地站在“大海”的“漁船”上,向崇高的美學傳統致敬。
“不太硬”作為“普通人突圍”的審美腳注,隱含著海明威藝術國度里“柔性美”的通兌性。面對人生的“至暗時刻”,桑地亞哥的內心也有恐懼、沮喪、擔憂和后悔;他深陷自我否定的泥淖,需要反復提醒自己摒棄消極、充滿希望;他充滿矛盾、時而謙卑,承認自己作為人的有限,卻仍敬畏自然其他生命的偉力。海明威并沒有刻意拔高老人的生命,只是把鮮活的生活根基與生命色調融入老人充滿寫實主義的“獨白系列”中,從而開拓出老人熔鑄普通人“柔性美”的藝術境界。這種藝術境界的本真源于“真實”,然而“真實”只有符合普遍人性的規律和普通讀者的期待視野時,藝術形象才具有“典型性”,才能引發相應的審美共通感。中西藝術之維在這一點上是共通的:《水滸傳》里打虎的武松,并非天生就是英雄,他喝醉后獨自上山過景陽岡,是為了不被店家嘲笑,打虎是一種近乎保存自己的本能;《西游記》里的孫悟空,同樣不是主動的秩序反抗者,他得道成仙后一直處于受欺騙、受歧視的狀態,大鬧天宮只是他對現存秩序表達不滿的自然反應;《紅樓夢》里“寶玉挨打”,賈政的做法也不能簡單地歸咎于所謂的“封建家長做派”:既要看到他因寶玉勾搭忠順親王的戲子琪官間接導致丫鬟金釧投井的怒火攻心,更要看到他面對大廈將傾的家族卻獨力難支、家門不繼的絕望與痛苦,或許這才是人之常情……類比桑地亞哥身上隱隱存在的“柔性美”,從側面揭開了“硬漢守望者”海明威的另一副藝術面孔。
“硬漢不太硬”,是《老人與海》這座藝術“冰山”背后藝術辯證法的統一。小說所呈現的“冰山風格”,既有“硬漢”桑地亞哥的生命歷險與體驗,也有“常人”桑地亞哥的本能書寫與重構。正如孫紹振先生對“海明威式藝術”所總結的那樣:“浮在表面的是人物平靜的動作和對話,而深邃的精神沉淀在敘述以下。”[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