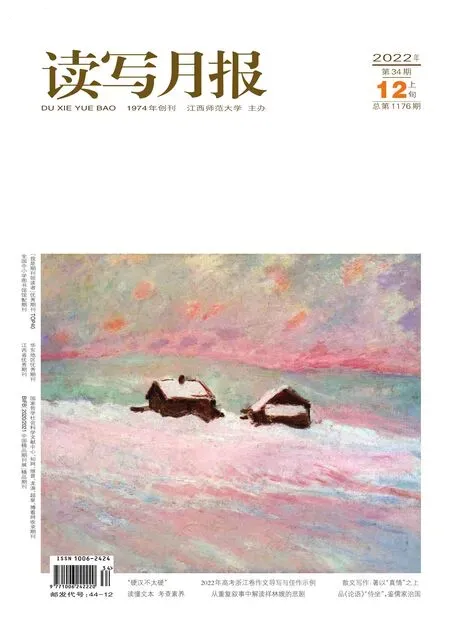從重復敘事中解讀祥林嫂的悲劇
陳海琳
丁玲說:“祥林嫂是非死不可的,同情她的人和冷酷的人、自私的人,是一樣把她往死地里趕,是一樣使她增加痛苦。”為什么所有人都一樣把祥林嫂往死地里趕?為什么所有人都一樣在增加她的精神痛苦?這似乎是一場共謀。細心的讀者會發現,《祝福》有大量重復性語句,魯迅這樣一流的小說家,他是不會寫毫無意義的重復句的,重復敘事中必有他的匠心。筆者試圖從重復敘事入手,來探尋祥林嫂的悲劇命運。
一、“畫眼睛”即畫命運
1.頭上扎著白頭繩,烏裙,藍夾襖,月白背心,年紀大約二十六七,臉色青黃,但兩頰卻還是紅的……但看她模樣還周正,手腳都壯大,又只是順著眼,不開一句口。
2.她仍然頭上扎著白頭繩,烏裙,藍夾襖,月白背心,臉色青黃,只是兩頰上已經消失了血色,順著眼,眼角上帶些淚痕,眼光也沒有先前那樣精神了。
3.五年前的花白的頭發,即今已經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臉上瘦削不堪,黃中帶黑,而且消盡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間或一輪,還可以表示她是一個活物。
對祥林嫂的命運,魯迅通過三次“畫眼睛”的肖像描寫做了最直觀的交代。魯迅把主要精力放在描寫兩頰和眼睛上,不變之中又有變化,三次形成縱向對比,可謂匠心獨運。魯迅先生說:“要極省儉的畫出一個人的特點,最好是畫他的眼睛。”眼睛是心靈的窗戶,“畫眼睛”手法可以讓讀者直接窺見人物的內心世界。
第一次描寫凝練精要地為我們呈現的是一個整潔樸素、溫順能干、對生活抱有希望的年輕婦女的形象。較第一次而言,第二次穿著未變,眼睛還是順著的,但兩頰由“紅的”變成沒有血色,眼角新添了淚痕,眼光沒有了精神。可以想象,再到魯鎮時,祥林嫂承受著喪夫失子的巨大悲痛,精神上受到了刺激。再對比第三處,兩頰的臉色已經由青黃變成了黃中帶黑,連之前的淚痕這樣悲哀的神色也消盡了,猶如枯燈,說明人物受到了精神摧殘,已經到了麻木無神的狀態。此處的眼睛刻畫最為精妙:麻木無神的臉上唯一能動的只有眼珠,眼珠偶爾轉動一下才能表示她還是個活物,祥林嫂已到了行將就木的絕境了。魯迅先生抓住眼睛進行描寫,從小處、細處、關鍵處為我們刻畫了祥林嫂一步步走向死亡的狀態,祥林嫂的命運走向通過“畫眼睛”手法被寫活了。
二、知識分子的逃避
1.無論如何,我明天決計要走了。
2.無論如何,我明天決計要走了。
小說中的“我”有多處心理描寫,雷同的一句話出現過兩次。第一處出現在“我”回到故鄉魯鎮后,發現故鄉的一切都沒有變——“年年如此,家家如此”。特別是觀察了四叔的書房后,“決計要走”的打算更堅定。四叔是個老監生,是封建禮教的捍衛者,書房中擺放著的都是理學家的書籍,貼的是與理學有關的對聯。封建學究式的書齋氛圍令“我”這個現代知識分子感到窒息,“我”這個“異己者”與停滯不前的“魯鎮社會”明顯是格格不入的。
第二處,“決計要走”是因為“我”前一天遇見了祥林嫂而產生了不安。她向“我”追問靈魂的事情,因為害怕擔責,“我”選擇用“說不清”等含糊的話來回答她,這無意中也許更增添了祥林嫂的精神痛苦。盡管“我”找了很多原因來自我寬慰,但還是免不了有種種不安和負疚感,所以“我”要走。過了一夜,不安之外又添了不祥的預感,在陰沉的雪天,“我”要走的心境達到了頂點。第二處的“決計要走”更深刻地表明“我”極度害怕祥林嫂的死牽扯到自身。錢理群先生分析說:“‘我’再次‘明天決計要走’,這再度離去就多少含有對家鄉現實所提出的生存困境的逃避性質。”
小說中的“我”是屬于同情祥林嫂的人,雖然“我”有善良的一面,但“我”的軟弱和無能更突出。因為一場對話,祥林嫂的故事與“我”的故事有了聯結。面對窮途末路的祥林嫂,“我”作為“昏睡中醒來的一員”,卻毫無救助的力量。唯一能做的就是保留最大的善意,用模糊中庸式的答案糊弄過去,以此尋求自己良心的安寧。當封建禮教張開吃人的血盆大口時,“我”想到的只有離開。小說中這兩句重復的話,深刻地代表了“我”這個現代知識分子的行為選擇——逃避!
三、四叔的默許
1.“可惡!然而……”
2.“可惡!”
3.“然而……”
四叔在小說中話語不多,出現更多的是“皺眉”這樣的神態描寫。這幾次的“皺眉”也很有嚼頭,四叔多次通過“皺眉”來發出管理家事的意見,很鮮活地塑造出專制、霸道的封建家長形象。
祥林嫂被衛老婆子和婆婆搶走后,四叔說了兩次“可惡、然而”,但都沒有講完整,魯迅留下了省略號讓讀者去思考。第一處的“可惡!然而……”讀者可能一下子還不太能捉摸到魯四老爺的心理。魯迅在第二、三處把“可惡”和“然而”分開來寫,讀者就能精準地捕捉到魯四老爺的內心了,簡單的幾個字的變換能看出魯迅文法的高妙。聯系魯四老爺與衛老婆子的對話可知,“可惡”主要是表達對衛老婆子的厭惡。衛老婆子作為中介商主要從事薦引女工的工作,從中牟利。但她又利欲熏心,勾結祥林嫂的婆婆合伙劫走祥林嫂,她“騎墻”的行為極其惡劣。況且這樣劫走仆人的行為會損傷魯家的臉面,所以四叔以“可惡”表達憤怒。最令人玩味的是最后的“然而……”。根據“然而”的轉折含義,我們大致可以判斷接下來的話應該是“不可惡的”或者說是“可以被理解的”,我們可以推斷出以下的可能:“可惡!然而祥林嫂理應被綁回去。”“可惡!然而祥林嫂走了更好。”“可惡!然而衛老婆子她們也沒什么錯。”這里的留白我們可以理解為四叔默許了衛老婆子她們的行為,并認為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在封建價值觀中,祥林嫂是屬于夫家的,族權可以任意處置她。在四叔看來,衛老婆子的行為合乎禮法,無可厚非。但四叔的默許間接地把祥林嫂逼向死地,讓祥林嫂遭遇更大的災難。
四、四嬸的嫌棄
1.“祥林嫂,你放著罷!我來擺。”四嬸慌忙的說。
2.“祥林嫂,你放著罷!我來拿。”四嬸又慌忙的說。
3.“你放著罷,祥林嫂!”四嬸慌忙大聲說。
四嬸是小說中比較善良的人,她愿意留下祥林嫂做女工,祥林嫂離開后還會偶爾提起她。祥林嫂講述阿毛去世的事情時,她的眼圈有些紅。毋庸置疑,四嬸的眼淚是真心同情祥林嫂的遭遇,她還重新接納了祥林嫂,讓她繼續在家里做女工。
祥林嫂的改嫁和再次喪夫被封建禮教視為“敗壞風俗”,違背了“從一而終”的傳統婚姻觀,因此她不再具有端福禮的資格。四嬸這三句話中,前面兩句先喊名字再說指令,態度上是比較溫和的,四嬸害怕祥林嫂碰祭祀的飯菜,所以著急地阻止她。最后一句換了語序,表達的效果卻有很大的不同。先喝令再喊名字,命令語氣更強烈,態度也更嚴厲激烈。第三次的斷喝讓祥林嫂明白即使捐了門檻也不會被寬恕,自己永遠不能被冷漠的社會接受。四嬸是和善的女人,誰會想到這句無意識的話卻是壓垮祥林嫂的最后一根稻草。軟刀子殺人不見血,這句話將祥林嫂推向了巨大的精神恐怖之中,從此她活得像小鼠,像木偶人。四嬸簡單的話語,很平靜也很日常,卻達到了吃人不留罪惡痕跡的效果。沒有恐怖感的恐怖,才是最令人窒息的恐怖,這才是魯迅先生的高明之處。
五、看客們的語言暴力
1.“我真傻,真的,我單知道下雪的時候野獸在山墺里沒有食吃……”
2.“我真傻,真的,我單知道雪天是野獸在深山里沒有食吃……”
3.“我真傻,真的,……”她開首說。“是的,你是單知道雪天野獸在深山里沒有食吃,才會到村里來的。”他們立即打斷她的話,走開去了。
阿毛被狼吃的文段出現了三次,祥林嫂不斷地跟別人講這段悲痛經歷,重復的訴說中隱含著祥林嫂內心難以釋懷的悲痛。第一處是祥林嫂重新回到四叔家,在堂前對四嬸說的話。“嗚咽,說不出成句的話來”,情感比較克制,畢竟自己和四嬸身份地位不同。第二處是祥林嫂在鎮上給大家講自己的故事,無所顧慮,悲傷的情緒就自然而然流露出來,“淌下眼淚、聲音嗚咽”的感情宣泄非常符合當時的語境。
細細品讀獨白內容,第二處的傾訴更加飽含感情,更接近祥林嫂真實的心理。“他是很聽話的孩子”比第一處“他是很聽話的”更細膩,更能體現出母親的憐愛。同樣,前文說阿毛“手上還緊緊的捏著那只小籃呢”,到了第二處在前面加上了“可憐”二字,那種難以抑制的喪子之痛被不動聲色地顯露出來。“我叫,‘阿毛!’沒有應”和“我叫阿毛,沒有應”,“阿毛!”前停頓了一下,這一聲呼喚還原了當時的場景,給現場聽眾一種在場感,仿佛阿毛還活著,反映了祥林嫂內心巨大的悲痛;第二處則是簡單的陳述,語氣比較平淡克制。“果然,他躺在草窠里”和“他果然躺在草窠里”也有區別,祥林嫂心里不愿意相信阿毛被狼叼走了,事實卻“果然”如此,突發的意外讓祥林嫂不得不面對兒子死去的痛苦現實。第一處將“果然”置前,起到強調的作用,語氣更加強烈,悲痛更沉重。
然而,祥林嫂不斷重復傾訴自己的慘痛經歷卻難換取別人的半點同情。第三處文段,看客們竟然拿祥林嫂的“臺詞”來堵住她的話頭,掐滅她傾訴的欲望,以此表達對她的極度厭煩。更可怕的是,當祥林嫂說:“唉唉,我們的阿毛如果還在,也就有這么大了。”看客們就會主動打趣道:“祥林嫂,你們的阿毛如果還在,不是也就有這么大了么?”人性最殘忍的地方莫過于在別人傷口處無情地搓弄,狼吃阿毛已經是人間慘劇了,然而更慘的是看客們吃祥林嫂。祥林嫂不知道,她在魯鎮唯一的存在價值就是充當看客們的“玩物”,而一旦被看得厭倦了,她的故事成了渣滓,那么她就被剝奪了存在的權利——這是祥林嫂不自知的最大悲哀!
魯迅說:“群眾——尤其是中國的——永遠是戲劇的看客。”這些百無聊賴的看客們是中國封建社會最底層的百姓,他們麻木無知、冷酷無情,通過咀嚼賞鑒別人的痛苦作為無聊生活的調味品,以此獲得精神上的滿足,以此顯示自己的優越。可悲的是,沒有人意識到這是對祥林嫂生命的摧殘!
可以說,祥林嫂的死亡表面上沒有劊子手,但其實是一場集體無意識的謀殺,其中“我”的自私與軟弱,四叔的冷酷和默許,四嬸的嫌棄和呵斥,還有看客們的嘲諷和厭棄等等,小說中所有的人都是制造殘暴的社會秩序和文化傳統的參與者。魯迅先生通過言語、神態、心理、行動方面的重復敘事,不變之處又隱含變化,以此揭露祥林嫂悲劇命運的根源。重復敘事手法,于細微之處寓有深邃的意蘊,增添了小說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