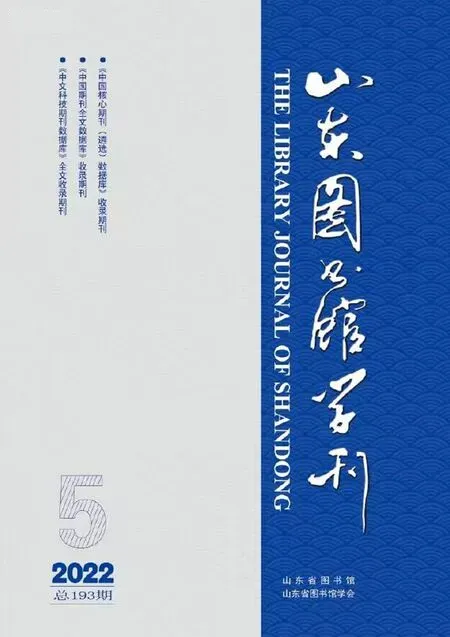沿襲傳統,實踐創新:基于《藏書記要》的孫從添文獻保護思想探析*
霍艷芳 謝鵬鑫
(1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山東濟南 250100;2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湖北武漢 430072)
《藏書記要》由清代著名藏書家孫從添所作,包括購書、鑒別、抄錄、校讎、裝訂、編目、收藏、曝書八則,涉及內容較廣,反映了古代私家藏書活動的全貌。文獻保護是私家藏書活動的重要環節,作者在總結前人經驗的基礎上,結合自己的實踐經驗,提出很多具有現代意義的保護措施,并得到許多藏書家的認可。雖然作者沒有專辟章節論述文獻保護,但從書中所提及的藏書措施來看,可以發現作者具有科學性、系統性傾向的文獻保護思想。對這種文獻保護措施與思想進行批判繼承,可為當下公共機構與私人機構的文獻保護工作提供借鑒。但目前國內對孫從添和《藏書記要》的研究多從清代私人藏書管理活動及其在圖書館學史上的貢獻方面進行論述,如韓淑舉《孫從添和他的“藏書紀要”》、劉俊鳳《〈藏書紀要〉對構建藏書管理體系功用的探討》、羅懷鳳《〈藏書紀要〉在清代圖書館發展史中的開拓意義》、劉刈青《孫從添及其在圖書館學研究中的貢獻》等,對其在文獻保護領域的價值尚未有足夠的重視和探討。本文在梳理原書資料的基礎上,從文獻保護措施切入,歸納孫從添的文獻保護思想,對《藏書記要》的文獻保護價值進行理論總結。
1 孫從添的生平和《藏書記要》的成書背景
孫從添(1692-1767),字慶增,號石芝,江蘇常熟人。平生業醫,因用藥出奇,世人喚其“孫怪”。平生無他愛好,雖貧而唯嗜藏書,家藏不下萬卷,自稱“老蠹魚”。著有《活人精論》《石芝遺話》(又名《石芝醫話》)《上善堂書目》等,與過臨汾合編《春秋經傳類求》。自創一套鑒購標準與求書方法,并極力探索藏書理論,在總結前人經驗的基礎上,結合親身藏書經歷寫成《藏書記要》一書。從該書自序可以窺知作者的著述原因,即“數年以來,或持橐以載所見,或攜篋以志所聞。念茲在茲,幾成一老蠹魚矣。同志欲標其要,不自量,記為竊八則”[1],簡單地說便是向他人傳授自己的藏書經驗,這與當時私家藏書的時代背景相吻合。
康熙年間“實事求是”的考據之風盛行,大批學者投身于古籍研究,民間私家藏書日益活躍,多地逐漸形成著名的藏書文化中心。孫從添的故里常熟即是清代藏書、出版和學術研究中心之一,當地濃郁的藏書氛圍促進了“常熟派”和常熟藏書文化圈的形成。常熟派提倡“善讀為善藏”“尊經而好古”[2]等理念,鼓勵世人多藏書,重視收藏較為稀少的宋元刻本、鈔本和稿本。藏書的數量越多,價值越珍貴,掌握確保藏書安全的方法就顯得更為重要。可以說,常熟派的藏書文化間接地促使私人藏書家費心思考如何保護珍貴藏書這一問題,促進當地文獻保護思想的發展。相比于同時代其他地區藏書家的藏書方法與經驗多見于口耳相傳,或見于零碎典籍之中,常熟派更加重視對藏書經驗進行總結與傳承,并留下大量藏書目錄、古籍善本題跋。值得一提的是,當地多出世代相繼的藏書世家,秘本珍籍在家族或同里藏書家之間輾轉流傳,促進藏書方法的提升和完善。在這些因素影響下,常熟地區形成了藏書收聚和保管的“措理之術”[3]。
孫從添在吸收前人豐富經驗成果的同時,與同時代的藏書家密切地交流分享,最終“這些經過不同時代與各式藏書家所檢驗過的各種藏書實踐,在經由作者的消化吸收后,還進一步撰述為具體的作品,成為流傳久遠并廣泛影響私人藏書理論發展的一個典型”[4]。《藏書記要》成書之初,主要以抄本形式流傳,嘉慶十六年(1811)黃丕烈將之編入《士禮居叢書》中首次刊刻。此后,該書被陸續編入《昭代叢書》《花近樓叢書》《述古叢鈔》《榆園叢刻》《藏修堂叢書》等中,并多次刻印[5]。
2 《藏書記要》中記載的文獻保護措施
無論古代還是現代,防蟲、防火、防潮、防霉、防盜等始終是文獻保護工作的重點內容。《藏書記要》中提及的文獻保護措施,在繼承前人經驗基礎上實現了“內外兼顧,防護并舉”,既強調做好藏品裝潢,注意文獻自身保護;也要求從藏書樓的大環境和書籍的小環境下手,營造出適宜的收藏環境;還提出將提高文獻自身耐久性與經常翻動、定期曝書等日常維護工作相結合。
2.1 營造良好的藏書環境
藏書樓是古代藏書的重要場所,相關建筑和裝具構成文獻保護的外部環境。從宏觀來看,除了建筑的營建方式以外,藏書樓所處的地理位置也是外部環境的重要影響因素,如果選址不當,就可能造成潮濕、生蟲等隱患,不利于對書籍的長期保存。比如常熟地處江南,夏季悶熱潮濕,容易滋生蟲蟻和霉菌,因此藏書樓應當修建在高于地表之處。從微觀來看,藏書裝具的選材、擺放等方面同樣會影響到防火、防蟲、防潮等工作的順利開展。
孫從添在總結前人經驗的基礎上,提出若干條具有指導性建議的藏書樓營建法則。在選址上需要遠離人員較為密集的“來往多門曠野之所”或是“近城市又無空地接連內室廚灶衙署之地”,兼顧文獻安全與防火要求,同時避免選在“卑濕之地”以防潮[6];在防火上,選用經過古人實踐證明過的“可無火患,而且堅久,今亦鮮能為之”的石倉,根據徽州庫樓的建造經驗,采用“四圍石砌風墻”的方式,如果做不到,“須另置一宅,將書分新舊鈔刻各置一室封鎖”,可以將發生火災的幾率降到最低[7];在設計上講究“四面窗欞須要透風,窗小欞大,樓門堅實,鎖要緊密,式要精工”[8],保障充分通風和切實防盜。
針對藏書的微環境,孫從添亦提出不少寶貴的意見。他指出書柜需要選擇不易泛潮的材料,“須用江西杉木或川柏銀杏木為之,紫檀花梨小木易于泛潮,不可用做”[9]。書架的設計要下格高闊,擺放不易緊貼窗戶和墻壁,而且放置書籍不要過于擁擠,需要留出適當的空間便于通風,“書架宜雅而精,樸素者佳。下隔要高,四柱略粗,不可太狹,亦不可太闊,約放書二百本為率。安置書架,勿于近窗并壁之處”[10]。如此種種措施,皆是為了達到防潮的目的。
書籍的擺放也有講究,“書放柜中或架上,俱不可并,宜分開寸許。放后亦不可放足。書要透風,則不蛀不霉”[11],如此能夠減少書籍被蟲蛀或生霉的風險。防蟲防霉藥物的使用方面,“柜頂用皂角炒為末,研細,鋪一層,永無鼠耗。恐有白蟻,用炭屑石灰鍋繡鋪地,則無蟻。柜內置春畫避蠹石,可避蠹魚。供血經于中,以避火”[12],通過使用“皂角”“炭屑”“石灰”“鍋繡”等鋪在地上達到防鼠、防蟻的目的,不過采用“春畫”避蠹和“血經”防火并沒有什么科學依據。
2.2 重視書籍裝潢工作
除了要關注外部環境,文獻保護也要做好書籍自身的防護工作。對書籍進行裝潢,從源頭上進行防護,是我國文獻保護工作延續至今的優良傳統。
孫從添在《藏書記要》“裝訂”一則介紹了毛氏汲古閣的經驗,“惟毛氏汲古閣用伏天糊裱,厚襯料,壓平伏,裱面用灑金墨箋,或石青石綠棕色紫箋,俱妙”[13]。從“伏天糊”“厚襯料”“灑金墨箋”“石青石綠棕色紫箋”等用料之講究,可以窺見汲古閣對裝潢工作的重視程度。此外,孫從添也提出了自己關于裝潢工作的一些看法,“至于修補舊書,襯紙平伏,接腦與天地頭并補破貼欠口,用最薄綿紙熨平,俱照補舊畫法”[14],從用料和操作技法兩個方面確保修復后的書籍能夠長久傳世。在配制的漿糊中加入具有防蟲防霉功用的藥物是修裱時的慣用做法,張彥遠《歷代名畫記》、高濂《遵生八箋·糊方》等文獻中都有所提及。孫從添認為“糊用小粉川椒白礬百步草細末,庶可免蛀”[15],他覺得使用淀粉做漿糊之外,再加入川椒、白礬、百步草等藥物就可以達到防蛀的目的,具有一定的科學道理,但是用今天的眼光來看并不是所有的藥物都能起到防蟲作用,如白礬不防蛀而能夠防霉。
對于裝訂打眼,孫從添指出“訂書眼要細,打得正。而小草訂眼亦然,又須少,多則傷書腦。日后再訂,即眼多易破,接腦煩難”[16],強調一次性訂好,否則日后補訂會對文獻造成無法彌補的傷害。關于裱糊和裝訂的時間,他認為“糊裱宜夏,摺訂宜春”[17]。對于函套的使用,認為“書套不用為佳,用套必蛀”[18],函套雖然精美,但是在常熟不宜使用。這些經過實踐活動檢驗后的經驗,提醒藏書家在文獻保護過程中需要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因時因地選擇藏書保管策略。
2.3 做好日常維護工作
文獻保護除了從環境和書籍自身采取預防性措施,還需要做好日常的維護工作。孫從添強調書籍分類由專人管理,要“將書分新舊鈔刻各置一室封鎖,匙鑰歸一經管。每一書室,一人經理,小心火燭,不致遺失,亦可收藏”[19]。除此之外,日常維護的重點就是曝書。
曝書是通過將文獻在干燥的環境中晾曬降低文獻的濕度從而使害蟲和霉菌無法生存、不再滋生的非常有效的物理方法[20],這種方法對技術和設備的依賴性不強,簡便易行,因此在藏書家之間逐漸形成曝書的風尚與傳統,即使到現在也有圖書館開展曝書活動。自2019年開始,國家圖書館國家古籍保護中心在全國范圍內聯合各省級古籍保護中心與古籍收藏單位開展中華傳統曬書活動,既是對中華傳統文化習俗的致敬與傳承,也是公藏機構展示鎮館之寶、分享保護經驗以及與愛好者進行交流的重要機會。
孫從添在《藏書記要》“曝書”一則中提到“漢唐時有曝書會,后鮮有繼其事者。余每慕之,而更望同志者之效法前人也”[21],表明他對以前的曝書活動神往已久,希望更多的人效仿這種行為,形成一股社會風氣。所以,他在《藏書記要》中詳細地介紹曝書過程和注意事項以資他人借鑒和參考。曝書時需要使用一個四塊“二尺闊,一丈五六尺長”的曬書板,用高凳擱起,置書腦于其上,兩面充分翻曬后,“連板抬風口涼透”才能收入屋內[22]。使用這塊特制木板的目的是便于狂風暴雨來臨時的迅速撤離,這種危機意識仍然值得今天關注。他還提出由于溫度原因,曝書選擇伏天和初秋,這一點與《藏書十約》等書提到的“七夕”“八九月秋高氣爽”等時節有所不同[23],不過為了避免手汗、頭汗等汗液沾上書籍,曝書需要在“早涼”時候進行[24]。也就是說,他認為曝書的最佳時間是伏天的早上,那時候不冷不熱,便于操作。他還指出曝書時需要“照柜書目挨次曬”[25],并“照柜門書單點進”[26],這種照柜門書單清點的做法能夠避免遺漏和錯亂,提高曝書效率,而對于“有該裝訂之書,即記出書名,以便檢點收拾”[27],將那些破損之書清點出來,便于及時裝潢。
除了曝書,編寫各類目錄和時常檢查也是日常維護的重要方面。孫從添認為,需要為藏書編寫大總目錄、宋元抄本刻本目錄、分類書柜目錄和書房架上書籍目錄,不僅能夠快速把握藏書種類和總數、版本情況,而且便于檢查和取閱,還可以照單催還外借的逾期之書,使之不易遺失。他還認為,藏書需要“時常檢點開看”[28],不僅能夠了解文獻受災情況,以便做出及時響應,而且通過翻動書籍,可以抖掉霉菌孢子和蠹蟲蟲卵,驚擾隱藏在縫隙深處的書蟲,起到很好的防霉防蟲功效。
3 《藏書記要》中蘊含的文獻保護思想
古代藏書家在漫長的藏書實踐過程中不斷摸索,形成不少文獻保護經驗,甚至凝聚一些保護理念或思想。明代是對書籍修復經驗和理論進行總結的集大成時期,既有《裝潢志》這種系統性論述歷代裝裱與修復經驗的專門著作,也有《長物志》《夜航船》等零散記載修復、裝裱等措施的作品[29]。在繼承他人理念的基礎上,孫從添又加上人員管理、曝書等文獻保護措施,構筑出較為系統的文獻保護的方法體系。綜合這些措施和注意事項,可以發現其中文獻保護理念雖然是實踐經驗的總結,但亦具有現代化的文獻保護思想的雛形。
3.1 藏書愛書,藏用結合
書籍作為知識的承載主體,其本身的價值是文獻保護的邏輯起點。孫從添充分認識到藏書具有積累知識和傳承文化的重要性,認為“圣賢之道,非此不能考證”[30]。他覺得“購求書籍,是最難事亦最美事,最韻事最樂事”[31],并在解釋“最美事”時說“夫天地間之有書籍也,猶人身之有性靈也。人身無性靈,則與禽獸何異?天地無書籍,則與草昧何異?故書籍者,天下之至寶也。人心之善惡,世道之得失,莫不辨于是焉。天下惟讀書之人,而后能修身,而后能治國也”[32]。在這種理念的驅使下,在家中極貧的情況下仍然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收藏書籍,積累到一定程度,“不待外求而珍寶悉備,以此為樂事,勝于南面百城多矣”[33]。雖然藏書得來不易,但是他不茍同前人“秘不示人”的做法,而持開放共享的態度,甚至鼓勵藏書在不同主人手中流通,“孫慶增有一枚藏書印為‘得者寶之’, 其意涵為‘得到 (該書) 的人應當向書的主人那樣愛護它’,以其使書籍得以長久流傳”[34]。可以看出,孫從添雖然珍視藏書但未走向極端,而是順其自然,兼顧人情世故的變化。
孫從添提倡對藏書進行充分利用,一方面通過閱讀可以獲得一種美妙的精神享受,“置之案頭,手燒妙香,口吃苦茶,然后開卷讀之,豈非人世間一大韻事乎”[35]?另一方面通過鑒別明晰該書版本源流,“如某書系何朝何地著作,刻于何時,何人翻刻,何人鈔錄,何人底本,何人收藏,如何為宋元刻本……”[36]將諸如此類的問題考證確切,如此才能提升辨別書籍真偽優劣的能力。除此之外,他贊同將書籍外借,只不過需要做好登記工作,“如有人取閱借鈔,即填明書目上,某年某月某日某人借或取閱,一月一查,取討原書,即入原柜,銷去前注。借者更要留心,若一月不還,當使催歸原柜,不致遺失”[37]。
孫從添藏書愛書和對之充分利用的意識可以詮釋他藏書行為的初衷和對藏書進行保護的根本宗旨。
3.2 以防為主,防治結合
以防為主,防治結合是我國文獻保護工作的基本指導思想,雖然《藏書記要》沒有專門提出這種保護理念,但書中所總結的文獻保護措施與這種理念不謀而合。
古代藏書家歷來重視預防性的保護措施,孫從添在《藏書記要》中專門列出“收藏”一則,從中可以窺知他做好預防工作的思路:一是從文獻損壞的外因著手最大限度防止或減少各種不利因素對文獻的破壞,不僅在藏書樓的選址、布局等方面下功夫,也要通過放置藥物或香料等物品進行防蟲、防潮、防霉工作;二是從文獻損壞的內因著手采取有效措施提高文獻自身抵抗外界不利因素和隱患的能力,比如對書籍進行裝訂,用加有藥物或香料的漿糊來防止書籍受到蟲害。三是強調在文獻保護過程中定期曝書和檢查,“收藏書籍,不獨安置得法,全要時常檢點開看,乃為妙也。安置雖妥,棄置不管,無不遺誤”[38]。日常檢查和整理既能夠避免錯亂,又可以起到保護作用,“案頭之書,三日一整,方不錯亂。收藏之法,惟此為善也”[39]。四是要做好人員管理,確保“每一書室,一人經理,小心火燭,不致遺失,亦可收藏”[40]。
但是書籍保護僅靠預防還不夠,孫從添認為針對有破損的舊書需要及時修復,比如“破貼欠口”[41],如果是宋元版書“有模糊之處,或字腳欠缺不清,俱用高手摹描如新,看去似刻,最為精妙”[42]。需要注意的是,《明清常熟派藏書“措理之術”探析》中提到孫從添在針對修補宋元版書所提出的方法,“與當代‘修舊如舊’,保持原貌的古籍修復原則是有一定差異的,是常熟派一貫的‘嗜宋佞元’理念的體現”[43]。
孫從添“以防為主、防治結合”這一理念對今天的文獻保護工作仍然適用,只有抓住了“防”,才能減少“治”的任務,只注意“治”不注意“防”,其結果必然是治不勝治,只有兩者相結合才能達到理想的效果。
3.3 因地制宜,因時而變
地理環境的不同對藏書狀態與保護措施影響很大,南方文獻收藏者飽受由濕熱蟲蟻導致的文獻蠹霉之苦,他們必須不斷尋找并改進適合于本地文獻保護的方法,才能使文獻傳綿久遠[44]。正如《藏書十約》中所說“南北地氣不同,是不可不辨者也”[45]。《藏書記要》中雖然沒有明確表達因地制宜的思想,但其保護措施中貫徹了這一理念。由于南北方的氣候差異,孫從添格外重視藏書樓的選址,認為要將藏書樓建在高于地表之處,避免南方容易發生的蟲害、潮濕現象。南北方的氣候差異對書籍裝潢也有影響,函套、夾板的使用需要與當地的通風、潮濕情況相匹配。針對南方潮濕的地理環境,孫從添建議“書套不用為佳,用套必蛀。雖放于紫檀香楠匣內藏之,亦終難免。”[46]
除了地理位置以外,不同季節對于文獻的保存具有重要的影響,古人很早就發現了溫濕度隨時間變化的規律,并在著作中提及因時而變的保護措施。從圖書裝潢到日常管理,大多數文獻保護措施都需要因時而變。裝裱用的書面,孫從添強調要“候干揭下壓平用,須夏天做秋天用”[47]。此外,他也指出“糊裱宜夏,摺訂宜春。若夏天摺訂,汗手并頭汗滴于書上,日后泛潮,必致霉爛生蟲, 不可不防”[48]。而在曝書方面,他也關注到不同時節曝書的不同效果,強調伏天曝書,不過是否伏天曝書更加有利則值得商榷。
4 《藏書記要》中相關文獻保護措施與思想述評
孫從添所提出的文獻保護措施大多是“承上啟下”的方法,既有繼承前人思想與做法的部分,又有自己的實踐創新。綜合全書來看,他的措施與思想深受時代環節與文化氛圍的影響,既有一定的先進性,也表現出一定的局限性。
4.1 先進性體現
《藏書記要》文獻保護理念的先進性不僅體現在“防治結合,以防為主”這一系統性的保護理念,而且表現在孫從添根據自己的實踐經驗所提出的創新方法,其中尤為明顯的是他在曝書環節所設計的新工具。在曝書活動中,孫從添使用四塊一丈五六尺長、二尺寬的曬書板,不僅可以作為搬運圖書的工具,避免直接搬運造成的損壞或混亂,在曝書時還可以隔絕地下潮氣,而且在狂風、暴雨等天氣突變的緊急情況下可以快速反應而直接連書帶板搬入屋內,減少圖書被大風吹爛、雨水打濕的可能性。總體來看,曬書板是非常實用的創造性工具,可以快速應對曝書中可能遇到的危機,體現了孫從添文獻保護措施的先進性,其中蘊含的危機管理思想同樣值得今天學習。
此外,孫從添的藏書理念的先進性也體現在他對傳統文化的傳承。孫從添深受當時文化因素的影響,正如前文所說,當時流行的實事求是學風與常熟地區的藏書文化,塑造了孫從添的文獻保護理念框架。他們所倡導的對書籍價值的重視,成為孫從添所追求的目標。歷代相傳的曝書活動,作為一種文化象征,成為當時讀書人的文化追求與傳統,也影響到《藏書記要》中的文獻保護措施。
4.2 局限性體現
囿于當時的時代環境與文化傳統,《藏書記要》的文獻保護措施不可避免存在一些局限性。在曝書環節,孫從添提出要將圖書“放日中”[49],這種直接放在陽光底下的做法可能會導致紙張受損、字跡退色等不良后果,雖然早在北魏末年賈思勰就在《齊民要術》中對曝書做出“須要晴時,于大屋下風涼處不見日處。日曝書,令書色暍”的提醒[50],但并沒有被孫從添等藏書家所重視。
此外,孫從添在文獻保護中用“血經”防蠹、用“春宮圖”防火在今天看來非常荒唐。這兩種事物在古代卻有獨特的文化意義,甚至引起廣泛的社會共識。“血經”即女子月經,在古代普遍被認為不祥、不潔之物,不過與將之妖魔化的看法相對比就是有人認為它是一種劇毒,無論什么生物碰到它都會引發可怕的后果,還有人認為它具有辟邪功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清末義和團運動中拳民認為染了經血的布條可以抵擋八國聯軍大炮的轟擊。“春宮圖”在古代被稱為“避火圖”,《春宮畫的厭勝社會心態》一文指出,在古人看來,由于春宮畫具有使“火神害羞”“陰陽相斗”等作用,因而能夠在日常生活中起到避火作用[51]。清末民初藏書家葉德輝就經常在冊書里中夾一兩張春宮圖,自言以此制服火神,回避火災。《物理小識》中提到“春宮圖謂之籠底書,以之辟蠹,乃厭之也”[52],也表達了春宮圖防蟲的作用。從現代的視角來看,使用“血經”“春畫”避火等措施并沒有實際的科學道理,但是透過這些看似荒唐的做法,恰恰能夠體會到古代私人藏書家聚書不易、愛書心切,希望能夠將之長久保存下去的迫切心情。
5 結語
《藏書記要》是我國古代私人藏書家的理論著作,對當時的私家藏書方法進行了經驗總結,并將之提高到科學管理的高度。雖然這些保護方法大多已經在藏書家之間廣為流傳,但是并沒有被專門論述。孫從添所做的總結和提升不僅為私人藏書家提供詳盡的書籍保護方法,對我們學習和傳承古代文獻保護措施也具有重要的意義。在認識《藏書記要》的文獻保護措施與思想時,我們還需要注意結合當時的科技發展情況與家庭經濟對他眼界的約束性,辯證地看待目前可能已經不實用的措施,吸收具有現代意義的保護理念,使這些傳統方法、理念與現代方法相結合,更好地去保護我國珍貴的文獻財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