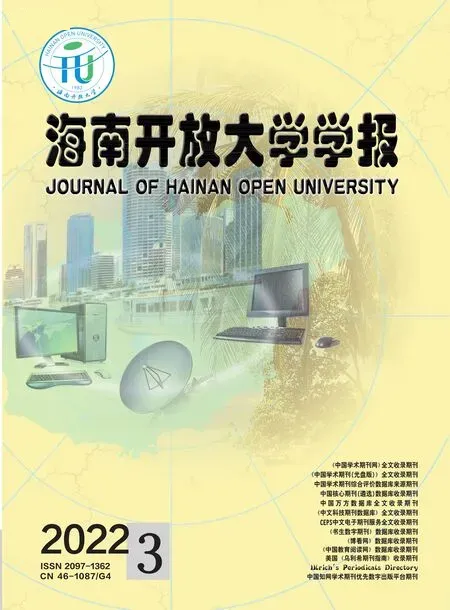從女傭看《舊東家》中性別與階級的隱喻
張萱萱
(1.同濟大學 外國語學院,上海 200082;2.上海行健職業學院,上海 200072)
島崎藤村在明治三十二(1899)年四月來到信州北部的小諸義塾擔任鄉村教師。受到鄉村生活的感染,他在思想上產生了寫實主義傾向,在創作上經歷了由浪漫主義向自然主義的轉變。《舊東家》發表于1902年,是島崎藤村的小說處女作[1]。小說以女傭阿定的視線作為敘述視角,以第一人稱回顧性敘述的形式講述了自己年輕時在荒井家的幫傭經歷和太太阿綾的出軌事件。由于小說中對偷情場面的露骨描寫、并將其與歌頌天皇的場景并峙的反諷設定、以及對原型人物木村熊二/華子夫婦造成的名譽損害,該作品在發表一個月后,以敗壞風俗罪遭到了明治政府的查禁。
《舊東家》的先行研究在考察作品中的女性角色時多集中于對原型人物的考證,或是從人的性本能——情欲和嫉妒的角度進行分析。作者在塑造女性角色時結合了自然主義手法和浪漫主義風格,在人物細節的刻畫上尤為精妙,然而在描寫作品的高潮部分——女傭終于下定決心向太太復仇的心理活動時,僅僅以一句:“我終于露出了女人的本性”來刻畫其心理動機,不免給人一種基于性別的刻板印象,以及隱隱流露出的經驗主義和本質主義傾向[2]。
島崎藤村曾在其他作品中談到《舊東家》是自己“寫實主義傾向孕育出的最初的產物”,選擇一位與自己思想、閱歷、社會地位相距甚遠的女傭的眼光作為敘述視角,確實能反映作家對客觀創作的追求。但不可否認作家局限于自己的身份立場,在刻畫不同性別階層的人物時會產生視線的盲點,導致一種基于性別和階級的刻板印象[3]。因此筆者通過對作品中女性角色主體性的挖掘,分析男性作者在塑造女性形象時的固定模式,揭示出其背后的權力機制是如何運作的。本論將在先行研究的基礎上從女傭阿定的身份特征、敘述特點、以及女傭與太太二元對立的人物構造來解讀作者的寫作策略與作品中性別與階級的隱喻。
一、女傭阿定的身份特征
我娘帶我離開家是三月初二——山村里都選定這一天外出。那天刮著風,微微地揚起地上的塵土。我們踏著夾雜著干沙粒的灰色泥土,朝著小諸走去。我娘頭上包著一塊新手巾,腳上穿著麻草鞋,我提著一個淡綠色的布包袱,跟在娘的后面。為什么只有在這樣的日子,我們娘兒倆才能這么走在一起呢!?我心里感到又是害臊,又是難過。當我們從青郁郁的麥地旁經過時,那些臉色同地里的泥土一樣的莊稼人,停下手中的鋤頭,好似故意地瞅著我們。一條寬闊的北國大路直通小諸。走上大路心里才感到輕松些。許多過路的行商圍聚像過去去驛站似的茶亭里休息。當時正好在砍伐大路兩旁的名貴的落葉松,大樹倒地的聲音,樹枝折斷的響聲,搬運工人的吵鬧聲,弄得大路上好似在打仗一樣。[4]
這是作品中阿定回憶自己從柏木村來到小諸的主家幫傭時沿路看到的風景。這一路上由農村風景到城鎮風景的切換,預示著這位農村少女從“農民”的世界來到了“商人”的世界[5],并且從道路兩邊正在進行的工事和對小學校這樣的近代建筑物的描寫中可以看到當時的小諸正向著近代商業都市快速地發展。
阿定幫傭的主家荒井家同樣是一個商人家庭,荒井家的老爺是銀行家,蓋新式房屋、娶東京女子做太太、并且立志要將東京的風氣移植到小諸來,從服裝打扮到言談舉止,革除一切舊弊。許多先行研究中提到作者將小諸作為小說舞臺背景時特別著重描繪其商業特征[6],如中山弘明指出:小說將小諸作為金錢和物資流通的據點,描繪其“商人道”,有著美化近代金融資本運作的隱蔽作用[7]。作品中荒井家的老爺被譽為“動一動小指頭就能調動小諸商業”的人,托老爺的福,小諸的商人們腰包鼓鼓的,銀行甚至打造了一座光輝奪目的金杯來表彰老爺的功勛。荒井家來往的客人也都是“鎮議會議員、大地主、商店老板、新聞記者”這些小諸的頭面人物[8]。可以說作者在創作時充分展現了明治時期資本主義的發展對日本城鎮及農村生活帶來的影響。
從荒井家的家庭結構來看,一對夫婦加上一個女傭、一個看門的老爺子,是典型的資產階級新式小家庭。主家與阿定簽訂的同樣是雇傭式的契約,當時女傭人的工錢每年18元左右,但阿定只要求主家賞賜一點太太的舊衣服,另外給做幾身合適的好衣服,因為阿定的娘擔心拿工錢的話會被阿定的爹拿去喝酒揮霍。
阿定在作品中經常回憶自己在農村時的艱苦生活:
柏木一帶的女人要在佐久的山崗子上生活,跟惡劣的天氣打交道,一輩子要幫著男人干沉重的活兒。就因為干這種沉重的活兒吧,我娘、我嬸娘姨媽,都有一副倔強急躁的脾性。我打十三歲那年就跟我娘下地干活。和我差不多年歲的姑娘還在拖著鼻涕,跳猴皮筋,而我已經開始懂得人世間的悲歡苦樂了。我家里孩子多,做小買賣又不在行,我爹游手好閑,根本指望不上,我娘雖比男人稍勝一籌,但靠她一雙手還是維持不下去,只好讓我到人家幫工糊口。[4]180
從阿定的敘述中可以看到,當地的農村婦女承擔了相當重的體力勞動,并且不止在農村,在小諸這樣的城鎮上,也是類似的情況。作品中提到小諸是養蠶的地方,家家戶戶幾乎沒有不養蠶的,可以說養蠶的收入是當地人家的主要收入來源之一,到了春蠶的季節,老宅子的女傭們“胸前掛著灰色的麻袋,出外去摘桑葉”的情景在作者的散文集《千曲川風情》中也有著同樣的記載:“腰上插著稱、背著麻袋的人們,從諏訪、松本等地向這座鎮上涌來[9]。客棧里一時擠滿了買繭子的人。這伙人背著蠶繭向各個客棧走去,給各條街道平添了不少活氣。”[10]
然而,無論是在小說還是散文中,小諸商業繁盛的背后,是當地婦女“就好似松井川河谷里的水車,每天都那么轉個不停。男人可以在長長的冬天游手好閑,女人還得不停地干活”的嚴峻現實。也就是說,無論是在小諸這樣以養蠶收入作為支柱產業的商業城市,還是周邊以農耕收入作為生活來源的廣大農村,婦女都是主要的勞動力,正是她們勤勤懇懇縮衣節食日夜不停地勞作,才支撐起了小諸繁華商業都市的表象[11]。她們不僅在家庭中承擔了生育及家務勞動這樣的再生產,為明治時期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剩余價值,還參與了社會勞動,卻不掌握生產資料、不參與收入分配。不僅如此,阿定的娘還要擔心阿定幫傭的收入被丈夫喝酒胡亂揮霍掉,在與丈夫爭吵時哭喊著:“打死我吧!要打就打死吧!”。阿定的爹在作品中唯一一次登場是喝醉之后登門向阿定的主家討煙,邊抽邊顯擺自己要去花柳街送藝妓,稱自己清醒時也是個“好樣的”體面人。
作家雖然竭力秉持“按照事物本來的樣子去摹寫”的自然主義創作理念,但在描寫小諸近代化和商業化的時代新面貌的同時,卻暴露出當地婦女在父權制及資本主義制度的雙重壓迫下艱辛的生活狀態。這可以說是作品以女傭作為敘述視角,從底層勞動女性的身份立場進行觀察和敘述時呈現出的特殊效果。
二、婚外戀的隱喻
《舊東家》是通過女傭阿定的回顧性敘述,以太太阿綾的出軌事件作為小說的主線來展開的。這位來自東京的太太給小諸當地保守的風氣帶來了一片“開化、奢侈”的新風潮:小諸一帶的女性將沉重的農活和家務視為自己的義務,“天沒亮就起身”“天空剛發白就下地”,阿綾卻“把家里當作玩樂的溫泉旅館,白天不做活,夜晚不休息”;當地的婦女崇尚艱苦樸素的生活——“連年輕的姑娘也要讓她們滿足于穿土布衣裳”,阿綾卻“早打扮,晚化妝”“頭發要由相生街的阿仙來梳,刮臉指定由岡源的老娘來刮,選料子的是大利的掌柜,做衣服的是馬場后街的良助——真是豪華講究到家了”;以及當地女性堅守著男尊女卑的傳統思想,“從來沒有夫妻倆一塊兒去賞過花,頭一次看到老爺太太手拉著手,親親熱熱地在屋子外面走路,簡直把她們嚇壞了”,相比之下阿綾每天在家中睡到日上三竿,家務全交給女傭做,丈夫回家從不到門口迎接,還經常在丈夫面前隨意發脾氣甩臉色,甚至在貞操觀念上也沒有受到嚴厲的約束——婚后不久便和東京來的牙醫發生了婚外情。
作者究竟為什么要塑造這樣一位東京太太的形象呢?[12]一方面從當時的散文和日記的記載中可以發現島崎藤村閱讀了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和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等作品,思想上受到了西方現實主義文學強烈的沖擊和影響;另一方面,雖然三年的小諸生活使藤村在創作上經歷了由浪漫主義詩歌到自然主義散文的轉變,并最終將小說確立為“表達自己思想的最合適的形式”,但不可否認的是在其作品中仍然能夠感受到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例如他在描寫阿綾的不倫戀情時采用了大量的夢的意象,阿綾在作品中被塑造成分不清夢境與現實,“一輩子跟夢兒做了伴了”的女人,由于擔心自己和牙醫的戀情被丈夫發現,阿綾做了這樣一個噩夢:
在一個好像是蘋果園的地方,老爺在默默地散步,一個人好像影子似地悄悄走到他的身邊,附在他的耳邊說了些什么話。于是老爺大怒,張開兩只手猛追太太。據說太太有兩三次幾乎就要被抓住了,最后把身上的衣服脫下扔掉,光著身子才逃脫了。[4]205
從這個夢境來看,無論是蘋果園、告密者(蛇)、還是赤裸的身軀都隱喻了圣經伊甸園的場景。島崎藤村曾在明治21年至26年加入基督教,基督教的教義和《圣經》中的故事對他的創作產生了深刻的影響[13]。例如伊甸園的意象曾被他融入到第一部詩集《嫩菜集》的《初戀》這首詩中,
你溫柔地伸出白皙的手
將蘋果嬌羞相贈
這秋日里成熟的碩果
恰似我最初的愛情[14]
從句中可以看到藤村把戀愛的覺醒和亞當夏娃偷吃禁果的場景聯系在一起,并把戀愛的覺醒看作是人性的覺醒予以歌頌。在同冊的最后一篇詩歌《逃水》中,他寫道:
戀愛正是原罪
原罪也是戀愛[14]
這首詩在描寫戀愛覺醒的同時,鮮明地體現出了罪的意識,暗示了藤村在戀愛思想上的轉變。而徹底將戀愛的覺醒和原罪意識等同起來的則是在他出版的最后一部詩集《落梅集》中,詩名就叫做《惡夢》:
不知何時
罪惡已深入骨髓
在我生命的舞臺上
也會上演那樣的罪嗎?[15]
詩句描述了人骨子里刻著罪惡,以及生命中注定背負罪惡,這里的罪惡指的應該是人與生俱來的原罪:好色、貪婪、說謊以及對金錢權力的追求等。那么在《舊東家》中,作者又希望通過阿綾的婚外戀表達一種什么樣的思想呢?水田宗子在考察婚外戀題材的小說時曾指出:“當一個對社會沒有用的人靠自身來充實自己的時候,失落的自我便顯出全貌,戀愛——通奸便成為充實自我的手段和自我審視的鏡子。”[16]她指出了婚外戀的反社會性和排他性。19世紀是西歐傳統婚姻觀、家庭觀動搖的時期,婚外戀意味著對傳統的性關系、婚姻、戀愛、家庭觀的批判和挑戰。《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等通奸小說批判了傳統婚姻制度的偽善性。
水田宗子在分析男性作者創作婚外戀小說的意圖時進一步指出:“婚外戀夫人是冒著身敗名裂的危險來尋求性的滿足的。換句話說,正因為婚外戀行為反制度,所以當事人認為這種行為既可以滿足戀愛和性欲的需求,還可以滿足自我,提供自我意識的根據”[16]85,于是作者就在婚外戀的太太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無論在西方社會還是當時的日本,男性都是被社會化的,很難脫離社會體制自由自在的生活,并且婚姻制度給男性開了綠燈:即使明治民法中禁止了重婚,男子納妾卻并不違法,相反妻子若和丈夫之外的男性發生關系,則以通奸罪論處。因此作家只能通過刻畫婚外戀的太太來體現一種超越制度道德標準的根源性道德,以及尋找到自我的存在。
太太是想到外面去散散心的,可是小諸是個勤儉樸實的小地方,茶道的先生搬到上田去了,謠曲的師傅改行到處去叫賣糖果點心,可看的可聽的東西很少,僅靠家庭中有限的一點樂趣,當然一想起來就覺得膩煩。以至連綢子手絹擤過一次鼻子就扔掉;在臥室里到處亂撒香水;梳得好好的頭發,只要不中意,馬上就毀掉,讓人重梳兩次三次;自從吃慣了夜宵以來,在吃過咸糠腌的小菜加木魚末的茶泡飯之后,還問“有什么更好吃的東西嗎?”從新醉月餐廳叫來的飯菜,嘗了兩三口就喂狗了。女人的愛好簡直是瞬息萬變。太太對一切樂趣都厭倦了,整天嚷著煩死了。
“每天每天都是一個樣啊!”太太靠在柱子上這么自言自語地說。輕浮的樂趣給太太的只是這么一句話。[4]186-187
從上文可以看出,阿綾的出軌是一種對小城鎮單調枯燥的生活的反抗,阿綾認為自己“被人世的鎖鏈鎖住,身不由己地被人拖著走,天天過著夢一般的生活”。婚外戀的行為是不道德的,所以給日常生活帶來一種刺激性,而阿綾只有在這種刺激中才能感受到生活的意義,找到自我的存在。島崎藤村通過描寫這樣的女主人公,展現了人的情欲本能與社會體制的對抗,這一方面體現出作者主張個人自由、贊美戀愛、肯定人性的浪漫主義思想,但另一方面同樣反映出作家在塑造女性角色時的固定觀念。阿綾確實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但她的精神世界里沒有任何高尚的東西——缺乏道德、貪圖享樂、沉溺于官能、不能深入思考問題。作家沒有賦予她思想和倫理上的高度,以便她能夠超越精神和感官上的匱乏,最終只能陷入婚外戀的官能刺激中無法自拔,走向毀滅。與此相對,在《破戒》中同樣受到制度迫害的男主人公丑松卻通過告白的方式獲得了新生。
三、女傭阿定的敘述視角
作者采用一位農村出身的女傭的敘述眼光和聲音來講述主家的故事,最顯而易見的效果就是凸顯來自東京的太太阿綾與小諸當地女性在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上的巨大差異,以及由此產生的一系列二元對立與戲劇沖突。例如農村出身的阿定在敘述中對節氣的變化、農耕的時節和各種祭祀活動特別敏感,經常通過對季節轉換的描述來刻畫時間的流逝、推進情節的發展;東京出身的阿綾卻“有時連日子也忘了,問我說:‘阿定,今天是幾號呀?’有時看到墻上的日歷,連聲驚呼日子過得真快。”又如作品中描寫小諸是養蠶的勝地,阿綾卻“聞到蠶兒的味兒心里就惡心”,對當地女性日復一日的辛勤勞作“付之一笑”。
《舊東家》雖然以太太阿綾的出軌事件作為主線展開,但女傭阿定卻不僅僅是事件的旁觀者,更是參與者,甚至可以說是推動事件發展的關鍵人物。由于女傭身份的特殊性,作品中阿定可以相對自由地穿梭于農村與城市,主家的新宅與舊宅,家庭的內部空間與外部空間,對各個登場人物進行觀察和描述,極大地擴展了作品的敘事空間。小說是以阿定的第一人稱進行回顧性敘述的,但作者卻沒有將阿定塑造成一個客觀的敘述者,而是利用她的身份立場向讀者展現了一個女傭主觀的、帶有階級地域色彩的敘述聲音。通過文本細讀我們能夠發現,阿定的敘述立場并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著小說情節的推進發生了明顯的轉變。本章將通過阿定的敘述特征和敘述立場的幾次轉變來分析作者的敘述策略和寫作意圖。
阿定初次見到太太阿綾時被其苗條的身段、姣好的容貌、精致的打扮所吸引,并且迅速從她漂亮的口音和白嫩的雙手判斷出她不是小諸本地的女人。阿定在太太面前對自己窮酸的打扮和娘又大又粗的手感到自卑,既羨慕阿綾年輕時髦的打扮,也羨慕老爺與太太和睦親熱的夫妻關系。隨著在主家幫傭時日的增加,阿定慢慢對荒井夫婦的關系有了新的認識,她注意到老爺和太太的婚姻并非表面上那么相稱:太太阿綾很年輕,老爺卻已經到了戴假牙和老花眼鏡的年紀;太太的美貌連身為女人的阿定都感到心動魄搖,老爺卻長著一副似哭非哭似笑非笑、滿是皺紋的怪臉;再加上老宅的女傭人們嫉妒太太的美貌,造了許多關于太太的謠言,阿定樸素的正義感使她在情感上漸漸偏向了被本地人孤立的外鄉人太太:“我一聽這些關于太太的謠言,真把我氣壞了”。
如果說上述這些心理活動的描寫還沒有超出一般女傭的身份立場和觀察范圍,那么阿定第一次明顯的立場轉變是從太太和她分享自己的秘密開始的:
“因為是對你,我才說啊。”說到這里,又吞吞吐吐不說了。
“今天晚上我跟你說的話,你要答應我跟誰也不說,就等于沒聽見。……不過,恐怕只有跟你我才能說出這樣的話。”
太太叮嚀又叮嚀,還好像有點兒說不出口的樣子;一到好像要說的時候,臉蛋兒一下子紅到耳根子。
太太終于放低了聲音,跟我說了她的心里話。這時我才知道她跟牙科醫生以前的關系。我的手被太太緊緊地攥在手心里,我的臉不覺火辣辣地發起燒來。再沒有比人家跟我坦露心里話而使我心軟了。太太跟我一說她憋在心里的苦惱,我終于對她感到可憐起來。我深深地同情她的處境,給她說了一些安慰的話。太太一聽我的話,像孩子似地啜泣起來。
我只好答應幫助她和牙科醫生約會,這時我才意識到太太像火一般熱的手放開了我的手。
……
有時候我也安慰安慰自己這種自我責備的心。太太的戀愛確實是不正當的,可她也確實太可憐了;她深更半夜背著人把眼淚流在床上,也沒有個可以推心置腹談心的女朋友。我一個人這么想想,也覺得寬慰起來。[4]190-191
從阿定的敘述中可以發現,她對太太的同情源于一種年輕女性間的共情,為此她無視了山里人保守的風氣,克服了自己背叛老爺的恐懼,與同她身份地位差距甚遠的太太建立起了同性間的“姐妹情誼”。
世上的老爺們多么需要體諒跟他們一塊兒生活的太太啊!——女人的命運就是這樣吧!盡管說是緣分,可是太太背井離鄉,等于是出外的游人,卻沒有一個真正同情她的人。光憑這一點,一個女人也會活不下去的。太太真是不幸啊![4]191
但必須指出的是,促使阿定下定決心幫助太太與牙醫偷情的關鍵因素并非僅僅出于這種女性間的“姐妹情誼”,其中還夾雜著無法忽視的經濟上的原因:
他(櫻井先生)是東京人,說他一看到這帶格子門窗的新式房子就想起了首都。要說從東京來的醫生我也見過,服裝打扮都像演員似的,儀表堂堂的卻不多。不過,唯有這位牙科醫生我覺得還長得不錯。
他來的時候總要給我帶點東西,他回去之后,看門的老爺子的手中肯定要攥著一枚銅幣。[4]188
……
“前些時候我就想把這個送給你。”太太一邊這么說,一邊往我手里塞。因為是晚上,那條紫縐絹的襯領看成好似豆沙色的。我吃驚地睜大了眼睛,不知道是要好還是不要好,一個勁地推辭。
“你要說不要,可叫我為難了。這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東西。你為我們干活很勤快,很合我的心意。……好啦,你收起來吧。”[4]190
以及阿定在自述中意識到自己在外貌和心態上的轉變:
我確實是變了。我一路上邊走邊想著自己,連我自己也深深地感到出來幫工以后的我和當年的我已經像換了一個人了。我在闊氣的生活環境中住慣了,不知不覺地也學起太太的樣兒來了。看起來我已經自然地形成了一種習慣了。當年我垂著發鬢兒,還有點孩子氣,現在腦袋后面拖個雀尾巴,前發留得很寬,有空也對著鏡子瞅瞅,偷偷地用剃刀刮臉,在澡盆里泡上很長的時間也沒人說我,盡情地洗滌身子,連指甲縫里的污垢也要洗剔干凈,有點兒愛美起來了。穿上太太賞我的那件漂亮的舊外褂,一定要襯上毛絲緞的領子,穿上短外褂時很注意領子上有沒有臟;系好衣帶去買豆腐時,如果不蓋上一塊小包袱皮,就會覺得丟人;醋瓶要藏在袖子里,走起路來輕飄飄的,嘴里還吹響著酸漿果。當我覺得柏木的朋友有點土氣時,往往就把娘也忘記了。哎呀!我對自己的變化也感到大為吃驚。出外幫工、辛勞艱苦似乎都已成為過去的事情。[4]207-208
從阿定的自述中可以看出她的自我意識在幫傭后發生了巨大轉變,她在太太的影響下不知不覺習慣了舒適的生活,忘記了原本干農活時的艱辛,逐漸開始有了愛美的意識,學著太太打扮起來。她的眼光也不再是原來樸素的農村婦女的眼光了,而是無意識地將自己與太太放到了同樣的位置,將資產階級奢侈的生活方式內化了,外出買菜時會在意路人的投向自己的眼光,不打扮一下就覺得丟人。阿定說自己“把娘忘了”,暗示著她忘記了自己的原有的身份立場,而是站在時髦的東京人的角度看待自己的家鄉,因此才會覺得“柏木的朋友有點土氣”。
然而這種脆弱的“姐妹情誼”和虛假的“身份認同”隨著太太同牙醫艷聞的傳開,很快就破滅了。太太對能夠自由出入家庭內部空間與外部空間、和老宅的女傭們溝通交流的阿定起了疑心,決心將她趕走,在老爺面前編造了許多阿定的壞話。在親耳聽到了太太對自己惡毒的污蔑,又目睹了與自己同樣從柏木到小諸幫傭的阿繼由于遭到主家的迫害而投水自殺之后,阿定終于清醒過來,意識到了自己真實的處境,導致其敘述立場發生又一次轉變:
這件事使我太震動了。我們同樣都是給人家幫傭的人,不能眼看著而沒有任何同情啊!我心中的氣憤、委屈都消失了,只覺得心頭十分凄涼。
……
最初來幫工的時候,盡管白天干了一天活,晚上頭一落枕頭,一定習慣地想起柏木,在被子里喊著“娘!娘!”地睡去。后來我漸漸地把柏木忘了,只是偶爾才夢見娘。而這天夜里我的心又飛向了柏木。我從來沒有像這天夜里這么想念過我的娘。……我的心里對東家家里的闊氣的生活再也不感到羨慕了。我想的盡是柏木的事情。……我想著想著,熱淚流出了眼眶,自己可憐自己地哭了起來。[4]208
此刻阿定才終于意識到自己同太太并非處于同一立場,即使同樣身為女性,她們的階級也是對立的。無論阿定如何憧憬太太的生活,她都無法跨越主仆的身份,成為和太太平等的人。在太太眼里她不過是替自己承擔家務的勞動力,以及幫助自己和牙醫偷情的工具罷了。當太太需要她時會賞賜籠絡她,一旦她威脅到太太的利益,則被毫不留情地犧牲掉。此時阿定反復想起自己的娘的情景,暗示著她渴望回歸生命的本源,重新構建自己的身份認同。只有再次回到自己原本的位置——從柏木來到小諸幫傭的貧苦的農村女性,才能幫助她找到自我,確立自己接下來行動的根據。
作者將阿綾對阿定的構陷及阿定向阿綾的復仇定義為“女人的本性”。然而結合小說的發展脈絡和當時的社會狀況我們可以發現,不同階層的兩位女性從互相幫助到互相攻擊,轉變的根本原因在于“自保”。作品中阿綾雖然依靠婚姻過上了富足的生活,但她的原生家庭經濟狀況堪憂,父親千里迢迢從東京來到小諸尋求老爺的幫助,身上連一件體面的衣服都沒有,如果失去了老爺這個經濟上的靠山,阿綾和她的家人可能會陷入貧困的生活。而阿定作為女傭,如果幫傭時落下不好的名聲,在小諸這樣風氣保守的地方就很難再找到愿意接收她的東家。阿定若是失去幫傭的工作,就會像同村的阿繼一樣走投無路,即使回到柏木幫娘干農活也難以糊口,可能還會遭受爹的暴力。
作者通過女傭的敘述視角建構起了東京太太與農村女傭這樣二元對立的敘事結構,實質上是將自己的創作放在“農村(傳統)文化”和“城市(現代)文化”兩種文化對比的價值體系中確立自己的寫作視角,作出自己的價值判斷。島崎藤村出身于信州的名門望族,對農村并沒有深厚的感情或復雜的鄉愁,只能站在城市人的角度對農村作純客觀的描寫。藤村的小說《巖石之間》曾被三好行雄評價為“與現實生活相對應的具有自傳性質的作品”,小說塑造了一個疲憊于城市生活而逃向農村的青年,然而經過了一段時間的農村體驗后,青年發出了“百姓是百姓,自己是自己”的感慨,認識到即使親自下地耕種,也不過是對農夫行為的表面模仿,根本無法深入他們的內心世界,自己只不過是個農村生活的旁觀者罷了。
在《舊東家》中藤村同樣是以城市(現代)文化的價值觀對農村(傳統)文化進行觀照、反思和批判的。“山里人的守舊性格簡直叫人可怕,見到一個跟他們稍微不一樣的外鄉人,就恨不得給人家迎頭潑上一盆開水”,“鄉下女人就是好奇,當太太花枝招展地從街上走過時,她們從土墻的窗戶里看著,從格子門的洞里瞅著,擠眉弄眼地發出一陣陣邪笑”,“太太這位外鄉人偏偏闖了進來,這只能叫人把她看作是帶來了一片開化、奢侈的東京生活的闖禍精”,“所以外鄉人太太反而比本地人老爺招來更多的憎恨”——這些鄉下女人窺探的目光和流言蜚語成了阿定復仇的武器,將沉溺于戀愛的太太逼入了絕境。作品中阿定的敘述立場雖然經歷了幾次轉變,但從“這天晚上我就這么偶然起了一點邪念。——這也是人在年輕的時候常有的事吧。”這句話中可以看出,當敘述者阿定站在現在的時間點上回顧過去的自己時,將自己幫助太太的行為定義為“年輕時犯的一個錯誤”,這明顯是以農村人的道德觀從批判的立場上進行敘述的。這也體現出了作者的寫作策略——將農村陳舊的道德觀念和保守的社會風氣看作是自由戀愛的對立面,通過描寫太太婚外戀的行為對其進行抨擊和反抗。
四、小說結尾的雙重構造
“行最敬禮!”——山崗子上會場里的叫喊聲傳到了屋子里。突然響起了外面的格子門被拉開的聲音。
“我回來啦!”說話的是太太的老太爺的聲音。
當老太爺叫第二聲的時候,兩個人睜大著眼睛回頭一看,見到老爺默默地站在身后。太太已經來不及推開男的,伸了伸身子,臉色唰地一下變得煞白。牙科醫生早已張皇失措,慌忙用左手頂著太太的下巴,右手作出象拔蟲牙的姿勢。
老太爺大概看誰也沒有出來迎接,自己大踏步進屋來了,只聽響起拉開紙拉門的聲音,接著走廊上發出吱吱吱吱的聲音。一陣恐怖感像閃電般從我的天靈蓋一直貫通到我的腳趾尖。
這時屋外響起了一片震耳的喇叭聲和大鼓聲,幾千人像象雷鳴般一齊高呼:
天皇陛下萬歲!天皇陛下萬歲![4]213
在作品結尾處,阿定揭發太太偷情的當天正巧是冬至,紅十字會北佐久總會在荒井家旁邊的小學操場上舉行集會活動,游行群眾高唱著《君之代》的場景與屋內太太偷情的旖旎場面形成強烈對比,正當“行最敬禮”的叫喊聲傳入屋內時,格子門同時被拉開,千人齊呼“天皇萬歲”的場景與太太偷情敗露的場景在屋內外同時發生這一設定值得探討與深究。
安丸良夫在《近代天皇像的形成》[17]中指出:1891年,日本要求小學制定節慶日儀式規定,確定了“參拜天皇御照”“奉讀教育敕語”“敕語相關的誨告與演說”等內容,“通過學校教育與青年團、在鄉軍人會等團體,天皇崇拜與國體觀念逐漸深入國民意識,形成了一種共通的觀念”,這意味著當時的小學是一個充斥著天皇崇拜思想的象征空間。作品中提到的《君之代》在1899年8月被日本文部省指定為學校必唱曲目,之后成為日本國歌。此外,“行最敬禮”的呼聲來源于1900年文部省制定的小學校令實行規則中,有“對天皇御照行最敬禮的義務”這樣的史實記載。這項校令強調了天皇的絕對性、神圣性與不可侵犯性,同時將“忠君=愛國”“天皇=國家”的意識形態植入人們腦中。
自1893年小諸義塾開辦以來,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1897年前后日本各地爆發了由大米價格波動引起的罷工運動,明治政府為了壓制勞工的暴亂,制定了治安警察法,剝奪了民眾的政治權力與思想自由;1899年《明治憲法》的頒布確立了天皇的絕對權力,日本國內的軍國主義思想開始抬頭;1890年頒布的《教育敕語》預示著儒家思想的復辟,以加強學校的思想教育為標志,日本迅速向專制主義國家轉變;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日本走上了對外侵略擴張的道路。島崎藤村自1899年至1906年期間在小諸義塾擔任教師,這些重要的歷史轉折點所引發的小諸社會風氣的劇烈變化,無疑會對創作于1902年的《舊東家》產生相應的影響。
小說結尾處阿定被屋外《君之代》的音樂所吸引,雖然看不清會場里的情況,卻看到“許多農民從布幕后面往里瞅著,有的孩子跑到木柵欄上往里看”,會場的演講內容阿定雖然不太明白,但“每句話還是聽得很清楚,不覺聽得入神了”。這個場景描繪了以阿定為代表的普通民眾,雖然搞不清楚“近代”的實質,卻仍然受到了時代潮流的沖擊。作者將這個場面與偷情敗露并峙的設定,揭示了作品結尾的雙重結構:一是《明治憲法》中君主立憲與絕對君權并存所造成的國家體制上的不可調和的矛盾;二是近代婚姻中的矛盾: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人們思想中的自由戀愛意識覺醒了,但另一方面儒家思想的復辟卻使得以經濟基礎為前提的介紹婚在社會中普遍盛行。就如同荒井家那棟外觀小諸風、內部結構卻是東京式樣的房屋一般,在彰顯著天皇權力的小學操場上,卻舉辦著象征人道主義的紅十字集會,作品結尾處一系列二元對立的象征符號,隱喻了日本近代化過程中的矛盾性,也暴露了日本近代化的虛偽性。
作者在描寫阿綾通奸敗露的場景時,將丈夫的目光、父親的聲音、以及門外高呼“天皇萬歲”的口號在同一時空中并列呈現的寫作手法,象征著阿綾對自由戀愛的追求在夫權、父權與君權三重壓迫下徹底破滅。荒井夫婦婚姻關系的破裂和小家庭的崩壞,也隱喻了作者對扼殺了女性主體性的夫妻關系和婚姻制度的悲觀態度。
五、小結
《舊東家》的先行研究普遍從性本能的角度解讀阿定的行為動機,認為作品通過女傭的視線展現了男性的嫉妒與女性的欲望,將阿定的復仇理解為嫉妒、背叛與回歸本性。但通過本論的一系列論證,可以看到阿定的意識轉變是從對女性命運的同情、對美好事物和浪漫愛情的向往到逐漸被金錢誘惑、被權力意識扭曲的過程。小說的結尾實質上是兩個既沒有權力也沒有自立能力的女性,出于對父權的恐懼而選擇相互構陷、斗爭的結果。阿定復仇的動機并不僅僅是對太太的怨恨和報復,而是在資產階級和父權的雙重壓迫下,認清了自己身為底層女性無力反抗的悲慘命運,從而選擇了依附父權——通過向老爺告密來保住自己的名譽與經濟收入。阿定與太太乍看之下是處于兩個社會階層、互為對立面的女性,但通過文本細讀可以發現兩個人同樣是被榨取性(生育)價值與勞動(家務)價值的近代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犧牲品。
本論通過對女傭阿定的身份特征、敘述特點、以及女傭與太太二元對立的人物構造的解讀,指出作品內部隱藏的性別與階級的雙重構造,揭示了在家父長制與資本主義制度雙重壓迫下的底層女性的悲慘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