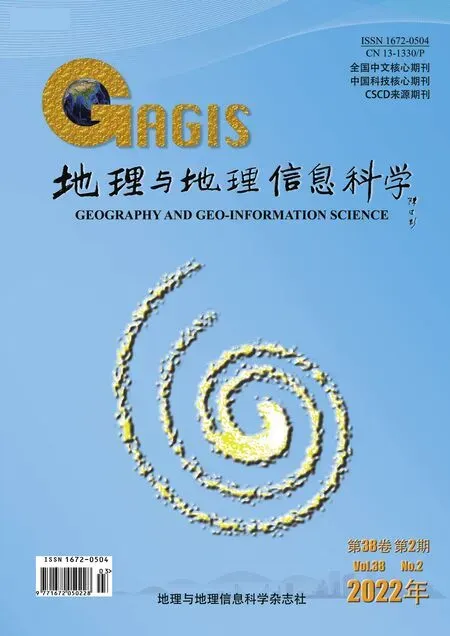基于企業(yè)組織機構的中國大陸航運中心層級體系與網絡聯(lián)系
郭 建 科,吳 莎 莎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遼寧師范大學海洋經濟與可持續(xù)發(fā)展研究中心,遼寧 大連 116029;遼寧省“海洋經濟高質量發(fā)展”高校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中心,遼寧 大連 116029)
0 引言
21世紀被聯(lián)合國稱為“海洋世紀”,越來越多的國家或地區(qū)通過海洋競爭全球資源。而國際航運中心是以區(qū)域經濟中心城市為依托,集商貿、物流、金融等航運要素于一體,位于國際航運網絡的戰(zhàn)略節(jié)點,在某經濟區(qū)域的港口群中處于主導地位的航運交通樞紐,其對國家或地區(qū)參與世界經濟分工與合作具有重要作用。
在國際貿易分工組織和航運技術變革的引領下,國際航運聯(lián)系網絡已經形成,部分學者利用集裝箱班輪船期數(shù)據在港口間建立節(jié)點、連接和網絡的基礎上,研討區(qū)域集裝箱港口體系的空間聯(lián)系格局[1],對中國國際航運網絡的結構特征和貿易特征進行分析[2,3];郭建科等用樞紐度模型、赫芬達爾—赫希曼以及復雜網絡方法構建“海上絲綢之路”航運網絡,分析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航運網絡空間格局[4,5],證明航運網絡具有“小世界特征”和“無標度特征”。但已有學者針對航運網絡的相關研究多集中在航運網絡結構特征及港口在網絡中的重要性和地位上,而航運中心是航運要素集聚的空間載體,航運企業(yè)驅動航運要素的集聚。國內外學者結合多元化航運產業(yè)表征港口之間和航運中心之間的聯(lián)系,研究表明:臨港產業(yè)集聚發(fā)展推動國際航運中心的建設,對港口城市空間結構演變產生影響[6];港航服務企業(yè)的發(fā)展趨勢[7]和組織行為會影響碼頭經營[8],進而影響港口運行[9]。近年來,有學者構筑航運要素指標體系研究港航服務業(yè)的集聚發(fā)展與空間狀況[10],從海洋產業(yè)[11]、港口物流企業(yè)[12]、中國郵船[13]方面對港口企業(yè)的空間格局和演化規(guī)律進行探究,或研究港航企業(yè)空間分布以分析港口的區(qū)位特征和空間聯(lián)系,探索航運服務集聚區(qū)的集聚驅動力[14-17]。
既有研究側重分析整體航運網絡的一般特征[18]。國內學者一是針對港口體系的演化特征[19]、空間聯(lián)系的拓撲結構[20]、資源流動程度與路徑展開研究;二是圍繞區(qū)域港口聯(lián)系的節(jié)點、密度與能級展開研究,主要涉及國家和港口群尺度;三是以單一行業(yè)或企業(yè)網絡為視角[21],對其空間格局、時空演化和動力機制等展開研究,缺乏航運全產業(yè)鏈的研究成果。基于此,本文從跨國航運企業(yè)組織地理布局的視角構建中國大陸航運網絡,定量分析航運中心節(jié)點和網絡聯(lián)系,識別航運中心的層級特征和聯(lián)系密度,以期進一步研究航運中心網絡體系,為探究中國航運中心網絡布局及發(fā)展方式提供參考。
1 研究對象、數(shù)據和方法
1.1 研究對象與數(shù)據
本文根據中國交通運輸部公布的港口數(shù)據及《全國沿海港口布局規(guī)劃》(2006年)的相關規(guī)定,基于沿海港口城市的歷史沿革和發(fā)展現(xiàn)狀,選取50個沿海港口城市構建中國大陸航運中心網絡。航運中心可分為以下3種類型:貨運型航運中心,主要提供貨物集散服務但不具主動操縱集散、影響調配的能力;服務型航運中心,指在國際航運中心資源配置過程中占主導地位的是航運服務業(yè)務;知識型航運中心,是以知識和創(chuàng)新廣泛應用和滲透于各種類型的航運業(yè)務之中,為航運業(yè)務的順利開展提供管理、決策和支持服務[22]。由此基于貨運、服務、知識3個層面界定航運企業(yè)組織(表1),構建指標體系測度航運中心的網絡關系,通過每個企業(yè)組織的官方網站查找企業(yè)組織的名稱、總部及分支機構所在地等信息,對數(shù)據收集整理并篩選出在中國大陸至少設有1個辦事處的企業(yè),最終確定航運企業(yè)組織137家,其中貨運型79家,服務型30家,知識型28家。

表1 航運企業(yè)組織分類及其測度指標體系Table 1 Classification of shipping enterprise organizations and their measurement index system
1.2 研究方法
(1)連鎖網絡模型。2001年,Taylor建立連鎖網絡模型并基于企業(yè)機構分布研究城市網絡[23],隨后該模型被廣泛用于不同區(qū)域[24]、不同要素[25]的研究。該模型利用企業(yè)分支機構服務值的設定構建世界城市網絡,在世界城市網絡分析中融入“流動空間”理念,通過對企業(yè)組織內部不同企業(yè)機構職能與規(guī)模等級賦值,將各級企業(yè)機構所在的城市相互關聯(lián),進而構筑以城市為載體的企業(yè)組織關系型矩陣,并測度出區(qū)域內城市網絡關系[26]。
(2)航運企業(yè)組織網絡構建。首先構建由50個航運中心和137家航運企業(yè)組織組成的關系矩陣,航運中心i中航運企業(yè)組織j的得分值Vij被定義為航運企業(yè)組織j在企業(yè)組織網絡中的服務值,即航運中心i的企業(yè)分支機構在航運企業(yè)組織j結構網絡中的地位或重要程度。航運中心之間的連通性用航運中心間的企業(yè)組織聯(lián)系強度衡量,即相對網絡關聯(lián)度Rab(式(1)),是航運中心a、b之間所有共同企業(yè)組織的服務值之和,其值越高,表明兩個航運中心之間的聯(lián)系越密切,在航運企業(yè)組織網絡中的地位越高,并會吸引更多企業(yè)組織將分支機構設置在兩個航運中心的組合之中。由此可構建一個50×50的航運中心關聯(lián)強度矩陣,單個航運中心a與其他所有航運中心的相對網絡總關聯(lián)度Na、整個網絡的總關聯(lián)度T和單個航運中心a的相對網絡關聯(lián)度La的計算公式見式(2)-式(4)。
(1)
(2)
(3)
La=Na/T
(4)
(3)航運中心綜合指數(shù)和分項指數(shù)。統(tǒng)計137家航運企業(yè)組織在中國50個航運中心的5種職能等級并賦予不同分值,即全球總部(5分)、區(qū)域總部(4分)、國家總部(3分)、分公司(2分)、辦事處或一般機構(1分)。為減少航運企業(yè)組織在航運中心設置分支機構時衡量標準不同所帶來的誤差,對原始數(shù)據航運中心服務值進行標準化處理并通過熵值法得出各航運中心的指標權重,進而利用綜合加權法計算各航運中心的綜合指數(shù)(表2);同理,分別由貨運、服務、知識要素的原始數(shù)據計算出各航運中心的分項指數(shù)(即貨運、服務、知識要素指數(shù))。
(4)集中化指數(shù)。為進一步分析航運網絡空間分布格局,借鑒衡量區(qū)域經濟集中化程度的洛倫茲曲線集中化指數(shù)CI(式(5))分析航運網絡的集散情況,CI接近1表示航運要素流趨于集中,CI接近0則表示航運要素流趨于分散。
CI=(X-Y)/(M-Y)
(5)
式中:X為各航運中心綜合指數(shù)累計百分比;M、Y分別為綜合指數(shù)集中分布時和均勻分布時的累計百分比總和。

表2 航運中心的綜合指數(shù)Table 2 Comprehensive index of shipping centers
2 中國大陸航運中心層級體系與功能分化
2.1 航運中心層級體系
基于跨國航運企業(yè)組織關系網絡的航運中心相對網絡總關聯(lián)度,利用ArcGIS 10.8的分層聚類法將50個航運中心分為5類(表3),可見中國大陸航運網絡層級分化特征明顯并呈現(xiàn)紡錘狀結構,位于不同層級的航運中心承擔不同的專業(yè)化功能。第一層級為全球性國際航運中心,僅有上海,相對網絡總關聯(lián)度Na為78.510,占整個網絡總關聯(lián)度的22.98%,表明上海處于中國整個航運網絡金字塔的頂端,與其他航運中心聯(lián)系最緊密,中心性功能較強;第二層級為區(qū)域性國際航運中心,包括深圳、寧波—舟山、青島、廣州、天津、廈門、大連,在各區(qū)域發(fā)揮重要樞紐功能,Na占整個網絡總關聯(lián)度的66.71%且占比最大,在航運網絡資源配置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日益受到跨國航運企業(yè)組織的青睞;第三層級為國際航運節(jié)點,Na占整個網絡總關聯(lián)度的8.94%,第四層級為地方性航運中心,Na占整個網絡總關聯(lián)度的1.34%,第五層級為地方性航運節(jié)點,Na占整個網絡總關聯(lián)度的0.02%,中、低(第三、四、五)層級航運中心的相對網絡總關聯(lián)度雖遠低于高(第一、二)層級航運中心,但航運中心之間形成密集的聯(lián)系對,橫向延伸了航運網絡的廣度,形成龐大的航運網絡以吸引運輸倉儲等基礎性港航業(yè)務,充當支線港和喂給港角色,促進了地域間航運要素的流通與交換。

表3 基于航運企業(yè)組織關系網絡的中國大陸航運中心層級分布Table 3 Hierarchical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mainland shipping centers based on the connection network of shipping enterprise organizations
2.2 國際航運中心的主導功能差異
航運樞紐對航運網絡具有重要控制作用[27],分析表明中國大陸航運中心形成以上海、深圳、青島、寧波—舟山、廣州、天津、廈門、大連為樞紐的八大國際航運中心。利用航運中心的綜合指數(shù)及不同要素指數(shù)計算航運中心的航運要素比重構成,并通過SPSS對航運要素比重構成進行聚類分析,劃分出四大航運中心發(fā)展類型(表4),其中貨運型航運要素比重均超過32.61%,表明國際航運中心的建設離不開發(fā)達的貨運產業(yè)以吸引高附加值航運產業(yè)集聚。由圖1可知,2019年集裝箱吞吐量與航運中心層級變化趨勢密切相關,其中八大國際航運中心的集裝箱吞吐量處于領先地位,這些航運中心均具備建設深水港、深水航道的硬條件,為其航運服務產業(yè)的發(fā)展提供扎實的基礎。

表4 八大國際航運中心航運要素比重構成Table 4 Proportion of shipping elements for the eight international shipping centers

圖1 中國大陸航運中心綜合指數(shù)與2019年集裝箱吞吐量的關系Fig.1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and container throughput of Chinese mainland shipping centers in 2019
(1)貨運型國際航運中心。寧波—舟山的貨運比重高達56.08%,遠超其他航運中心的貨運比重,青島貨運比重為48.11%,珠三角地區(qū)的廣州(47.27%)、深圳(43.65%)、廈門(41.15%)貨運比重均超過40%,而環(huán)渤海地區(qū)的天津、大連由于腹地經濟支撐不足,其貨運比重較低。同時,寧波—舟山航運中心發(fā)展態(tài)勢良好且綜合指數(shù)僅次于上海國際航運中心,貨運功能是其核心功能,良好的港口基礎建設和完善的集疏運體系是其持續(xù)發(fā)展的驅動力量。
(2)貨運—服務型國際航運中心。服務型航運要素中跨國銀行、勞合社及國際保賠協(xié)會成員、中國郵輪母港與證券交易所的網絡重要節(jié)點主要分布在上海、深圳、天津和廈門,分別為64、24、18、15家,服務比重均超過32%,遠高于其他航運中心。上海、深圳、天津和廈門航運中心集聚的服務型航運產業(yè)以無形產品為主,服務消費與供給的即時性、信息的流通與傳遞對市場環(huán)境要求高,服務型企業(yè)組織之間還因存在相互依存關系而有著大量的業(yè)務聯(lián)系,在規(guī)模效應下,上海、深圳、天津和廈門航運中心資源規(guī)模大、航運產業(yè)基礎強,進一步吸引航運產業(yè)要素不斷匯聚。
(3)貨運—知識型國際航運中心。知識型航運企業(yè)組織在上海、廣州、青島、大連航運中心的機構分支分別為58、23、22、36家,而在廈門、天津、深圳的機構分支較少(共45家)。知識型航運要素是以知識和人力資本為基本生產要素,知識資本轉移和傳播較實體產業(yè)轉移慢[20],其區(qū)位選擇是跨時間的長期動態(tài)的過程,從而導致形成和轉變相對較慢,上海、廣州、青島、大連航運中心集聚的高等教育專業(yè)、國際航運協(xié)會、海事法律仲裁機構、國家開放政策等知識航運要素規(guī)模龐大,發(fā)展成為知識型航運中心的潛力相對較高。
(4)綜合型國際航運中心。上海貨運、服務、知識航運要素所占比重均在30%左右,要素分布均衡。總體看,上海航運企業(yè)組織的總部及分支共234家,班輪航線密集程度最大,覆蓋航線472條,相比其他航運中心集聚了大量的航運產業(yè)要素,依靠高度集聚的航運產業(yè)基礎可降低聯(lián)系成本,通過循環(huán)累計因果機制使這一集聚趨勢持續(xù)強化,新的航運產業(yè)和服務業(yè)態(tài)也在集聚的基礎上不斷交叉融合、擴展衍生。
3 中國大陸航運中心網絡聯(lián)系
3.1 航運網絡空間聯(lián)系的整體特征
3.1.1 相對網絡關聯(lián)度分析 航運中心間的聯(lián)系是因國際經濟貿易需求而產生的運輸聯(lián)系,并經航運企業(yè)組織分布在不同航運中心而實現(xiàn)。分析航運網絡的整體空間格局,目的在于考察中國大陸航運中心的主要組織方向,但因航運中心聯(lián)系數(shù)量過多,難以逐一分析,所以提取相對網絡關聯(lián)度前210位聯(lián)系構成主要航運中心間的網絡進行分析,結果表明:1)航運網絡穩(wěn)定在以高層級航運中心為重要節(jié)點的多核心結構。相對網絡關聯(lián)度前210位的航運中心構成的網絡共涉及34個航運中心,其總的相對網絡關聯(lián)度為144.266,其中與上海、深圳、寧波—舟山、青島、廣州、天津、廈門、大連產生聯(lián)系的為141.920,占總數(shù)的98.37%。這表明高層級航運中心與其他航運中心產生的聯(lián)系強度均較高,同時隨著相對網絡關聯(lián)度降低,關聯(lián)線數(shù)迅速減少,直觀反映了高層級航運中心構成航運網絡的基本框架,網絡骨架穩(wěn)定在深圳/廣州—上海—天津—大連/青島的菱形空間結構(圖2)。2)低層級航運中心的空間關聯(lián)較弱甚至存在斷層。低層級航運中心間的空間關聯(lián)性仍不夠緊密,從而使得整個航運網絡的要素流動不暢通,具體表現(xiàn)為低層級航運中心相對網絡關聯(lián)度普遍低于0.001,其相對網絡關聯(lián)度的總和為2.346,僅占總數(shù)的1.63%。目前,低層級航運中心發(fā)展相對孤立且發(fā)展方向不明確,自身缺乏承接輻射的基礎條件、人力資本,創(chuàng)新資源匱乏。

注:審圖號為GS(2020)4619號,底圖無修改。
3.1.2 不同航運要素網絡聯(lián)系分析 巨大的航運網絡使資本、產品、人員伴隨各種信息和知識在航運中心之間流動,網絡化、層次化和功能多元化是航運中心發(fā)展的必然趨勢,利用ArcGIS 10.8分層聚類功能分析不同航運要素航運中心的層級特征,并基于航運中心間最強和次強相對網絡關聯(lián)度,結合貨運型、服務型、知識型航運要素指數(shù),利用Gephi生成網絡圖(圖3),以揭示其網絡結構特征。

圖3 基于不同要素航運中心間強次聯(lián)系的中國大陸航運中心“軸—輻”圖Fig.3 "Hub-and-spoke" diagram of Chinese mainland shipping centers based on strong and sub-strong connections among shipping centers with different elements
(1)貨運型航運要素網絡中處于第一層級的有上海、深圳、寧波—舟山、青島,排名前五的聯(lián)系對為深圳—上海、上海—寧波—舟山、深圳—寧波—舟山、上海—青島、上海—廈門,整體形成更高效、穩(wěn)定的多中心網絡體系,全國性樞紐港—區(qū)域性樞紐港—干線港—支線港—喂給港層級體系明顯。從貨運要素分布看,造船廠、跨國航運公司、全球貨代物流公司和國際航線等勞動和技術密集型行業(yè)與集裝箱網絡關聯(lián)密切,因而其業(yè)務活動傾向于分散化布局,網絡結構輻射較廣,是許多航運中心的主導產業(yè)。
(2)服務型航運要素網絡中處于第一層級的有上海、廣州、深圳,排名前五的聯(lián)系對為上海—深圳、上海—天津、上海—廣州、上海—大連、上海—廈門,均與上海的聯(lián)系較強,其他航運中心的聯(lián)系較少且相對網絡關聯(lián)度偏低。與貨運型、知識型航運要素網絡相比,服務型航運中心的最強和次強聯(lián)系對數(shù)量明顯減少,涉及30個航運中心節(jié)點,比貨運型航運節(jié)點少20個,比知識型航運節(jié)點少19個。從服務要素看,由于航運服務行業(yè)的內在屬性,受自然條件的限制相對較小,對信息聯(lián)系和社會關系的依賴程度較高,服務資源規(guī)模大、產業(yè)基礎強的航運中心可突破地域限制,服務多個航運中心。
(3)知識型航運要素網絡中處于第一層級的有上海、大連、寧波—舟山、廣州、青島、天津,排名前五的聯(lián)系對為寧波—舟山—大連、大連—青島、大連—上海、上海—寧波—舟山、上海—廣州,相對網絡關聯(lián)度強的聯(lián)系對主要集聚在第一層級,且第一層級航運中心的輻射范圍明顯大于貨運型和服務型航運要素網絡,形成較完整的“軸—輻”網絡體系。從聯(lián)系對看,航運中心間的強次聯(lián)系流近半數(shù)與上海有關,其相對網絡總關聯(lián)度占整個網絡總關聯(lián)度的42.5%,航運網絡以上海為核心并向全國輻射,其中大連、寧波—舟山、廣州、青島、天津具有較弱程度的次中心發(fā)育態(tài)勢,航運中心間“軸—輻”功能協(xié)作增強,實現(xiàn)了聯(lián)動發(fā)展。
3.2 區(qū)域航運網絡聯(lián)系的差異分析
根據航運中心最強、次強首位聯(lián)系以及區(qū)域航運中心聯(lián)系,結合航運中心綜合指數(shù),利用Gephi生成網絡圖。如圖4所示,中國大陸航運中心呈現(xiàn)局部密集的網絡格局,圍繞上海和寧波—舟山、深圳和廣州、天津和青島以及廈門和福州、海口組成龐大的“3+2”區(qū)域聯(lián)系網絡格局,長三角區(qū)域是連接中國大陸航運中心最重要的區(qū)域網絡。從各區(qū)域航運網絡的內部分析,天津/青島/大連、上海、廈門、深圳/廣州、海口和各區(qū)域航運網絡內部航運中心相對網絡關聯(lián)度總和與對應區(qū)域航運網絡內部總關聯(lián)度的比值分別為47.11%、59.53%、54.68%、54.55%、42.05%,表明國際航運中心具有較高的首位度,在區(qū)域航運網絡中占據重要地位,其中上海最突出。

圖4 中國大陸航運中心首位聯(lián)系區(qū)域網絡分布Fig.4 Network profile of the first contact areas of Chinese mainland shipping centers
由表5可知,區(qū)域航運網絡內部總關聯(lián)度、區(qū)域航運網絡外部總關聯(lián)度(區(qū)域航運中心與其區(qū)域航運網絡外航運中心的相對網絡關聯(lián)度總和)及其內外部比值均呈現(xiàn)長三角、珠三角、環(huán)渤海、東南沿海和西南沿海區(qū)域依次遞減趨勢,相較于東南沿海和西南沿海區(qū)域,長三角、珠三角和環(huán)渤海區(qū)域航運中心在中國大陸航運網絡中聯(lián)系對多且對內對外總關聯(lián)度較高。長三角區(qū)域航運網絡內部總關聯(lián)度最強且與其他區(qū)域航運中心聯(lián)系密切,能突破地域限制集聚較多的首位聯(lián)系,航運產業(yè)的發(fā)展更具有活力和自發(fā)性,其航運中心上海以發(fā)達的城市群經濟和成熟的航運市場機制,對全國沿海地區(qū)的航運要素形成較強的“虹吸效應”,全區(qū)域形成“內外雙修”的局面;環(huán)渤海和珠三角航運中心主要與長三角航運中心建立最強和次強聯(lián)系,其內外部比值遠低于長三角區(qū)域,其次,環(huán)渤海和珠三角區(qū)域內部的航運市場發(fā)展差異性較大,形成以外向引領內向均衡發(fā)展的格局,為開拓腹地市場、服務接納航運產業(yè)轉移和入駐夯實基礎。在區(qū)域網絡的研究中,珠三角與長三角相比對內對外關聯(lián)度稍弱,需要說明的是,本研究將港、澳2個航運中心排除在外,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珠三角區(qū)域的地位。

表5 五大區(qū)域航運網絡內外部關系Table 5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lationships of the five regional shipping networks
3.3 集中化指數(shù)分析
從企業(yè)組織關系網絡考察單個航運中心與其他港口聯(lián)系圈的集中化程度,可以反映航運中心海上腹地聯(lián)系的廣度和強度。航運中心網絡聯(lián)系集中化指數(shù)(CI)(圖5)呈現(xiàn)三方面特征:1)不同航運中心網絡聯(lián)系集中化程度差異較大。總體看,航運中心層級越高,其網絡聯(lián)系CI越高,具有國際航運職能的前三層級航運中心的CI下降相對平穩(wěn),而第四、五層級的地方性航運中心及地方性航運節(jié)點的CI波動較大,且與前三層級航運中心差距明顯。2)綜合CI與分項CI呈現(xiàn)不同特征。綜合CI與貨運CI隨航運中心層級的降低而逐漸減小,二者的決定系數(shù)R2達到0.8891,說明在目前的發(fā)展階段,我國單個航運中心的“綜合聯(lián)系圈”取決于其“貨運聯(lián)系圈”。集中化程度在前三層級航運中心變化穩(wěn)定,在第四、五層級航運中心則出現(xiàn)巨大的波動,說明航運中心層級越高其對外聯(lián)系的“朋友圈”越穩(wěn)定。服務CI與綜合CI的決定系數(shù)R2為0.5584,兩者相關性較低,珠三角區(qū)域和長三角區(qū)域的大部分航運中心的服務CI在0.62以上,集中化程度較高。知識CI與綜合CI的擬合R2為0.3369,兩者相關性極低,前者呈無規(guī)律波動變化且數(shù)值整體低于后者。3)服務、知識CI波動明顯。服務CI僅在第一層級航運中心的波動較小,在其他層級航運中心的波動較大,而知識CI整體波動較大,表明服務、知識要素在航運網絡的分布趨于分散化,國際航運中心在航運體系中的樞紐地位被削弱,航運中心更傾向于均衡化、網絡化發(fā)展,空間差異趨向縮小。

圖5 中國大陸航運中心不同航運要素集中化指數(shù)Fig.5 Centralization index of different shipping elements of Chinese mainland shipping centers
4 結論與討論
國際航運中心是航運要素集聚的“洼地”,使航運業(yè)產業(yè)形成集群,提升全球航運資源配置。本文基于航運企業(yè)組織機構布局數(shù)據,采用社會網絡分析法和ArcGIS 10.8、Gephi可視化工具,揭示中國大陸航運中心層級體系與網絡聯(lián)系的一般特征。1)中國大陸航運中心層級體系形成紡錘狀結構,分為全球性國際航運中心、區(qū)域性國際航運中心、國際航運節(jié)點和地方性航運中心、地方性航運節(jié)點5個層級,且位于不同層級的航運中心承擔不同的專業(yè)化功能,上海、深圳、寧波—舟山、青島、廈門、廣州、天津、大連八大國際航運中心發(fā)揮重要的樞紐功能,形成以深圳/廣州—上海—天津—大連/青島為基本網絡骨架的菱形結構,中、低層級航運中心充當支線港和喂給港的角色,其聯(lián)系對數(shù)量大幅增加,但低層級航運中心的空間關聯(lián)較弱甚至存在斷層,使得整個網絡的航運要素流動不順暢。2)不同航運要素網絡聯(lián)系和層級分布顯著不同,貨運型航運要素形成上海、深圳、寧波—舟山、青島四大國際航運中心,服務型航運要素形成上海、廣州、深圳三大國際航運中心,知識型航運要素形成上海、大連、寧波—舟山、廣州、青島、天津六大國際航運中心。由于航運產業(yè)的內在屬性和區(qū)位稟賦特性,貨運型航運要素網絡體系最穩(wěn)定且成熟,服務型航運要素網絡聯(lián)系相對較弱,輻射范圍最小,知識型航運要素網絡形成較為完整的“軸—輻”結構。八大國際航運中心航運要素集聚程度已具相當規(guī)模,呈現(xiàn)上海向綜合型國際航運中心發(fā)展,寧波—舟山向貨運型國際航運中心發(fā)展,廣州、青島、大連向貨運—知識型國際航運中心發(fā)展,天津、深圳和廈門向貨運—服務型國際航運中心發(fā)展的態(tài)勢。3)不同航運中心綜合集中化指數(shù)差異大,隨航運中心層級降低而逐漸減小。貨運集中化指數(shù)與綜合集中化指數(shù)高度擬合,集中化程度在第一、二、三層級航運中心變化穩(wěn)定,在第四、五層級航運中心波動性巨大,表明航運中心層級越高,對外聯(lián)系圈越穩(wěn)定,而服務與知識型集中化指數(shù)波動性巨大,說明目前我國單個航運中心的“綜合聯(lián)系圈”主要取決于 “貨運聯(lián)系圈”。中國大陸航運中心呈現(xiàn)“3+2”區(qū)域格局,長三角區(qū)域形成“內外雙修”的格局,是連接中國大陸航運中心最重要的區(qū)域網絡,環(huán)渤海和珠三角區(qū)域外向聯(lián)系較突出。
本文初步探討了航運企業(yè)組織全產業(yè)鏈的中國大陸航運中心的層級分化、網絡關聯(lián)度、區(qū)域網絡格局以及多視角航運要素網絡聯(lián)系與層級分布情況,揭示了網絡節(jié)點層級性、網絡關聯(lián)性及網絡差異性等空間特征。由于航運產業(yè)機構數(shù)據更新速度快,數(shù)據獲取難度較大,可能導致網絡構建不全,且缺乏網絡的縱向演化特征,未能對航運機構的布局變遷、航運機構進入時間路徑對應的航運中心時空特征進行分析;加之受連鎖網絡模型的限制,僅考慮了企業(yè)地理布局聯(lián)系,未能深入研究企業(yè)內聯(lián)系與企業(yè)間聯(lián)系,有待后續(xù)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