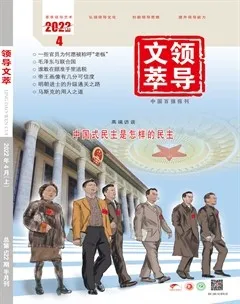烏克蘭:“歐洲之門”的困境
孔田平
烏克蘭素有“歐洲之門”之稱,2013-2014年曾與俄羅斯兵戎相見,如今再次成為全球地緣政治的焦點,其命運受到國際關注。
烏克蘭成為現代獨立國家的歷史僅有30余年,但在其土地上曾經上演過一幕幕至今對烏克蘭國運仍有深刻影響的歷史戲劇。今日烏克蘭的土地曾是多民族共有的家園,烏克蘭人、俄羅斯人、波蘭人、猶太人、韃靼人、白俄羅斯人、保加利亞人、希臘人、亞美尼亞人、德意志人、羅馬尼亞人等長期在此生活。直到16世紀,烏克蘭作為地區名稱才被廣泛使用,當時意指“波蘭王國的邊境地區”(“烏克蘭”在斯拉夫語中有“邊緣”“邊疆”“邊境”之意)。
1667年,俄波簽署《安德魯索沃停戰協定》,沿第聶伯河瓜分烏克蘭土地,俄羅斯獲得“左岸烏克蘭”(第聶伯河東岸),波蘭控制“右岸烏克蘭”(第聶伯河西岸)。烏克蘭人把1648-1667年這段歷史視為烏克蘭人對波蘭壓迫的反抗時期,俄羅斯人則認為這段歷史是“迷失的烏克蘭溪流重歸俄羅斯大河”的時刻。
從18世紀末到20世紀初,烏克蘭土地一直是奧地利帝國(后來的奧匈帝國)和俄羅斯帝國這兩個帝國的一部分。在俄羅斯帝國內部,分布在第聶伯河東西兩岸的人被稱為“小俄羅斯人”,這個地區則被稱為“小俄羅斯”。而烏克蘭土地上更多的人則自認為“魯塞尼亞人”。
第一次世界大戰導致奧匈帝國和俄羅斯帝國崩潰。十月革命后,在烏克蘭的土地上曾成立烏克蘭人民共和國、西烏克蘭人民共和國(“利沃夫”)。1918年底至1921年8月,紅軍為解放烏克蘭與白軍、波蘭軍隊、烏克蘭軍隊和哥薩克農民武裝展開爭奪廝殺。1922年,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加入蘇聯,此后蘇聯在當地推行本土化政策,鼓勵烏克蘭語的使用。1954年,蘇聯將克里米亞州劃歸烏克蘭蘇維埃共和國。蘇聯時期,烏克蘭是蘇聯的農業、鋼鐵、軍工生產基地,也是黑海艦隊和蘇聯核武庫所在地。
蘇聯解體后,烏克蘭事實上成為有核國家。1994年美國、英國和俄羅斯與烏克蘭簽署“布達佩斯備忘錄”,烏克蘭以棄核為條件換取安全保障,各國尊重烏克蘭的獨立、主權和邊界。烏克蘭獨立30年來,國家被寡頭等既得利益集團俘獲,未形成穩定而成熟的政治體制,國家構建的任務至今都沒有完成。2004年親俄政治家與親西方政治家的選舉之爭引發“橙色革命”,2013-2014年因亞努科維奇總統拒絕簽署與歐盟的聯系協定爆發“廣場革命”,最終導致克里米亞被并入俄羅斯,烏克蘭東部成為沖突區。
烏克蘭不僅是自身歷史的塑造者,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俄羅斯歷史的塑造者。在俄羅斯帝國時期有“大俄羅斯”“小俄羅斯”和“白俄羅斯”的概念。烏克蘭與俄羅斯不同的歷史敘事成為影響烏俄關系的一個因素。2003年時任烏克蘭總統庫奇馬出版了《烏克蘭不是俄羅斯》一書。2021年俄羅斯總統普京發表長文《論俄羅斯人與烏克蘭人的歷史統一》,強調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是“同一個民族”,現代烏克蘭是蘇聯的產物。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則聲稱,很難認為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有什么兄弟情誼。
烏克蘭處在西方與俄羅斯之間,其地緣政治選擇備受大國等重要國際行為體的關注。就面積而言,烏克蘭國僅次于俄羅斯是歐洲第二大國。烏克蘭曾是俄羅斯向歐洲供應能源的樞紐,但“北溪-2”天然氣管道的建成削弱了其在歐洲能源供應中的地位。
獨特的地理位置使烏克蘭成為影響歐亞大陸地緣政治格局的重要國家。在蘇聯解體的過程中,作為蘇聯第二大加盟共和國的烏克蘭發揮了關鍵作用。獨立的烏克蘭成為歐亞大陸地緣政治的敏感地帶。
1997年,美國著名的地緣政治專家布熱津斯基認為,“烏克蘭是一個地緣政治支軸國家。沒有烏克蘭,俄羅斯就不再是一個歐亞帝國。少了烏克蘭的俄羅斯仍可爭取帝國地位,但所建立的基本上是一個亞洲帝國,并且更有可能被卷入與覺醒了的中亞人的沖突而付出沉重代價”;“如果莫斯科重新控制了擁有5200萬人口、重要資源及黑海出海口的烏克蘭,俄羅斯將自然而然重獲建立一個跨歐亞強大帝國的資本。烏克蘭喪失獨立將立即影響到中歐,使波蘭變為一體化東部前沿的地緣政治支軸國家”。
烏克蘭能否保持獨立,不僅直接影響俄羅斯,也會影響波蘭等中歐國家。在歐盟和北約擴大之后,烏克蘭事實上成為俄羅斯與歐洲之間的緩沖地帶。早在2014年3月初俄在克里米亞有所動作之時,布熱津斯基就說,如果俄羅斯準備奪取克里米亞,最終就會擁有克里米亞,而烏克蘭將會永遠失去克里米亞,也就永遠不會原諒俄羅斯。經歷了2013-2014年的烏俄關系危機,烏克蘭的地緣政治選擇更加明確。2019年,參與歐洲一體化和“歐洲-大西洋一體化”作為國家發展愿景被寫入烏克蘭的憲法。
當前俄羅斯與烏克蘭沖突的升級,源于冷戰后歐洲安全結構未能考慮俄羅斯的安全關切,未能建立一個公平、包容的和平秩序。隨著冷戰結束,蘇聯主導的軍事聯盟華約宣布解散,而美國主導的北約并未退出歷史舞臺。
在2007年的德國慕尼黑安全論壇上,俄總統普京嚴厲抨擊北約東擴,強調北約過去曾承諾不會在德國東邊部署軍隊,俄認為這是北約對俄安全所作的保證,但北約軍力日益逼近俄羅斯。
烏俄關系緊張升級后,俄方提出了“歐洲安全條約”方案,沒有獲得美西方的積極回應。這個方案包括北約從中東歐國家撤軍,回到1997年的狀態;撤銷2008年北約布加勒斯特峰會決議,確保烏克蘭和格魯吉亞不加入北約。西方拒絕俄羅斯的建議,希望討論相互安全保證和軍控等現實問題。力主歐洲“戰略自主”的法國總統馬克龍與俄羅斯開始討論歐洲安全秩序,認為如果俄羅斯不安全,歐洲也不會安全。由于歐洲安全體系涉及多方利益,近期形成容納俄羅斯關切的歐洲安全體系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烏俄關系的困境在于雙方安全關切的沖突及信任的缺乏。2014年失去克里米亞、頓巴斯成為“凍結的沖突區”之后,烏克蘭把實現自身安全的希望寄托于加入北約,但這構成對俄利益的根本性挑戰,是俄不可接受的“紅線”。2021年普京曾警告“烏克蘭正一步步被拖入一場危險的地緣政治游戲”,“成為對抗俄羅斯的跳板”,“只有與俄羅斯合作,烏克蘭才有可能獲得真正的主權”。普京曾把蘇聯解體稱為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在蘇聯解體30年之際,他又將蘇聯解體描述為“以蘇聯為名”的“歷史上的俄羅斯的解體”。今天,俄羅斯仍未完全從帝國解體的創傷中恢復過來,重現昔日輝煌仍是俄精英夢寐以求的目標。烏克蘭既已選擇“脫俄入歐”之路,就要直面烏俄關系無解的現實。烏克蘭想要叩開“歐洲之門”,但這扇門的鑰匙掌握在包括俄羅斯在內的大國手中,烏克蘭無法掌控自身命運。
(摘自《世界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