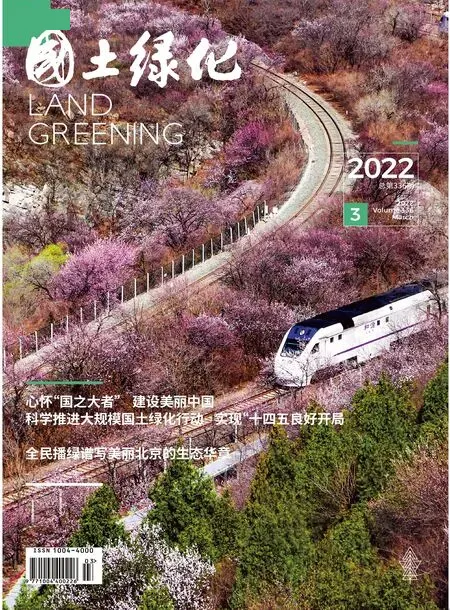榆樹婆娑
潘春華

榆樹,又名春榆、白榆等,為榆科落葉喬木,分布于我國東北、華北、華中、西北及西南各地。榆樹花先葉開放,在葉腋處呈簇生狀,進入四月中旬結成翅果,即“榆莢”,俗稱“榆錢兒”。榆樹樹干通直,樹形高大,虬枝茂密、綠蔭婆娑,適應性強,生長快,是城市綠化、行道樹、庭蔭樹、工廠綠化、營造防護林的重要樹種。其老莖殘根萌芽力強,可制作盆景。
我國榆樹栽培歷史悠久,先秦時已廣泛栽植。《詩經?唐風》中提到過榆樹:“山有樞,隰有榆。”漢代有“壘石為城,植榆為塞” 之說。唐代長安,大街兩側及排水溝旁皆廣植榆樹和槐樹,且株行距離整齊劃一。陜西省咸陽市永壽縣甘井鎮境內存有一棵南北朝時期的古榆樹,距今已有1600 余年的樹齡。該樹高近20 米,主干粗大,樹身7 人合抱。樹冠覆蓋面積242 平方米,樹根凸露地面,盤根錯節,酷似蛟龍臥地。更為神奇的是,樹身表皮極似豹皮紋身,四季色變,甚為罕見。
古往今來,不少文人騷客留下了許多有關榆錢的詩詞佳話。唐代詩人施肩吾《戲詠榆莢》詩曰:“風吹榆錢落如雨,繞林繞屋來不住。知爾不堪還酒家,漫教夷甫無行處。”北宋詩人歐陽修在《和較藝書事》中寫道:“杯盤餳粥春風冷,池館榆錢夜雨新。”清代詩人郭誠在《榆莢羹》詩中贊美:“自下鹽梅入碧鮮,榆風吹散晚廚煙。揀杯戲向山妻說,一箸真成食萬錢。”
清乾隆時,有一落魄文人無意中寫了一首榆錢詩,竟引出一段惺惺相惜的佳話。某年,“隨園老人”袁枚偶過河北良鄉,見旅舍壁上題有一詩:“滿地榆錢莫療貧,垂楊難系轉蓬身。離懷未飲常如醉,客邸無花不算春。欲語性情思骨肉,偶談山水悔風塵。謀生消盡輪蹄鐵,輸與成都賣卜人。”末書“篁村”二字。袁枚讀后大為激賞,便寫了一首和詩,內有“好疊花箋抄稿去,天涯沿路訪斯人”之句。可是人海茫茫到哪兒去訪這位篁村先生呢?不想十幾年后,袁枚在一友人家里見到一位名叫陶云藻的客人,知此即是“篁村”后,大喜,述前事。兩人感慨久之,遂訂交成好友。
榆樹既沒有槐的才干功名又無柳的姿態風流,之所以能贏得古人青睞,概因它的葉、花、莢、皮、根皆可當糧充饑,是一種“活命樹”“吉祥樹”“救荒樹”,是歷史上災荒年景的“救命”樹種。

榆錢
《本草綱目》記載:榆嫩葉炸,浸淘過可食……三月采榆錢可作羹(湯),亦可收至冬釀酒。瀹過(即浸漬后)曬干可為醬,即為榆仁醬也。榆樹葉纖維少,味道不苦不澀,是荒年填補糧食空缺的主要食物來源。榆樹花和榆錢,串串誘人,是天然的營養食品。《帝京景物略》云:北京每到四月,“榆初錢,面和糖蒸食之,曰榆錢糕”。榆樹的皮和根均可當糧充饑,把榆樹皮的外層老皺皮刮掉,將里邊的一層嫩白粘皮揭下來用石頭砸爛,再經過數次淘洗過濾曬干后,就可以摻上些粗糧、谷糠或野菜捏成“榆皮粉窩窩頭”吃。
青黃不接的春荒之際,吃沒了榆樹花、榆錢,再吃榆葉,吃凈了榆葉就干脆扒榆樹皮充饑。在歷史上饑腸轆轆的年代,榆樹的價值便突出了。先秦時人們已發現了榆樹的救荒功能。《神農本草經》稱,榆樹皮“久服輕身不饑,其實尤良”,將之與“槐實”“枸杞”等,同列為“上品”。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稱:“荒歲,農人取皮為粉,食之當糧,不損人。”
因為榆樹有這些特殊用途,所以古時家家不忘栽上幾棵榆樹。民諺云:“栽下榆樹防饑荒,家有榆樹心不慌。”東晉辭官歸隱的陶淵明,在院中便栽植了榆樹,他在《歸園田居?其一》中說:“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后檐,桃李羅堂前。”每到柳絮飄逸的春季,采摘榆錢成為一景,真所謂“柳絮飄逸似雪花,榆錢糊口可當家。攀枝哨鳴孤膽在,暗許心愿意無瑕。”
古人對榆樹的俗稱“榆錢”也很在意。明李時珍《本草綱目?木二》“榆”條釋稱:“其木甚高大,未生葉時,枝條間先生榆莢。形狀似錢而小,色白成串,俗呼‘榆錢’。”“榆錢”諧音“余錢”,古人栽植榆樹,也有討口彩、求吉利寓意,即所謂“ 榆錢、榆錢,家家余錢”“陽宅背后栽榆樹,銅錢串串必主富”。
中醫認為,榆錢及榆樹的皮、葉、根皆是治病除疾的良藥。榆錢味微辛,性平;皮葉味甘,性平。榆錢有安神健脾功效,用于神經衰弱,失眠,食欲不振,白帶等癥;皮、葉可安神、利小便,適用于神經衰弱,失眠,體虛浮腫治療。救荒時,榆樹的食藥價值更為珍貴。
然而,明文震亨《長物志》則另有理解:“槐榆宜植門庭,極扉綠映,真如翠幄。”清代名醫陳庭敬在《堪輿手記》中也說:“宅第欲求人安逸,東種桃柳西榴榆,南種青梅與紅棗,北種杏花高樹立。”因為榆樹的枝葉可擋住西曬太陽,故栽于宅之西最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