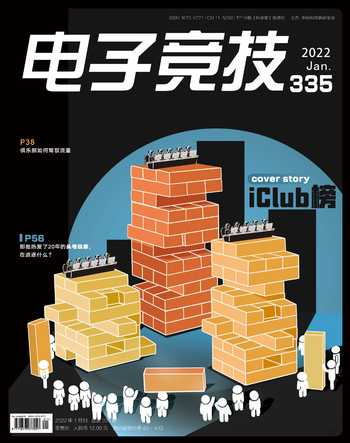用勇氣和智慧迎接改變
楊直
“昨天你說我快奔三的人了,也配打職業?今天你叫我哥,說我二十出頭未來可期?”
電競圈從不缺少梗,哪怕在身陷困境之時。
2021年9月1日前,LPL、KPL等賽事聯盟紛紛發布了旗下賽事選手年齡合規調查和調整的通知,哪怕為此付出的代價是重新規劃已經定好的賽事流程。
這意味著,之前各個賽事關于年齡的規定將不再有效力,18周歲將成為唯一的標準,那些年齡不夠的選手將提前“退役”。
沖擊是顯而易見的。
某職業聯賽轉會期的“標王”年齡剛滿16周歲,同一聯賽里另一支隊伍剛剛從青訓提拔上來的三名主力選手,也都剛滿16周歲。有的賽事聯盟被迫臨時開啟“二次轉會”。
即便一些俱樂部反應再慢,從通知發布的第二天起,隊員招募標準的第一條都調高了年齡下限。激進一點的,甚至隱晦地傳遞出一種不管代價如何的倉促。
考慮到一些已經開始尋求轉型的前青訓選手,俱樂部在這些人身上顯性或隱性的投入也將成為沉沒成本。
轉型的陣痛來得如此快、明顯,以至于面對突如其來的變化,很多粉絲都略顯悲觀。在一些調整公告的下方,高贊的回答幾乎都在說同一件事情:電競產業即將失去自己的未來。
即便正在經歷轉型的陣痛,也不必如此悲觀。
的確,青訓儲備的意外流失會對電競現有的訓練體系形成直接的沖擊,但儲備的池子里仍有余量,未來幾年里,電競產業并不會直接陷入“選手荒”的困境。
而默認的“年齡與成績”之間的聯系也不如想象中那般牢靠。
就像雜志主編在8月30日的專欄里提到的:
“根據Liqiupedia上的數據,S9英雄聯盟世界冠軍FPX奪冠時,5個成員里,只有Tian是低于20歲的。FPX的中單選手Doinb那年是23歲,如今是25歲;下路雙人組那年是21歲,如今是23歲。顯然,在今年的英雄聯盟賽事里,我們仍然能看到FPX表現出的統治力,25歲的Doinb好像更強了。也沒有任何科研機構的數據表明,電競是一個需要從15歲就開始訓練的項目,也沒人知道年齡和競技水平之間的關聯拐點在哪里。”
以18歲為節點,向前看,存在著體系性的解決方案;向后看,訓練體系的革新將支撐選手在年齡上整體進行平移。
無論如何,這都不是一個死局,一切取決于電競行業如何應對。
2021年上半年,曾有一小段時間,電競產業向外充分展示了“戒網癮”的能力。但在硬幣的另一面,當涉及到“未成年人”的問題時,電競仍然無法獨善其身。
在16-22歲,或者一個更寬的年齡跨度里,選手在俱樂部的體系里不停高速流轉,更多20歲出頭就退役的選手隱沒在沒人注意到的地方。

這里就有一個悖論:當電競在某個人16歲的時候將他“救出深淵”,納入俱樂部并教會其名為“電競職業”的技能時,一旦他表現不佳,那么電競將再次把他推回這個深淵,而且,他將擁有更少脫離深淵的可能性。
這時,俱樂部和選手之間實際上構建了一種非常奇怪的關系。
一個直接的對比恰恰是剛剛分手的巴塞羅那和梅西。因為看上了他的天賦,巴塞羅那從梅西13歲時開始為他治療“荷爾蒙生長素分泌不足”。從那時起,二者一同譜寫了現代體育的一段佳話。
延長選手或明星選手的職業生涯,早已不單純有著商業化上的需求。
在個體層面,它將減少選手所面臨的不確定性,并在群體層面給予整個產業更強力的合理性。這是過去幾年里電競聯盟在選手退役保障上十分用力卻始終不可得的結果。
在競技層面,這次奧運會上老運動員們的表現充分證實了,它將讓選手迭代的過程更具備彈性。換句話說,今天的很多擔憂將會被徹底地抹除。
更重要的是,調整之后的電競行業將可以預見地呈現出另一種全新的面貌,這恰恰是電競產業當下需要的。
2016年之前,在實用主義的維度,電競接納了那些傳統意義上的網吧少年,對內滿足了選手迭代的需求,對外則妥善安置了這些人。
不僅如此,電競還讓他們得以收獲巨大的財富,獲得“重啟”人生的鑰匙。
但從2016年往后,隨著影響力的擴大,電子競技賽事早已過了“單純論輸贏”的階段,賽事、選手乃至整個電競行業都在主動或被動地承擔起越來越大的責任。
像是沿著馬斯洛夫的需求之塔向上走一樣,電競產業需要在更高的維度證實自己的價值。
于是,整個電競產業開始以一種極為明顯的方式尋求來自主流評價體系的認可:對高學歷的偏愛。從職業賽事到業余賽事都是如此。
對內,一個更完美的明星選手對于一個市場化運營的商業賽事而言,永遠利大于弊;而對外,電競也需要一個或多個“楊倩”來獲得更廣泛受眾的認可。
這次規范化的調整讓后者成為現實的概率不再是零。
任何一項賽事,當其得到更廣泛受眾的注意時,選手總會作為一種標志率先進入人們的視野。他們要接受來自各個維度的審視,這就是我們常說的主流的評價體系。
電競不可能對抗它,只能尋求它的認可。考上大學,休學成為職業選手和在基礎教育階段過早地離開學校,成為職業選手,存在著本質的不同。
不僅僅是整個產業不再需要為選手的年少無知和年少輕狂埋單,更重要的是賽事品牌得以根本性地重塑,這在無形中穩固了整個行業的根基。
說到底,比起金蛋會被孵蛋的鵝壓碎,下蛋的鵝難產而死才是最壞的結局,但很明顯,情況遠未到那個地步。
用勇氣和智慧迎接改變,而非抱著既有路徑不放,才是當下應有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