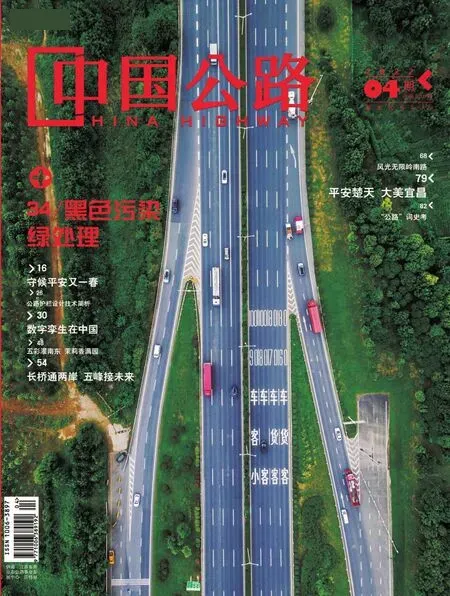“公路”詞史考
文 周緒利 周佳楠
通過對我國交通史、道路史、公路史的研究,筆者發(fā)現(xiàn)對于古代道路、現(xiàn)代公路和高速公路的概念及發(fā)展,是基本清晰而準確的,但于“公路”一詞的演變過程卻挖掘不足,缺少從古代到近現(xiàn)代公路的文化發(fā)展脈絡(luò),特別是近代公路的發(fā)展情況闕如,實有必要進行探究,以供參考利用。
從“路”說起
文字、術(shù)語、概念具有發(fā)展性、多樣性。自從有了人類在大地上行走,便有了路,并逐漸有了路的概念。隨著文字、文化、文明的演進,“路”在本義“道路”“通行的地方”這一基礎(chǔ)上,產(chǎn)生了許多引申含義,變得豐富起來。
《爾雅·釋宮》稱“路、旅,途也。路、場、猷、行,道也。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歧旁,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劇驂,八達謂之崇期,九達謂之逵。”《論語》中子曰“予縱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易·說卦》記載,“艮為徑路。”
《爾雅·釋詁》又稱“路,大也。”王在焉曰路。“路訓大也,君之所在、以大為號,門曰路門、寢曰路寢、車曰路車。”皆取中正通達之義。西周中期青銅器“史懋壺”上便撰有“親令史懋路筮”的銘文。

秦直道示意圖
《周禮·地官》則對“途、徑、道、路”等析分有度。文中記載“遂人掌邦之野。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途;千戶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有注曰“遂徑途道路,皆所以通車徒于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途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
此外,“路”還通“輅”,是一種車,多為君王等所用。《左傳》“大路越席”注為“大路:玉路,祀天車也。”至今留存于成語的“篳路藍縷”便出自于《左傳·宣公十二年》,“篳路”即柴車。“路”也通“露”,指暴露、敗壞。
而東漢許慎編纂的《說文解字》中對“路”的描述是“道也,從足從各。”清段玉裁作《說文解字注》指出:《釋宮》“一達謂之道路”,此統(tǒng)言也;《周禮》記載“澮上有道、川上有路”,此析言也;《爾雅》《毛傳》稱,“路,大也”,此引申之義也。
《詩經(jīng)》里共十一首含“路”字,義分五類。其一,為《遵大路》中的“遵大路兮,摻執(zhí)子之手兮”,為“道路”本義;其二,為《生民》中的“實覃實吁,厥聲載路”和《皇矣》中的“帝遷明德,串夷載路”,為“大”;其三,為《宮》中的“松桷有舄,路寢孔碩”,為“大”、為“正”;其四,為《崧高》中的“王遣申伯,路車乘馬”和《渭陽》《采薇》《采芑》《采菽》《韓奕》中的“路車”,皆為“車”;其五,為《汾沮洳》中的“美無度,殊異乎公路”,也為“車”,但“公路”與“公行”“公族”同義,是指“貴族”,即掌公車的人。
至今,《辭海》里“路”的十三個義項里,除第一項的“道路”、后四項的“車”“大”,通“露”及用作姓氏以外,其他八項都是“道路”的近義和擴展,如“門路”“紋路”“思路”“路線”“路程”“方面”“種類”“行列”等。宋元時期,“路”還被用作行政區(qū)名。《現(xiàn)代漢語詞典》里少了“車”“大”、通“露”等含義,九個義項中除姓氏以外,其余類似。可見,“路”是通行的、寬泛的,“公路”一詞的基礎(chǔ)是扎實的。
古代“公路”
在古代,“公路”一詞出現(xiàn)的頻率并不高,遠低于“路”“道”及“道路”,作本義時更屈指可數(shù)。如《詩經(jīng)》中《大東》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何草不黃》云“有棧之車,行彼周道。”史上先有周道,后有秦馳道、直道,明清的官道、大路、驛路等。與發(fā)達的道路相比,可以說是幾無公路。“公路”的用法比較單一,主要可分為以下四種情形。
其一,路車,轉(zhuǎn)指官職、掌公車的人。見于《詩經(jīng)·汾沮洳》“美無度,殊異乎公路”及相關(guān)文獻。《詩經(jīng)正義》孔穎達疏“公路與公行一也,以其主君路車謂之公路,主兵車之行列者則謂之公行,正是一官也。此公族、公行,諸侯之官,故魏、晉有之。”
其二,人名。三國時期的袁術(shù)(?-199年),字公路,汝南汝陽(今河南省商水縣)人,袁紹的從弟,東漢末年軍閥。北魏酈道元所著的《水經(jīng)注》載“洛水又東,合水南出半石之山,北徑合水塢,而東北流注于公路澗。但世俗音訛,號之曰光祿澗,非也。上有袁術(shù)固。”“淮陰縣城西二里,有公路浦,昔袁術(shù)自九江東奔袁譚,路出茲浦而得名。”公路澗舊志在偃師縣南三十里。范仲淹詩《和人游嵩山十二題》其一為“公路澗”,曰“嵩高發(fā)靈源,北望洛陽注。清流引河漢,白氣橫云霧。英雄惜此地,百萬曾相距。近代無戰(zhàn)爭,常人自來去。”因為袁術(shù)的緣故,至今還留存了“公路澗”“公路浦”“公路城”“公路壘”等地名。
其三,道路本義。如唐房玄齡等人合著的《晉書》載,廣陵人劉頌在郡上疏,其中有“何異放兕豹于公路,而禁防盜于隅隙。”這里的“公路”就是道路的意思。
其四,正路、言路。如《宋名臣奏議》載上官均奏“薦舉之人唯權(quán)與舊,則公路塞而真才棄矣。”子先上陳“將使公路日清、私請漸塞。”劉安世奏“賄賂盛行、塞公路、綱紀大壞。”宋李燾著《續(xù)資治通鑒》載李淑嘗上時政十議,其中有“任職則浮夸,貢言則擊搏,輒飾智詐,不畏譏誚,驕蹇貪冒,甚非公路。”宋周必大撰《文忠集》有“圣主大開公路,臨照百官。”明黃仲昭《八閩通志》載宋上官愔言“宜謹號令,振士氣,杜私門,開公路。”
近代“公路”
近代,無疑是“公路”概念發(fā)展承前啟后的重要時期。“道路”分化,始于上海開埠,中外交匯、交流、交融,互鑒進化。但長期以來,由于挖掘尚待深入,史料多有欠缺,佐證不夠有力,研究未成系統(tǒng)。現(xiàn)做簡要考證補充,突破口和主線來自上海租界《土地章程》系列的中、英文本。

上海租界沿革圖
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后(1842年8月),清政府被迫簽訂的中英《南京條約》,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要求中國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處為通商口岸。1843年11月17日,上海開埠。此后,根據(jù)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1854年、1869年和1898年等各版本的《土地章程》,上海租界不斷擴張。
正是《土地章程》中記載了官方表述的道路,即真正意義上的“公路”,當時的各項中英對應(yīng)翻譯,為學術(shù)研究提供了史料。特別是1845年的第一版《土地章程》尤為珍貴,然而由于歷史原因原件無存,在很長時間里,流傳、通用的都是以1869年第三版《土地章程》為基礎(chǔ)的《上海洋涇浜北首租界章程》,或個別英文回譯本,中文原文、中英文的先后順序都未認定,實無法作為論據(jù)。直到1992年在英國國家檔案館重新尋回中文抄件及英譯文藏本,才解開了謎團。
可以明確的是,1845年的第一版《土地章程》由江南分巡蘇松太兵備道(上海道)宮慕久會同酌議,懸掛新關(guān)告示,并抄送英國駐上海領(lǐng)事巴富爾,由麥華陀(W.H.Medhurst)查照譯出,通知各租戶遵照。英文版稱為“Shanghae Land Regulations”于1852年1月17日登載在《北華捷報》(North China Herald)。
該《土地章程》內(nèi)容共二十三條,有七條涉及道路,其中第十八條有“不得占塞公路”這一說法。從中英文對照來看,主要有:“路徑(roads or paths)”“大路(large road)”“打繩舊路(Old Rope Walk)”“官路(government roads及public road)”“直路(straight road)”“街道(streets and roads)”“公路(public roads)”。“路基、寬路”和其他路都翻譯為“road”。由此可見,當時把公路理解為“公共道路”,而尚未譯作現(xiàn)慣用的“highway”。

表一 《土地章程》中所提及的“道路”中英文對比

表二 《上海洋涇浜北首西國租界田地章程后附規(guī)例》第十條的中英內(nèi)容對比
另一個疑問是,當時“公路”一詞是否被大眾普遍使用了呢?答案是肯定的。從1847年起,上海道出具的大量出租地契(“道契”)中,普遍使用“西至公路”“南至公路”“北至公路”等來標明土地的位置。如英冊第一號道契中所提及的寶順洋行第八分地“東至黃浦灘,西至公路,南至第九分租地,北至公路。”其西為今四川中路,南為漢口路,北為九江路。再如第五十三號道契中所提及的位利孫第七十五分地“東至華民吳姓界,西至公路,南至公路,北至公路。”
1845年《土地章程》的回譯本見于1933年徐公肅、丘瑾璋所著的《上海公共租界制度》“上海地皮章程”(1989年《上海公路史》附錄),及1957年王鐵崖編纂的《中外舊約章匯編》“上海租地章程”,現(xiàn)擇要對比(詳見表一)。
1854年7月,英、美、法領(lǐng)事宣布了經(jīng)三國公使共同簽字的第二版《土地章程》,共十四條,但未與華官商議。英文版各稿分別刊登于1853年7月30日、1853年8月27日、1854年7月8日的《北華捷報》。中文版則刊載于1900年的《約章分類輯要》和1905年的《約章成案匯覽》,分別被稱為《美英法三國公使合示上海租地章程》和《上海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在這一版的章程中,有兩條章程涉及“道路(road)”,而在其附件《發(fā)租洋涇浜地基條款》中的第五條有“按圖留出公路”的說法。
1869年9月,駐京的英美法俄德五國公使暫行批準了第三版《土地章程》及后附規(guī)例,也未提交清政府。這版章程被稱為《上海洋涇浜北首租界章程》(Land regulations and Byelaws for the foreign settlement of Shanghai,north of the Yang-jing-bang),載于《約章分類輯要》和《約章成案匯覽》等。《章程》內(nèi)容共計二十九款,其第六款“讓出公用之地”中出現(xiàn)“road”九處,中文譯為“道路”“馬路”“街路”各兩處,減譯兩處,譯為“公用公路”一處、衍增一處,蓋因第六款標題中出現(xiàn)“public use”、附則中多次出現(xiàn)“highway”所致。
《章程》附則的名稱為《上海洋涇浜北首西國租界田地章程后附規(guī)例》,內(nèi)容主要是對溝渠、道路等公共設(shè)施的管理,共四十二條,其中涉及“街道(street)”“公路(highway)”較多,英文詞匯大為豐富,反而增加了中文翻譯的難度,特別是第十條。(詳見表二)。第九條中有三處“highway”,標題和文中兩個被譯為“馬路”,另一個被譯為“道路”。

《上海洋涇浜北首租界章程》第六款
“street”多譯為“街道”,但在第十八條中則被譯為“公路”。“footpavement”譯為“行人往來走道”。第二十四條中“public road”和“public highway”都譯為“公路”,“foot-path”譯為“行人走道”。第二十六條中還出現(xiàn)了“carriages(馬車)”和“vehicles(車輛)”。
1893年3月,美國租界《新定虹口租界章程》中的第二條和第四條兩次出現(xiàn)了“公路”。
1898年9月,在1869年版基礎(chǔ)上稍有增補的第四版《增訂上海洋涇浜北首租界章程》共三十款,除新增第三十款“Buildings”,譯為“房屋”以外,還在第六款下補充了a、b兩條,分別是“VIa.Land for public roads”譯為“馬路基地”,“VIb.Railways”譯為“鐵路”。a“公共道路用地”中出現(xiàn)了“new roads”和“existing roads”,分別譯為“新路”“舊路”;b中一處“public road”被譯為“公路”。后又于1906年3月第六款增加了“VIc.Construction of new roads”即“建筑新路”。
上海租界《土地章程》的演變,不但是中國近代史上清政府衰落、列強巧取豪奪的真實寫照,也是公路概念衍化的生動記錄。關(guān)于租界的多次爭議、擴界和《土地章程》的修訂,也常與筑路有關(guān)。從1845年第一版《土地章程》中“路”的豐富分類,到1869年第三版《土地章程》中關(guān)于“路”的英文表述的多樣化,不正是時勢運轉(zhuǎn)的具體反映嗎?
在其他文獻中,1891年(光緒十七年)由唐贊袞撰寫的《臺陽見聞錄》提到,“安平公路,不測風潮,倘不隨時修補,須費浩繁。”光緒二十年《安平縣雜記》也有“近莊堡之公路,歸莊耆分派壯丁出莊顧守,循途相接,以防賊匪劫害途人等事”的記述。
而1897年譚嗣同所著《仁學》中,則以“公路”指“公用鐵路”。提出“若慮俄國之擾也,則先修歐亞兩洲東西大鐵路,東起朝鮮,貫中國、阿富汗、波斯、東土耳其,梁君士但丁峽,達西土耳其,作為萬國公路,皆不得侵犯之。”
歷史總是在輪回中前進。此后,隨著列強介入修筑鐵路的熱潮、政局的進一步動蕩,甚至改朝換代,路政稍興而公路仍弱。
1919年11月,北京政府公布了《修治道路條例》。查閱1919年的《申報》,涉及“公路”的僅有《浦東碼頭公路案之結(jié)束》一文。1920年也僅有《寶山籌辦全縣公路之動機》和《寶山籌備全縣公路之計劃》這兩篇文章。
1919年《美國公路工程師手冊》的術(shù)語定義,將“公路”定義為“The entire right-of-way devoted to public travel”,即“供公眾通行之完全設(shè)施”,包括人行道及其他公共空間,至今仍有沿用。
現(xiàn)代“公路”
現(xiàn)代公路是汽車時代的產(chǎn)物。1956年,由美國人休斯(L.I.Hewes)等編著的《公路工程》中說,“1920年以來方可稱為‘汽車時代’,因為在此期間公路交通成為了主角。”1987年我國交通部標準《公路工程名詞術(shù)語》中,將“公路”定義為聯(lián)結(jié)城市、鄉(xiāng)村和工礦基地等,主要供汽車行駛、具備一定技術(shù)條件和設(shè)施的道路。
一百年前,隨著汽車公司在各地涌現(xiàn)、汽車路興起,現(xiàn)代“公路”逐漸進入人們的生活。
1920年10月,粵系軍閥陳炯明率軍回粵,將全省軍路處改組為全省公路處,下設(shè)四個公路分處,擬定開辟全省公路計劃,力謀地方交通之發(fā)展。蓋軍路注重軍事、適用于軍行,公路則普及交通,軍事而外,凡地方文化、農(nóng)工實業(yè)無不交受其益。據(jù)惠州《大石橋碑記》載“民國九年秋,粵軍歸自閩,陳公兢存閔惠兵災(zāi),議員曾國琮暨惠鄉(xiāng)先生商撥糧食救濟會款十萬元,筑公路以助之。鳳綸、友仁董其事……”
1922年6月《道路月刊》(第二卷第一號)載張友仁在“廣東平樟公路之經(jīng)過及各縣公路之狀況”一文中寫道“粵于民國初元,陳前督兢存倡辦軍路,未成而止。七年,在閩南筑路,始定名曰公路。招附近鄉(xiāng)民為工,兵士亦有作工者,筑成路百余里。九年,由閩返粵,設(shè)省公路處,于是公路之議起。”“雷州各屬公路亦已次第興筑。是皆現(xiàn)年公路之實況也。”同期雜志《閩議會主張省路民有》一文提出,“修治省公路經(jīng)費,業(yè)就全省丁糧厘金附加征用,省公路應(yīng)定為民有性質(zhì),蓋省公路原為鐵路或電車路之初基……”
實際上,1921年9月“以提倡各省分筑馬路為要義”的中華全國道路建設(shè)協(xié)會在上海創(chuàng)辦后,于1922年3月起出版的《道路月刊》第一、二期中,使用的是“長途汽車馬路”這一表述。
《道路月刊》第三期(第一卷第三號)開始連載會員吳靜存著《道路行政淺說》,序曰“不佞上年主任滬海道地方自治講習所教務(wù)時,曾講述道路水利及土木行政學一科。”在論述“道路之性質(zhì)及種類”時,對“公路”與“私路”進行了專門分辯,“公路或私路皆可謂之曰道路。公路與私路,依何標準而區(qū)別乎?曰私路者,只事實上供公眾之通行;而公路者,供公眾之通行,為法律上所公認者也。”“公路者,其供于公眾通行之目的,為法律上所公認。換言之,依國家或公法人或依國家之特許公開,予公眾之通行者也。”雖然語焉拗口,但的確強調(diào)了“公路”的法定內(nèi)涵。該文還收錄于內(nèi)務(wù)部編定、1922年4月泰東圖書局出版的《地方自治講義》等。
同一期雜志的《福建之筑路潮》一文中提到,“上年提出籌辦全省公路議案,議員李永年提出建筑建安公路,該時已設(shè)全省公路籌辦處。‘修治省道之大綱’中說,實依循粵陳駐漳時之原有計劃,省中雖設(shè)有公路籌備處以專其責,惟某縣抽收丁糧附加公路捐、某縣設(shè)立公路捐局,即耳不絕聞。日前省長署曾于省議會提出修治公路咨詢案。修治省公路經(jīng)費,應(yīng)就全省丁糧厘金附加兩成。各縣此前有抽收鹽厘等項指定為公路費用者一概撤銷,其已抽取之款均充為公路經(jīng)費。”此外,雜志還刊有《上海縣署布告拆遷有礙公路之屋墓》一文。

《道路月刊》載中國北部道路圖
總體上看,這一階段,上海、福建、廣東等省份在公路理念、學術(shù)、組織和修建等方面開風氣之先,全國各地筑路潮如火如荼。從此,交通建設(shè)進入了名副其實的公路時代。據(jù)《中國公路史》記載,1921年全國公路里程有1185公里,1949年全國公路里程僅8.08萬公里,1978年全國公路里程達89.02萬公里。后自20世紀80年代中起,我國邁入了高速公路跨越式發(fā)展的新時期,公路建設(shè)更是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2020年全國公路里程達519.81萬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達16.09萬公里。
通過回顧“公路”一詞的演變過程我們可以看出——從古代到近現(xiàn)代公路的發(fā)展歷程,恰與我國社會、經(jīng)濟、科技發(fā)展的重要節(jié)點相吻合,這從一個側(cè)面表明,公路事業(yè)的發(fā)展進步,要以國家的繁榮昌盛為根基,以人民群眾的美好生活需求為導向,勇往直前,通達新時代的道路必會越來越寬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