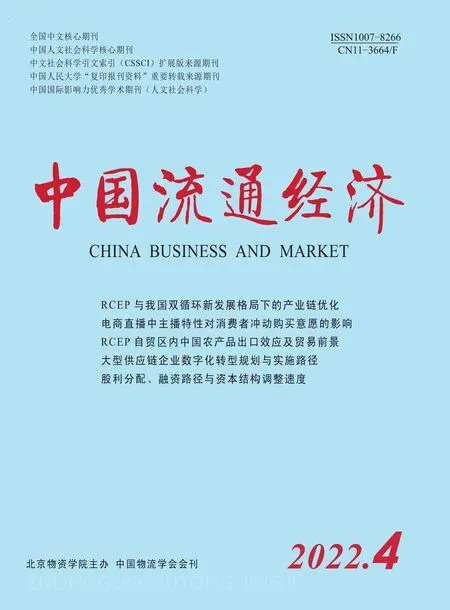股利分配、融資路徑與資本結構調整速度
——基于動態調整模型的NLS預測方法
鄒 燕,白慶輝
(1.北京物資學院會計學院,北京市 101149;2.北京聯合大學商務學院,北京市 100025)
一、引言
股利分配是保護投資者利益、培育資本市場長期投資理念的重要手段。2020年發布的《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質量的意見》(國發〔2020〕14號)①鼓勵上市公司通過現金分紅、股份回購等方式回報投資者,切實履行社會責任;2021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要多渠道增加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完善上市公司分紅制度,切實保障投資者利益。在實踐層面,隨著我國上市公司的成長和發展,近年來上市公司現金分紅取得了積極進展。據統計,2001—2011年,我國上市公司現金分紅占凈利潤的比例僅為25.3%②,2012—2019年上市公司現金分紅占凈利潤的比例提高到32.36%,與境外成熟市場40%的分紅率更為接近。然而,目前我國現金股利分配仍存在分配數量低、分配穩定性差、分配理性不足等問題。
股利分配行為不僅僅是一個數量問題,它對資本結構、融資行為等也會產生重要影響。股利分配通常伴隨著企業資本結構調整、融資行為的同步發生,這是因為企業分配股利時需要考慮投資需求、融資需求及資本結構調整等因素。目前針對股利分配問題,學術界已經形成了股利無關論與股利相關論兩大派別。股利無關論是推動早期股利研究的重要基礎[1],后期的股利相關論主要包括信號傳遞理論、代理成本假說理論等[2-3]。針對資本結構與融資行為問題,學術界主要圍繞資本結構決策形成了關于資本結構和融資行為描述的權衡理論、啄序理論與市場擇時理論等[4-7]。這些研究為股利分配行為與資本結構調整、融資行為研究提供了不同的視角,但這兩項研究相對獨立,無法充分揭示股利分配與融資行為、資本結構調整之間的內在關聯機制。本文認為,股利分配行為與企業融資行為密切關聯,在一定程度上股利分配行為是融資行為的一個子集。這是因為,在發放股利的時候,企業首先需要確定內源融資比例,預估負債融資與股權融資容量以及目標資本結構。理性的股利分配行為應與融資行為匹配、協同,兼顧滿足企業投資者需求、融資需求及調控資本結構等多重目標。但在實踐中,企業超額分配股利后會出現高負債融資或股權融資、資本結構大幅偏離最優資本結構的現象;股利分配行為極可能成為大股東分紅式套現的套利工具,企業會通過實施掩飾性的融資來緩解資金壓力,忽視投資者利益及財務風險。根據已有研究并結合我國股利分配的理論與實踐,有必要深入研究股利分配行為與融資行為路徑對資本結構調整速度的影響,以期為治理股利分配行為、提高融資效率、優化資本結構提供經驗證據。
二、文獻綜述與研究假設
股利分配問題一直備受關注,自從莫里迪安(Modigliani)等[1]在1958年開啟了資本結構與公司價值無關的MM理論研究先河后,逐漸形成了股利相關論與股利無關論兩大派別。股利無關論是推動早期股利研究的重要基礎;現代股利相關論的經典理論主要是代理理論、信號傳遞理論等[2,8]。其中代理理論認為,在代理模式下,經理人往往存在自利動機,他們試圖通過在職消費、過度投資來提高自己的薪酬待遇。當企業自由現金流量充足時,這種自利行為更為凸顯。為了治理代理人的這種無效投資行為,控股股東可以通過調節股利分配來調整經理人控制的自由現金流從而減少經理人控制的資源以約束經理人行為。代理理論認為,發放現金股利有利于提升公司價值,降低代理成本[2-3,9]。而反對發放過多現金股利的掏空假說則認為,大股東與中小股東之間由于持股懸殊而存在利益沖突,大股東往往會忽略中小股東的利益,通過實施超額現金股利政策來轉移公司現金資源以達到掏空上市公司的目的[10-11]。在投資者保護較差的國家,這些控股股東從持有現金中獲取私人利益的能力更強[12]。與代理理論的視角不同,信號傳遞理論認為,股利分配行為具有信號傳遞作用,且由于企業管理當局與投資者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管理者為了向投資者傳遞公司未來經營良好的信號,往往會通過發放現金股利來強化投資者對公司前景的認可[13-17]。希利(Healy)等[14]發現,企業盈利變化與股利調整行為之間存在一定的關系。古勒(Gugler)等[18]提出,當大股東與小股東之間存在利益沖突時,股利分配及變更公告會傳遞有關沖突的新信息,股利被視為監控大股東行為的指針函數。孔小文等[15]發現,發放現金股利的樣本從股利宣告前14 天起累積超額收益率緩慢上升,并一直維持到股利宣告后20 天,這證實我國股利分配行為存在顯著的市場反應。楊熠等[3]的研究發現,我國股利政策只能發揮有限的信號傳遞作用,對公司未來業績發展解釋能力不足。
在實踐層面,為了保護投資者利益,培育資本市場長期投資理念,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將現金股利分紅與企業再融資掛鉤,學者們將這一制度總結為“半強制分紅政策”。研究表明,在半強制分紅政策背景下,有融資需求的公司股利分配意愿和分配率更高,融資動機顯著削弱了股利的信號作用[17,19]。可見,我國股利分配行為具有迎合制度監管效應[20],不是完全自發的股利分配行為。此外,對股利分配與過度投資、大股東持股比例、公司治理等變量關系的研究對優化股利分配政策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9,16,20-27]。
股利分配行為通常與企業籌資活動、資本結構調整密切關聯。已有文獻表明,對這三者關系的研究屬于融資行為—靜態資本結構—動態資本結構—股利分配的研究范疇。關于融資行為,在委托代理模式下,管理者并不愿意放棄控制權,也不愿意提供對控制權有損害的信息,這時企業需要引入債務資本以迫使管理層提供對債務人及投資者有效的外部信息[28]。考慮到股權稀釋成本和違約風險,風險較高的公司更傾向于銀行貸款,相對安全的公司更傾向于發行債券,介于兩者之間的公司更傾向于發行股票和債券[29-30]。這些研究主要從融資行為出發,對企業的資本結構決策進行評價,從靜態視角探索資本結構成因。也有學者指出,企業的資本結構是一個動態調整的過程。貝克爾(Baker)等[4]、弗蘭克(Frank)等[5]、弗蘭尼(Flannery)等[6]構建了觀察資本結構調整速度的動態模型,檢驗并豐富了市場擇時理論、啄序理論以及權衡理論[31-32]。我國學者主要結合上市公司數據對資本結構的調整速度及影響因素進行檢驗,經驗證據表明我國上市公司存在目標資本結構及同群效應[33],權衡理論對資本結構調整速度起著主導作用[7,34-37],而市場擇時理論與啄序理論在相對約束條件下具有一定的解釋力[38-39]。隨著研究的細化,學者們還從經濟周期、融資約束、企業金融化等維度檢驗了其對資本結構調整的影響。比如,江龍等[37]檢驗了經濟周期與企業融資約束對資本結構回調的影響,發現調整速度存在正周期性特征和逆周期性特征;李井林等[39]對資本杠桿倍數與股權融資之間相關性進行了研究;田新民等[40]發現,企業金融化會影響企業融資行為和資本結構,即金融化程度越高,企業股票崩盤風險越大,資本結構調整速度越慢;劉礫丹等[41]分析了融資約束對資本結構調整速度的影響;任碧云等[42]發現,高管的金融背景對企業融資策略有顯著影響。關于股利分配,呂長江等[38]通過構建結構方程驗證了公司資本結構、股利分配與管理層股權比例變量之間互為因果的關系;范宏偉等[43]將股利分配作為影響資本結構調整的決定變量,發放現金股利會加快資本結構調整速度;侯麗等[44]考察了控股股東股權質押對資本結構動態調整的影響,發現控股股東股權質押對資本結構動態調整的抑制作用主要依賴于發行股票和現金分紅。
綜上所述,將股利分配行為與資本結構、融資行為進行關聯的研究還不夠豐富,一些文獻在關注股利分配因素時,把股利分配行為作為前置變量[36-37],忽略了股利分配行為與資本結構調整、融資行為之間的關聯機制。在實踐中,股利分配是企業在綜合考慮各方面因素后做出的行為決策,與融資決策、資本結構決策密切相關,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三者之間的關系。本文認為,適當的股利分配應與融資行為相協調,這有助于優化資本結構,其原因是股利發放行為與資本結構調整過程往往是并發進行的,企業可通過調節股利分配行為調節公司籌措外部資金數量。企業發放現金股利時需提前預估負債容量、財務杠桿壓力及股權融資比例,融資行為的直接后果是改變了企業的資本結構。當發放的現金股利較少時,企業對內源資金安排的自由度會更大,此時,富有效率的投資將有利于增加股東價值,企業向目標資本結構調整的預期速度會更快;當發放的現金股利較多時,企業會放棄資金成本較低的內部資本,轉而尋求外部資本,由于外部籌資成本和交易費用的存在,企業向目標資本結構調整的預期速度會變慢。由于不同資金來源的資本成本和財務風險不同,不同的融資路徑對資本結構調整將表現出異化調節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1:融資活動包括股利分配與資本結構調整,理性的股利分配行為會加速企業向最優資本結構調整,非理性的股利分配行為會阻礙企業向最優資本結構調整。
H2:股利分配屬于內源性融資,其他債權性融資和股權性融資屬于外源性融資,不同融資路徑對資本結構調整存在異化調節作用。
本文擬借助資本結構動態調整模型來檢驗研究假設,研究主要變量關系如圖1所示。

圖1 變量關系
三、研究設計與樣本選擇
(一)研究設計
本文關注的焦點問題是股利分配行為對資本結構調整速度的影響以及不同融資路徑產生的調節效應。根據現有研究,用現金股利分配率(DIV_out)來度量企業股利分配行為。為估計資本結構調整速度λ,本文參考弗蘭尼等[6]、連玉君等[7]、呂長江等[38]的方法,構建模型1:

其中,BDR表示企業的賬面資本結構,為了使研究結論穩健,回歸時參照弗蘭尼等[6]的計算方法將其替換為市值資本結構MDR;BDRi,t+1-BDRi,t表示企業從t期到t+1 期的實際資本結構調整,即DISi,t+1;BDR*i,t+1-BDRi,t表示企業從t期到t+1 期的預期資本結構調整,即DIS*i,t+1;λi,t+1表示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7]。模型1是非線性模型,因此,用非線性回歸(Nonlinear Least Square,NLS)方法進行擬合,用高斯—牛頓迭代法估計回歸模型的參數[7]。
為了預測企業的目標資本結構BDR*,構建模型2:

研究表明,目標資本結構(BDR*)通常與公司的贏利能力(EBIT)、投資機會(Q)、固定資產折舊(DEP)、資產結構(FA)、研發投資(RD)、公司規模(SIZE)及行業負債水平(IND_m)等因素密切相關[6-7]。贏利能力強的公司通常有充足的自由現金流和較強的償債能力,公司傾向于提高負債率,但也可能因優先使用內部資金而負相關;擁有良好投資機會的公司往往容易獲得資本垂青,并利用高杠桿進行風險投資,進而導致資產負債率更高;折舊攤銷具有較強的稅盾效應,折舊攤銷較多的公司可能會控制負債規模;公司資產結構代表公司變現和抵押能力,通常與負債率正相關;公司規模越大,公司抗風險能力越強,因此,公司規模與負債率正相關。
為得到動態調整速度λi,t+1,將模型2的計算結果代入模型1得到模型3。

為檢驗假設1,構建模型4。

根據模型4預測:當理性的股利分配行為加速企業向最優資本結構調整時,回歸系數β1顯著為正;當非理性的股利分配行為阻礙企業向最優資本結構調整時,回歸系數β1顯著為負。調整惰性理論認為,當公司偏離最優資本結構較遠時,由于外部融資成本較高,偏離最優資本結構較遠的公司反而會表現出調整惰性[7],調整惰性用預期資本結構調整的絕對值|DIS*i,t+1|度量。模型4 控制了調整惰性、公司規模、投資機會因素對調整速度的影響。
為檢驗假設2,引入股利分配率與融資路徑的交乘項,并構建模型5。

其中,變量DEBTi,t代表負債融資路徑,變量EQUITYi,t代表股權融資路徑。交乘項的回歸系數γ5和γ6捕捉了企業發放股利后再度負債融資或股權融資對優化資本結構的調節效應。
企業相對負債率是制約企業資本結構調整速度的重要影響因素,本文通過杠桿率LEV_high來度量企業的相對負債率,在模型5中引入杠桿率并設計交乘項股利分配率×負債融資路徑×杠桿率和股利分配率×股權融資路徑×杠桿率,構建模型6:

其中,回歸系數γ7和γ8反映了高杠桿水平下企業負債融資和股權融資對資本結構的調整作用。
模型中各變量定義及計算方法如表1所示。

表1 變量定義及計算方法
(二)樣本選擇
2005年以前,我國參與股利分配的公司少,分紅總額低。2005年,有621 家公司實現現金股利分配,占上市公司總數的45%,分紅金額高達729億元③,可見2005年是我國現金股利分配的一個新起點。因此,本文選取2005—2020年數據作為研究樣本,公司財務數據來自CS?MAR 數據庫④,公司實際控制人數據來自CCRE 數據庫⑤,行業分類代碼參考《上市公司行業分類指引(2012年修訂)》⑥。制造業范圍廣,公司多,使用兩位代碼,其余行業使用一位代碼。在原始樣本基礎上,剔除金融、銀行、保險、資不抵債的樣本,2020年新上市的公司樣本,原始數據缺失的樣本以及標有ST、*ST、PT股票的樣本,并用STATA15軟件對數據進行處理。為消除極端值的影響,對主要連續變量進行1%的截尾處理。樣本特征如表2所示。

表2 樣本特征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從表3來看,分配現金股利的公司賬面資本結構水平為0.235,市值資本結構水平為0.159;不分配現金股利的公司賬面資本結構水平為0.313,市值資本結構水平為0.199。這說明,從總體來看分配股利的公司財務風險相對較小,企業資金壓力對股利分配的滲透性相對較弱,而未分配股利的公司對負債資金依賴更多,總體債務風險相對更大,行業總體層面數據特征亦是如此。總體來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實際偏離上一期資本結構幅度基本平穩,結合極端值可見,也有少數公司當期去杠桿幅度高達0.145,還有少數公司的負債率水平提高了0.154。分配現金股利的公司規模相對較大,贏利能力相對較強,但公司的市場估值相對保守。這些數據特征說明,我國規模大、贏利能力強、財務風險小的公司更趨向于發放現金股利。然而,實踐證明,有的企業在發放大額現金股利的同時進行了大規模的債權融資或股權融資,這些企業的股利分配行為可能會與融資行為產生利益沖突,干擾企業最優資本結構調整速度,股利分配行為可能會損害中小股東利益,使現金股利分配成為向大股東輸送利益的通道。比如,某上市公司2018年實施股權融資24.63 億元,累計分紅派現為24.64億元,幾乎是當年凈利潤的兩倍,公司融資行為與股利分配行為的合理性備受質疑。因此,股利分配行為與融資行為之間的協調關系可能會影響最優資本結構調整速度,下文將通過實證方法分析這一問題。

表3 變量描述性統計
(二)相關性分析
根據表4,各變量間相關系數都相對較小,變量間不存在嚴重的共線性問題。由表4可知,賬面資本結構與現金股利分配率的皮爾遜相關系數為-0.180,市值資本結構與現金股利分配率的皮爾遜相關系數為-0.120。行業負債水平與現金股利分配率的皮爾遜相關系數為-0.078。這說明,企業分紅率與企業負債水平負相關,負債結構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企業的股利分配行為。

表4 變量的相關系數
(三)實證回歸結果與分析
1.股利分配行為對資本結構調整速度的影響
根據非線性回歸方法,在模型4迭代運算之前需要得到參數的初始值。方法為:第一步,對模型2 進行靜態線性擬合;第二步,將其預測值代入模型3,計算資本結構動態調整速度;第三步,將資本結構調整速度代入模型4,估計參數初始值;第四步,對模型進行迭代運算并估計參數。初始化回歸結果如表5所示。由表5可知,股利分配行為對資本結構調速的回歸系數為0.703,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同時模型的調整擬合優度接近0。從其他列可以看出,非線性估計模型的股利分配行為與資本結構調整速度都顯著負相關,模型擬合優度全部提高到80%以上,這說明非線性估計提高了模型的估計效率。從總樣本回歸結果來看,股利分配行為對資本結構調整速度的回歸系數為-0.011,且在5%的水平上顯著,這說明我國上市公司股利分配行為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企業向最優資本結構調整,股利分配行為沒有與資本結構調整行為實現有效的統籌協同。對同一家樣本公司而言,其在不同年度可能采取不同的股利政策,這會直接導致企業股利發放行為不連續,而有的公司上市多年后也不發放股利。為了避免這種因股利政策不同而導致的樣本選擇性偏誤,去掉完全不分配股利的公司樣本,其余樣本被界定為分配樣本(分配股利的樣本),分配股利樣本的回歸結果與總樣本基本一致。分析認為,企業資本結構偏離最優資本結構對資本結構調整速度存在一定的影響,融資約束也是資本結構調整不可忽視的重要影響因素。因此,把偏離最優資本結構的程度即調整惰性按分位數排序分為低中高組,挑選出偏離程度最低和最高的組別作為調整偏離樣本組。分析認為,股利支付率包含了企業融資約束信息。因此,對股利支付率進行分位數排序后,保留股利支付率相對較高和較低的組別作為股利偏離樣本組。表5中數據證實調整惰性、融資約束對資本結構調整速度存在一定的干擾作用。通過控制變量可以看出,企業估值越高,企業資本結構調整速度越快,這說明良好的市場評價有利于促使企業回歸到最優資本結構水平,資本市場發揮了一定的治理作用;公司規模越大,公司資本結構調整速度越慢,這說明企業總體資金需求規模影響了資本結構調整速度;公司調整惰性變量說明公司在資本結構偏離較大時,有強烈的資本結構調整意愿。

表5 不同股利分配行為下的資本結構調整速度
2.股利分配行為對資本結構調整速度與最優偏離比率影響的時間趨勢
表6中的資本結構調整速度及最優偏離比率由全樣本非線性回歸擬合得出。由表6資本結構調整速度數據可知,分配現金股利組的資本結構調整速度為0.133,不分配現金股利組的資本結構調整速度為0.114,但二者之間不存在顯著性差異(差異T值為-1.143)。結合中位數來看,分配現金股利組的資本結構調整速度為0.022,不分配現金股利樣本組的資本結構調整速度為0.041,二者之間存在顯著性差異(差異T值為2.236)。從中位數分布來看,分配現金股利組的資本結構調整速度比不分配股利組的資本結構調整速度更慢,這可能是因為股利分配調節了內源性融資數量。相對外源性融資而言,內源性融資在調整數量、調整成本等方面都比外源性融資更具有優勢。從時間分布趨勢來看,各年調整速度存在快慢交錯分布的特點,這說明資本結構調整時間跨度長于一個會計周期,上年調節行為與本年調節行為之間存在一定的更迭關系。

表6 不同股利分配行為下的資本結構調整速度與最優偏離比率
最優偏離比率等于最優資本結構比實際負債率。連玉君等[7]認為,當最優偏離比率為1 時,公司處于最優資本結構水平;當最優偏離比率大于1時,說明企業負債不足。由表6最優偏離比率數據可知,各年分配現金股利組的最優偏離比率基本都顯著高于不分配現金股利組,這說明分配股利企業的實際資產負債率水平低于最優負債率水平。其原因,一是企業股利分配不足,分配股利后企業資金仍有冗余,企業沒有充分利用負債融資來調整資本結構;二是企業在現金股利分配后通過負債這一外源性融資路徑來調整資本結構可能受到了資本市場的限制,致使企業杠桿水平較低。
3.企業股利分配背景下融資路徑對資本結構調整速度的調節效應
為檢驗假設2,我們對模型5 進行回歸分析,回歸結果如表7所示。從表7數據可知,股利分配行為與資本結構調整速度顯著負相關,這說明股利分配行為阻礙了企業向最優資本結構的調整。從股利分配率與負債融資路徑、股權融資路徑交乘項的系數來看,交乘項系數大于零且顯著,說明發放股利后企業負債融資和股權融資都起到了優化資本結構的作用;與股權融資路徑交乘項系數顯著大于與負債融資交乘項系數,說明不同的資本調節路徑存在異化調整作用。從杠桿率與股利分配率、融資路徑的交乘項回歸系數來看,當企業處于高杠桿運行水平時,股權融資對資本結構調整速度的異化作用被進一步放大,而負債融資從總體上來看對資本結構調整的阻礙作用進一步突出。對高杠桿的企業而言,只有股權融資才能發揮優化資本結構的作用。

表7 融資路徑對資本結構調整速度的調節效應檢驗結果
結合最優偏離比率指標進行分析可知,企業發放現金股利后,應優先采用負債融資以便資本結構回調。但上述經驗證據表明,分配股利后股權融資和負債融資對資本結構都具有修復作用,企業表現出股權融資偏好,并可能與融資行為產生沖突,這種沖突關系極可能被股權融資偏好所掩蓋。下面我們將檢驗二者間沖突關系以全面評價股利分配行為。
4.基于融資理論的股利分配行為與企業融資策略關系檢驗
根據融資理論,如果企業發放的現金股利較少,且資金需求大,那么融資行為更符合啄序理論假說,企業向目標資本結構調整的預期速度也更快;如果企業發放的現金股利較多,企業放棄了資金成本較低的內部資本,此時,企業需要充分考慮資金成本、稅收政策等因素以權衡決策,企業融資行為更符合權衡理論假說。如果外部籌資成本高且資本市場有效性不足,那么企業向目標資本結構調整的預期速度會更慢。只有當股利分配行為與融資策略適配、協同時,資本結構優化的目標才能得以實現;而當股利分配行為與企業融資策略沖突時,資本結構優化目標的實現將受到阻礙。根據融資理論,股利分配行為與融資沖突存在兩種情況:一是當企業股利分配過少時,企業資金需求小,融資策略不符合啄序理論假說,企業因截留過多利潤而導致資金冗余過剩,資本結構偏離最優目標;二是當企業股利分配過多時,企業資金缺口大,但企業會放棄資金成本低、容易獲取的內部資金而采取市場擇時手段進行股權融資,此時股利分配行為與股權融資相沖突。為觀察股利分配行為與融資行為的關系,借鑒貝克爾等[4]、弗蘭尼等[6]、連玉君等[7]的做法,在資本結構調整模型1 中加入資金缺口變量DEF和市場擇時變量MB,建立模型7。

其中,變量DEF測度企業融資是否符合優序融資理論,變量MB測度企業是否采取了市場擇時行為。將模型2代入模型7得到模型8。

其中,若回歸系數λ、γ、η顯著,說明企業資本結構調整分別采取了權衡融資、啄序融資和市場擇時行為。我們假設不分配股利企業的回歸系數γ顯著,而分配股利企業的回歸系數η不顯著,否則企業股利分配行為與融資行為存在一定的沖突關系,進而影響資本結構調整速度。由于市場擇時變量在計算累積市值時受新冠肺炎疫情沖擊較大,故模型8 的回歸區間為2005—2019年,結果如表8所示。

表8 不同股利分配行為與融資策略下資本結構回歸結果
從賬面資本結構變量對應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不分配股利組的公司資本結構調整速度為0.561,而分配股利組的資本結構調整速度為0.435,這說明不分配股利的公司資本結構調整速度快于分配股利的公司資本結構。從權衡理論視角來看,企業放棄資金成本低、融資便利的內源性融資轉而尋求外部融資的行為會影響資本結構調整速度,使資本結構回歸到最優資本結構的時間周期更長。從資金缺口變量(DEF)的回歸系數來看,無論公司是否發放股利,資金缺口都不是影響企業負債融資的關鍵因素,這說明在一定程度上融資行為與資金需求之間是脫節的。股利分配不足或企業內部資金相對冗余都會影響最優資本結構回調的速度。在各分組樣本回歸中,市場擇時變量(MB)的回歸系數都與資本結構變量顯著正相關,這說明我國上市公司股權融資存在市場擇時行為。對分配股利的企業而言,企業超額發放股利與市場擇時融資是相互沖突的,這是因為股利分配行為與股權融資行為并沒有優化資本結構,企業可能會借助股利分配實施利益輸送。上述分析說明,股利分配行為與融資行為之間存在一定的沖突關系,且對資本結構調整具有干預機制。
將因變量改為市值資本結構并進行回歸分析可知,不分配股利的公司融資行為并不符合啄序融資理論,而分配現金股利的公司采取市場擇時行為,與賬面資本結構變量回歸得到的結論一致。同時,對不分配股利組和分配股利組的系數差異進行鄒檢驗(Chow test),數據差異在1%的水平上顯著(p值為0)。
5.穩健性檢驗
(1)股利分配行為對資本結構調整速度的影響:基于靜態調整速度檢驗
在模型1中,假設所有公司都存在一個相同的平均調整速度,即模型1中λ為常數。考慮到樣本回歸區間比較長、資本結構調整跨度大、各年之間可能存在較大差異等,同時為克服系數變化所帶來的問題,借鑒Fama-MacBeth兩階段回歸法[45]進行處理,回歸結果參見表9FM 列。表9FE 列代表控制了固定效應的回歸結果,IV 列表示用工具變量法得到的回歸結果。如果上一期資本結構不能完全調整到最優資本結構,那么將影響當期資本結構,因此,本文選取滯后一期變量作為當期資本結構的工具變量。由賬面資本結構變量BDR的回歸系數可知,不分配股利組的資本結構靜態調整速度普遍快于分配股利組,如在FM 列,不分配股利組的調整速度為0.159,而分配股利組的調整速度為0.079,分位數回歸結果與此結果一致。分析表明,股利分配行為對資本結構調整速度具有顯著的阻礙作用,在實施股利分配行為前應考慮其對優化資本結構的影響,從而提高股利分配效率。

表9 不同股利分配行為下賬面資本結構的靜態回歸結果
考慮到市值對公司價值及資本結構的影響,本文用市值資本結構作為公司資本結構的替代變量。回歸結果(表10)表明,不分配股利組的資本結構調整速度顯著快于分配股利組的調整速度,與賬面資本結構下的回歸結果一致。

表10 不同股利分配行為下市值資本結構的靜態回歸結果
(2)融資路徑的調節效應:基于動態復合模型檢驗
為檢驗不同融資路徑對股利分配行為與資本結構調整速度的調節效應,借鑒田新民等[40]、劉礫丹等[41]的方法,分步構建影響資本結構調整速度的動態復合模型。
首先,根據模型1和模型2構建模型9:

其中,變量X表示影響資本結構調整速度的因素,如股利分配行為、融資路徑等。
其次,將模型2和模型9代入模型1,得到模型10:

其中,β1是復合變量Xi,t+1BDRi,t回歸系數的相反數,它反映了觀測變量X對資本結構調整速度的影響。
在表11 中,DIV_out×BDR的回歸系數為0.114、0.049,β1為-0.114、-0.049,這說明股利分配行為對資本結構的影響為負且顯著,股利分配阻礙了資本結構回調。從股利分配、融資路徑與資本結構的復合變量回歸系數可知,無論是負債融資路徑還是股權融資路徑,在企業分配股利的背景下都會起到加速資本結構回調的調節作用,這說明股利分配行為如果破壞了企業的最優資本結構,后續融資行為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修復作用,股權融資與債權融資對資本調節路徑存在異化調整作用。

表11 動態復合模型檢驗結果
為觀察企業性質對調節作用的干擾,通過對比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樣本的回歸結果,發現非國有企業樣本中股權融資的調節作用始終大于負債融資的作用,這可能是我國國有企業負債規模大、負債率高的緣故。深度負債將導致企業進一步遠離最優資本結構,股權融資將進一步擴大國企存量,這對規模較大的國企而言并不會產生顯著的影響。在我國債務融資市場上,多數上市公司只能通過銀行貸款獲得資金,而這一資金來源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銀行的信貸計劃,實踐中銀行實施的通常是優先滿足大型國有企業需求的歧視性政策[7]。這是導致國有企業在控制杠桿后負債融資調節力度大于股權融資調節力度的另一個重要原因。而對非國有企業而言,企業負債率相對較低,提高企業杠桿水平能較好地發揮利息的稅盾效應,又因規模相對較小,股權融資亦是增加公司價值的有效路徑。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研究結論
股利分配行為是企業內源性融資決策的重要考量因素,其通過影響外源性融資比例與資本結構產生聯動反應。理性、適度的股利分配行為應考慮企業資本結構優化問題,同時與融資行為相匹配、協同,兼顧企業投資需求、融資需求及資本結構調控等多重目標;反之,股利分配過少或過多都可能與外源性融資行為產生目標沖突,進而阻礙企業回歸到最優資本結構水平。本文系統地研究了股利分配行為、融資路徑與資本結構動態調整的關系,通過實證分析得出:
第一,股利分配行為顯著地阻礙了企業向最優資本結構回調。分配現金股利公司的資本結構調整速度更慢,股利分配行為沒有實現與資本結構調整行為的有效統籌協同。第二,企業債權融資和股權融資都起到了優化資本結構的作用,但不同的融資路徑存在異化調整作用。當企業處于高杠桿運行水平時,股權融資對資本結構調整速度的異化作用被進一步放大。第三,股利分配行為與企業融資策略之間或存在沖突關系。其具體表現為:當股利分配過少時,融資策略不符合啄序理論,偏離融資需求;當企業股利分配過多時,企業采取市場擇時手段進行股權融資,與超額股利分配行為沖突,這些沖突會導致企業非效率的股利分配行為與非理性的融資行為,并將沖突關系傳遞到資本結構層面,進而影響資本結構調整速度。
(二)政策建議
股利分配行為一般需要考慮經濟周期、貨幣政策、通貨膨脹等宏觀因素的影響,而這些因素會對公司流動性和融資環境產生直接影響。此外,股利分配行為還需要考慮企業生命周期、盈利狀況、公司戰略、投資需求、融資需求、法律因素、投資者偏好等眾多微觀因素的影響。良好的股利分配行為是企業權衡各方面因素后作出的理性決策。但實踐證明,由于股利分配行為影響因素涉及面甚廣,公司分配股利的自由裁量權非常大,而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和投資者很難找到理性評價股利分配行為的量化準繩。因此,面對股利分配行為的叢林,我們需要找到一面能判斷股利分配合理性的濾鏡。理性的股利分配行為應與融資行為相協調,從而有助于優化資本結構;反之,非理性的股利分配行為可能會因為利益空間博弈而與融資行為不協調,最終阻礙資本結構的優化調整。鑒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要鼓勵贏利能力強、公司規模大、現金充足、財務風險可控的公司積極分紅,主動分紅,引領資本市場融資與投資并重的新風向;第二,建議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逐步探索建立分紅行為積分制,加強行業現金分紅的自律能力,以促進自律分紅、理性分紅局面的形成;第三,針對企業大額分紅并激進地負債融資或股權融資的行為,尤其是企業融資約束嚴重或高杠桿的情況,構建企業理性分配股利、理性融資的評價指標,探索與股利分配行為關聯的行為沖突測試體系,確保股利分配行為和融資行為的真實性和有效性;第四,持續修訂并完善上市公司現金分紅的規定,尤其是上市公司現金分紅方面的信息披露規則,讓投資者充分透視股利分配行為,發揮股價的信號傳遞作用,構建良好的股價反饋機制。
注釋:
①參見http://www.csrc.gov.cn/csrc/c100028/c1000689/conten t.shtml。
②數據來自http://www.csrc.gov.cn/csrc/c100028/c1002542/c ontent.shtml。
③數據依據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披露信息計算,詳見http://www.csrc.gov.cn/csrc/c100028/c1002542/content.sht?ml。
④數據來源于https://www.gtarsc.com/。
⑤數據來源于http://www.ccerdata.cn/。
⑥數據來源于http://www.csrc.gov.cn/csrc/c100103/c145202 5/content.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