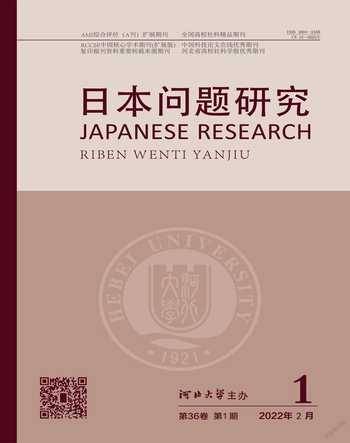經驗、知識與政治:晚清民國時期中國知識分子的富士山認識
向卿 郭雯
摘 要:晚清民國時期中國文人的富士山認識構建了富士山作為日本代表、國家和民族精神的象征、神山、絕景、避暑勝地等多重形象和意義,也塑造了它作為“異國之山”“東亞之山”“文明之山”的多重面孔,總體上也呈現出從“客觀敘述和贊美”向“贊美和批判并存”的立場轉變。這種認識是主體與對象在一定時空內基于經驗而發生知識性·情感性聯系的過程,既立足于中國文人關于富士山的體驗和知識,也受到近代文明觀、中日關系變化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它也對中國人的自我認識和日本人的富士山認識產生了影響。
關鍵詞:晚清民國時期;中國知識分子;富士山;跨國境;文明觀
中圖分類號:G125;C9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2458-(2022)01-0055-14
DOI:10.14156/j.cnki.rbwtyj.2022.01.007
引 言
正如曾邀王韜赴日的日本學人所說“至東瀛者,自古罕文士。先生若往,開其先聲,此千載一時也”[1]385,除朱舜水等明末遺臣,晚清以前少有中國名士東游日本,故鮮有關于富士山的記錄。即便有,大多也是道聽途說,如從未去過日本的明初政治家宋濂的《賦日東曲》第三首。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后,隨著中國被迫打開國門,中日之間斷絕已久的公務往來重新開啟。不少官員和文士(以下簡稱“知識分子”或“文人”)開始赴日公干或私訪,如黃遵憲、王韜、康有為等。他們通過閱讀、目睹、攀登富士山等方式,形成了晚清民國時期(1840—1949)中國文人的富士山認識。這些認識是經驗、知識和政治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內容,對中日兩國也有不同的意義。可以說,它既是中日跨文化交際的一個典型案例,也是百年間中日政治、經濟和文化關系的一個縮影。
對于這一重要問題,國內學術界缺乏足夠的關注,相關研究也近乎空白。迄今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古代,也多局限于富士山的形象及其變遷、日人創作的富士山漢詩解讀、泰山與富士山的漢詩對比等主題①。鑒于此,本文基于數據庫②,采用文獻分析法對晚清民國時期中國文人的富士山敘事及其認識進行系統考察,并探討異文化間“相互認知”的形成原理。
一、富士山的多重形象和意義
晚清民國時期是中日兩國在“西方”這個巨大他者下重構各自自他認識的重要階段。這種重構后的相互認識不僅構成了近代中日兩國相互體認的基礎,也影響甚至主導了現代兩國的相互認識。這一時期中國文人的富士山認識就是其典型。
在日本,富士山不僅是國內最高峰,也是具有特別意義的存在。隨著中日交往的展開,中國文人也意識到了其特殊性——極致的物質屬性和特別的文化屬性。他們在接觸了這座對日本有著特殊意義且被其大力宣揚的“山”后,對它產生了不同于日本其他山峰的特殊印象。在晚清民國的不同時期,因為塑造其認識的因素不盡相同,故他們形成了關于富士山的“日本代表”“日本國家和精神象征”“信仰對象”“審美對象”“享樂對象”等不同的形象和意義。
(一)從“日本代表”到“日本國家和民族精神的象征”
民國時期,中國文人已意識到“切腹”“櫻花”“富士山”等是日本獨特且聞名于世的現象[2]。這說明,認為富士山對日本有特殊意義,是他們的共識,也構成了其富士山認識和敘事的前提。不過,明確視它為日本國家和大和魂的象征,則是民國以后的事情。
在晚清,中國文人雖未明確視富士山為日本國家的象征,卻意識到它對日本的特殊意義,視其為與櫻花、琵琶湖同等的日本代表風物。他們認識到,富士山具有成為日本代表的唯一性、極致性等物質特征,如“極致”的山高、千載積雪、“難以描繪”的絕景等。黃遵憲較早介紹了該山作為“直立凡一萬四千一百七十尺”的日本第一山的特性,也描述了其“狀如芙蓉,四面皆同”“四時戴雪,浩浩積白,蓋終古不化”(《日本國志》卷十)等奇異性,奠定了國內學界富士山極致化敘事的基礎。稍后,黎汝謙、康有為、蔣智由、高旭等又對它做了極致性描述:“天際搖白影,積雪何嵯峨。……太古噴火跡,巖石镕紛拏。焰熄堆磅礴,方頂平不頗。上切恒雪線,寒溫度殊差。碧波紅日間,高擁銀髻髽。我欲事測量,積高算幾何?”[3]他們尤其強調了其得造化之功的神性和難以描述的風景極致性。“不見乎,富岳盤旋地軸撐天起,山勢蜿蜓疾走如游龍。造物磅礴凝結此物質,橫絕東亞海國氣象雄。此山生平未曾睹……此山雄偉描狀難逼肖,詩人到此往往筆力窮。咄爾狡獪恣簸弄,驅遣六甲奪取造化工。”[4]此論體現了中國文人“初識”富士山的認識前提,故雖有少量客觀介紹,更多的是對其毫無掩飾的審美性贊美;論者大多是晚清一流學者,故其論在當時具有極大的影響。
不過,如“清漪飄渺落山影,如見西湖浸葛嶺”[5] “記昔齊魯游,泰山曾經過。巖巖半青霄,胸襟與蕩摩。渡海復見此,靈奇足怪嗟。……昆侖天之柱,俯影瞰中華”[3]1204等所述,這種初識又體現了以中國神山話語為標準的傾向,而其思維基礎便是中日一體意識。因此,如“坤維盡處聳兜離,回拱神州鎮九夷”(黎汝謙《夷牢溪廬詩鈔》卷五)、“我欲挾泰山置諸三島間,又欲移富士環以五湖水由來。此土同亞洲山海神靈供驅使……求之二千年前一徐福,至今猶隱神山麓。秦時男女能胎育,我與諸君原一族。雖有聚散燕西勞東,若論契合苔異岑同。要與諸君追壺公,一齊跳入丹壺中。騰霄仙氣常相通”[6]等所示,晚清文人是在“東亞文化”的視域內來看待和認識富士山的。當然,通過這種對富士山的特征化和對比描寫,它作為日本代表的特性便被突顯出來。
同時,日本官知也在大力宣揚富士山作為日本代表的屬性。例如,中國文人著述和報刊屢屢提及的“富士(山)艦”就是其表現之一。“君不見地底火力億萬斤,勃乎爆發海之隅……高者秀為富士岳,屹然出海如斧斫;低者沒為琵琶湖,合沓中州乘斗樞”[7]“一朵芙蓉擎碧空,千秋鎮護日之東。攀臨欲極仙峰秘,須及炎威赫赫中”[1]458等,這些有關富士山的譯介也說明了這點。這一狀況無疑影響了中國文人的富士山認識。如“瓊瓊杵尊娶木花笑耶姬,姬為富士山神”(《日本國志》卷三十四)、“窈窕天神疑絕世,惹人笑煞木花開”[8]等說法,就可認為是受江戶日本形成的“富士山神木花開耶姬”說之影響的結果。66DBC426-1084-4E1A-B9AE-31DE04CCCD64
可見,基于主體經驗并受日人富士山認識和宣傳的影響,晚清文人形成了以富士山為日本代表的認識。“山則富岳……水則琵琶湖”[1]459“景收富士山巔雪,船過琵琶湖里天”[9]“巍哉此山高,麗哉櫻之花”[3]1204等是其典型表現。這種認識不僅奠定了民國文人視富士山為日本國家象征的思想基礎,也如“突兀著現象,鐫入民性多。此邦矜國粹,風物舉誰夸”所示,隱含了以它為日本民族精神之表現的意味。
在此基礎上,民國學人逐漸認識到,富士山具有足以支持它被符號化的物質和文化屬性,而由此視其為日本國家和民族精神的象征。在此,它不僅被當成了日本的代表風物,還獲得了超越自身的隱喻意義,成了日本國家和日本精神的代名詞。“居菲律賓而不到碧瑤,猶之居美洲者而不游黃石公園……居日本者而不游富士山”[10]“以山水論,則太行與富士爭雄,琵琶共洞庭一色”[11]“設立各該國家特有之名勝,如中國之長城、日本之富士山……”[12]等,都是以富士山為日本代表的典型論述,其結果是形成“卓君常語人,以‘到富士去的話,作為‘到日本去的代替”[13]“知道有‘日本的,一定知道日本有‘富士,正如知道日本有‘櫻花一般”[14]等顯示的“富士山即日本”的固定認識和文化圖式。
顯然,對富士山作為日本國家的標志,民國文人不僅予以肯定,還隨著日本侵華野心的暴露而視它為日本軍國主義的標志,展開了對它的政治批判。他們或悲嘆以該山為表現的日本侵略主義對中國的侵害——“光榮燦爛的雙士碑,快要給東鄰富士山上吹來的白雪掩沒了”;或憤慨日本的狂妄——“大日本三日之內,即可完全占領中國,將來必捕汝等禁之于富士山之巔云云”;或激憤日本對華滲透之深——“另一張是傀儡‘訪日紀念郵票,中間的圖案,千不畫,萬不畫,卻畫著日本富士山的山景”;更多學人則呼吁國人奮起,發出了“驚醒神州夢,擊破富士缺”“快!快扛我們的大刀,肩起我們所長槍,沖!沖!沖到那富士山頭上”“殺到扶桑三島時,富士山頭看落日”“它就是中國今后抗爭的一支更有力的洪流。這支洪流,從華南、華西,展到華東、華北,流過鴨綠江,沖到富士山”等“攻占富士山”的抗日怒吼。還有人揭露了其所象征的日本軍國主義的丑惡本質。張光宇于《華中周報》(1943年)刊登漫畫《富士山頭的跳舞》,描繪了象征富士山頂的巨傘下群魔亂舞的日本人及通往柏林和羅馬的兩條道路,強烈批判了德意日法西斯主義;豐子愷于《導報》(1946年)刊載漫畫《富士山增光》,描寫了高出該山的兩顆巨樹、突兀的鳥居和一連串寫有“民主”的燈籠,暗示并批判了近代日本缺乏民主或反民主的反動性;雪門認為富士山、櫻花等都是日本對外擴張的象征符號,堅決要求避免其對國人尤其是兒童的毒害,“驅我們幾千萬坦白孩子的心,日和桃太郎、太陽旗以及一切繪有櫻花、富士山的玩具相接觸,是不是危險的事?我并不想倡什么狹義的帝國主義,然而斷不能讓含有侵略野心的帝國主義來浸染我們孩子的心!”[15]顯然,這是一種超越審美領域的抵抗視角的政治敘事,是“九一八事變”后中國學界富士山敘事和認識發生轉折的重要表現。不過,與這種主流敘事相比,少數人也嘗試將審美性與政治性相剝離,認為作為自然風景的富士山原本是一座“崇高而和藹”的巍峨山峰,“代表著大和民族的驕傲”[16],而與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無關。這類看似“中立”而應予以批判的觀點,也從另一側面說明了中國文人以富士山為日本國家象征之意識的普遍性。
既為國家象征,自然就與日本精神密切相關。關于這點,民國文人論述不多,也大體是在宗教、道德、藝術等領域展開。例如:王亮提出,有人因富士山千載積雪而以“天皇比富士山”[17],是以“皇基鞏固,萬古不移”,暗示其為“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的象征;有人提出“據友邦人士談,靈峰高潔秀麗之姿,可以代表雄偉剛健、崇高博大之大和民族性”[18],對其頗有附和之意;朱民威認為富士山是武士道的表現之一,“這座山給日本人一些夸大的狂妄鼓勵,加上鮮美易凋的櫻花,與日本柔順的女德,結合而成日本武士精神”[19];對于遠東審判時日本戰犯所詠“空籠煙霧長,云山兩茫茫。唯有富士雪,皚皚照遠方”的詩歌,有人評價“詩中承襲日本文學舊例,以櫻花及富士山為生命之象征”[20],認為富士山是日本人生死觀的體現;等等。可見,中國文人雖對富士山與日本精神的關聯做了多種解釋,卻較為籠統,也沒有形成統一意見。不過,也如“用泰山的精神消滅富士山之魔影”[21]所說,他們仍是確立了“富士山是大和魂象征”的觀念。
由上可見,從日本代表到日本國家和大和魂象征,富士山形象和意義的民族化和政治化色彩越發濃厚、突出,這不僅構成了中國文人眼中的富士山的主要面孔,也影響了他們對該山其他側面之形象和意義的認識。
(二)神山、靈峰
認為富士山是神山、靈峰,是晚清民國文人關于它的另一重要印象。在晚清,對中國文人來說,突然在日本見到一座堪與泰山比肩的特別高山,他們在感嘆大自然造化之神奇的同時,也認識到了富士山的獨特性和奇異性。康有為、蔣智由、高旭等高度評價了它的“奇異”面貌:“峰顛積雪照白日,高入青天一萬尺。云容容兮在中央,芙蓉碧瓣在下旁。倒入明湖影奇絕,黛色波容共明滅。有如白頭仙人擁玉女,縞衣羽裳飄瓢舉。白銀宮闕現華巖,金沙寶盾善見處。”[5]895他們雖未明確斷言它為神山,卻從靜態、動態或兩者結合的角度贊頌了其千載冠雪、撐天山高、獨特山形、奇絕湖影、旭日、夏如頑冬等奇異化的景象,塑造了富士山“驅遣六甲奪取造化工”“詩人筆力難以描述”或“高插重霄,山巔積雪不消,非游屐所能到此”[22]等神奇面孔。這些奇異化描寫是在東亞視域下對富士山的特殊性所做的“內部認定”,不僅易為中國人接受,也奠定了此后它在中國被視為神山、靈峰的經驗和歷史基礎。
不過,這種認識因有使富士山絕對化而致“主體消除”的風險,故民國學人即便有此看法,也不普遍。比如,有人認為“視富士山為圣山”只是日本人的自我認識[23],甚至并不是所有日本人的看法,只是“在一部分日本人眼中是當作神山來朝拜的”[24]。再者,對他們來說,富士山畢竟只是“異國之山”,故也并非“不可撫摩”。因此,“這便是被人羨慕的富士靈峰,一個火山爆發后的洞!歷史的陳跡”“靈峰富士”“誠為冠絕宇內之秀岳、靈峰也”等說法,不僅只出現于民國中后期,也大多是從風景的角度看待該山或不經意附會日人之說的結果日本人慣來重視向中國宣揚富士山的神圣性及其優越性。“九一八事變”前后,為了宣揚富士山這一屬性并由此鼓吹大東亞思想,日本學界創建了不少華文報刊如《東華》(1928)、《新醫藥觀》(1929)、《華文大阪每日》(1938)等,刊載了“神山鐘得秀靈氣,萬古巍然東海州”(宮原賢三《題富士山圖》,1932)、“高擎紅日立蒼穹,標得神州(指日本)千古崇。一氣秀靈鐘在此,巍然永鎮大瀛東”(手塚藤二郎《富士山》,1932)、“秀靈而峭拔,天下少比儔”(三浦豐二《游富士五湖》,1933)、“芙蓉萬仞玉孱顏,八朵玲瓏霄漢間。終古居然東海鎮,偉容卓絕五洲山”(森部逞禪《富士山》,1934)、“壓制四海的靈峰(富士山)”(鶴田吾郎《大東亞戰爭壁畫展覽會》,1942)等大量詩文。這些詩文以宣傳富士山神圣性、民族象征性及其優越性的方式,宣揚了日本作為“亞洲統治者”的合法性和正當性。。而且,以之為神山、靈峰,還因符合中國自古就有的“蓬萊傳說”“徐福傳說”等傳統思維這點也為“傳聞徐福引船去,方丈蓬萊至今在。……何須苦求不死藥,持此差可參神仙”(梁煥均《東游放歌》,1912)、“蓬山無意搜靈藥,目向滄溟一濯纓”(汪榮寶《蘆洲富士倒影……》,1928)、“三神山秀嶺,富士首推崇”(黃綬《伏日偕黃桂霖陳液華夜游日本富士山》,1935)等詩文所證實。;也如“靈峰富士山為世界人士憧憬的對象”[25]所述,還可能受到了歐美人相關認識的影響。66DBC426-1084-4E1A-B9AE-31DE04CCCD64
可見,富士山作為“信仰對象”,是與中國文人最不相干的形象,故他們能以局外人的身份看待它。他們雖然普遍承認該山的奇異性,卻并不完全贊同它的“神山”屬性。因此,他們既有像“車上的女人們,當火車經過這山前的時候,大家都合掌頂禮,在我們中國這種事情大概只是鄉嫗們的玩意,但在日本是不足為奇的”[26]“德川時代,富士講社盛興,登山朝拜者,身著白衣,腰系響鈴,登山之日,虔誠沐浴,以示六根清靜而朝寶山。登山次數愈多,則以為莫大之光榮,所衣白衣遍捺證印,此亦習俗之一也”[18]43等說明日本人信仰虔誠的論述,也有據此批判其迷信之論。高旭批評:“淺間神社所祭之神為女神,名木花開耶姬,游人爭拜之,其迷信如此”[8]38。對于戰敗后東京流行的“富士山將爆炸”的謠言,馬軍批評說:“大街小巷的東洋佬,都在把神秘之事當正經……迷信之談哄動全國,如此幼稚之舉實在是頗可笑。”[27]顯然,這一論述與日人宣傳的“富士山并不是攀登的山啊!卻是仰望的山呢”[28]的形象相違背,說明中國文人在看待該山時具有較強的自主性和自由性。
(三)絕景
認為富士山是一處奇觀絕景,幾乎是晚清民國文人的共識,也構成了其富士山敘事的另一主流。他們如此主張的理由是它作為奇觀的風景奇異性和極致性。以“千年積雪”為例,它可說是晚清民國文人的共識和固定認識。因為這點,一些學者甚至認為雪是構成富士山絕景的最大元素:“秀潔絕塵的富士,這不是火山,而是雪山”“蓋終古不化,故亦‘雪峰”。以“山與旭日”為例,化成的《登富士山》、田雨的《登富士山記》等是描寫并贊美這一景致的典型,它們共同塑造了“天邊的云,一陣紫,一陣黃,又一陣紅,變幻著種種顏色,叫人覺著美麗、愉快,然而卻沒有法子形容得出”的富士山旭日絕景。可以說,這種贊美性描寫通常也不僅限于其中的一種元素,而是多種元素的綜合。
晚清時期,以康有為、蔣智由、高旭、孫景賢為代表的富士山風景描寫奠定了中國以其為“絕景”的經驗基礎。他們基于中日一體意識,形成了對它的一邊倒式贊美乃至羨慕。例如,康有為在盛贊富士山“山嶺積雪,冬夏不化,云在中層峰在下,倒影湖中,澄鮮幽絕,誠異觀也”后,對它表現出“惜非吾土難淹留,王孫芳草解幽愁”的艷羨之意。中國學人甚至對其風景或山高感到了壓力。例如,高旭面對其所象征的“日本之崛起”,而欲通過對它的矮小化來化解,“亞細亞洲著名高山共有五,也窳勒斯得山推巨宗。……果達因奧斯典亦峻絕,富士雖高對之為附庸。此外新高山之高度足與富士并。……支那高山原自有,考夫曼峰頂天拔地萬古云滃滃。若以尊卑長幼之禮論,富士屬弟子列當鞠躬”[4]107,并希翼“大唐仁貴征東定三箭,何日得再高掛天山弓”。這種揚我貶他的認識,從另一側面反映了近代以來富士山及其象征意義對中國文人的自我構建所產生的巨大壓力。
至民國,對于富士山作為風景的側面,文人們整體上保持了高度贊賞的態勢。他們不僅繼續贊美其“秀潔絕塵”[29]“霧鬢云裾絕代姿,也能妖艷也能奇”[30]等風景的奇異性和極致性,也肯定其“的確有她那特殊的美處,有她那濃厚的親和之光現露著……對于富士山,可以從畫里的傾慕,進而為實地的親炎,那是何等有意味的事”[31]“山峰伸入雪片里,山上堆著潔白的雪,望過去叫人有愉快和崇高的感覺”[32]等帶給人們的美感和快感,還有人以“途次倉卒,不及登富士山為缺憾”[33],或坦承“蒞其地者無不羨其美麗而莊嚴”[34]。
還如“櫻花是代表日本的國花,和富士山一樣的著名于全世界”[35]“翌晨破曉已行近富士山……小泉八云《登山游記》所述之風景,頓現目前,一若吾正偕彼日本化之愛爾蘭文豪,共柱杖躑躅積雪四被之熔巖間者”[36]等所述,他們也開始在世界范圍內來看待和定義富士山的風景。這意味著,它的意義不僅獲得了普遍認可,還發生了被“樣本化”的價值提升。換言之,隨著認識的加深,中國學界逐漸形成了以富士山或其風景為一種價值判斷標準的意識這種思維自民國以后就已十分普遍,相關論述更是比比皆是,如“墨西哥京城附近有一火山……形勢風景與日本之富士山相似”“惟夏威夷島有高山二……兩山終年積雪不化,與日本富士相似”“已死之火山,其山巔時露白色,與日本富士山相仿佛”“煙山……峰頂積雪呈奇觀,全美無出其右,較之日本富士,猶高出三倍”“曼洋火山,所謂菲島之富士山”“恰巧三年前,也是九月。在日本箱根蘆之湖畔望富士山的時候,也就是這樣境界。我卻在三年后的今日,來到日內瓦,忽然出神叫著:‘就像看了富士山似的。”“起伏著的紫金山在西首靜峙著,有一高峰突尖銳,頗類日本的富士”“達馬溫德山在德黑蘭城東北,波斯人對于這座山的愛重不亞于日本的夸耀富士山”等。。顯然,這是一種剝離了政治性而對富士山進行普遍化對待的思維,不僅極大提高了它的地位而使它成為一種所謂“獨立的”價值源泉,還為其民族化奠定了更牢固的思想基礎。由此,它不僅被認為是“日本美”的重要構成——“日本在中國東方的海里……扇形的富士山、燦爛的櫻花,處處顯出她自然風景的清麗”[37],還被捧為“世界上兩塊‘風景之區、享樂之鄉”的“萬山之王、眾岳之宗”[17]23,“誠為冠絕宇內之秀岳靈峰也”[18]42,“足與世界名勝并駕齊驅”[38],甚至體現了一種“偉大的”人性之美——“她是如實地代表著整個自然界的母性愛的一部分,而告訴我們以自然而不因人事的變遷而失掉她的美,減掉她的親和之光”[33]47。顯然,這種認識不僅造成了不少人對富士山的“迷戀”——“這些年頭,提到日本心里總是不舒適,然而仍然忘不了富士山”[24]78,也對日人借富士山構建自我的作業提供了外部證明。換句話說,它不僅為日本擺脫中國神山話語體系提供了依據,也為富士山所象征的大和魂的獨立性乃至“優越性”提供了證明。
與此同時,中國一些學人,如張玉森、王亮等,或闡述富士山登山史,或引用歷史上中日兩國學者(如宋濂、林羅山、賴山陽、安積良齋、黃遵憲等)贊頌富士山的漢詩,以論證富士山作為絕景的歷史合理性。66DBC426-1084-4E1A-B9AE-31DE04CCCD64
這種富士山普遍化和歷史化的作業增強了它作為絕景的合法性和說服力,也不自覺地為以它為日本國家和精神象征的思維提供了物質基礎,進而為“將日本精神、興東亞精神寄托于富士靈峰,象征東亞光明”[39]的日本侵略主義提供了辯護。
不過,與這種主流敘事相比,少數人對作為風景的富士山不以為然,不太認可它的“偉大”或“美麗”。有人指出,富士山是“用泥土做成一座穿頂的假火山”[40];凌叔華(1900—1990)坦言:“我向來沒想過富士山是怎樣巍大,怎樣宏麗,值得我們崇拜的……所以富士山在我腦子里只是一座平凡無奇的山”,由此嘲諷“日本人連一國最崇拜的山都要制造出來”[41];曾今可認為,“富士山除了那山巔的永不融化的積雪是別無可取的……櫻花能如富士山一樣,自然更說不到偉大或深刻的印象了”[14]46。這種審美性的否定評價雖然可能源自基于抗日情緒的富士山政治批判,卻也代表了客觀認識富士山的“第三只眼”。
總之,對作為風景的富士山,中國文人大多呈贊賞和肯定態度,尤其是對它的普遍化和歷史化作業不僅建構了富士山之美的合法性和優越性,也為它所象征的日本精神提供了合法性。對它的風景批判在民國時期雖只占少數,也可能是受政治批判之影響的結果,卻對破除當時中國多數文人的富士山迷戀和日本人的富士山絕對化宣傳有重要意義。
(四)避暑勝地
在中國文人眼中,富士山還是一座可以避暑消夏的享樂之山。晚清時期,他們雖未明確此點,卻也有了“日本入秋以后,反覺暑氣薰蒸……然客有自富士出來者謂,上月二十六號已降雪一次,同在一國之內而冷暖大不相同”“凜冽森寒去弗留,此間六月著重裘”[8]39等富士山適宜消夏的描寫。民國以后,隨著近代休閑思想的傳播,中國文人開始用“避暑勝地”等字眼描述富士山的這一形象。例如,基督教報刊《時兆月報》(1929)的封底曾以中立的語氣說“富士山是日本的一個名勝……山頂終年積雪,為夏日避暑的勝地”;莫奭在《中國漫畫》(1936)上刊登“若干年后中國要人避暑廬山和莫干山之外,尚有一勝地富士山”的漫畫,以嘲諷的口吻道出了其為避暑地的事實。同時,子駿、田雨等還以親歷者身份介紹了游日之客和日人盛夏登山消暑的盛況,“日本消夏的趣味不完全趨重海水游泳,而一部分卻往山里消夏,因此登山成為時髦流行的事情了”[24]79。這說明,富士山作為避暑勝地,本身與政治無關,故得到了民國文人的廣泛認可。
(五)晚清民國文人對富士山的認識特征及其變遷
綜上可見,晚清和民國兩個時期中國文人的富士山認識和敘事雖有很強的繼承性,卻又有明顯分別。晚清文人對富士山大致形成了作為日本代表和絕景的兩種形象,整體上對它呈現出客觀敘述和贊美的肯定性評價,也對其絕景及其象征的“日本的崛起”感到了巨大的壓力。因為是“初識”,其認識既有客觀介紹或轉述的側面,也較少受到日本人的富士山宣傳、“近代思維”等因素的影響,故不僅更具神秘化色彩,也由此體現了更多的經驗主體性。民國以后,隨著對富士山認識的加深,又受中日關系變化、日本人宣傳等多種因素的影響,中國文人不僅對它形成了“日本國家和精神象征”“信仰對象”“審美對象”“享樂對象”等多種形象,也逐漸向“贊美和批判并存”的立場轉變。對其之批判以政治批判為主、審美性批判為輔,始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集中發生于“九一八事變”之后,而與民國時期對日認識的整體趨勢相符;對它的審美性批判始終只是少數,很大程度上亦起因于日本對華經濟擴張和軍事侵略的逐步展開。故此時期中國文人的富士山認識不僅有經驗的側面,也更多體現了知識和政治的內容。
二、晚清民國文人富士山認識的成因
多種因素規定了中國文人的富士山認識,其決定性因素是主體自身的經驗和知識,而日人的富士山傳統認識和宣傳、中日關系變化、近代文明觀等,也對中國文人的富士認識有重要影響。
第一,經驗即直接體驗和間接經驗是形成中國文人富士山認識的決定因素。他們的富士山敘事大多源于遙望或攀登該山的直接體驗。因為“真實的”體驗帶來了從感官到心靈的強烈沖擊,以致多數人不自覺地對它產生贊美之情乃至“多少有些戀戀不忍舍”[42],而形成了片面贊美或贊美占主流的富士山敘事。這種認識一旦確立,就具有相對穩定性和持久性。閱讀、聽聞等間接經驗也是塑造其富士山認識的另一方式。不過,它也因臆想性而有易被主體不斷修正的特征。例如,關于富士山的起源,晚清時期曾被援用的“近江國地坼,湖水湛,富士山出”(王先謙《日本源流考》卷一)等說法,至民國后幾乎不被提及。從這點上說,中國文人的富士山認識主要依靠的是主體的經驗,故有相當的自主性和自由性。
第二,“近代的知識”且多數時候是通過日本獲得的“知識”,對中國文人的富士山認識也有不小的影響。這主要是指近代文明觀和認為“風景與精神密切相關”的思維。首先,劉海粟等肯定富士山體現了“日本民族追求光明的心情”[43]或“象征東亞光明”[39],就是承認日本文化兼采東西方之所長的結果。這種認識不僅根植于富士山自身的物質屬性,還使它披上了“文明”的外衣,構建了它作為“極致風景”和“文明象征”的現實合理性,也由此對當時及其后中國人的富士山認識構成了雙重壓力。其次,自赫爾德建立體系化的“風土論”后,認為風景與精神密切相關就成為一種“近代的”思維。這種思維在近代日本盛行一時,是其構建自我的一種重要理據[44],也影響了中國文人的富士山認識。史學家王樹枬(1851—1936)關于風土與國民性的看法就是典型。他沿襲日本教育家山路一游區分“國民教育”和“道德教育”的觀點,指出“各國之民,皆各有特別之性”,而國民特性“蓋由土地(即內地)、疆土(即領土)、歷史而生也”,故風土尤其是一國的代表風物對其國民性的形成有重要意義。他進而認為“日本富士山、琵琶湖,皆特別之山水也。國民睹此山水,無不生其愛國之情,此國民之特性,由土地而生也”[45]。植物學家胡先骕也認為富士山構成了日本宗教與藝術的源泉,“此山不僅為蓬瀛三島之名勝,實為全國人民精神生活之所寄。……矧日人浪漫性成,酷嗜美術,則富士不但以壯偉動其宗教之忱,且以秀麗起其美術之愛也”[36]12。后來,陳靈秀又進一步論述了日本風景與精神的密切關系,認為“滋養日本精神,其風景之影響于情感,可謂大矣!”[46]這些都說明,民國學界確立了風土與國民性密切相關的思維范式。受其影響,有學人甚至認為一國之物件都與國民性相關,“中國的玩具,自有中國國性的特色;一種物件的出產,總難脫離時代和環境的關系,所以玩具也不能逃出這重范圍”[15]。這意味著,中國學人的富士山認識不僅深受“風土與精神”之近代思維的影響,還自覺或不自覺地做著“富士山是日本精神象征”的論證,并為其提供著所謂“科學的”“外部的”依據。66DBC426-1084-4E1A-B9AE-31DE04CCCD64
第三,日本人關于富士山的傳統認識作為“知識”也對中國文人的富士山認識有重要影響。在晚清,雖因之前中日之間缺乏雙向的知識交流,而致中國文人對日人的富士山傳統認識了解不夠,也因這點較少受到它的影響。但民國以后隨著中日交流的深入展開,他們的富士山敘事就明顯受到了日人傳統富士山認識的影響。關于其山形的“白扇倒懸”“芙蓉(峰)”“八面玲瓏”等說法是其典型。
“白扇倒懸”是民國文人塑造富士山特殊性的重要元素,而在晚清它幾乎不被提及,有的只是“墜白帽”“高擁銀髻髽”“白銀闕”等自主性描述。這說明,他們幾乎未受石川丈山(1583—1672)詠“仙客來游云外巔,神龍棲老洞中淵。雪如紈素煙如柄,白扇倒懸東海天”后,日人確立的“白扇倒懸”之富士山形象的影響。與此相對,民國文人如凌叔華、張玉森、王亮、陳靈秀等不僅引用了這一說法,還對它極為肯定。“山作八字形,日人謂其白扇倒懸,信然。”[47]“昔人有詠之為‘白扇倒懸東海天,洵不誣也。”還有民國文人在此基礎上采用了“一扇撐天險”“扇形的富士山”“折扇倒垂似的山形”“遠看像一把倒置的扇子”等說法。當然,對富士山在使用“白扇倒懸”的同時,他們也有“山神戴白帽”“像醫院的女護士般戴著白帽亭亭地玉立著”等描寫。這說明,他們關于富士山山形的認識既有一定的主體性,也深受日本人傳統認識之影響。
視富士山為“芙蓉峰”,始自鐮倉僧侶對它的描述如“雪貫四時磨碧玉,岳分八葉削芙蓉”(虎關師煉《濟北集》卷二)、“八葉白蓮之靈岳,五智金剛之正體也”(玄棟《三國傳記》卷十二)、“其形合蓮花似,頂上八葉也”(《塵荊抄》卷十一)等。,至江戶則成了日本文人的固定認識。在中國,目前可見最早如此描述的是黃遵憲,為“其狀如芙蓉,四面皆同”。稍后,王韜游日時也說“從橋上南望,芙蓉峰隱約可見。芙蓉峰者,富士岳最高頂也”,又引奧田遵《富岳詩》之說——“一朵芙蓉擎碧空,千秋鎮護日之東”。這表明兩人都認可以富士山為芙蓉峰的說法。因為他們都與日本文人交往甚密,故很難斷定其看法究竟是受日人影響之結果,還是基于主體經驗的認識結果。不過,高旭所詠“芙蓉八朵悉清凈,妙歷華嚴第一天”,及其注釋“富士山頂八峰環繞,故有八芙蓉之目”[8]39表明,它很可能是前者。雖然晚清文人廣泛使用“芙蓉(峰)”來稱富士山,且日人也向中國大力宣傳它的這一形象,然民國文人卻很少采用這一稱呼,即便有也大多是引前人之說,如王亮所引黃遵憲之“拔地摩天獨立高,蓮峰涌入海東濤”和安積艮齋之“萬古天風吹不斷,青空一朵玉芙蓉”。
關于富士山形的描寫,還有一個重要形容即“八面玲瓏”。它源自富士山圓錐型的山形,始于鐮倉禪僧對它的美化——“八面都無向背處,從空突出與人看”[48]。江戶時代以后,經宣傳和教育這種“完美無缺”的富士山形象便成了日人的共識。在中國,晚清文人幾乎沒有類似論述;至民國,關于該山為“圓頂”的形象,君豪的《殘春小語》、王桐齡的《箱根游記》、辛爾的《富士山遠景》等都有所提及,可斷定為學人的共識。不過,直接以“八面玲瓏”來描述者并不多見,僅有“富士還是方繞看的一樣,嬌然立著,若不是八面玲瓏的圓錐體,哪會如此?”“巍峨富岳高千仞,八面玲瓏出一頭”等少數幾例。由此可知,這一說法亦可能是受日人富士山認識之影響的結果。
第四,明治維新以后,日本官知不僅對內,也著力向中國乃至全世界宣傳富士山作為國家和民族精神象征的形象。例如,1917年11月22日駐滬日本報界為即將赴日的中國記者舉行歡送宴,其中井手三郎致詞說:“諸君此次赴日歸來,其效果必可化除兩國向來之誤會,增進親善之睦誼,并冀諸君一游富士山,又藉知日本之國體,再游伊勢大宮,可知日本之歷史。”[49]此論雖以“誤會”掩飾了日本對華的侵略企圖,卻大力宣揚了富士山作為日本國體象征的形象。又如,“九一八事變”前后,日本學界相繼創建了《東華》《華文大阪每日》等專門面向中國讀者的漢文雜志,以富士山神圣性和優越性的宣揚為鼓吹大東亞思想的重要環節,“富士山為日本代表之山,聞名于世界”[50]。尤其是1928年8月在東京創刊的《東華》雜志,打著“謀求振興東亞文藝”的幌子,在1932—1936年間刊登宣揚富士山的漢詩達30余首,成為當時日本鼓吹侵華正當性的重要輿論陣地。
中國一些學者對這種“轟炸式”宣傳的批評也可說明這點。劉一之指出,日本向華傾銷的物品“常常附著一張藝人所設計的廣告畫——蔚藍的天,或者浮著綣舒的云帷,或者襯著黃昏中醉了的晚霞,在這輕悠、動人的背景中,往往嵌襯著一個潔白的尖頂,這說是富士頂上的雪”[51];凌叔華認為“一向所看見的富士山影子,多是一些用彩色渲染得十分勻整可是毫無筆韻的純東洋畫與不見精彩的明信片,或是在各種漆盤、漆碗上涂的色彩或金銀色的花樣” [41]12。這些批評,不僅說明日本的對華富士山宣傳是一種從物品到文藝乃至宗教的全方位作業,也從另一角度說明中國文人的富士山認識受到了它的影響。
中國一些學者則對這種宣傳給予“積極回應”。換個角度說,他們對日本乃至富士山的“異常關注”,發揮了附和乃至傳播日人富士山宣傳的作用。對他們來說,近代日本一度“領先”中國,所以這種回應不僅是知日的一種途徑,也是可以實現自立自強的重要方式。這種歷史規定性使其有時不得不接受了日人的相關宣傳,甚至還因“內部東方主義”立場賦予富士山對抗西方的性格,而對其寄予厚望。一方面,為了介紹和理解日本,他們譯介了不少有關富士山的論述,如《日本少年歌》《富士與日本阿爾卑斯》《富士山》等。這些“外部”譯介形成了對富士山民族性和“優越性”的“確認”,不僅附和了日人的相關宣傳,也對其在中國的傳播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一方面,這種關注使“富士山變形”“富士山大雪”“瑞典皇儲富士登山”等成為中國文人眼中的“新聞事件”,也使其風景之類的照片成為新聞界的“寵兒”。例如,何鐵學乘赴日游歷之機,攝影含富士山之內的照片七百余幅,“歸國后為使國人認識日本起見,特將所得選出佳者二百余幅,放大裝幅,歷在廣州、南京、天津、北平等地公開展覽,得各地人士之好評”[52],還被認為對理解日本及于我們自己的發展都很有裨益[53]。再如,1943年4月-6月日本國際文化振興會在華舉辦了名為“振興東亞之文華,以資風教”而實為文化侵略宣傳的“現代日本畫展”。該展覽分三次在北京、南京和上海舉行。其精選日畫66幅,其中一幅是橫山大觀所作以富士山為背景的“黎明”。該畫以日本在亞洲最早承受朝陽的地理優勢來宣揚日本文明的“先進性”和“優越性”,也“如愿地”在藝術性和民族性上受到劉海粟、顏文梁等繪畫名流的高度贊賞:“橫山大觀‘黎明,墨筆富士山,斫輪老手,雄穆二字,當之無愧。”[54]“寫富士山朝陽初露,皚皚白雪,反映天空,山下清煙彌漫,觀托山頂,極為雄壯,將日本精神、興東亞精神寄托于富士靈峰,象征東亞光明。”[39]可見,這種以富士山為“東亞文明之光”的思維和敘事,不僅做出了符合日人宣傳目的的解釋,還增強了它作為“文明的超克”之象征的合法性。顯然,中國學界對富士山的特別關注既受到日人富士山宣傳的影響,又出于合力抵抗西方之目的,因而最大可能地推動了這種富士山形象在中國的傳播。66DBC426-1084-4E1A-B9AE-31DE04CCCD64
第五,中國學人的富士山認識還受到中日關系變化這一政治因素的影響。晚清時期,學者大多對中日兩國持“同文”“親睦”[1]392意識,故對富士山也呈現一邊倒的贊美甚至羨慕。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隨著日本侵華野心的暴露和實際展開,對富士山中國學界轉向了“贊美和批判并存”的立場,甚至視它為“惡魔日本”的象征。這種批判立場的形成,無疑是受政治因素影響的結果。
綜上可見,晚清民國文人的經驗和知識作為主體自身的內部條件,日人的富士山傳統認識和宣傳、近代文明觀、中日關系變化等作為外部條件,共同塑造了他們的富士山認識。
三、晚清民國文人富士山認識的影響
晚清民國文人的富士山認識,對當時中國人的自我認識產生了積極和消極的影響,同時也構成了中國富士山認識的歷史和傳統,影響乃至左右了現代中國的富士山認識;它也作為一種“知識”發揮了跨文化或跨國境的作用,即對日本人的自我認識產生了影響。
首先,中國文人的富士山認識是促使中國形成“國山”論的重要原因。關于這點,學界的論述并不多見,其典型則是《定泰山為國山芻議》。該文認為,如同“日本以富士山代表其大和魂,號召國民仰若神圣”一般,近代國家都有“國民所瞻仰,民族歷史家所歌頌,詩人所贊美,以范鑄其民族、其國民之品格”的國魂及其“具體之象征”——“國山”和“國花”。以富士山和泰山為例,該文認為,前者代表了侵略且衰老的大和魂,后者則代表了和平且朝氣活潑的中國魂。“日本帝國主義者,以富士山為國山,因而號召其所謂‘大和魂,以妄肆侵略而不顯。富士山……其山嶺終年積雪,如白頭翁,為民族已衰老之象征;又為火山之遺體,是大和民族已為殘骸;又其山土石雜陳,已不純粹。泰山則不然,‘觀日為泰山上之壯舉,可以暢吸宇宙之朝氣,滿山飛瀑如練,象征中華民族活潑潑的精神;全山皆為石山,巖石巍巍,極有骨格,蒼松翠柏,最能耐寒,挺秀千古,非如富士之不毛也。”[21]6根據泰山的這種優越性,作者主張運用“具有剛健中正四大德性”而足以代表中國國魂的泰山精神“消滅富士山之魔影”。可見,作者關于兩山的描述雖因情緒化而略顯無力,卻也說明其“國山”認識某種程度上是“意識”到了富士山之后的產物。從這種意義上說,它實際上促進了中國的民族國家建設,可算是對中國的積極影響。
與此相對,這種認識也使作為風景、日本精神象征和“文明象征”的富士山對中國人形成了強烈的壓迫,使它成為自我敘事時無法避免甚至是難以逾越的“山”。對于作為風景的富士山,中國文人大多持贊美或羨慕的肯定態度,承認它作為“風景”的極致性和獨特性。相反,對它進行審美性批判的學者極少。可以說,這種風景贊美作為一種固化的認識基本壟斷了中國的各種話語通道,恰如江戶學者荻生徂徠所唱“秋色將欲盡,芙蓉峰上雪,寒色照人來。不知中華有此好孱顏否?”[55],給中國人造成了極大的“風景的壓力”。而且,中國媒體爭先報道的“美艦隊擬游富士山”“瑞典皇儲富士登山”“‘蝴蝶夫人逝世:臨終前變為基督教徒,要求安葬在富士山麓”“富士的美景是日本的特征,為世界所贊美,日本人都是為富士美景所陶醉”等消息,更使中國文人意識到,富士山的極致之美也是被西方認可的美。這進一步造成了他們的焦慮和不安,以致形成“這些年頭,提到日本心里總是不舒適,然而仍然忘不了富士山”的兩難之境。因為這種固化了的富士山絕景形象不僅給中國人造成了“中國缺乏此等絕景”的風景壓力和假象,還為它所象征的日本民族精神乃至“東亞光明”及其合理性提供了一定的物質支持。
富士山和櫻花都被認為是日本國家和大和魂的象征。晚清民國初期,中國文人一度對大和魂極為肯定。他們幾乎一致認為“大和魂即武士道”,甚至也認為它是一種“怪物”[56],卻又不得不承認它對日本近代化所起的巨大作用。“我東鄰之日本,其人數僅當我十分之一耳,然其人剽疾輕死,日取其所謂武士道大和魂者,發揮而光大之。……彼日本區區三島興立僅三十年耳,顧乃能一戰勝我,取威定霸,屹然雄立于東洋之上也。曰:惟尚武故。”(梁啟超《論尚武》)“日本居扶桑,蕞爾三島,人口不過六七千萬,居然能躍為一等國,稱雄于世界。考其強盛,在于明治之維新,采取他人之長,以改革其政制,效仿西歐,而不廢其祖遺之國粹——武士道·大和魂,即其致強之所由起也。”[57]這種大和魂論隱藏了一個重大命題即“日本的近代化獲得成功,正是因為有了大和魂”,而其重要表現就是作為“優越的祖遺之國粹”和“近代文明象征”的富士山。這一思維給中國學人的中日相互認識尤其是富士山認識造成了“雙重的壓迫”。一方面,它給中國文人造成了“中國無山可與富士相抗衡”乃至“中華精神不適應于近代社會”的假象乃至壓迫;一方面,富士山還被認為是承載了日本作為“一等國”形象的“文明標志”,甚至被認為是兼采東西方文化之長而比西方文明“更高級”的日本精神的象征,而這更給中國人造成一種“富士山乃至日本無法被超越”的假象乃至“近代的壓迫”。在此背景下,不僅日本被一些國人當成是“文明的異國”[58],富士山也“被證實”為一座“成功的”神圣之山,“既可寄托‘優越的日本精神,又可寄托興亞精神的”文明之山,而“登山”也被認為是“領略其文明景象”[59]的“朝圣之旅”。顯然,這種認識極大妨礙了此時期中國的主體性和民族性建構。而且,遺憾的是,它還作為一種逐漸被固化了的“傳統”影響了其后中國人的富士山認識乃至自我認識。
其次,中國文人的富士山認識也對日本人的自我認識產生了影響。因為這種影響的發生不僅與中日政治、經濟和文化關系密切相關,也與話語主導權之所在緊密相關,故不同時期中國文人的富士山論述在對日影響上也有著截然不同的命運。
晚清時期,基于中日兩國文人普遍認可的“同文同源”意識,不少日本人仍對中國文化保持著崇敬的態度。這從黃遵憲、王韜等人滯日期間,日本人與他們展開的熱烈交流便可窺知一二。王韜記錄黃遵憲與日本人的交往說,“日本人士耳其名,仰之如泰山北斗,執贄求見,戶外履滿,而君為之提倡風雅,于所呈詩文,率悉心指其疵謬所在。每一篇出,群奉為金科玉律。此日本開國以來所未有也”(《日本雜事詩序》)。與黃遵憲相交“最深”的石川英也自述,“入境以來,執經者、問字者、乞詩者,戶外履滿,肩趾相接,果人人得其意而去”(《日本雜事詩跋》)。可見,他們滯日時受到了日人的尊崇,其贊美富士山的詩文自然也對日本人產生了影響,因為它增強了日人對于富士山的自信。《日本雜事詩》及其“富士山”詩(“拔地摩天獨立高,蓮峰涌出海東濤。二千五百年前雪,一白茫茫積未消。”)在日本的命運就是明證。該詩集高度評價明治維新,極力贊美日本的政治改革、社會氣象和風景,故受到日人的追捧,不僅于1880年被大河內輝聲立碑紀念,還在日多次再版。尤其是該詩被認為“確實適合于詠唱斯山”[60],因而被收入《昭和漢文入門》(山田準,1934)等教科書之類的書籍。這些情況說明中國晚清文人的富士山認識對日本人的富士山認識產生了影響。66DBC426-1084-4E1A-B9AE-31DE04CCCD64
與此相對,隨著甲午戰爭以后中日自他關系的歷史性轉換,幕末以來部分日人極力構建的“落后的”中國形象被逐漸“坐實”,故對日本來說源自中國的“富士山贊美”已不再是不可或缺。因而在“弱者”被任意欺凌的近代,中國學人的富士山論述最終只是被一味地無視或踐踏,而難以發揮跨文化的作用,且這種狀況也持續到了現在。例如,2012年日本政府提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富士山申遺書,所引歷史上外國人關于富士山的論述全是西方學者的論述[61],實際上其申報主旨“富士山:信仰的對象與藝術的源泉”很早就已由中國學者所指出——“矧日人浪漫性成,酷嗜美術,則富士不但以壯偉動其宗教之忱,且以秀麗起其美術之愛也”[36]12,但這卻完全未被提及。可見,即便他們的富士山論述具備有利于日本人構建自我的元素,卻因力量關系等因素而被有意或無意地掩蓋或無視。不過,無論它是否對日人的富士山認識產生影響,其以贊美為主的富士山論述對增強日本人對富士山的文化自信始終具有外部的支撐作用。
可見,中國文人的富士山認識因文明觀、中日關系等因素在不同時期對中國人和日本人的自他認識產生了不同的影響。而其最大問題是構成了中國富士山認識的傳統,影響甚至左右了現當代中國人的富士山認識。
結 論
對晚清民國文人來說,富士山始終是一座“特別的”山峰。這種特殊性意味著,富士山既是一座“異國之山”即異文化視域下的山峰,還是一座“東亞之山”即東亞文化視域下的山峰,也是一座“世界之山”即文明觀視域下的山峰。換言之,中國文人的富士山認識是“經驗”與“政治”、“中日間文化”與“異文化”、“東方”與“西方”三組概念所共同規定的范疇。或者說,“經驗”“知識”和“政治”共同塑造了他們以贊美為主的富士山認識。
第一,中國文人的富士山認識是主體與客體基于經驗發生知識性·情感性聯系的過程和結果。“經驗”是指他們對富士山的直接體驗和間接經驗,是塑造其認識的內部因素;“情感”是指因中日關系變化導致的對富士山的態度和立場,是塑造這一認識的“政治”因素和外部因素;“知識”是指關于富士山的傳統認識和當時占支配地位的價值觀,是介于內部和外部之間而塑造其富士山認識的中間因素。基于“經驗”,他們形成了以贊美為主的富士山認識,不僅承認其獨特性和對日本的特殊意義,甚至使它成為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山峰判斷標準;有關富士山的傳統認識和近代文明觀作為“知識”則影響著他們的富士山認識,即導致他們接受了不少日本人關于富士山的看法,甚至以其為“文明的象征”;日本對華侵略導致的兩國關系惡化,促使中國一些學者開始視富士山為日本侵略主義的象征,而展開了對它的批判。可見,對于跨國境事物的認識,不僅取決于主體對客體的審美體驗和認知水平,還受限于因“跨國境”導致的主體對客體的政治態度和情感。
第二,中國文人的富士山認識也是“中日間文化”與“日本文化”這組概念所規定的范疇。前者是指中國文人認識富士山的東亞文化視域,后者是指作為“異文化”的日本文化,它們都是一種 “作為知識”的存在。對一部分中國學人來說,富士山首先是一座“東亞之山”,既有東亞的共性,又有日本的特殊性。這種認識的思想基礎便是中日“同文同源”意識,也是中國文人普遍秉持的一種理念。“中日兩國,同種同文,繪畫亦同一轍”[54]80“……優游海外,觀賞富士山奇景,或參與櫻花佳節,而且大家都屬黃種,何必有分彼此,再照遺傳說起,日本還是我們的子孫呢”[62]等表述足以證明這點。可見,“同文同源”是此時期中國多數文人看待日本事物的一個重要視角。因為這點,他們非但不敵視富士山,反而對它抱有相當的親近感和認同感,不僅視其為與中國有著深厚文化淵源和地理關系的“東亞之山”,還較自覺地接受和認可了兩國文人歷史上關于富士山的形象定位。與此相對,在他們眼中,富士山還是日本文化規定下的“異文化之山”,即大和魂的表征。這種思維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中國人富士山認識的轉變,即從一戰前對大和魂及富士山的贊美轉向一戰后贊美和批判相兼的立場。總的來說,因為“同文同源”的一體化意識,他們的富士山認識反而更易受到日本人傳統富士山認識及其意識形態宣傳的影響,因而不僅具有附和其宣傳,甚至被惡用于增強日本侵華之合理性的可能,實際上在一定程度上也發揮了日本對華侵略之“幫兇”的作用。可見,東亞或東亞文化作為一種范疇和尺度,對中國人的富士山乃至日本事物的認識具有很強的規定性。
第三,中國文人的富士山認識還是“東方”與“西方”這組概念所規定的范疇。它既是一種對近代化及其觀念的反動,又是在文明觀大逞其威的時代不得不接受其規定性的悲壯之聲。一方面,這種認識是東方自主性的吶喊,體現了一定的“保衛東方”乃至抗衡西方的“內部東方主義”意識。富士山妖所說的“尤其是最近的國民崇尚時髦、醉心西洋,忘卻日本原來的長處”等“國民無秩序的時候”,就以地震或噴火來警戒[28]120,以及劉海粟肯定日本繪畫兼采東西之所長等,就是這種意識的典型表現。可見,這種中日一體意識使中國學人一度對富士山寄予厚望,而這也是他們視富士山為東西文化調和之象征,對其不吝贊美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他們的富士山認識也受到了近代文明觀的影響和束縛。這不僅導致富士山被構建為日本獨特性乃至“優越性”的表現,還因日本近代化的“領先性”而使它被認為是“文明的象征”。這不僅給中國人的富士山認識乃至自我認識造成了“近代的壓迫”,也構成了近代日本脫離中國文化射程的典型事例。可以說,在東方無法定義自我的近代,這種普遍存在的、一時的“近代的壓迫”也成了規定中國文人富士山認識的一個重要維度。
可見,晚清民國文人塑造了富士山作為“異國之山”“東亞之山”“文明之山”的多重面孔,而對它的認識則是主體與對象在一定時空內基于經驗發生知識性·情感性聯系的過程和結果。這一過程生成了中國文人關于富士山的新認識和新意義,而它們經過時間的演繹又將成為“傳統”在將來發揮作為“知識”的作用。這反映了主體認識異國事物的一般機制和原理。66DBC426-1084-4E1A-B9AE-31DE04CCCD64
[參 考 文 獻]
[1]王韜.扶桑游記[C]//王曉秋.日本日記·甲午以前日本游記五種·扶桑游記·日本雜事詩(廣注).長沙:岳麓書社,1985:385.
[2]任鈞.漫談自殺[N].申報,1946-04-05(24472·6).
[3]觀云.富士山[J].新民叢報匯編,1903:1204.
[4]天梅.游富士山[J].醒獅,1905(1):105-106.
[5]更生.蘆湖樓正望富士山[J].清議報,1899(14):895.
[6]陳明遠.重九日為黎星使陪宴……[N].申報,1889-10-17(5926).
[7]志賀重昂.日本少年歌[J].新民叢報,1902(2):103.
[8]天梅.游富士山雜詩[J].復報,1906(5):38.
[9]傅云龍.長酡亭即席有敘[N].申報,1888-04-21(5388·4).
[10]顧文初.碧瑤游記[N].申報,1922-01-03(17555·17).
[11]自由談·短訊[N].申報,1929-11-05(20339·12).
[12]大華考而夫球場今日開幕[N].申報,1931-04-18(20847·16).
[13]卓別麟的新憧憬[N].文藝新聞,1931(40·3).
[14]曾今可.富士雪與熱海泉[J].大上海人,1936(5/6):46.
[15]雪門.兒童和玩具[J].晨報副刊,1925(12).
[16]黃烽.巍峨的富士山[J].廣東婦女,1940,2(5):27.
[17]王亮.日本“富士山”詩[J].新民報半月刊,1941,3(16):23.
[18]張玉森.靈峰富士游記[J].警聲,1940,1(3):42.
[19]朱民威.日本初航記[N].申報,1946-06-23(24551·7).
[20]日判刑首惡戰犯,多賦詩留作墓志[N].申報,1948-11-16(25414·2).
[21]易君左,王德林.定泰山為國山芻議[J].江蘇教育,1933,2(1/2):1.
[22]災后雜言[N].申報,1891-12-04(6690).
[23]日富士山噴巖[N].申報,1931-07-21(20939·9).
[24]子駿.登富士山記:東游雜記之一[J].逸經,1936,17:83.
[25]日本風土:富士山及五湖[J].特寫,1937(13):7.
[26]行之.從東京到日本的古都[J].新人周刊,1936,2(30):596.
[27]馬軍.東京的神秘之謠:富士山將爆炸?[J].辛報周刊,1946(8):7.
[28]中川太郎.富士與日本阿爾卑斯[J].康駒,譯.文藝,1936,3(3):116.
[29]辛爾.富士山遠景[J].道路月刊,1936,50(3):8.
[30]胡適之.車中望富士山[J].讀書通訊,1946,122:9.
[31]韓逋仙.初度訪富士[J].日華學報,1933,42:43.
[32]化成.登富士山[J].現代青年,1937,6(3):33.
[33]若渠.日比谷公園游記[N].申報,1920-12-10(17174·14).
[34]日本之城堡及美術[J].大陸畫報,1934(2).
[35]倪貽德.櫻花[J].金屋月刊,1929,1(3):52.
[36]胡先骕.旅程雜述[J].學衡,1924,28:12.
[37]若因.讀書日記之一[N].申報,1936-12-16(22856·20).
[38]田雨.登富士山記[J].大東亞月刊,1942,2(1):63.
[39]劉漢儒.記現代日本畫展[N].申報(汪偽),1943-06-15(24853·4).
[40]顧天錫,余干成.小學校抗日救國運動的實際[J].地方教育,1931,30:34.
[41]凌叔華.登富士山[J].現代評論,1928,8(193):12.
[42]徐朋武.富士山下轎夫訪問記[J].禮拜六,1936(651):9.
[43]劉海粟先生談日本畫[J].雜志,1943,11(4):78.
[44]向卿.身份認同與被創造的民族、文化[J].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20(5):39.
[45]王樹枬.學記箋證:卷一(成俗)[J].中國學報,1913(5):10.
[46]陳靈秀.日本風景與日本精神[J].遠東貿易月報,1941,4(8):48.
[47]若渠.東行漫記:下[N].申報,1920-12-12(17176·14).
[48]大智禪師.大智禪師偈頌[C]//禪門曹洞宗典.東京:鴻盟社,1919:521.
[49]游日記者之餞別宴會[N].申報,1917-11-23(16085·10).
[50]日本鐵道省國際觀光局.富士山為日本代表……[J].日本,1943(2):5.
[51]劉一之.櫻花及其他[J].中國空軍季刊,1936(5):126-127.
[52]鐵華游日影展[N].申報,1935-12-02(22488·15).
[53]陳抱一.觀“鐵華游日影展”后[J].新世紀,1935(2):30.66DBC426-1084-4E1A-B9AE-31DE04CCCD64
[54]錢瘦鐵.觀現代日本繪畫展題記[J].雜志,1943,11(4):80.
[55]吉川幸次郎.民族主義者としての徂徠[C]//吉川幸次郎全集:第23卷.東京:筑摩書房,1968:364.
[56]日本佛教歸還中國[J].東方雜志,1904(5):27.
[57]英.日本皇族之現狀[N].申報本埠增刊,1931-11-26(21067·5).
[58]辛爾.高田馬場之窟[N].申報本埠增刊,1935-12-04(22490·1).
[59]醒公.文明禍[N].申報,1917-01-07(15772·15).
[60]布施知足.遊記に現はれたる明治時代の日支往來[M].東京:東亜研究會,1938:13.
[61]日本國政府.世界遺産一覧表への記載推薦書[DB/OL].( 2018-06-20)[2021-08-10]. http://www.fujisan-3776.jp/history/index.html.
[62]歐陽君毅.購買外匯與捐款[N].申報本埠增刊,1937-08-12(23084·13).
[責任編輯 孫 麗]
Experience, Knowledge and Politics: The Understanding of Mount Fuji by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Era
XIANG Qing, GUO We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China)
Abstrac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era, Chinese scholars understanding of Mount Fuji constructed multiple images and meanings of Mount Fuji as a representative of Japan, a symbol of nation and national spirit, a sacred mountain, a superb view, and a summer resort. It also endowed it with multiple faces, including “the mountain in a foreign country”, “a place in East Asia” as well as “the mountain of civilization”, thereby overall manifesting a shift from “objective narration and praise” to “the coexistence of praise and criticism”. This understanding was a formative process of knowledge and emotion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the object based on experience in a certain time and space. It was not only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of the Chinese literati about Mount Fuji, but was also influenced by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views of modern civilization and changes in Sino-Japanese relations.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exerted an impact on the self-knowledge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 Japanese knowledge of Mount Fuji.
Key words: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era; Chinese intellectuals; Mount Fuji; cross-border; view of civilization
收稿日期:2021-10-10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江戶時代日本人的身份建構研究”(13BSS016)
作者簡介:向 卿,男,博士,湖南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日本文學與文化、日語翻譯研究。
① 主要研究有樊麗麗《論日本近世的富士山形象及形成要因》(《長春師范大學學報》2017年第8期)、唐千友《日本漢詩中的富士山形象研究》(《安徽大學學報》2012年第6期)、向卿《江戶時代外國人眼中的富士山》(《日語學習與研究》2019年第6期)、李杰玲《富士山漢詩研究》(黃山書社,2020年)等。
② 本文以“富士”“富岳”和“不二”為關鍵詞對“近代數字文獻資源全庫”“中國基本古籍庫”“瀚堂近代報刊數據庫”做了檢索,在剔除其中表人名、地名、物名(如“富士丸”“富士艦”“富士煙”“富士紙”“富士紗廠”“富士康”“富士公司”等)等與本文無關的項目后對數據進行了分析。66DBC426-1084-4E1A-B9AE-31DE04CCCD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