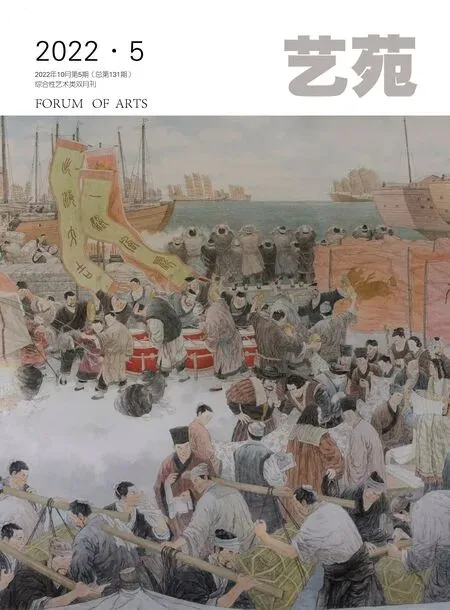從《一串珍珠》看“新派”電影本土化改編策略
韓筱蔓
“改編”是一個經久不衰的話題。自1913年亞細亞影戲公司出品的短片《新茶花》起,對西方經典文學進行改編的電影便在中國電影舞臺上陸續登場。回顧這段改編史,我們發現無聲電影時期(1913年-1931年)是中國電影改編外國文學作品“次數最多、片目最豐富的時期”[1]。其中,“新派”電影公司出品的改編電影以其獨特的電影美學風格值得我們關注。
陸弘石在《無聲的存在》一文中,將中國電影早期創作人員分為“新派”和“舊派”。所謂“新派”,是指“受過西方高等教育或接受過五四運動思想影響和洗禮的歸國留學生、新文藝工作者和電影愛好者”[2],如李澤源、梅雪儔、侯曜等。他們所創作的電影因“追求影片的畫面美感、渲染歐式的生活方式、宣揚民主自由的西方思想”[1]而被稱為“新派”電影,與注重傳統道德觀念的明星、天一等“舊派”電影公司的作品形成對照。
《一串珍珠》由“新派”電影公司長城畫片公司出品,改編自莫泊桑的短篇小說《項鏈》,由李澤源導演、侯曜編劇。長城畫片公司由留洋愛國青年在紐約創立,1924年遷回上海。“長城”初至上海,招攬侯曜為編劇。一邊是有著留洋經歷的李澤源,一邊是土生土長接受中國教育的侯曜,在這樣“中西合璧”的背景下,《一串珍珠》既有西方電影技術和觀念的應用,也有中國傳統思想的融合,是跨文化背景下改編的良好范本。
關于《一串珍珠》的改編研究文獻,內容多集中于:一,中西文化比較視野下的文本分析,如秦喜清《在中西文化比較視野下——〈一串珍珠〉解讀》;二,西風東漸背景下的電影史論研究,如高小健的《西風東漸與早期中國電影——重讀〈一串珍珠〉》。本文立足于前人基礎,以《一串珍珠》為例,試圖總結在中西方文化交融的背景下“新派”電影的本土化改編策略,為中國早期電影的跨文化改編問題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一、語境重構:時空、主題
改編不存在于真空之中,改編創作如同它的原作一樣總在語境中表達。改編的創作語境包括了時間、地點、媒介、文化和接受等要素,琳達·哈琴在《改編理論》中認為,接受語境決定了改編本中的語境變化。如何讓《項鏈》變成20世紀20年代的上海故事?侯曜通過重新構建語境,將故事用本土化的方式呈現,讓不同背景的文化在銀幕上相遇并適應,產生了新的精神混合物。
“何處”是有關改編的重要問題,地點的變化會引起文化關聯的改變,而這最終會影響電影的呈現與觀眾的接受。在《一串珍珠》中,侯曜將故事發生的地點從法國挪移到了中國上海。為何《一串珍珠》的故事要發生在上海?從利益角度來看,發生在中國的故事更利于中國觀眾接受,且彼時上海的電影公司眾多,長城畫片公司也于1924年遷入上海,在上海進行拍攝無疑更為便利。從創作角度來說,上海,這個國際性大都市具有豐富的文化含義,也只有上海可以包容《一串珍珠》中的情與愁。上海自鴉片戰爭簽訂《南京條約》后,從漁村變為通商口岸,包含了不同階層的人和不同樣貌的空間,有了貧富之別,有了城鄉之分。這里有一夜暴富的神話和富麗堂皇的洋樓,也有瞬間破產的可憐人和茅草鋪頂的土屋。正是這樣一個集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于一身的城市,才能用空間講述故事,才能包含《一串珍珠》中主人公一波三折的人生跌宕。
《一串珍珠》在將故事地點轉移到上海時,將原劇中的人物名稱、人物關系等內容也進行了本土化改編。在人物名稱上,侯曜略施諷刺之計,道德敗壞的小偷名“懷仁”,膽小齷齪的會計叫“如龍”。同時,侯曜豐富了原文的人物關系。在《項鏈》中,主要人物關系簡單明了,除了主人公駱塞爾夫婦,還有出借項鏈的伏來士潔太太、富有的若爾日·郎波諾一家。中國是一個人情社會,社交網絡復雜,所以在侯曜筆下,《一串珍珠》不僅保留了原文的人際關系,還將原文簡單介紹的若爾日·郎波諾夫人改寫為傅美仙與馬如龍的副線,更添加了勢利眼的親戚,熱心鄰人張三等角色。雖是以《項鏈》的故事框架為主,但已將原文改頭換面,豐富為一場中國式的人情冷暖。
“何時”也是關于語境重構的重要問題。在《項鏈》中,莫泊桑將重點放在了人物描寫與空間描寫之上,將時間的變換隱藏于字里行間。但在《一串珍珠》中,侯曜多次強調時間的變換,如字幕中多次出現的“第二天”,小紙條中的“二月初三”,王玉生與周全談話時背后的座鐘等。這些有關時間的表述側面展現了西風東漸的文化背景。時間是人們在認識和改造客觀世界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東方社會以農耕文明為主,主張人與自然是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故形成了 “‘天人合一’的圓式時間觀念”[3]。改變這種圓式時間觀念的正是近代西方鐘表的傳入。西方提倡“線性時間觀念”[3],講究對時間的精確拿捏,所以有了計時工具的出現。《一串珍珠》中對時間的強調表現出創作者受西方文化影響深刻。除了對時間的表述外,李澤源和侯曜還設計了很多帶有西方文化色彩的小細節,比如小偷傳遞給馬如龍的小紙條中,不僅有中文筆跡,更有英文翻譯附在其后,這都體現了西風東漸背景下語境的轉變。
語境制約著意義,當語境改變之后,故事的主題也發生了變化。《項鏈》創作于1884年,在當時的法國社會,資產階級革命已取得勝利,資本主義經濟的蓬勃生機帶來了人們對物質的向往,同時也帶來了階級分化、人的墮落等社會問題。小說通過描寫瑪蒂爾德借項鏈、丟項鏈、賠項鏈、得知假項鏈的故事,在道德層面諷刺了小資產階級的虛榮心,在社會層面揭露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弊端,同時通過瑪蒂爾德的生存困境,揭示了“人與現實的錯位”[4]這一具有普遍意義的精神困境。
侯曜是從“五四”走出的電影家,他接受了胡適以問題劇為導向的“易卜生主義”,認為電影具有“宣揚文化”和“改造社會”的強大功能[5],故侯曜的早期創作多以“問題劇”而聞名。在進行《一串珍珠》的編劇工作時,侯曜依舊從社會問題的角度出發對原文本進行改編。首先,“《一串珍珠》是攻擊虛榮的”[6]。這是一場因“虛榮”而起的風波,因為玉珍的虛榮,所以借來了珍珠項鏈;因為馬如龍的虛榮,所以他找人偷了項鏈,也導致了后續悲劇的發生。其次,“《一串珍珠》是提倡懺悔的”[6]。侯曜認為懺悔比法律道德的約束更加有力,能讓社會的罪惡減少,而這種懲惡揚善、良心感化的主題正是符合傳統儒家的道德要求的。所以馬如龍在結尾交代了自己的錯誤,并把職務讓給了王玉生,秀珍和傅美仙也懺悔了自己的虛榮,故事在懺悔中走向了大團圓結局。
從法國到上海,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從人類困境到道德勸誡,相同的故事框架,不同時空背景的作者交出了不同的答卷。如果說莫泊桑在《項鏈》中發掘人類精神困境,那么侯曜在《一串珍珠》中便依順中國傳統道德文化,試圖寓教于電影,將批判勸誡深入人心。這正如侯曜在《影戲劇本作法》中所言:“影戲是表現人生,批評人生,調和人生,美化人生的藝術品。”[7]
二、意象重構:財富的象征符號
(一)假鉆石與真珍珠
在《項鏈》中,莫泊桑用一串鉆石項鏈串聯起了整個故事:借項鏈、丟項鏈、賠項鏈、得知假項鏈的真相。鉆石項鏈是財富的代表,也是虛榮的投射,所以瑪蒂爾德拿到鉆石項鏈時想“那東西真地壓得倒一切”。瑪蒂爾德為自己的欲望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當伏來士潔太太說出昂貴的鉆石項鏈原來是假貨時,瑪蒂爾德會作何表情?我們不得而知,因為故事戛然而止,鉆石項鏈所代表的財富意義也如夢幻泡影,瞬間失去價值。莫泊桑正是憑借假項鏈的無意義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可悲的物化統治現狀。
在《一串珍珠》中,項鏈的材質從鉆石變成了珍珠。鉆石是更偏向西方審美文化的飾品,珍珠才更貼近中國人的喜好。珍珠被譽為“東方之美者也”,自古被顯赫人家當作裝飾用品,且珍珠具有藥用價值,可謂兼具實用與審美的價值。所以當鉆石項鏈變成珍珠項鏈后并不顯突兀。侯曜對“項鏈”的改編不僅在于材質的變動,還在于對項鏈自身財富價值的承認。侯曜沒有同原文一般,將項鏈貶值為“假”,而是承認了珍珠項鏈的實際價值,只是所賠償的珍珠項鏈價格比原項鏈貴五千元。這與莫泊桑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財富批判持截然相反的態度。究其原因,“侯曜對珍珠項鏈的處理還是沿襲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財富觀念”[8]。中國傳統儒家道德并不排斥對財富的欲望,排斥的是由于財富而引起的倫理顛倒,故《論語·里仁》有言:“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侯曜并不否認項鏈所具有的實際價值,而是否定由于財富所帶來的虛榮風氣,并將虛榮弱化為女性的身份特點,忽略了階級、社會層面的因素,從而削減了原作對社會批判的力度。從這點來看,侯曜的問題意識是種局部的、保守的道德勸誡。
(二)布鞋、人力車、洋車
在《項鏈》中,莫泊桑對交通工具的描寫非常粗略,集中于駱塞爾夫婦離開聚會后尋找項鏈時的情節:駱塞爾夫婦只找到了“像是夜游病者一樣的舊式轎車”,當駱塞爾先生尋找項鏈時,將所有有可能的地方都“走了一個遍”。莫泊桑隱晦地通過交通工具暴露出駱塞爾夫婦的窘迫。
在《一串珍珠》中,交通工具不僅僅是人物境遇的側寫,更是財富的象征符號。據統計,在《一串珍珠》共647個鏡頭(包括字幕),其中包含交通方式的鏡頭共計42個[9],主要交通方式包括汽車、黃包車、步行,分別對應了上、中、下的社會階層,上層社會的傅美仙是乘坐汽車出行的,底層社會的小伙計是步行出門的。隨著故事的發展,人物的出行方式也發生了改變,以王玉生和秀珍夫婦為例,在參加宴會前,他們的主要出行方式是黃包車;參加宴會時,秀珍是乘坐汽車出門的;王玉生出獄后,他是靠步行四處找工作的。通過人物前后的出行方式對比便可看出,交通工具是種財富的象征,而擁有更多財富的人,才能掌握話語權。乘坐小汽車的秀珍是上流社會的主角,步行找工作的王玉生是底層社會的棄兒,在這個“人情薄似春水”的社會里,財富的象征符號無處不在。
三、敘事重構:早期“影戲”理論的實踐
(一)從單線敘事到雙線敘事
《項鏈》有著簡明清晰的敘事結構,全文通過鉆石項鏈的串聯進行單線敘事,基本邏輯為:借項鏈、項鏈丟失、賠償項鏈、得知假項鏈。但侯曜在進行改編時,將單線敘事拓展為了雙線敘事,王玉生、秀珍的家庭故事與傅美仙、馬如龍的婚姻故事時而平行時而交叉,形成對比,最終在結局交匯為一點,得到了美滿結局。
為何侯曜要增加敘事線索,形成對比效果呢?這要從侯曜《影視劇本作法》中的“穿插”一章說起。何為“穿插”?“凡兩景相接處接得非常得當,使劇情格外曲折有趣,這種聯接法就叫做穿插。”[10]換句話說,“穿插”就是蒙太奇手法。侯曜尤其談到了“對比穿插”的方法,他認為“對比穿插”使“悲者愈顯其悲,喜者愈見其喜”[10]。在“批評虛榮,提倡懺悔”主題先行的情況下,“對比穿插”無疑能更加突出貧與富、真與假的戲劇性效果。于是便有了傅老太做壽大宴賓客與秀珍帶著孩子艱難度日的對比,有了馬如龍做會計輕松工作與王玉生在車間辛苦勞動的對比。隨著對比穿插的豐富,兩條明晰的故事線索被整理出來,形成了雙線敘事。同時,雙線敘事具有“花開兩朵,各表一枝”的特點,類似章回體小說,符合中國傳統敘事邏輯。且雙線敘事可以減少單一情節的單調和乏味,同時建立起雙重敘事空間,使影片情節更為流暢豐富。兩對夫婦,互為謎題與謎底,兩種人生,皆為虛榮與貪婪所擾。在雙線交替敘事中,觀眾自然而然地對虛榮進行反思,從而達到侯曜理想的“為人生的藝術”目的。
(二)敘事時序的變化
從現存影片文本來看,“《一串珍珠》可稱為中國電影首次出現倒敘段落(鏡語)的電影文本”[2]。倒敘的概念來自文學理論,雖然倒敘的手法常被西方文學所應用,但中國古典文學也不乏倒敘的使用,比如《紅樓夢》開篇對無才補天之石經歷的倒敘,既引出了人物,又暗示了賈府覆滅的必然。侯曜的倒敘靈感或許便來自中國傳統市井小說。中國傳統市井小說擅長用人物關系鋪陳復雜故事,用因果關系表現人倫理念,用和諧圓滿當作最終結局,在“三言”“二拍”中常有體現。《一串珍珠》亦有此特點,上文提到,《一串珍珠》在改編時豐富了原作的人物關系,且以珍珠項鏈為串聯道具,在因果關系的邏輯鏈中展現虛榮帶給人的苦果和懺悔所帶來的大團圓結局,可見此種猜想并無不可能。
在《一串珍珠》中,共有五處倒敘,分別集中出現于王玉生出獄后找工作時和馬如龍被張懷仁威脅及道出事件真相時。前者將王玉生出獄后所受的冷待與之前同朋友們杯酒言歡的場景相對比,在對人物悲慘境遇的烘托中,揭示出“有酒有肉是朋友,世態炎涼,人情薄似春水”的道理。后者還原了事件真相,從馬如龍被小偷勒索到他說出自己雇人偷項鏈的真相,為觀眾補齊了故事的前因后果。侯曜通過倒敘,將觀眾的目光從道德勸誡投放至人物的心路歷程,為這滿篇的道德說教增添了些許人情味。
四、結語
從《項鏈》到《一串珍珠》,侯曜通過語境、意象、敘事的重構,用傳統文化的血肉填充西方故事的骨架。《一串珍珠》雖是個案,但此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派”電影人士的文化選擇:一方面,“新派”選擇接受西方的文化影響,改編西方經典文學作品為電影;另一方面,“新派”也繼承了中國傳統背景下的文化脈絡,對西方故事進行了本土化改編,無論是時空、主題,還是意象與敘事技巧,都可見“新派”對改編電影本土化的思考。在中西方的雙重影響下,碰撞出了《一串珍珠》,碰撞出了民族電影獨特的文化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