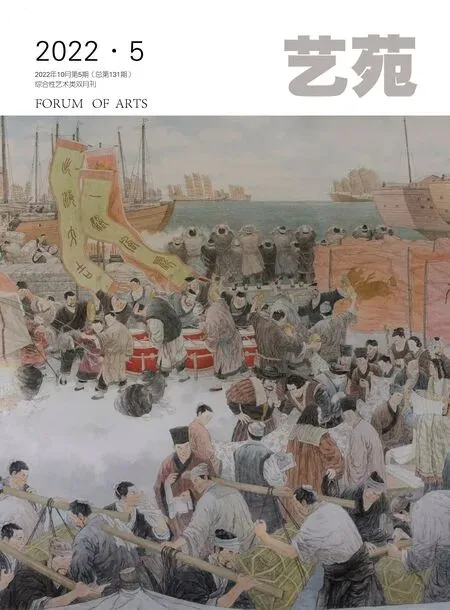梅里亞姆“觀念—行為—聲音”三維模式釋義
梁以韜 熊曉輝
美國音樂人類學家梅里亞姆認為:“聲音的產生離不開人,聲音的產生與特定的人文生態環境關系密切,聲音創造者的社會背景與文化背景對聲音的產生起著決定性作用。”[1]4他指出音樂的“聲音”不僅是“聲音”本身,還是一種具有人文與社科雙重學科性質的“聲音”。他所指的這種“聲音”是一種具有存結構性、系統性并在于人類行為中的聲音。他還認為:“產生聲音的行為離不開相應的概念來支撐。”[2]36-45因此,梅里亞姆根據產生聲音的觀念和行為及聲音中的音樂三者間的關系,提出了著名的“觀念—行為—聲音”三維模式。
一、梅里亞姆的音樂人類學觀念
在學術生涯的早期,梅里亞姆從北美印第安地區和非洲盧旺達等國家中的大規模田野調查中汲取了許多寶貴的研究經驗。但他早期的音樂文化研究范式,多為通過研究人類的文化背景與社會背景去解釋人類的各種音樂現象,即“通過‘人’來研究‘音樂’”。
在梅里亞姆的中后期學術生涯中,他的研究范式逐漸轉變為了“通過‘音樂’來研究‘人’”。著名的音樂人類學家內特爾(B Nettl)評論梅里亞姆:“首先,他是人類學家。”[3]51-54可見,梅里亞姆一生研究的精力更多是放在音樂人類學中的人類學成分上。梅里亞姆積累了大量學識后,發現大部分與音樂相關的文獻資料偏向于對音樂本體的研究。這種情況導致音樂人類學中的人類學成分被忽視,音樂學成分被過度夸大。梅里亞姆認為:“音樂不是一種單純的聲音現象,而是一種人類行為的體現,它與人類活動存在必然的聯系。”“音樂是一種特殊的集合體,由人的行為、觀念以及聲音本體三者共同構成,而且音樂是一種具有特殊意義的,需要人類后天學習的一種特殊的行為,音樂本身的結構如音調高低、持續時間等結構性因素受音樂創作者所持有的文化觀念控制。”基于此,梅里亞姆在1964年先后提出了“觀念—行為—聲音”三維模式、“文化中的音樂研究”與“作為文化的音樂研究”等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經典音樂人類學研究范式。
在梅里亞姆之前,傳統的西方學界常常將音樂視為一種按照音樂本身的邏輯規律運行的封閉系統[4],音樂本身與音樂生產者的關系性不強。梅里亞姆認為,需要在研究音樂的過程中運用人類學的視野和方法,以便探究音樂中所蘊含的人文層面和社會層面的奧秘,并需要在研究中“將音樂當作一種由人為他人創造的人類現象”。梅里亞姆對音樂進行解析時,運用的研究視角主要集中于音樂“怎樣”、音樂“為什么”等角度上。而在梅里亞姆之前,音樂學界更多是在研究音樂“是什么”的問題。梅里亞姆的獨特視角決定了他對音樂人類學學科的身份定位與理解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
學界普遍認為,梅里亞姆的《音樂人類學》一書的出版代表了音樂人類學的正式誕生。在該著作中,他闡述了“音樂人類學是‘音樂的音樂學’與‘音樂的人類學’的融合性學科,二者缺一不可”的觀點。“沒有‘音樂的人類學’,音樂人類學是存在某種偏見的音樂學;沒有‘音樂的音樂學’,音樂人類學僅僅是文化人類學的一個特異性分支。”[5]39-43對人類學在音樂人類學中研究的可行性、重要性等進行嚴格論證后,梅里亞姆從理論層面上先后對音樂人類學的學科概念界定、學科研究方法等進行了深入探討與總結,并以此為基礎將“行為”作為一個新的音樂人類學研究角度進行確立,最終發展成為“觀念—行為—聲音”三維研究模式。
二、“觀念—行為—聲音”三維模式的內容
基于人類學研究視角提出的形式,是“觀念—行為—聲音”三維模式內涵的重要體現之一。通過人類學的研究視角與方法,“觀念—行為—聲音”三維模式將“音樂產生于音樂行為,而音樂行為產生于音樂觀念,觀念反作用于音樂的聲音”中的基本邏輯進行了解讀[6]92-95,最終從理論維度上給音樂的產生與功能等問題提供了答案。
(一)“觀念—行為—聲音”三維模式的形式
梅里亞姆認為,盡管音樂人類學的研究范式中存在兩種維度——音樂學維度與人類學維度,但這兩個維度沒有優劣之分。在梅里亞姆之前,多數西方學者在音樂人類學的研究中過分依賴音樂學的方法,卻沒有將人類學的方法置于一個合理的地位。這一現象致使了音樂人類學在發展過程中,人類學成分與音樂學成分二者逐漸失衡。梅里亞姆試圖通過轉變音樂人類學的研究視域,把音樂作為人類的后天習得行為看待,以縫合音樂人類學中人類學和音樂學之間的割裂。“要了解一種音樂為什么以當下的結構方式存在,必須深入研究音樂行為的形成歷史及生成原因,還有為了產生所需的特定聲音組織形成,作為音樂行為產生的前提條件,音樂的觀念是如何被組織的;又是為何被這樣組織的。”[7]67-68梅里亞姆認為,音樂“是什么”與“在哪里”不是音樂人類學的研究重點,研究的重點內容應偏向于音樂“為什么”與“怎樣”。前兩個問題在梅里亞姆眼中是屬于音樂學的探究內容,在他看來,音樂人類學要體現本身的學科價值就應該對特定文化中的音樂進行研究,以闡明音樂的“為什么”與“怎樣”,從而進一步解答出音樂的功能與來由等問題。
(二)“觀念—行為—聲音”三維模式的內涵
人的“觀念”作為一種非實體的、抽象的思維模式,會受到政治因素、宗教因素、民族因素等社會文化層面上的因素的影響。而人的行動是與人的觀念有密不可分的聯系,從另一角度上看,觀念促成人的行為的產生,是人進行行動的先決條件。梅里亞姆認為,“觀念”為引導人類行為的重要因素之一,與音樂文化相關的觀念對人的音樂行為起到十分明顯的影響,對音樂的生活與生產起決定性作用。反之,人的行為產生的音樂亦會反作用于人的觀念,進而影響后續行為的產生。梅里亞姆在他的著作《音樂人類學》一書中曾寫到:“如果一名音樂人類學家需要對音樂進行系統性地分析,那么他必須將研究音樂觀念作為研究的基礎,因為人類的音樂行為深受與之相應的音樂觀念的影響,深刻解音樂觀念才可以真正的理解音樂。”
音樂人類學家比爾斯在《美國印第安人人類學手冊》一書中對梅里亞姆的理論研究成果給予了一個十分簡明扼要的評價:“梅里亞姆的《音樂人類學》使學界開啟了音樂人類學研究范式的新思潮,他本人十分在意對文化中音樂的研究,他將觀念、行為、聲音三者有機結合并統一于音樂的理解之上。”[8]梅里亞姆認為音樂產生于音樂行為,而音樂行為產生于音樂觀念,因此他的“觀念—行為—聲音”三維模式的內在邏輯構成為:“觀念”決定著“行為”,而“行為”進一步產生“聲音”。
美國著名音樂人類學家內特爾針對梅里亞姆的“觀念—行為—聲音”三維模式整體性曾做出如下評述:“盡管音樂的悅耳性等方面有所欠缺,但是與這類音樂有關聯的音樂觀念卻體現出濃厚的趣味性。梅里亞姆在《音樂人類學》一書中詳盡說明了這一具有重大意義的轉折點,通過‘觀念—行為—聲音’三維模式去詮釋音樂,這一切問題似乎被解釋的簡單明了。‘聲音、觀念、行為’這三個結構成分對梅里亞姆而言是同步的,其中任意一個成分會同時對另外兩個成分產生影響。”梅里亞姆將“觀念、行為、聲音”整合為一個整體,他從理論維度對“觀念—行為—聲音”三維模式的互相作用機理進行了闡述,著重強調音樂的聲音具有結構性、系統性,同時音樂的聲音不能離開人類的行為單獨存在,必須被看作是一種具有文化性的特殊產物。
音樂行為被梅里亞姆劃歸為三類:第一類是與身體相關的音樂行為,這些行為出現于人操控身體進行發出聲音的過程中,以及與發聲相關的肢體姿態中,是在制造音樂過程中的一種有機體反應;第二類行為是與語言相關的音樂行為,這是一種可以反映隱藏在音樂之下的潛在概念的行為,可對相關的音樂系統進行語言層面上的表述;第三類是與音樂的社會行為,即相關人員在某一與音樂相關的特定事件中所表現出的行為模式。這類模式可劃分成音樂家的行為和非音樂家的行為,當中的音樂家行為涉及音樂專業性和職業性。前兩種音樂行為被梅里亞姆劃分為廣義的音樂體系組成部分,兩種行為都是人類通過與音樂相關的觀念進行機體上的表達而出現。其中,對音樂的身體行為了解程度較低;對音樂的語言行為了解相比較多,但僅僅為語言行為相關的原始信息數量較多。音樂的語言行為還沒有被某種具有概括性的模式將該類型的信息有機結合起來。梅里亞姆認為相關的學者在對音樂本體研究過程中,往往忽視了作為音樂的重要組成部分的與音樂相關的身體行為和語言行為,沒有對上述兩種行為給予足夠的關注度。音樂的聲音產生于各種音樂行為中,脫離這些音樂行為就無法產生音樂的聲音。與此同時,音樂產品會對聽眾有所影響,作為受眾的聽眾會對產生音樂的“音樂家”進行判定。如果作為演奏者的“音樂家”和聽眾雙方都在觀念上對音樂產品持有認可的態度,則與音樂相關的觀念會進一步加強并再作用于音樂行為的本身,最終這種作用的影響會進一步體現在音樂的聲音中。反之,評價者持有不認可的觀念,會影響演奏者通過某種路徑去創造出更為接近被評價文化所認可的音樂。
三、“觀念—行為—聲音”三維模式的特征
梅里亞姆“觀念—行為—聲音”三維模式植根于結構主義的分析模式。在他的“觀念—行為—聲音”三維模式中,“觀念”對應文化本體,“行為”對應藝術本體,“聲音”對應音樂本體。作為音樂產生的先決條件,人類的行為可以反映出人的信仰、三觀、態度等觀念,具有一定的主觀能動性。他的“觀念—行為—聲音”三維模式落腳于這個顯而易見但又容易被忽視的文化現象,并將音樂作為文化的一部分放置于文化的事實中,把音樂概念融入人的行為和與人的觀念相關聯的文化視野中。[9]在梅里亞姆的“觀念—行為—聲音”三維模式中,可以明顯看出文化功能主義理論的影子,但功能主義往往沒有正視人的人文需求。梅里亞姆卻在功能主義的立場上,創新性地將“觀念—行為—聲音”三維模式融入了人文性與社會性,這些特征使得該模式的研究視角更全面與完善。
(一)“觀念—行為—聲音”三維研究模式中的功能性
梅里亞姆通過帶有功能主義傾向的觀點,將“文化中的音樂”放置于音樂人類學的研究視野中。他認為研究者從整體入手研究音樂時,要從聲音、觀念、行為三者的關系中切入,進而發掘音樂的語意能力。
人類學家瑪利羅伏斯基指出:“文化的功能是其在人類活動中的重要性體現,該結論的主要意義在于人類活動的系統,這并非偶然產生的,而是配置齊全的、有組織的、永恒的。”梅里亞姆在受到瑪利羅伏斯基的影響下,提出音樂所具有的十大功能,并以此為基礎在《音樂人類學》一書發表了“觀念—行為—聲音”三維模式。梅里亞姆在《音樂人類學》中寫到:“因為研究者在研究特定人群的音樂時都要考慮到全部這些因素,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究竟能否構建一個理論研究模式把這些因素一并囊括。這個模式必須統籌兼顧民間評價和分析評價、文化背景和社會背景、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相關研究角度以及與音樂相關的方方面面。這里建議在相關研究中采用一種形式簡單卻可以滿足上述全部條件的研究模式(即“觀念—行為—聲音”三維模式)。”[1]4
梅里亞姆的“觀念—行為—聲音”三維模式將音樂的聲音視為一種“會影響音樂觀念和音樂行為”的結果,他的三維模式通過結構主義的思維捋順了音樂產生的邏輯。在梅里亞姆眼中的音樂活動具有前因后果特征,“觀念、行為、聲音”其中任意一個節點的變動皆會對另外二者產生一系列直接或間接的影響,鮮明地體現出“觀念、行為、聲音”三者都是具有特定層面功能屬性的。綜上所述,梅里亞姆的“觀念—行為—聲音”三維模式體現出了明顯的功能主義屬性,該屬性使得音樂人類學中的人類學特征得到體現,為研究者開啟了音樂人類學研究的新視角,促進了文化視闕中的音樂功能與音樂整體體系的系統性研究。
(二)“觀念—行為—聲音”三維研究模式中的主觀能動性
梅里亞姆的“觀念—行為—聲音”三維研究模式的重點之一在于闡述音樂的生成過程,該模式體現出的主要學術觀點之一是:音樂的出現不可離開人類的主觀能動性。在梅里亞姆看來,對任何一種音樂體系進行理解與解剖的最重要的先決條件之一是對音樂與非音樂進行區分。關于音樂與非音樂之間的界定,梅里亞姆認為:1.音樂往往是與人相關的,與人類不相干的聲音如小鳥的“歌唱聲”不能被當作音樂;2.音樂中的聲音必定存在一定規律性,如隨意敲打樂器產生的聲音不能被當作音樂;3.音樂要有時間連續性,即必須要有一定持續的時間。在產生音樂的聲音這一過程中,音樂創造者的音樂思維與音樂行為二者之間有密不可分的關聯。梅里亞姆認為,由主觀意識引導肢體,進而產生的“音樂”才是“音樂”,若是在無主觀意識的情況下,人類制造出的聲音不可被認定為“音樂”,對“音樂”是與否的界定亦是離不開人的觀念。從上述界定中可看出,梅里亞姆眼中的音樂是具有主觀能動性的、人類獨有的一種特殊文化,真正的音樂活動必定是依賴人的本體與主觀意識存在的,離開了人的本體與主觀意識存在的“音樂”不能被稱之為真正具有文化屬性的音樂。
(三)“觀念—行為—聲音”三維模式中的泛用性
梅里亞姆主要研究的音樂文化種類包括非洲的巴松葉族音樂文化、北美的印第安族音樂文化、歐美的爵士音樂文化、伊朗的波斯族音樂文化等,在這些差別迥異的音樂文化中,研究者可通過“觀念—行為—聲音”三維模式所提供的結構主義分析思維,去詮釋與之相應的音樂文化內在運行邏輯。在人類制造出的任意一段音樂中,皆存在音樂觀念、音樂行為、音樂本體這三個邏輯節點,三者的深隱層面和表象層面皆體現在音樂活動中。
梅里亞姆“觀念—行為—聲音”三維模式的內涵之一是:“在人類各類廣泛的音樂活動中,必定是先有音樂觀念的產生,進而以觀念引導人類做出與音樂相關的行為,再通過生產音樂的行為制造出音樂的聲音,音樂的聲音反過來影響人的音樂觀念。這是一個環環相扣、在各類音樂文化中皆存在的現象。”這個內涵不僅解釋了音樂活動的產生原因,還探明了廣泛存在于各類音樂文化的音樂動態變遷的來由與結果。不論是嚴肅少變的宗教音樂與風趣善變的流行音樂、外向非洲地區音樂與內斂的東亞地區音樂等,各類音樂人類學研究者都可以借用梅里亞姆的“觀念—行為—聲音”三維模式詮釋音樂內的一系列于關于音樂“怎樣”、音樂“為什么”等前人難以察覺卻又顯而易見的關鍵性問題。
(四)“觀念—行為—聲音”三維模式中的人文性與社會性
梅里亞姆在“觀念—行為—聲音”三維研究模式中映射出“音樂即文化”觀點。通過“音樂即文化”這一觀點,梅里亞姆進一步闡述了“音樂”不僅應該被理解為音樂作品本身,還應該將它理解成一種人類特有的文化行為這一理念。與梅里亞姆同一時期的音樂人類學研究者們在對“音樂”這一現象進行研究時,往往將研究范式的主體劃定在音樂的聲音與音樂的結構中。對這種研究范式,梅里亞姆持有不同觀點,他認為音樂的產生不可獨立于音樂的生產行為之外,要對“音樂”進行整體性的詮釋,就不僅僅只能把研究的重點放置于音樂作品的維度上,而且更為重要的是要對生產音樂作品的音樂行為進行深入探究并論證。在研究中,梅里亞姆將行為當作一種用于研究藝術的方法與媒介,而不將行為當作目的。梅里亞姆這一創新性的音樂人類學學科思維,在理論維度上將音樂學與人類學的割裂處進行了系統性的縫合,促進這兩個學科從某種程度上進行了極為有深度的對接與整合。
著名音樂人類學家博爾斯曾在他的著作中寫到:“在音樂中,聲音的內容表達和形態表述受人類社會某種特定文化的影響,音樂的形態模式和表達模式就是音樂的文化模式。”受博爾斯的觀念影響,梅里亞姆本人在研究中十分在意“具體文化中的音樂”,他將“觀念、行為、聲音”三者有機結合并統一于音樂的理解之上。梅里亞姆眼中的文化是一種人類累積學習的行為,而音樂行為是隸屬于學習行為的一種復雜類型。梅里亞姆認為馬琳諾夫斯基提出的七項人類的“生物—社會需求”理論,僅可對教育、經濟、政體等社會科學類的現象進行詮釋。“人不可能遏止對自身的評論,以及對自身或他人行為、渴望和價值觀的敘述說明和闡明解釋”[1]4,導致“生物—社會需求”理論無法適用于對藝術、宗教、哲學文化等人文科學類現象進行詮釋。從另一維度上看,梅里亞姆認為人類不僅有“生物—社會需求”,更有對生命意義、人生情感等人文層面德需求。但在人類的文化現象中,人文性與社會性都是普遍蘊含在內的,當人類的社會層面的需求被滿足時,會引起人文層面的反應,而社會層面的反應亦與人文層面的需求息息相關。
“觀念、行為、聲音”三者之間的密切關系,除了體現出音樂的人文性,亦有音樂的社會性顯現。梅里亞姆通過“觀念—行為—聲音”三維模式,提出音樂的“聲音”和產生音樂的音樂“行為”組成了某種有關聯性的系統。梅里亞姆的三維模式針對“聲音”與“行為”的研究注重了音樂系統的完整性,同時在研究中兼顧了人文維度和社會維度這兩個維度。不僅如此,梅里亞姆通過“觀念—行為—聲音”三維模式進一步從理論維度上說明了“音樂”不僅僅是一種特殊的人類獨有的事件,更是一種獨特的社會事實現象。因為“音樂”本身雖不具備意義,但作為人類文化的代表,“音樂”不可脫離于其相關的文化系統,音樂作品會在某種程度上受到社會文化層面的反饋影響。
四、結語
在20世紀中期音樂人類學中音樂學層面與人類學層面存在研究范式上割裂的背景下,梅里亞姆通過“觀念—聲音—行為”三維模式,將音樂學與人類學重新縫合成一個整體。梅里亞姆的“觀念—聲音—行為”三維模式,將與音樂相關的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兩方面的內容進行了整合,并兼顧了對音樂本體、形式、審美、發生激勵等方面的研究。梅里亞姆的“觀念—聲音—行為”三維模式從音樂的概念、本身、行為等維度對音樂進行了某種整體性的探究,該模式將音樂人類學中人類學成分提升到一種與音樂學平衡的平衡點上,將人類學作為一種研究的視角與方法,有力地證明了三維模式本身對音樂人類學的發展具有劃時代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