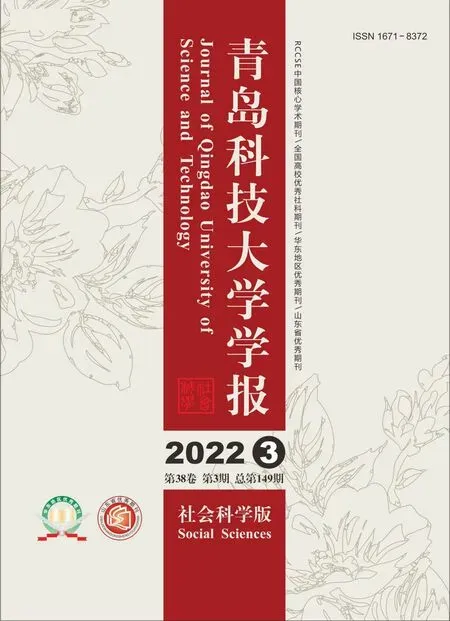鬼畜視頻亞文化現象的生成及其傳播研究
——以B站網絡傳播的鬼畜視頻為例
○ 徐祥運,徐博昌
(1. 東北財經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遼寧 大連 116025;2. 北京大學 心理與認知科學學院,北京 100871)
一、引言
互聯網技術的社會化發展促成與現實社會相關聯的互聯網虛擬社區的生成,這符合麥克盧漢的預言,即“進入電子文明后,人類將重新部落化”[1]。虛擬社區最突出的社會性特征在于,互動于網絡空間的成員也是現實社會結構中的一員。網絡社會的匿名性、靈活性等特征,使現實社會結構中的社會成員可以在網絡空間中根據本我真實的社會角色期待,實現不同于現實社會的社會角色扮演。因此,無法在現實社會結構中獲得表達的社會亞文化在網絡社會中逐步生成。其中,網絡視頻平臺作為網絡文化的媒介載體在網絡文化的生成、傳播與表達的過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參與者年輕化是網絡視頻的一個主流發展趨勢。由青年一代主創,與傳統影視作品內容與風格迥異的各類惡搞視頻呈井噴式發展,鬼畜視頻就是其中一類引人注目的惡搞視頻,是本文所要探討的鬼畜文化的典型代表。鬼畜視頻涉及二次元文化、彈幕文化等諸多網絡亞文化,同時,由多種文化融合而成的鬼畜文化具有與單一文化不同的特點。鬼畜視頻起源于有彈幕網站鼻祖之稱的日本niconico彈幕網(簡稱為N站),鬼畜視頻的國內媒介載體是B站(bilibili),通常被稱為嗶哩嗶哩。本文將以B站的鬼畜視頻為分析對象,闡釋鬼畜文化的社會生成、表達特征、傳播生態與傳播趨勢。
二、鬼畜視頻的類型、特征和文化生產策略
(一)鬼畜的概念演化和視頻類型
作為一種文化媒介,鬼畜視頻指的是一種剪輯率、重復率、聲畫同步率極高的視頻形式,旨在實現洗腦或爆笑的效果,吸引廣大年輕受眾作為迷群。鬼畜視頻大多取材于經典影視作品橋段、二次元動漫等年輕人熟悉的領域,這些素材的文本和配樂在后續制作中被不斷地剪拼和重構。雖然鬼畜視頻的素材多源自已有的視頻,但其制作卻需要創作者具備一定的作曲或視頻后期制作技術,因此,鬼畜視頻始終是一種小眾愛好。
“鬼畜”(きちく)一詞直譯自日語,本是佛教世界六道輪回中淪落餓鬼道和畜生道的簡略并稱,原指“身語心業皆不清凈者”[2]。漢傳佛教文化根據因果規則將佛和眾生分為十大法界,其中在世間罪過深重之人會在往生后進入餓鬼法界、畜生法界,即因貪欲癡想心,造作下品十惡,而感畜生的果報。慳貪不舍,不知布施、修福,不明白因果,不遵守戒律,多行惡事,造諸惡業,則感餓鬼的果報。
鬼畜視頻中鬼畜一詞的含義顯然已發生偏離,其含義與某物或某人賤賤的搞笑相近,而不再是貶義詞,或更接近于阿多諾意義上的“著魔”(The fetishism)的心理狀態,即一種“沉溺于某種神秘性而非邏輯性的狀態”[3]。鬼畜文化中的文化主體主張“不瘋魔,不成佛”。在社會主流文化刻板規訓下,個人在心理層面需要合理的渠道宣泄情緒,在社會層面也需要一定的社會建制形成科賽意義上的“社會安全閥”[4]機制。鬼畜文化借用了佛教文化中的“瘋、魔”以解構刻板主流文化,承載、傳達通過多重社會流動渠道和機制實現社會身份、地位的文化訴求,因此鬼畜文化具有豐富的后現代意蘊,而不再是一般意義上的文本再生產。總體而言,鬼畜文化堅持這樣一種內在的哲學理念,即“實在是一種共同的幻覺,不存在未受他人污染的個人感知”[5]22-23,對傳統文化的批判是其宣揚自我的有效方式。
鬼畜視頻通常可分三類:音M A D、人力VOCALOID和鬼畜調教。
音MAD是一種使用素材中的聲音對所選的BGM(背景音樂)進行演奏的視頻形式。音MAD的核心是音頻,其由兩大組成部分,一個是BGM,另一個是素材中的聲音(稱為樂器)。以第一部有影響力的音MAD作品“最終鬼畜藍藍路”為例,BGM所選取的是同人音樂“U. N. オーエンは彼女なのか”(中文譯名為“U. N. OWEN就是她嗎?”),樂器則來自視頻素材中麥當勞叔叔說話的音頻。視頻只有包含原視頻作品中的BGM與素材中的樂器這兩個核心音頻要素,并使用素材樂器對BGM進行演奏,才可以稱得上是音MAD。
人力VOCALOID(日語:ボーカロイド,是一款日本開發的用于電子音樂制作的語音合成軟件),則以人聲音頻素材為核心,常常先將某人說話的音頻打散成單個音節制成音源,然后將這些單音節在UTAU、麥樂迪等調音軟件中按選定的曲譜重排,從而讓此人的人聲實現歌唱效果,仿佛是在用VOCALOID軟件制作歌曲。目前B站上以調音為主的作品大多屬于人力VOCALOID類,注重歌詞的再現與歌唱。相較之下,傳統音MAD對樂器的切片制作、節奏感和畫面要求更為細膩,技術難度最高。
鬼畜調教是B站鬼畜區于2016年再版后的新分類。與“調教”一詞在鬼畜視頻圈內的含義相反的是,這一分類指那些沒有對音頻進行任何調音、不含歌曲元素二次創作的鬼畜視頻。這類鬼畜視頻在音頻編輯上的技術性大大降低,制作者往往直接將現成的視頻畫面與BGM和沒有曲調的人物話音進行重組,即可作為鬼畜視頻上傳。其特色和難點在于通過音頻和視頻的拆解和統合,以快閃、重復的畫面,動感、強勁的BGM和再造、搞怪的臺詞三位一體的方式表現其沖擊力。由于調音的缺乏,此類鬼畜視頻的成品多為rap風格,制作難度最低[6]。
(二)鬼畜視頻的生成過程和表達特征
在鬼畜文化的一般文化情境中,“真實的大眾媒體基本上都是想轉移人們的注意力,精英媒體建立了一個框架,而其他媒體在這個框架內運作”[5]22-23。因此,對主流大眾媒體的“復制”與“拼貼”成了制作鬼畜視頻的常用手法,即將原視頻的能指和所指分裂,使能指和所指的意義鏈斷開,然后再對被拆散的原視頻元素進行重新組合,再造出具有全新意義的文本,從而為受眾帶來全新的觀感體驗。扭曲原文的意義,在文本的意義空白處嵌入主觀觀點,是鬼畜視頻的生產者對原文進行另類解讀、解構與重構的常用手段。
對素材人物進行夸張化改造、個性化處理也是鬼畜視頻的常用手段。高不可攀的明星在鬼畜視頻中可以被任意玩弄,這種巨大的反差使鬼畜文化的生產者在娛樂的同時,收獲了自我主導權的認同和文本生產的成就感。早期鬼畜視頻中的人物以動漫和影視作品中的人物為主,注重角色的獨特行為和幽默語言。而近年火爆的鬼畜視頻作品則關注明星符號的挪用,如“Are you OK?”中的雷軍、“我的洗發水”中的成龍、“雪姨敲門”中的王琳等等。
戲謔與反諷是鬼畜文化表達的核心,顯示了鬼畜文化對權威的反叛與挑戰,具有明顯的后現代性。對嚴肅題材進行再加工,使之變得可笑、無厘頭是鬼畜視頻的戲謔,對原文本嚴肅的含義進行顛覆是鬼畜視頻的反諷。在鬼畜視頻中,越是嚴肅的題材在被戲謔和顛覆時產生的笑點越多。鬼畜文化的生產者就是用這種解構的方式使元話語和元敘事失效,從而達到瓦解主流文化的嚴肅性、抗拒精英文化統治的目的。在這個過程中,鬼畜文化還推動了一種新的文化消費模式的形成,生產者在拼貼、戲仿和反諷的再創作中體驗了文化解構的快感,消費者也在這種共同的狂歡中得到了釋放解壓,獲得了情趣迷群的互動交流與社交快感。
鬼畜文化作品的文本幾乎沒有限制,涉及的題材多種多樣,表達形式也沒有邊界。鬼畜文化文本特立獨行,不是任何其他文化的附庸。它是被消費的對象,也是被生產的對象。在鬼畜文化愛好者這一亞文化迷群中,創作者與接受者的界限并沒有那么清晰,生產者與消費者的身份往往被集于一身。
(三)鬼畜視頻的文化生成策略
鬼畜視頻文化策略的內核是抵抗,外顯是狂歡。這種亞文化訴求的抵抗與狂歡,不僅在鬼畜視頻的內容之中可以看到,而且在觀看、分享與傳播鬼畜視頻的迷群身上也可以看到。
借助原有文本的框架,置換其內容,顛覆其文本,賦予其另類的解讀和意義是鬼畜視頻的文化策略。這種拼貼、戲仿、解構是對主流文化約束的抵抗,是在狂歡式文化中獲得被壓抑的快感的途徑,“在狂歡中,人與人之間形成了一種新型的相互關系,通過具體感性的形式、半現實半游戲的形式表現出來”[7]。巴赫金的狂歡文化被費斯克歸納為三種形式:一為儀式化的奇觀,二是喜劇式語言作品,三是各種類型的粗俗話語[8]。這三種形式在鬼畜文本中都有不同程度的顯現。鬼畜視頻常將權威性的經典文本作為自己的模仿對象,并在對權威經典文本的解構、顛覆中,獲得躲避現實、冒犯權威的狂歡體驗。鬼畜視頻的模仿不僅是為了獲得滑稽娛樂狂歡的外顯效果,更反映了鬼畜文化策略的核心—反抗,即表達一種精神,一種態度,一種對各種限制、束縛、權威、框架的不滿與突破。通過剪裁拼貼,主流文化的敘事被瓦解,精英階層的話語霸權被挑戰,原有的權威性和完整性被粉碎和摧毀。
與一般的視頻不同,鬼畜視頻是對敘事和意義的消解,它的無邏輯性和對思考的不斷打斷,致使觀眾放棄了理解視頻敘事的企圖,而將注意力轉向了單純的滑稽和娛樂。在這種被打碎了的意義與淺層次的狂歡娛樂中,受眾暫時擺脫了常規的社會身份和社會角色,脫離了主流文化的束縛與要求。總之,觀看鬼畜視頻的過程是一場狂歡,是對精英文化規訓的一種反叛。它反映了大眾對宣泄與自我解放的追求,即便這種宣泄與自我解放是暫時的、脆弱的。
三、鬼畜文化的傳播生態
(一)鬼畜文化的傳播環境
鬼畜文化傳播以鬼畜視頻為技術媒介。B站作為我國鬼畜視頻最主要的發布與傳播平臺,在創立之初便設置了專門接受鬼畜作品投稿的鬼畜分區。鬼畜區屬于一級板塊,與“廣告”“科技”等板塊并列。B站雖多次改版但未曾動搖鬼畜區的位置,可見B站對其重視程度。B站對鬼畜區長期的支持和培養使其擁有了特殊的鬼畜文化氛圍,成了鬼畜視頻的沃土。
用戶制作完成鬼畜視頻后,經過簡單審核便可投放在B站供其他用戶觀看、點贊、發彈幕、評論和轉發。只要用戶具備基本的操作設備并接入互聯網,便可隨時發布各種格式的鬼畜視頻,傳播門檻較低。由于點擊量高的視頻會被推薦到首頁供用戶觀看,對鬼畜視頻的觀眾來說,單純的點擊觀看就能成為主動傳播的一種形式。
借助互聯網,鬼畜視頻的傳播突破了時空限制,能在短時間內到達相當大范圍的群體。彈幕帶來了實時互動與分享的體驗,增強了觀看者的參與感,使得鬼畜視頻的傳播始終在交互的語境下進行。傳播者與接受者在傳播關系中的角色被重新定義和調整。接受者不再僅僅滿足于獲得信息,而是開始通過各種手段和方式進行信息發布和觀念傳播。正如丹尼斯·麥奎爾所說:“最初的受眾存在,是由傳播者和接受者之間的巨大差異形成的,但現在這一點再也不能站得住腳了。”[9]每一個鬼畜視頻的受眾似乎同時成了新一輪的傳播者,助推此類視頻在網絡上迅速走紅。
(二)鬼畜文化的傳播主體
1. 鬼畜視頻的生產者:宣泄解壓、尋求交互與個性實現
凡向B站鬼畜區上傳過原創作品的up主都是鬼畜視頻的生產者。他們有的已在B站鬼畜圈聲名大噪,傳播了如“【春晚鬼畜】趙本山:我就是念詩之王!【改革春風吹滿地】”等點擊逾千萬并擴散到圈外的娛樂、音樂平臺的“神作”,有的則在反復的學習與創作中推進“傳播游戲化”的狂歡。鬼畜視頻作者之所以有如此強烈的生產與傳播動機,與以下因素有關:
第一,大量鬼畜視頻生產者的創作初衷是較為單純的情感宣泄和減壓。王蕾等人通過對12位B站鬼畜up主的訪談發現,不少up主認為自己在現實中性格內向,不善交流,他們巧借鬼畜視頻歇斯底里、反叛主流的特色外衣,減少了因網絡環境中的自我暴露引發的害羞與局促感[10]。他們通過B站這個匿名共享的平臺,利用經過文飾的自我發泄和獨白,排遣自己壓抑的情感。鬼畜視頻惡搞、吐槽、調侃的建構背后,隱藏著創作者負性情緒的集中釋放。
但鬼畜視頻創作者的情緒動機不止于單純的發泄。鬼畜視頻的去中心化、解構權威、戲謔拼接特質展現了鬼畜愛好者群體在互聯網語境下的亞文化審美特征。鬼畜視頻的傳播一旦被其創作者看作是一種獨特文化符號的擴散,就會使身處現實壓力與焦慮之中的創作者更容易啟動“合理化”的心理防御機制,也就是對自己創作的鬼畜作品給予積極評價,認為其不是兒戲,而是體現了一種特立獨行的態度,他們也在煩瑣的調教、剪輯、配字、加特效等編輯工作中帶入更多的積極情緒。因此,許多鬼畜視頻的創作過程可理解為對長期壓力事件的一種應對反應。up主們通過沉浸式的視頻剪拼不但使自己遠離生活中應激源的威脅,而且通過縱情幻想、夸張惡搞內容,從現實世界中抽離出去,調節自己的情緒。
第二,鬼畜視頻生產者在不同范圍和層級上獲得了人際需求的滿足。這種滿足首先來自粉絲的好評、聲援以及和粉絲之間的彈幕、評論互動。在王蕾等學者的訪談中,有多位鬼畜視頻up主表示,“如果粉絲少了的話我的創作欲望可能就不會那么高”[10]。這表明鬼畜視頻生產者并非單純的自娛自樂,他們很大一部分的成就動機與自我認同來自粉絲對他們的正向評價。當鬼畜視頻生產者認為自己扮演著奉獻新異觀感的“創造者”角色時,他們便有了繼續這種文本解構與媒介記憶重構游戲的充分動機。
其次來自不同生產者之間組成的交流群體。例如由“A路人”“癢局長”“伊麗莎白鼠”“吃素的獅子”四名技術高超的鬼畜up主組成的“四大欠王”組合,經常在B站合作鬼畜視頻,乃至在其他游戲和娛樂視頻中聯動,吸納了大量粉絲。這種“鬼畜up群體”大多是年輕的、缺乏實際經濟與社會資本的群體,但他們卻能夠在鬼畜營造的媒介景觀和亞文化氛圍中獲得社會贊許,甚至形成與當下諸多短視頻平臺上的“網紅”類似的明星效應,增進了成員的自我效能感。另外,在網上取得的社會支持也成為up主應對壓力的資源,使他們感到在相當程度上的被關心、被尊重。鬼畜創作新手們,也由于“鬼畜圈”戲謔、輕松的文化氛圍得以將外源性的壓力最小化,并且容易通過焦點效應,直覺地高估觀眾對自己作品的關注度和自己在某一時期實際擁有的粉絲數量。這些因素誘導數量巨大的新人up主開啟正反饋式的熱情創作,為鬼畜視頻的盛行打下堅實的“基層建筑”。
第三,鬼畜視頻的創作是視頻生產者對個性化和自我價值實現的追求。人同時具有社會價值和個人自我價值,且需要獲得社會對自我價值的肯定以確立自我價值。在以精英文化為主體的社會文化中,鬼畜視頻作為一種社會亞文化和技術文化,宣揚和表述了視頻生產者的個性化和自我價值實現的追求。首先,鬼畜作品所需的媒體碎片重構、語素拼接和意義再生產,對個性化與創造力提出了內在要求。up主往往需要充分調動發散性思維,“拼湊”出最具搞怪效果,最貼合“萌”“腐”“基”等亞文化氛圍的畫面、音效和臺詞[11]。up主們主觀上也希望在作品中追求新異,體現自己的特色。而從主體身份來看,鬼畜up主以青少年居多,他們的自我同一性,也就是對自己的身份、自己在社會中所能扮演的角色的知悉和認同,尚處在發展的關鍵期。創作鬼畜視頻可能是這些年輕人進行自我同一性探索的新興渠道—生產和傳播鬼畜視頻的過程是年輕up主對自我權力主體身份的界定過程,他們利用新媒體時代的技術賦能,對視聽文本進行過去只有權威傳統媒介才有權進行的編輯與再生產工作,最終打造了一種以諧謔偽裝形式繁衍于網絡空間的鬼畜亞文化形態。鬼畜亞文化形態包含著追求個性表達、展現自我價值的冒險精神。
其次,鬼畜視頻的創作對普遍的個體而言是一項難度頗大的任務。從前期調教(UTAU等軟件)、混音(Adobe Audition等軟件)到視頻的線性整合(Sony Vegas等軟件),乃至更專業、精巧的音MAD類型等鬼畜視頻所需的“扒譜”(FL Studio等軟件)、修圖(Adobe Photoshop等軟件)工序,up主需要熟練掌握多種媒體編輯軟件,完成不計其數的視頻、音頻碎片的拆分重組工作,還要對節奏、加字幕、添加貼圖和特效。up主在克服種種技術難關、花費時間心血完成了一個鬼畜視頻后,無疑是完成了一項自我挑戰,滿足了個人成就動機。這種個人挑戰的完成作為一種獎勵,對那些成就需要較高的up主尤為重要。這類up主傾向于認為粉絲的數目并不會影響自己的創作熱情,而更多地把成就感歸因于自我認同。與其他文化與藝術形式的創作者一樣,他們觸及了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中的最高層級—自我價值的實現,包括問題解決能力、個人理想、創造性等的發揮。
2. 鬼畜文化的消費者:麻痹與自嘲式解壓、特定情緒體驗的追求與相似性的社交
鬼畜文化的傳播本身是相對小眾的,依賴以青年人為絕對主力的群體,他們追求對話地位的平等和社會等級的消解,不惜以粗鄙和插科打諢的方式“放肆”地表達自我。鬼畜視頻則是生產者與消費者的共同狂歡帶來的文化衍生物。日趨成熟的剪輯技術和素材共享機制,以及對圈內群體較強的文化吸引力等特征,決定了鬼畜視頻生產者與消費者的身份界定并不像一本書籍的作者和讀者,或是一部電影的演員與觀眾那樣明確,他們的心理活動有許多相似之處,因而對鬼畜視頻消費者的心理解讀也部分涵蓋于前述生產者的內容。本部分側重于對鬼畜視頻的文化消費行為進行補充分析。
首先,觀看鬼畜視頻仍是一種壓力應對行為。鬼畜視頻是以一種助人忘卻壓力的“分心物”姿態呈現在其消費者面前的。鬼畜視頻觀眾中的“生力軍”80后、90和00后,往往需要在生活中應對學業、求職、置業等重大事件下的壓力。而以后現代、無厘頭、語言游戲等為特征的鬼畜視頻成為他們的解壓新選擇,讓他們轉移注意焦點,從應對生活壓力的辛苦之中暫時解脫出來,暫停認知資源的消耗。與更早出現的、令許多人沉迷的網絡影視劇、游戲等類似,鬼畜視頻成了能讓其觀眾放松自己乃至麻痹自己的廉價精神食糧。這在王蕾等學者的研究中獲得了證實,近一半受訪者表示其觀看鬼畜視頻的原因是“無聊看看,談不上喜愛”[10],說明部分人群觀看鬼畜視頻屬于一種沒有強烈主觀意識卷入的時間消磨,而這種對時間的消磨很可能源于生活情景中對“正統”工作的倦怠。
其次,鬼畜視頻的畫面變換、詞曲混剪、內容韻味等要素往往能夠激發并滿足其消費者特定的情緒訴求。一方面,鬼畜視頻的快節奏、強韻律音頻配合沖擊性的夸張、抽搐、洗腦畫面,可以通過視聽的雙通道突顯來攫取注意,給予觀眾一定的物理性情緒刺激。這與人們游玩公園的娛樂設施或觀看好萊塢大片時體會到的欣快感類似。另一方面,B站具有多種特定內容的鬼畜視頻,它們能夠從語義上喚起各種特征性情緒(并可能與特異性的減壓方式有關)。如以“童年”“經典”“記憶”為招牌,《哆啦A夢》《武林外傳》《植物大戰僵尸》等當下青年一代熟悉的動畫、影視劇、游戲元素為素材的“回溯式”鬼畜[12](“【葛平】童年收”等),呈現了喚起高度青春懷舊的情緒,容易讓人們啟動“退行”的心理防御機制,重新沉浸于童年游戲般的、單純無慮的美好情緒體驗中,以一種欠成熟的方式應付或逃避生活中的挫折或應激事件。又如少數以“局座”張召忠的經歷(如“【局座】水手”等)、經典抗日劇《亮劍》(“【亮劍】浮夸”等)等為素材的“正能量”鬼畜作品,它們往往填詞嚴肅、文學性高且配樂激昂。可以肯定,這些作品的內容寄托了克服困難的信心,甚至國家榮譽感、民族自豪感等不同于個人的痛苦呻吟的正向情感,堪稱鬼畜中的寶藏。B站鬼畜圈有著“就怕鬼畜玩感情”的說法,可以認為,尋求積極的情緒喚起是觀看者消費這類備受稱贊的特殊鬼畜作品的動因之一。
最后,鬼畜視頻的消費者也期望通過觀看鬼畜加入符合自己興趣的社交群落,尤其是共同喜好某些特定鬼畜內容的青年亞文化群落,在“大家一起看”的社會互動中獲得認同與滿足感。人們更傾向于與自己更相似、有較多共同興趣點的個體交往,而鬼畜視頻豐富的素材基礎和B站龐大的青少年用戶基礎使得這種“相似性”很容易被發掘,受眾可以輕松借由鬼畜圈加入“二次元”“金坷垃”“兄貴”等多種更加細分的鬼畜題材愛好群體,獲得基于十分具體的相同愛好的持久交流機會,建立比單純社交網站中的人際關系更親密、信任感更強的社交強關系。“早在20世紀20年代,弗洛伊德就運用物理學知識指出,人是一個能量系統,這系統必須對外開放,與外部環境發生能量交換,才能維持平衡。”[13]顯然,觀看鬼畜視頻并形成相應社交群體,是鬼畜視頻消費者與外部世界發生能量交換,達成個體能量系統平衡的有效方式。
3. 鬼畜文化生產者與消費者在網絡媒介中的互動
社會互動是文化建構的結構性機制,鬼畜視頻作為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互動結點促成了鬼畜文化的社會交互。up主和粉絲在網上交互的文化基礎是趣緣性聚合。不論是鬼畜視頻生產者還是消費者,他們基于B站評論區、up主粉絲群等網絡社交媒介,通過對鬼畜視頻臺詞的自發性吐槽和新解,進一步鞏固“鬼畜圈文化”,并形成自己的虛擬人際圈,共享同一個話語體系,甚至發展出許多“行話”“黑話”,成為與主流文化格格不入的符號語言系統和游戲形式。鬼畜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具有一定的粉絲追隨關系,更有著基于自創的共同文化的穩固聯系紐帶。這種群體內的網絡社交使得成員之間得以發現越來越多的相似性,個人與社會通過媒介緊密聯結,內群體歸屬感增強。另外,基于鬼畜視頻的社交互動形成的第二媒介景觀,強化了與他人的同在感和共同感[14]。這種社交場景營造的虛擬在場感,彌補了青年群體現實中意義感的迷失,借助新媒介聚集的鬼畜迷群可謂一個不受時空限制的情感共同體。
視頻中的彈幕是鬼畜up主與粉絲網絡互動的一個特殊媒介。彈幕可以看作觀看者對視頻內容的即時性吐槽反饋,其語言同樣具有狂歡化的表現形式[15],將“行話”“黑話”和“拼貼”語言的游戲功能發揮到了極致,如“duang”“人群中鉆出一個光頭”“awsl”等彈幕,這些來源龐雜、語法使用隨意化的文字內容,脫離了具體的鬼畜語境便是一些莫名其妙的語言碎片。總體而言,彈幕語言是鬼畜愛好者的內部游戲,其語言本身具有缺乏穩定性、廣泛性、規范性的缺陷[16],但同樣反映了新媒體時代青年人對話語權的爭奪,對主流文化的抵抗。
四、鬼畜文化傳播中的問題及傳播趨勢
(一)鬼畜視頻傳播引發的社會問題
鬼畜視頻自傳入國內至今,以B站為主陣地已經興盛發展逾10年,在其火熱傳播的背后也隱藏著一些問題。這些問題或如波茲曼所描述的:“一切公眾話語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并成為一種文化精神。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都心甘情愿地成為娛樂的附庸,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17]
第一,鬼畜視頻所宣揚的包含臟話、丑化、顛倒是非等低俗或病態元素的小眾文化,僅僅是無可厚非的狂歡式解壓排遣,還是一種應該予以遏止的不健康價值觀?大量鬼畜視頻背后的惡趣味傳播、自我麻痹、審丑等問題不容小覷,它正在打破正統電視節目對受眾的審美引導和審美統治。人們雖然主動選擇了鬼畜視頻這種讓普通個體也能一展創作力和價值追求的新路徑,同時也過于理所當然地接受了這個選擇的“審丑”隱患。這其實是從一種形式的自我麻痹換到了另一種形式。應理性看待鬼畜視頻,一方面,鬼畜視頻作為一種新形式給傳統影視傳媒行業帶來的新審美取向,即對特定原始素材的剪輯和拼接的確會再創造出夸張搞笑的效果,值得部分影視作品、節目和廣告借鑒;應當尊重人們對擺脫各種束縛的狂歡盛宴的訴求,即訴諸鬼畜視頻爭奪大眾文化的話語權。這從某種程度上也能倒逼大眾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創新發展。另一方面,對鬼畜視頻的負性內核不應抱有理念上的認同,對言語粗鄙、極度惡搞歷史文化和名人榜樣的高度價值扭曲的作品應堅決予以抵制。鬼畜視頻偏頗的形象塑造不應被無限放大和誤用,“亞文化”不應導致青少年群體“亞健康”的價值觀。
第二,鬼畜視頻極富惡搞性和反叛性的內容建構,是否會對嚴肅、莊重的傳統文化構成“污名化”影響,損害人們對主流文化的認知?鬼畜作品大量取材于如86版《西游記》《童年》《水手》等經典正統影視、歌曲片段,其剝去它們的文藝價值,改造成內核空化、缺乏深意的視聽刺激,成為青年亞文化群體內的文化玩具。這種對權威傳統文化的消解,在喜好鬼畜視頻的青年亞文化群體中形成內群體偏好的同時,也將本來嚴肅的事物同低級趣味聯系在一起,再經過群體極化,容易使青少年將正常表達的主流文化歸為外群體事物而產生反感和敵意。為解決此問題,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發布《關于進一步規范網絡視聽節目傳播秩序的通知》,強調視聽節目內容必須積極健康,同時呼吁加強青少年群體對經典原作和一切再創作作品的辨識教育。
第三,鬼畜視頻的取材多為對著作權歸屬他人的作品進行盜用和挪用,細究起來必然引發一系列糾紛。一方面,鬼畜視頻不經允許地挪用了原視頻或音頻素材所有者的版權,在一定意義上構成侵權。另一方面,鬼畜視頻與原影視或音頻作品在著作權中的改編權上常常存在沖突;同時,鬼畜視頻對聲音、臺詞的隨意篡改,也侵犯了某些原素材表演者的傳播者權,也就是保護其表演形象不受歪曲的權利。有效防止鬼畜視頻的生產傳播對原作著作權的損害,僅靠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的規范似乎稍顯機械和遲緩。有學者建議構建著作權集體管理平臺,讓鬼畜視頻的創作者和素材著作權人取得直接溝通和聯系;加強剪拼類短視頻發布平臺的注意義務,要求B站等平臺在保證協議的基礎上對視頻內容進行更實質的審核,利用避風港原則和紅旗原則對平臺實施獎懲;加大宣傳力度,讓群眾更加了解《關于進一步規范網絡視聽節目傳播秩序的通知》等相關文件[18]。
(二)鬼畜視頻的商業化傳播趨勢
當不強調其荒誕、無厘頭的特性時,鬼畜視頻作為一種廣義上的二次創作的音視頻形式,一種獨特的視頻風格,能否被更加大眾的文化市場接納,并成為一種商業化的傳播形式?對鬼畜視頻進行選擇性地摒棄與收編,棄其無度惡搞的文化糟粕,取其動感變換的剪輯創作形式等亮點,提高鬼畜視頻的思維和技術含量,可將其推廣到廣告營銷、企業宣傳等相關應用領域。
目前鬼畜視頻向更為大眾的文化市場的邁進還處在初級階段。從鬼畜視頻與廣告的結合來看,最初意義上的鬼畜廣告指的是鬼畜視頻中的廣告植入,譬如以喜之郎果凍、旺旺牛奶廣告為素材的鬼畜視頻,也就是“被鬼畜了的廣告”。這類廣告本身就具有極致夸張、旋律洗腦等鬼畜特性,但這些鬼畜特性與人們對產品屬性認知的關系有待進一步研究。而有意識地運用鬼畜視頻高度重復的洗腦風格的廣告,或稱為“鬼畜視頻硬廣告”,如優信二手車廣告、Boss直聘廣告等,希望通過刺激人們對信息的不斷復述而增進人們對品牌的機械記憶,但其在增進顧客的品牌認知和情感認同上還需下功夫。此外,需要思考和權衡的是爭取面向大眾還是繼續在特定小眾群體內深入發展。
少數鬼畜素材人物本身則因鬼畜界對其以往素材的挖掘和搞笑再創作而走紅。例如央視《變形記》的一位主人公王境澤,他在節目中大喊“就是餓死,也不吃(當地云南山村的)一點東西”,后來卻捧著當地的炒飯說“真香”。此搞笑片段的鬼畜化傳播讓王境澤的形象為人熟知,甚至讓“真香”一詞成為“言行不一”的代名詞,在非鬼畜迷群的年輕人當中也廣為流傳。部分商家,如游戲《無盡大冒險》,注意到了這位鬼畜紅人的影響,請他進行廣告代言,讓王境澤演繹對宣傳產品從置之不理到欲罷不能的“真香”過程。但這僅僅屬于一種蹭熱點的廣告宣傳策略,與鬼畜形式風格和其一般內涵的利用關聯不大,產生的廣告效應也往往只針對小部分人群。而王境澤這樣的素材人物,在從鬼畜到廣告的一系列過程中塑造了更鮮明的公眾形象,成為潛在受益者。
(三)鬼畜文化從小眾文化走向大眾文化的傳播趨勢
鬼畜視頻及其所代表的亞文化最先吸引的是熱衷于此的“迷群”,但隨著鬼畜視頻在中國新媒體環境下的演變,其已經從局限于彈幕視頻網站特定分區的小眾文化逐漸向更符合普通網民觀感的相對大眾文化過渡[6]。即小眾文化通過挑戰精英文化,正在實現自身的大眾化。在這一過程中,“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為現代性的解構提供了條件”[19]。一方面,B站鬼畜視頻的主導類型由在形式、載體、技術上難度較大的音MAD、人力VOCALOID轉變為更簡易、更調侃搞笑的鬼畜調教,后者的理解門檻較低,讓不熟悉亞文化圈內符號用語和文字游戲的普通觀眾看后也能會心一笑。另一方面,鬼畜調教視頻相比已經體系化的經典鬼畜素材,納入了相當一部分與時事熱點聯系緊密的人物素材,如成龍代言霸王洗發水、雷軍參加小米4i印度發布會、特朗普發言等,這些惡搞熱點事件或者名人的鬼畜視頻對普通公眾而言有較大的吸引力。從這個意義上,鬼畜視頻與傳統的報紙諷刺漫畫類似,一般受眾可以從中品讀到對時事熱點的生動辣評,存在大眾化傳播的潛力。
鬼畜視頻還出現了和其他網絡短視頻結合發展的態勢,即一種媒介技術層面上的技術匯聚效應促使鬼畜文化獲得更進一步的擴散。近年來鬼畜視頻借助抖音、快手等移動端短視頻媒介平臺迅猛發展,而這些平臺的鬼畜視頻獲得了比B站鬼畜愛好者更龐大的用戶基礎。鬼畜視頻與網絡短視頻的互動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短視頻APP中的網紅被吸納為鬼畜素材人物,引發鬼畜視頻在短視頻網紅粉絲群體內的傳播;二是抖音等音樂短視頻APP提供了大量節奏鮮明、便于配合鼓點和調整播放速度的潮流音樂,為新的鬼畜視頻創作提供了背景音樂參考。
五、總結與展望
本文基于心理學、社會學和傳播學的綜合視角,對鬼畜視頻這一小眾網絡文化衍生物進行解讀,從在解構與重構中生成,到在網絡環境中由具有特定心理動機的主體傳播,再到傳播中容易引發的社會問題和傳播態勢進行了全過程分析。以鬼畜視頻為代表的鬼畜文化傳播包含的問題豐富而復雜,相關研究還不夠全面和深入。未來有關鬼畜視頻的研究可以著眼鬼畜視頻的傳播偏好與傳播者人格特質之間的相關性,解讀鬼畜圈中出現的一些具體現象,如某些低齡up主為了博關注而單純投遞“大勢所趨”作品的現象與他們的虛榮心滿足之間的關系;也可以結合斯坦福大學精神專家阿布加歐德醫生提出的“網絡人格”觀點[20],分析鬼畜視頻嘻哈、大膽的表達方式與網絡人格“缺乏約束”的核心特征之間的關聯,警示人們提防鬼畜視頻傳播中可能順帶傳播的五種負面心理力量,也就是自負、自戀、邪惡、退化、沖動的網絡人格“五宗罪”;還可以結合克萊·舍基的“認知盈余”觀點[21],將鬼畜文化創作看作人們借助互聯網技術工具對自由時間的一種利用形式,對互聯網創造的“參與文化”熱潮提出新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