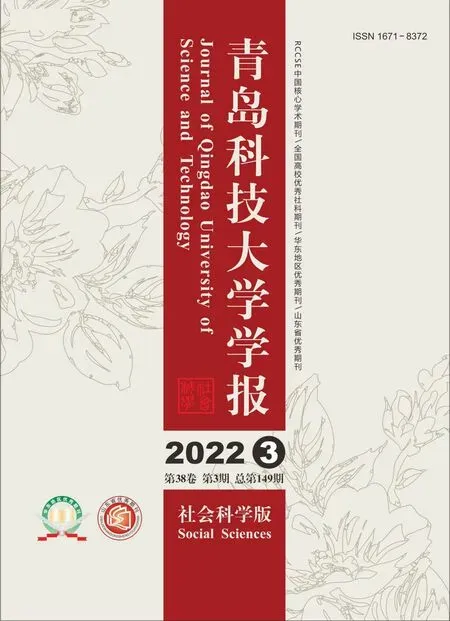阿爾都塞文本閱讀策略及其對馬克思藝術生產論的建構
○ 蔣繼華
(鹽城工學院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江蘇 鹽城 224051)
在馬克思主義文本理論史上,法國文論家阿爾都塞的文本閱讀策略可謂獨樹一幟。這不僅僅因為阿爾都塞以結構主義的框架考察社會現實,尋求決定社會發展的問題結構,更因為其圍繞意識形態與藝術生產,重新詮釋讀者與文本的關系,以原創性理論思維給出獨特的文本解讀框架,揭示文本表面漂浮的現實“癥候”及意識形態的產生機制,形成“生產性”的文本閱讀和批評模式,鑄就了馬克思主義詮釋學的批判向度。這一切體現出對馬克思藝術生產論的建構,顯示出對馬克思藝術生產思想的繼承與發展。
一、阿爾都塞文本閱讀的新創見:“癥候式閱讀”對“柵欄式閱讀”的超越
自有文學活動以來,對作品的閱讀、理解和欣賞就應運而生,或者說,閱讀和創作相伴而行。除了少數經典之作被束之高閣,或藏之名山,一般人難以接觸外,應該說,絕大部分作品進入閱讀者的視野,其價值在閱讀者的品鑒和欣賞中得以實現。但長期以來,文學閱讀存在一種現象:在作者、讀者、文本等要素中,以作者為主體,服從于文本思想而忽視讀者、控制讀者,進而剝奪讀者參與文本意義創造的傳統一直無法撼動。艾布拉姆斯在《鏡與燈》中從世界、作者、作品、讀者等要素出發,區分出模仿說、實用說、表現說、客觀說等批評方法,其中模仿說審視藝術品和世界的關系,表現說、客觀說分別基于藝術家的主觀創造和作品的自足存在。這里尤值得一提的是實用說。在艾布拉姆斯看來,實用說以欣賞者為中心,但實用說繼承了賀拉斯的衣缽,把藝術當作一種通過技巧、規則或者制作手藝而感染欣賞者、引發欣賞者必要反應,并以此決定詩的藝術規范、批評準則和審美標準的人工產品。因此,實用說突出創造者對欣賞者的影響以及藝術的勸諭教化功能,這也是從賀拉斯到18世紀絕大部分批評理論所具有的特征。顯然,這幾種批評方法都以作者為主體,突出作者的天賦創造及其作品對讀者的審美反應,其結果是作者的主體性被無限放大,讀者被逐漸淡化,讀者成了文學活動的背景[1]。由此出發,讀者對文本的閱讀和欣賞要放棄自己的想象,迎合作者的本意,贊同作者的意圖,還原文本的意義,領略文本帶來的快感,也就是說,讀者沒有參與文本意義創造的話語權力。這就必然引發“什么是閱讀”的追問,指向的是閱讀的終極價值。
1965年,阿爾都塞在巴黎高等師范學校《資本論》研討班上,提出了對(馬克思的)文本如何進行深層閱讀,以實現對文本真實意義乃至真理的揭示問題。在研討班的報告《讀〈資本論〉》中,阿爾都塞明確指出,作為哲學家閱讀《資本論》,首先應該注意研究對象的特殊性問題,并對研究對象進行發問,即《資本論》的對象在哪些方面區別于古典(甚至是現代)經濟學,又區別于青年馬克思的著作特別是《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兩個區別”的發問關系閱讀的有效性問題,即“閱讀何以可能”。阿爾都塞針對馬克思閱讀斯密和李嘉圖經濟學著作的情況提出兩種完全不同的閱讀策略:“柵欄式閱讀”和“癥候式閱讀”。“柵欄式閱讀”是指閱讀就像是通過“柵欄”一樣進行瀏覽和直接看,“柵欄”帶有的某種理論成見、理論基準使得閱讀者把作品的思想觀點當作現成的東西而不對閱讀對象提出任何問題,閱讀是回顧式的、直接而明晰的。阿爾都塞舉例說,通過“柵欄式閱讀”,馬克思指出了斯密著作中看不見的空缺,簡單補充了斯密的空白,這使得斯密的著作以馬克思著作為尺度,通過馬克思的著作被看到,閱讀的結果無非是對斯密的空白、缺陷、出現和不出現的總結,由此獲得兩者一致性和不一致性的記錄,即注定在馬克思的著作中只能看到馬克思已經看到的東西,馬克思由此變成了斯密。而對于斯密著作中完全的空缺產生的原因,沒有給予說明和深刻探究,這就帶來“看”的“心理學缺陷”和“看”的缺陷造成的閱讀疏忽。顯然,傳統“柵欄式閱讀”的癥結在于摒棄“看”和忽視的相互聯系及其內在機理,把全部文本閱讀歸結為“看”的簡單關系再認識,把事物的本質歸結為客觀存在的簡單條件,尋求以上帝的眼睛、真理的幻想和認識的自映的神話、黑格爾的絕對知識洞察一切事物,把現實變成有聲的語言,把書面語言變成直接真理。于是,天幕洞開,歷史的文字只有一種聲音。對此,德里達認為,在這個時代,文學文本內容總存在著哲學命題,其語義學與主題學帶有某種形而上學,通過主題、語態、形式、體裁表現出來,閱讀與寫作、符號的創造與解釋、作為符號組織的一般文本處于次要地位,真理或由邏各斯構成的意義處于優先地位,而所指與一般邏格斯直接相關,能指指稱著永恒的真理[2]。這就影響了從歷史文字中讀出真實內容的可能性。阿爾都塞指出,歷史的真實不可能從公開的語言中閱讀出來,而是取決于某種結構聽不出來、閱讀不出來的自我表白,只有從被思維的歷史和歷史理論出發,同閱讀的宗教神話和黑格爾的絕對知識相決裂,才能夠說明閱讀的歷史觀。例如:文本閱讀中的空缺如何產生,它與理論發現是什么關系?文本的顯性表述與隱性結構又是何種關系?這些都關系文本閱讀能否成為真正的科學。
這就引出了“癥候式閱讀”。不同于“柵欄式閱讀”對空白結構的忽視,“癥候式閱讀”科學詮釋了空白的產生以及“看”的認識機制,從而使其成為一種方法論詮釋學。阿爾都塞這樣界定“癥候式閱讀”:“所謂征候讀法就是在同一運動中,把所讀的文章本身中被掩蓋的東西揭示出來并且使之與另一篇文章發生聯系,而這另一篇文章作為必然的不出現存在于前一篇文章中。”[3]21“癥候式閱讀”的要義在兩個方面:一是揭示沉默的字句、被掩蓋的問題和隱性的結構,即傳統“柵欄式閱讀”視而不見的空缺。二是這種閱讀關涉顯與潛的關系,隱而不顯的部分是重點,此即阿爾都塞所言的“一篇文章”與“另一篇文章”發生聯系,或者第二篇文章從第一篇文章的“失誤”中表現出來,從而在現有文本中看出空缺,在問題框架中以新的理論生成發現文本的斷裂性,形成新的問題。這實際上是理論的顛覆、過渡與轉變。今村仁司在《阿爾都塞:認識論的斷裂》中提出:“一般來說,被給予的言說是由兩個主題(思路)構成的,即是由顯在的主題和潛在的主題,或者用空間的概念來說,是由可見的空間和不可見的空間構成的。第二種閱讀方法,在閱讀顯在的可見的主題=空間的同時,也把潛在的不可見的主題=空間作為顯在的可見的來理解。”[4]161阿爾都塞以馬克思對古典經濟學關于勞動價值的定義為例,分析“癥候式閱讀”的實現方式。古典經濟學對于“勞動的價值”的表述是:“‘勞動’的價值等于維持和再生產‘勞動’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阿爾都塞認為這句話沒有任何意義,例如什么是維持勞動?什么是“勞動”的再生產?獨具慧眼的馬克思做出了與眾不同的回答:“勞動(……)的價值等于維持和再生產勞動(……)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馬克思在“勞動”和“再生產勞動”附近指出古典經濟學回答中的兩個空白(文字中的刪節號),即古典著作本身沒有說出的沉默,而這種沉默恰恰是它特有的話。馬克思通過在表述中引入和重新建立古典經濟學空缺的“勞動力”價值概念,生產出存在的空白,即“什么是勞動力價值”。由此,馬克思提出沒有表述出來的問題,使古典著作的沉默得到揭示。
“癥候”源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指疾病在人體呈現的癥狀。弗洛伊德認為神經病癥候與病人的內心生活和“隱意識”有相當大的關系,因而“癥候”是有意義的。弗洛伊德舉例說,前來看病的患者忘記關門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無意義的,它泄露了患者對醫生的態度。通過對這種小小的“癥候”性動作的分析,弗洛伊德提出“癥候”動作有其動機和目的,可以推知更重要的心理歷程,同時這種“癥候”性動作在病人的意識之外。由此可知,“癥候”和潛意識之間存在互相代替的關系,即“癥候”是潛意識活動的結果。“這個意義必先為潛意識的,然后癥候才可發生。癥候不產生于意識的歷程;只要潛意識的歷程一成為意識的,癥候必將隨而消滅。”[5]顯然,“癥候”的意義指向了在場和不在場(某種潛意識的活動)的存在。對阿爾都塞有重要影響的還有拉康。拉康的鏡像理論揭示主體的虛妄想象性,突出無意識結構的本質以及語言的能指鏈在無意識運作機制中的重要作用,推進弗洛伊德的學說從疾病學向社會存在的轉變。這一切都對阿爾都塞的文本閱讀產生重要影響。顯然,對文本閱讀而言,閱讀就是不斷地尋找言說的沉默、缺失等“癥候”,探查文本背后的深層結構,即“把痕跡(常常采取充實的形式的空隙、空白、真空、闕如等)作為暗號來解讀”[4]164。這種空白、罅隙、沉默等沒有看到的東西,在阿爾都塞看來正是閱讀所要尋求的東西,即“生產了一個新的、沒有相應問題的回答,同時生產了一個新的、隱藏在這個新的回答中的問題”[3]16。“癥候式閱讀”專注于尋找文本“內在的黑暗”和潛藏的問題,而這些問題是看不見的,要靠閱讀來實現。這就涉及“認識的觀念”的改變。
二、阿爾都塞文本閱讀與意識形態的生產
文藝與意識形態的關系一直是西方馬克思主義關注的重要論題。事實上,阿爾都塞對“癥候式閱讀”的標舉與其對意識形態的重視密不可分。
首先,在阿爾都塞看來,意識形態是與科學相對立的幻象。在《保衛馬克思》(1965)中,基于20世紀60年代斯大林教條主義在法國的盛行以及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泛濫,阿爾都塞借用雅克·馬丁的總問題和巴歇拉爾認識論斷裂的概念,以結構主義立場切入馬克思主義,提出馬克思的思想以《德意志意識形態》(1845—1846)為標志,存在“認識論斷裂”—從“意識形態”向“科學”的轉變,即以1845年為界,將馬克思思想分為“意識形態”和“科學”兩個階段。由此,馬克思同以往的意識形態哲學信仰相決裂,其思想發展中的認識論斷裂標志著一種新的哲學觀即辯證唯物主義的出現。正如1972年6月阿爾都塞在《自我批評材料》一文中所言,他20世紀60年代這樣做的主要目的是保護馬克思主義免受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真實威脅,證明馬克思主義同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勢不兩立,并同資產階級意識形態進行堅持不懈的斗爭,作徹底的和持續的決裂[6]218。這一切寓意阿爾都塞以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區分兩種不同理論形態的特殊差異性,并對以往哲學信仰予以清算,解決“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被軟化等在新時期遭遇的理論問題,實現“保衛馬克思”的目的。但阿爾都塞同時指出,意識形態是具有獨特邏輯結構的表象體系,它既不是胡言亂語,也不是歷史的寄生贅瘤,而是作為社會歷史生活的基本結構和人類世界的客體,強加于絕大多數人,被人們所體驗、感知、接受和忍受,當然這一切是在無意識的條件下以“意識”的形式出現。在這種情況下,意識形態是人類對生存世界的體驗和想象,人類社會把意識形態作為自己呼吸的空氣和歷史生活的必要成分分泌出來,而把意識形態作為手段或工具使用的人們會不自覺陷進意識形態的包圍之中,以主體的方式存在,實踐著意識形態的承認功能及各種儀式[7]。由此,和科學相比,意識形態雖是一種虛妄的幻化的表象體系,但指向人類世界本身,其實踐職能和社會職能壓倒理論職能或認識職能。這就將意識形態拉回到社會生產中。
其次,阿爾都塞文本閱讀策略旨在暴露意識形態的深層支配機制及其對社會現實的體驗和想象本質。由于意識形態是與科學相對立的幻象,在其影響下,人們看到的只是一種表象體系。如何破除意識形態的迷障,揭示意識形態具有的虛假幻象,凸顯意識形態包裹的現實,就成為理論家們面臨的問題。阿爾都塞認為,意識形態從不會說“我是意識形態”,其功能的發揮是通過呼喚或傳詢的鏡像結構,而且意識形態正不斷威脅著“對實證事物的理解”,包圍著科學,并把科學搞得面目全非。為此,越過阻礙認識現實的意識形態迷霧,同哲學意識形態相決裂,走向科學知識和真實的世界,是保證哲學實證性的關鍵。在這方面,阿爾都塞提出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解釋要依靠嚴格的閱讀方法,這種閱讀方法區分同一個詞的不同概念,看出一個詞是否有這個概念,通過詞的作用認清概念的存在,確定概念的本質[6]20。通過“癥候式閱讀”的選用,阿爾都塞進入馬克思思想的深處,尋求無意識的問題結構,將意識形態與馬克思主義哲學區別開來。這就開啟了處理文藝和意識形態復雜關系的文本意識形態觀,凸顯了對文本生產的重視。
在《一封論藝術的信》(1966)中,阿爾都塞在回答文藝和意識形態的關系時指出,藝術是使人們覺察到或感覺到的某種暗指現實的東西,它給予人們的乃是“從中誕生出來、沉浸在其中、作為藝術與之分離開來并且暗指著的那種意識形態”[8]521。也就是說,滲透于文本中的意識形態基于審美效果的實現,在文本內部造成一定的距離,形成文本—意識形態的離心結構,讀者以體驗的方式覺察到意識形態的存在。正因為這種離心狀態,所以才能窺破意識形態的幻象,實現對意識形態的批判和生產。在《抽象畫家克勒莫尼尼》一文中,阿爾都塞指出克勒莫尼尼作為抽象化的畫家,畫出人和物體、場所、時間等之間的真實關系,表現山巖、骨骼、植物、動物等和占支配地位的意識形態觀念之間的距離,顯示畫家把他的“創作意圖”銘刻在由他創造的思想物質性中。例如一把椅子的扶手或者一件工具延長了人和動物瘦骨嶙峋的四肢關節,表征從一個起源出發的世系順序,甚至是一種唯物主義的順序。在阿爾都塞看來,人和自然之間有直接關系的意識形態為克勒莫尼尼的畫作提供了靈感,或者說克勒莫尼尼畫作中表現的事物差異,首先是意識形態意圖差異的邏輯表現,畫作從而成為特殊歷史的一部分。在這個意義上,克勒莫尼尼畫中直接表現社會關系、生產關系或階級斗爭將毫無意義,因為控制著人們的具體存在,即關于人們和物體之間關系的日常意識形態結構,“永遠不能用它的在場、用原型、正片和凸雕來表現,而只能用跡象和作用、用不在場的標志、用副片和凹雕來表現”[8]533,其可取的做法是畫出可以看得見的對象之間的聯系,描繪出支配其確定的不在場。這些跡象、標志、副片和凹雕以“癥候”的形式表現另一種不在場的規律,即隱匿于文本深處的結構,它左右著作品意義的表達。由此,所謂“意識形態的生產”即在文藝—意識形態關系中,通過在文本內部制造距離,暴露意識形態的沉默和缺省,建構不在場的存在。
當然,“癥候式閱讀”、文本意識形態的生產與阿爾都塞標舉的“總問題”息息相關。阿爾都塞認為空白、沉默和斷裂等是文本固有的“內在黑暗”,有著隱在的總問題。例如:對于古典經濟學而言,死抱著舊的問題,對理論的“內在黑暗”視而不見,缺乏“看得見的東西”和“看不見的東西”的問題式轉換和兩者勾連的有機紐帶,因而存在“看”的缺陷。事實上,可以“看得見的東西”是在一定場所和范圍內,對理論總問題的反思。“總問題領域把看不見的東西規定并結構化為某種特定的被排除的東西即從可見領域被排除的東西,而作為被排除的東西,它是由總問題領域所固有的存在和結構決定的。”[3]18由于總問題會帶來表層的各種癥狀,這就需要運用“癥候式閱讀”,才能洞悉沉默、空缺的深層機理,把被非本質的外殼所遮蓋和包裹的內核暴露出來,同時穿透意識形態幻象,發掘意識形態的結構、形象及其深層支配作用,揭示其如何建構現實存在。也就是說,理論和認識只有不斷地生產出對總問題的反思,才能揭示總問題,實現意識形態的生產。
三、阿爾都塞文本閱讀策略對馬克思藝術生產論的建構
馬克思將藝術看作生產的一種形式,進而提出藝術生產論,體現了其對藝術性質的獨特認識。20世紀以來,包括本雅明、阿爾都塞、馬謝雷、伊格爾頓等在內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從政治經濟學、哲學、文化等方面對馬克思的藝術生產論進行繼承和發揚,拓展了藝術生產論的當代空間,體現了藝術生產的當代訴求。在這一過程中,阿爾都塞以獨特的文本閱讀和闡釋策略開啟文本和意識形態的新關系,實現了對馬克思藝術生產論的建構,標志著藝術生產論的當代轉換。
首先,阿爾都塞的文本閱讀策略推動了“藝術生產”功能從“創作”向“批評”的轉換,催生了文藝批評的新范式。具體而言,馬克思首創的藝術生產論主要是基于社會實踐分析商品經濟條件下的藝術生產規律,在一定的歷史形態中考察文藝,揭示物質生產對藝術生產的影響作用。如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提出:“當藝術生產一旦作為藝術生產出現,它們就再不能以那種在世界史上劃時代的、古典的形式創造出來。”在《剩余價值理論》中,馬克思區別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認為密爾頓創作《失樂園》得到5鎊,是非生產勞動者,為書商提供工廠式勞動的作家,是生產勞動者。馬克思關于藝術生產的論述揭示了藝術具有的二重性:一方面,藝術作為按照美的規律來建構的審美形式,是一種特殊的生產;另一方面,在商品經濟時代,藝術生產不可避免地與資本發生某種關系。總體而言,藝術生產是精神性和商品性的有機結合。“但是,無論是馬克思本人,還是該理論的傳人,都將‘藝術生產’概念用以界定創作活動,亦即藝術活動整個過程的前端,而將處于這一過程后端的閱讀和批評歸入‘藝術消費’的范疇,對其生產性問題并未置論,而‘癥候解讀’理論恰恰開辟了這一論域。”[9]應該說,在馬克思藝術生產論從創作向批評的轉換中,阿爾都塞功不可沒,主要表現在阿爾都塞著眼于文本深層結構分析,以“癥候”的探尋顛覆傳統文本的確定意義,實現對線性閱讀的超越,尤其通過對意識形態邏輯結構的審視和考察,鑄就文本意識形態的生產機制,擴大藝術生產的視閾,形成新的文藝批評范式,啟發后人的文學生產思想。“在‘生產原則’下,馬克思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就成為一種新結構的生產,這觸及了阿爾都塞新詮釋學的批判向度。”[10]阿爾都塞提出:“我所說的解釋是認真的和有系統的解釋,是建立在真正具有哲學、認識論和歷史知識基礎上的解釋,是依靠嚴格的閱讀方法的解釋,而絕不是單憑一得之見而作出的解釋(盡管人們單憑一得之見也可以寫出書來)。”[6]18由此,經阿爾都塞的文本閱讀和闡釋,馬克思的藝術生產論跨出政治經濟學視野,進入文學批評領域,彰顯自身的價值。阿爾都塞的文本闡釋豐富了馬克思主義詮釋學理論。
其次,以“認識的生產”構建“生產性”的文學批評模式。阿爾都塞文本閱讀和闡釋的新向度在于發掘文本的深層支配特質和意識形態的幻象,尤其通過馬克思對古典經濟學文本的閱讀分析,以結構主義的方法深挖隱藏文本背后的總問題,“必須徹底改變關于認識的觀念,屏棄看和直接閱讀的反映的神話并把認識看作是生產”[3]15。這對構建“生產性”的文學批評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這里涉及對“生產”的理解。阿爾都塞認為,認識加工其“對象”,但不是加工現實對象,而是加工它的原料。由此,“生產”這個詞表面上意味著把隱藏的東西表現出來,實際上意味著改變已經存在的東西,即“生產”是一種認識的生產,彰顯認識的創造性和能動性。而當認識是一種理論創造的時候,它加工的原料(如表象、概念、事實)由其他實踐(包括“經驗”實踐、“技術”實踐或“意識形態”實踐)所提供,產物為“知識”(科學真理)[6]140。由此,文本闡釋助推意識形態走向科學實踐。在這一過程中,阿爾都塞極力反對傳統主體性的“美學創造”話語,因為它是一種自發的意識形態語言,遮蓋了藝術的內在生成真相。為此,必須打破意識形態的鏡像,同意識形態進行決裂,意識形態的內在批判成為可能,這也就形成文本意識形態的生產。這一點對西方馬克思主義藝術生產理論產生深刻影響。阿爾都塞思想的繼承者、法國批評家馬謝雷在1966年出版的《文學生產理論》一書中提出,文學批評是按照一定的生產流程,對文本的矛盾、混亂、含糊等狀態進行意義闡釋,構建能“生產知識”的批評模式。伊格爾頓認為阿爾都塞和馬謝雷關于文學和意識形態的關系認識具有深刻的啟發性:“科學的批評應該尋找出使文學作品受制于意識形態而又與它保持距離的原則。”[11]文學闡釋和批評必然是一種知識建構、意蘊創造的生產活動,它意在重構文本,將批評引向文本意義的增值,揭示意識形態掩藏的社會現實。
作為西方馬克思主義藝術生產論的代表,阿爾都塞以“癥候式閱讀”實現對文本閱讀的新創見,同時體現了其對藝術生產與意識形態關系的處理。“癥候式閱讀”策略既推動了馬克思藝術生產論“批評”維度的深化、推進和轉換,又實現了批評的知識建構功能,顯示了批評具有的創造性,成為當代馬克思主義文論的新景觀。這一切不僅維護了西方馬克思主義藝術生產論的批判立場,更昭示著“藝術生產”在意識形態、審美文化、政治批評等方面迎來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