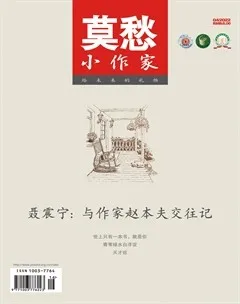羅得島海邊的一朵紅紅的玫瑰
8月是羅得島最浪漫的季節。
海面上帆船點點,雖然那是富人的享受,但也可以成為窮人的風景;海浪拍打著綴滿貝殼的礁石,輕重得當,仿佛擔心把礁石拍碎;站在海邊,海水散發出我最喜愛的海藻的味道,這大自然的饋贈,讓我的嗅覺迷醉;有的海鳥從弗吉尼亞飛來,有的海鳥往緬因州方向飛去,但它們都要在我們面前盤旋,仿佛它們已經知道我剛剛去過那里;島上那些大得離譜、豪華得不像話的房子,依然驕傲地占據著島上最佳的地理位置,雖然一百年前的主人已經不在,但它們依然看著遠方,看著大海,看著海上的帆船和海鷗,像一百年前一樣。
從地圖上看,羅得島州的州府叫“普羅維登斯”。從字面看,這個地名對于中國人來說,一點意義也沒有;但是,再看看其英文Providence(按普通名詞解釋,即天賜;天堂;天意),才知道它的確配得上做羅得島州的首府。有著米開朗基羅天頂畫《西斯廷教堂》里的蔚藍的海水的羅得島,我們就更能理解它的州府為什么叫“天堂”。
“羅得島”和“羅得島州”通常被我們混稱。更多情況下,人們認為羅得島州就是一座具體的島;或者,羅得島州就是在島上。這都只對了一半。羅得島州作為美國最小的一個州,其全名是羅得島與普羅維登斯莊園州,這也是全美最長的州名,由于州名太長,人們便在習慣上稱它為“羅得島州”。羅得島州的版圖包括與馬薩諸塞州和康涅狄格州相鄰的大陸部分,以及伸入大西洋中的、以新港為主體的島嶼部分,我們通常所說的羅得島指的便是伸入海里的這一部分,即狹義的“羅得島”,是羅得島州最具特色、最為精華的部分。當然,由于整個羅得島州版圖很小,從該州的任何地方到海邊都不會超過半個小時的車程,所以它又被稱為“海洋之州”。
這是8月中旬的第一天,我們在普羅維登斯這一側租住的民宿里吃完早飯,做完清潔,關上大門,就算是成功退房。開過兩座跨海大橋,我們來到了新港那邊的羅得島上。
天藍得讓人目瞪口呆。沒有一絲云彩的天上,只有一枚碩大的、獨自燃燒的太陽。有海島,有藍天,有陽光,生活便更像生活。
走在羅得島上,既是走在現實中,也是走在歷史的長廊里。差不多是在400年前,殖民者在這座當時還是荒島的土地上烙下了最初的腳印。印第安人把這座島賣給清教徒時,它連名字都沒有。就像歐洲人給新大陸本來沒有名字的地方一一貼上歐洲的地名那樣,這片本屬于印第安人的荒島易手之后被貼上了“羅得島”的標簽。
“羅得島”其實是個希臘名字。在愛琴海的東南部,在作為希臘文明起源地的克里特島的東北方向,就有一座小島叫羅得島。作為希臘的第四大島,它離希臘本土很遠,卻與土耳其隔海相望。我發現,用老歐洲的“羅得島”來命名新大陸的這座荒島,顯然不是照搬照抄,當屬于神來之筆,命名者顯然是比較了兩座島的共同之處。雖然美國的羅得島瀕臨大西洋,但從其風光看,碧藍的海水,陡峭的巖壁,令人產生一種置身于地中海的錯覺。
8月的陽光,一點也不吝嗇;它照著富人,也照著窮人;它懷抱百年大樹,也讓小草通體透明。走在8月,走在陽光下,走在羅得島上,就是將整個人交給陽光,交給海風,也交給自己散漫的遐想。
羅得島新港海邊南端,是游人最愛去的地方。在這里,羅得島以柔軟的曲線伸向海中,形成一個不明顯的半島,確切地說是一個弧形的海岬。朝西看,可以看到羅得島州的大陸部分;往南、往東看則是浩渺的大西洋。站在這海岬,我忽然想起了卞之琳的那首叫《半島》的詩:
半島是大陸的纖手,
遙指海上的三神山。
小樓已有了三面水,
可看而不可飲的。
這一天是周六,海邊的游客特別多。有放風箏的,有漫步的,有坐在海邊看書、發呆的。8月的陽光雖然有點火辣,但海風總能把溫度調節到宜人的程度。開車到海邊停下,從車上搬下躺椅、遮陽傘、書、狗和一天的飲食。也看書,也看海;看大海的時候看書,看書的時候看看大海,人文與自然在天地之間獲得了和諧,肉體與精神在知識與自然之間達到了一種平衡。在這個全美最小、最早宣布脫離英國的海邊之州,“自由”被這8月的陽光和海水解釋得格外清楚。
正往前走著時,忽然一個畫面深深地吸引了我。在海邊草地的長椅上,一對約莫70歲的老夫婦面朝大海悠閑自得地坐著。他們有一句沒一句地聊著天,更多的時候則是看著海、看著天發呆。老婦人穿一件藍色的背心,盡量讓自己暴曬在陽光下;她的頭上戴一頂遮陽帽,帽子上別著一朵紅紅的玫瑰。吸引我的正是這朵玫瑰。它是遠近唯一的一點紅色,而這一點紅色立刻被我上升到了美學的高度。我想起王爾德說過的,美是不實用的。這頂遮陽帽,如果沒有配上這朵玫瑰,遮陽的效果一點不會差;這頂遮陽帽,即使配上了這朵玫瑰,遮陽的效果肯定不會因此變得更好。所以在我看來,老婦人遮陽帽上的這朵玫瑰,完美地詮釋了什么是唯美主義。
一朵紅紅的玫瑰,雖然只是一個小小的裝飾,但人在70歲時,還在意、還記得在帽子上別一朵玫瑰,這就是一種生活的態度,也是一種追求美學的生活。羅得島上8月的太陽,很響亮,也很寧靜;天依然藍得可以照見我們的靈魂,而我們的靈魂也像一座打開了所有門窗的屋子,任海風自由貫穿;海水輕柔地拍打著岸邊的礁石,那些礁石在這座島還不叫“羅得島”的時候就在那里;點點白鷗像被風吹亂的音符,在陽光中變奏出不同的樂章。老婦人帽子上的這朵紅紅的玫瑰像一朵小小的火焰,把人類對美的向往悄悄地點燃。我不禁想起蘇格蘭農民詩人彭斯的那首詩《紅紅的玫瑰》:
啊,我的愛人像朵紅紅的玫瑰啊,
六月里迎風初開,
啊,我的愛人像支甜甜的曲子,
奏得合拍又和諧。
玫瑰被彭斯寫進這首詩之后,天下的詩人再用玫瑰表現愛情,都會被王爾德指責為“庸才”。但是,用一朵紅紅的玫瑰來裝點我們的生活,讓它在羅得島8月的陽光下綻放,這一定是對生活的熱愛,也是對唯美主義生活態度的最好實踐。
繞過這處海岬,我來到19世紀美國的交通大王、鐵路大亨范德比爾特的故居“聽濤山莊”。坐在這座豪華得不可思議的老宅的石階上,看著遠處的海浪用白色的牙齒舔著礁石,看著朝海平線飛去的海鷗,不斷浮現在我眼前的還是那朵紅紅的玫瑰。
陳義海:教授,比較文學博士(博士后),雙語詩人,翻譯家,中國作協會員。兼任江蘇省比較文學學會副會長,西南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客座教授等。主要從事跨文化研究、文學翻譯和詩歌創作。出版各類著(譯)近三十種。曾翻譯出版《傲慢與偏見》《魯濱遜漂流記》《苔絲》、“格魯兒童文學系列”等。其第一部英文詩集《西茉納之歌和七首憂傷的歌》2005年在英國出版。曾兩度獲得江蘇省紫金山文學獎(詩歌獎、散文獎)等。
編輯 木木 69137296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