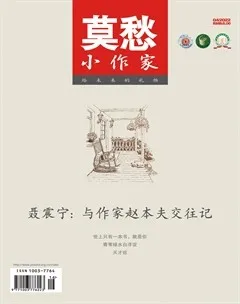解謎
這些年,趙萬中在江西、安徽、浙江都找過礦,翻山越嶺、跋山涉水,有路沒路的地方,他都要去。
1
秋天的早晨,趙萬中站在院子前等我們。他穿了件暗紅色的襯衫,與臉上蕩漾著的笑意呼應著,顯出一種樸實的喜氣。趙萬中長得敦敦實實,一張又圓又亮的臉,泛著光,一副常年在山野里享受清風皓月照拂的樣子。他說話大嗓門,笑起來時從喉嚨深處發出嘎嘎嘎的響聲,是個性格爽直的人。但后來發現,他粗中有細,說話滴水不漏。
老趙的家在一片安靜的桂花林深處。門前是條鄉村公路,半天才有一輛車經過,偶爾駛過的車輛驚動樹梢上的鳥扇動翅膀,葉子嘩啦啦響的動靜加深了山村才有的靜寂。桂花的暗香一陣陣波浪似的涌來,時濃時淡,如裊裊炊煙撩起人的鄉愁。
“難得在家,通常這種晴好天氣,我都在山里一趟趟地轉,看山,找泥。”老趙說
他說的泥,就是紫砂原礦料。
院子有小半個籃球場大小,邊上有塊隆起的小坡特別顯眼。老趙上前掀開蓋著的塑料布,原來是一堆土。
這是大紅袍原料呢!他細心地爬到土堆上蹲下來,生怕踩壞了腳下這些看似平常的泥塊,從中挑挑揀揀地捏起一塊泥巴在掌心來回地搓,說這料好啊,陳腐幾個月了。
關于大紅袍有兩種說法。一種是加入石黃后的紅泥,稱之為大紅袍,特點是可塑性、延展性強,泥片彎曲時不易斷裂,燒成溫度大約在1040℃,收縮比例在45%-55%。老趙一聽,便說:“這是練泥的商家混淆視聽,其實跟大紅袍一點關系沒有。”說到這里時,老趙一再強調,石黃就是石黃,練不成大紅袍,真正的大紅袍不會加石黃。
還有一種所謂的大紅袍,是把適量的天然鐵紅粉加入含氧化鐵成分較高的夾層泥中,成型后再經過窯燒,壺體的泥質會變細,砂粒小,密度大,結晶高,色澤大紅。經過茶水泡養后,壺體越發艷紅熱烈。也有人將之稱為大紅袍。
但老趙一聽,連連否定。
老趙篤定地說,我這院子里堆著的就是大紅袍,沒有加石黃。
我問老趙,不加石黃或者不加砂,純粹的大紅袍是不能單獨成型的吧?
老趙說,能。
再怎么問,老趙就只是讓詞語在嘴里打轉轉,只說能。我知道,老趙的這個能,是留有余地的“能”,他可能是不想涉及大紅袍里加料的內容。
我問老趙,這是哪座山頭上的大紅袍料?
他憨厚地一笑,笑容里有著山里人的純樸,也透著那種走南闖北見過世面后的精明,只說是廣德的,具體的位置就不肯多吐一個字了。
我會意,不再追問。這是找礦人的飯碗,千淘萬淘出來的,輕易泄露了,自己還吃什么呢?紫砂礦料的復雜與神秘,由此可見一斑。
2
山里人家,地大,樹多,房子之間相距得遠。繞過一片地后,又看到一堆堆的土。老趙說,都是好泥料呢。每年起碼有50位練泥的老板從他這里拿料。他翻山越嶺,四下找泥,一年當中能轉手賣出3000噸左右的礦料。
老趙說,找礦料的、練泥的、做壺的、賣壺的,這個產業鏈當中就數找礦料的最辛苦,危險系數也大,掙得的錢卻是最少的。
有多苦呢?從前采紫砂泥,是拿命換。現在技術條件比以往先進了,難度系數降低了,但依然是件不容易的事。就說眼前這堆大紅袍,為了這點泥,他夜夜住在山腳下,天一亮就上山選料、找料,忙碌到天黑再下山。
“像這種高檔的泥選都是我自己動手。不能依靠工人動手的,他們不懂紫砂,大紅袍跟別的料不一樣,是夾在泥層中的,我去的這些礦山通常產的是燒琉璃瓦的料,價格與普通紫砂相比是極便宜的,每噸也就60元。大紅袍就夾在這些普通的礦層中,一點點細的一條線,細到只有10厘米左右的厚度。如果手腳毛毛糙糙的不知輕重,很容易就碰壞掉了。”
采礦找泥的苦,在從前不亞于行船、磨豆腐和打鐵。紅泥接近地表層,露天開采多些。而紫泥和綠泥埋藏很深,明代周高起《陽羨茗壺錄》中有“皆深入數十丈乃得”,明代吳梅鼎《陽羨茗壺賦》中有“若入淵兮百仞”。雖然老趙不是采礦的,但要從礦層中、石頭中找到好紫砂,也是不容易的事。
老趙是快50歲的人了,選起泥來仍然不輸年輕人。他說,從小吃苦長大的,不怕苦。每次出門,他都是獨自帶著洋鎬、榔頭、鐵釬等等各種各樣的工具上山,這些工具原先采礦時也會用到,現在科技發達,時代進步了,開礦采礦挖料都有大型機器。老趙作為一個選料找料的人,他習慣手上拿件家伙,心里踏實。老趙找料的動作既精細,又穩準狠,看過他找泥選料過程的人都說,他專注的樣子不同于平時跟人說話時的笑嘻嘻。削、刮、剝、砍、砸、撬、鑿這些都是老趙選泥時常用的動作。也有行內人質疑,說你是選料又不是挖礦開采料,有這么辛苦嗎?老趙笑笑,苦不苦,自己知道。
要找到好料,能吃苦只是身體上的事,還得專業,懂行,不斷學習,要跟得上形勢,要練出火眼金睛一樣的識砂辨砂的本領。這些年趙萬中在江西、安徽、浙江都找過礦,翻山越嶺、跋山涉水,平均每3年就得換一輛車,目前開的已是第6輛。有路沒路的地方,他都要去。
有人勸他,說你這樣多累,打幾個電話,委托別人把礦料送到家就行了。
老趙不依,他堅持自己去找,得自己站在大山腳下,親眼看到夾在一層層砂土中的礦料才行。但凡遇到好料,他會興奮,勞累頓時不見。但這種興奮的機會也是很難得,更多的時候,往往一出去就是20多天,一無所獲。
找礦這一行,老趙一做就是30多年。礦料有幾百種,判斷礦石的質量不能僅憑感覺,肉眼也只能看個大概,要燒出來才能最終判定能不能買。每次找到礦料后,他都是先拿個100斤,回來試燒,看成色不錯,再決定大量買進。燒出來的試片主要看色澤,看泥巴是否干凈,還要看后面是適合用球磨機粉碎,還是用普通機器粉碎等等。
對于泥料,從名稱、產地、泥性到配料,趙萬中都了然于胸,張口就來。他指著一塊看起來不起眼的泥說,“這是青泥,從靠近新疆那邊拉回來的,可以拼到紫泥里燒低溫壺。”泥料的特性千奇百怪,比如白麻子,價格不便宜,也不太容易找得到,其作用全在于它的顆粒,與別的泥料拼配在一起后,可讓燒成后的紫砂壺呈現出更明顯的砂質感。
泥練好后以什么價格賣出去?老趙嘿嘿地直笑,說這個不好講的,也講不好,要看跟什么泥料配的,各行有各行的門道,他保證出手的是好礦料就行了,礦料有問題是他的事,到了下一個環節,能練成什么質量、定多少價就全由下家自己負責了。
這個老趙,能說的他可以爽爽快快地說,不能說、不想說的,那是半絲口風都不肯漏一點氣的。
老趙懂配泥。他有配方,但藏在心里:“好多做壺的人都不會配泥,直接到賣泥料的商家門口,直接喊,我要朱泥,我要紫泥。付了錢,買了就走。練泥的人當中,也不是個個都懂泥,來買料時直接喊,我要紫泥,我要段泥,料子都是我配好了給他們拉走。現在有許多博士、碩士在做壺了,本科生做壺的那就更多了,有文化的人做起壺來應該比老輩的懂得更多,以后應當都能慢慢懂得配泥的。”趙萬中說時,綻開笑意。壺手如果懂泥,他作為提供礦料的人是開心的,與內行打交道,彼此都可以少走許多彎路。??
3
趙萬中1969年出生,中學畢業后,買了輛摩托車,零零散散地送些客人。從湖?送到丁山,5元錢送一個人。去掉油錢,每趟也就掙個兩三元。有一次拉了位丁山人,對方說我包下你的車,你開車拉著我,跟我上山一起去找泥。
去哪里找泥呢?去黃龍山,那時每噸礦料才幾十塊錢。有時也到外山去。趙萬中從此就天天跟著他在山上跑,他教會了趙萬中怎么看泥,什么是紫泥,哪種泥能掙到錢,而不是光往家里撿石頭泥巴。從零起步,到真正學到一點門道,趙萬中花了3年多的時間。每個山頭上的泥都不一樣,光泥土就有幾百種,且不說從中找到值錢的泥,能把這幾百種泥叫出名字來,都已經是了不得的本事了。當然,真正的好泥料并不是光憑眼睛看就能確定的,眼睛看只是第一步,所看到的第一眼不一定就是燒出來的樣子,只有經過窯燒后出現的效果才是真實的。好看的泥巴不一定好用,找礦料的人都懂這道理。
盡管經驗很足,但老趙并不回避他也有過“敗走麥城”。他說:“我這個年紀的人,雖然一直不停地在學習,但不懂的地方也不是沒有,大腦里空白的地方不少,要學的地方很多。”
他說起了前兩年發生的一件事。
在安吉的某座山上,他找到一種色澤發青的泥料。按照他的經驗,發青的泥料,應該是段泥,通常燒出來不是發白就是發黃。盡管心中有底,但做事周到的他還是照著慣例買了100斤回來。剛送到窯上試燒,門外就響起了汽車馬達聲,有老主顧來買料了,說要買黃皮段泥。老趙說,正好找到了新料,試片還沒燒出來呢。老主顧信任他,當然也是自信,說段泥嘛也是常規的泥料,翻不出什么新花樣來,再說你老趙也是江湖上走遠路的,不會看走眼的。老趙一聽這話,自然也是開心。
于是,兩人就憑著以往對泥料的經驗,做了這筆買賣,付款后,沒等著泥片試樣出窯,買家就拉走了一車的料。哪知,失手了,出窯后的試片,是紅色的,不是通常段泥的色彩。老趙懵了。至今,他也沒能找到這次失手的原因,只籠統地說,礦發生變化了噢。經不住我一再追問,他只好說,我也解釋不清了,可能只有地理學家才知道這個神秘的原因吧。我從他的話音里,聽到了某種懊惱,是那種做事認真的人因為偶爾一次失手而產生的無盡的失落。
“既然懂泥性,會配泥,又能找到好礦料,為什么不索性開家練泥坊呢?開展一條龍產業多好啊。”
“哪是這么簡單,如果我練泥的話,誰還來拿我的礦料呢?我把原先的主顧都變成了競爭對手,就沒有人跟我玩了。再說了,人在社會上走不能光想著自己做大做強,最根本的就是要讓跟你有聯系的每個人,都能吃上一個飽肚子,這樣我們自己也才是安全的,才能讓自己吃飯的日子更長久。不能因為能干,就通吃,這樣會把路都走絕了哇。”
現在的宜興,僅制作紫砂壺,大約每天要消耗掉30噸左右的紫砂泥料。1990年,權威地質勘探的結果是,宜興紫砂礦料的探明和保有儲量為90萬噸。2013年,市場上普通紫泥2000元每噸,底槽青泥2萬元每噸。到2021年,價格上漲十幾倍不止。如果還以“本山”“外山”來打價格戰,或者一味排擠“外山”泥,不承認“外山”泥對繁榮紫砂業所帶來的價值,那么紫砂將只能成為供奉在少數人案頭的文物。
“對宜興人來說,泥料不存在缺失的問題。市場根本不必恐懼。”這句話沒錯,但前提是,之所以宜興人不必擔心紫砂料的儲備,是因為有趙萬中這類人的辛苦勞作,他們從外山源源不斷輸送礦石到宜興大大小小的練泥工坊。
如果沒有趙萬中他們這些人走出宜興去找礦料,宜興十幾萬紫砂行業的從業人員就沒有飯吃。且不說黃龍山現在封山了,就是以前敞開了開采,因為設備和技術的原因,一天的開采量也只有30噸上下,只夠滿足當時的用量。稍微動動腦筋也能想明白,即使有些人號稱自己家里儲存了當年的老料,又能存多少呢?
“嚴格來說,配方就那幾種,只要愿意去學,都能學會。但有幾個人肯像趙萬中這樣下苦功夫去學的?那些做壺的人一味說自己的泥料是黃龍山的,我寧愿相信他們是不懂,而不是為了賣個好價格故意撒謊。”行業內一名知情人說。
趙萬中說:“如果我跟別人說我這是黃龍山的料,那我不是要賺大發了。但那是撒謊。我不說這是黃龍山的料,那不明擺著就是外地的嘛,很直白,都知道的哇。”
“我找礦料不是為了發大財,錢不是那么好賺的,好賺的錢也輪不到我啊,首先是要讓自己開心,所以我天天在路上,看看山,看看水,也是享受,十天半個月的找不到礦,我也就犯不著生氣。”趙萬中說,每年都有新開的礦,也有關掉的礦,所以光住在家里不管用的,那樣怎能知道哪座山上的礦關了還是停了?三天兩頭就得出門去找好一點的料。
他家里現在還存著一萬多噸的礦石,如果僅僅滿足于過日子,早就夠了。對于自己這樣長年累月在山里刨食的人來說,需要花大錢的地方不多。趙萬中說到這些時,少見的不茍言笑,每一分錢都得來不易,那不是錢,是一個個滴汗的日子。?
冬天到了。趙萬中減少了出門的次數。每日里泡壺野山茶,換著不同角度看著積攢下的石頭,幫著妻子做做家務。有時抓起南瓜干喂雞,擔心雞被凍著,便用熱水把南瓜干浸一下再給雞吃。他說,他家的雞從來都不肯睡在雞窩,都是飛到桂花樹上睡,那些雞還有野性。他沒考慮到,有野性的雞應該不喜歡被熱水浸過的食物。無論是雞或者別的生命,一旦習慣了使用火,就脫離了野性。萬物都是這樣,紫砂,一經淬火,山野之性盡失,宛如重生,浮躁之氣全然去盡,閑寂之中安然度過一生。
韓麗晴: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著有作品多部。散文集《意思》獲第七屆江蘇省紫金山文學獎。
編輯??? 沈不言?? 78655968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