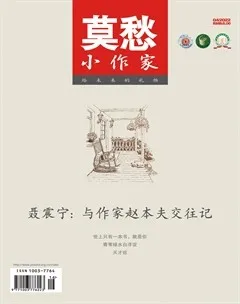我家的“文物”
我家有一架“上海牌”鋼琴,從我有記憶以來(lái)便一直佇立在琴房的一隅。琴的外立面上有很多深淺不一的劃痕,還落了厚厚的一層灰。掀開(kāi)琴蓋,里面本該潔白的琴鍵都已泛黃,黑鍵也早已沒(méi)了光澤,摸上去就像被砂紙打磨過(guò)的一樣,音也不大準(zhǔn)了。
據(jù)父親說(shuō),這架琴是20世紀(jì)50年代購(gòu)置的,年齡比他還大嘞!當(dāng)時(shí)我們國(guó)家沒(méi)法自己生產(chǎn)鋼琴,說(shuō)是“上海牌”,實(shí)際上只有外面的木殼子是由上海鋼琴?gòu)S生產(chǎn),內(nèi)芯則是從德國(guó)原裝進(jìn)口來(lái)的。買(mǎi)時(shí)花了一千三百多元錢(qián),在那個(gè)年代可是個(gè)天大的開(kāi)支。祖母是大學(xué)的聲樂(lè)老師,有了鋼琴后,在教學(xué)上方便了許多。后來(lái)父親也是坐在這架鋼琴前開(kāi)啟了他的音樂(lè)生涯,走上了音樂(lè)道路。
然而到了“文革”,這架鋼琴遭遇了滅頂之災(zāi)。當(dāng)時(shí)全國(guó)都在“破四舊”和批判“崇洋媚外”,鋼琴不僅是典型的“崇洋媚外”,還是“資產(chǎn)階級(jí)生活方式”的一個(gè)象征。祖父母商量了好久,為了不惹禍上身,決定把琴賣(mài)掉。他們通過(guò)各種渠道推銷(xiāo),竟連一個(gè)愿意買(mǎi)的人都沒(méi)有。祖父母把鋼琴的價(jià)格越降越低,一直降到了40塊錢(qián),還是無(wú)人問(wèn)津。祖父把心一橫,對(duì)祖母說(shuō):“這鋼琴,不賣(mài)也罷!再說(shuō)了,你是學(xué)音樂(lè)的,兒子也要練琴,家中總歸還是要有一架鋼琴的。”就這樣,勉強(qiáng)留住的這架琴,竟也不知不覺(jué)地一直用到了我出生。
我從4歲開(kāi)始在父親手把手的指導(dǎo)下學(xué)琴,那老舊的鋼琴又煥發(fā)出了第二春。學(xué)琴的過(guò)程無(wú)疑是艱辛的,琴鍵上沾滿(mǎn)了我的汗水與淚水。我也經(jīng)常哭鬧著說(shuō)不想再練了。可每當(dāng)我觸摸著譜架上那道因長(zhǎng)年累月架譜而留下的印記時(shí),每當(dāng)我看著琴身上歲月留下的刮痕時(shí),每當(dāng)我回想起這架琴坎坷的身世時(shí),我仿佛看見(jiàn)坐在琴前苦練的父親,看見(jiàn)在動(dòng)蕩年代里徹夜不眠商量這架琴歸屬的祖父母。想到這些,我就會(huì)重新整理好自己的情緒,抹干眼淚,重新扎進(jìn)五線(xiàn)譜中……
現(xiàn)在,家中已經(jīng)換了新琴,但我們依然收藏著那架老鋼琴。雖然它已黯淡無(wú)光,但在我心中卻光輝燦爛;雖然它的聲音已不再明亮清澈,但在我心中卻是如“大珠小珠落玉盤(pán)”一般美妙動(dòng)聽(tīng)。
劉秋池:江蘇省南京市金陵匯文學(xué)校初三(15)班學(xué)生
指導(dǎo)老師:潘瑞青
編輯 木木 69137296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