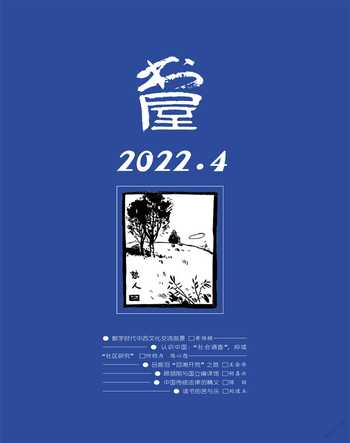徐志摩與民國(guó)舊詩(shī)人的往來(lái)
潘建偉
趙毅衡先生寫過(guò)一本很有趣又很有啟發(fā)的書,名為《對(duì)岸的誘惑》,以個(gè)案的形式敘寫了二十世紀(jì)上半葉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四十四位人物,其中第一篇寫的就是徐志摩。趙先生在這篇文章中提到,徐志摩留學(xué)英倫時(shí)所結(jié)交的皆是當(dāng)時(shí)的著名人物,比如曼殊菲爾、威爾斯、康拉德等作家,墨雷等批評(píng)家,還有桂冠詩(shī)人布里基思,當(dāng)時(shí)知識(shí)界的領(lǐng)袖狄金森,社會(huì)主義思想家拉斯基等。他總結(jié)道:“現(xiàn)代中國(guó)文人,在西洋活得如魚得水的,徐志摩恐怕是一枝獨(dú)秀。”這話說(shuō)得一點(diǎn)不過(guò)分。筆者不妨模仿一句:“五四”新文人,在舊文學(xué)界活得如魚得水的,徐志摩恐怕也是一枝獨(dú)秀。
作為中國(guó)現(xiàn)代詩(shī)歌星空中一顆最耀眼的明星,徐志摩總是受到萬(wàn)眾矚目。但當(dāng)代幾乎所有的徐志摩傳記,包括梁錫華的《徐志摩新傳》、趙遐秋的《徐志摩傳》、宋炳輝《新月下的夜鶯:徐志摩傳》以及韓石山的《徐志摩傳》等較著名的在內(nèi),都很少提到他與民國(guó)舊詩(shī)人的往來(lái)。韓石山的《徐志摩傳》特列“交游”一卷,可是其中所述人物,除了梁?jiǎn)⒊⒄率酷撆c吳宓之外,未見當(dāng)時(shí)舊詩(shī)壇人物的蹤跡。根據(jù)筆者近些年所搜集的文獻(xiàn)資料,徐志摩所交往的舊詩(shī)人中至少有如下二十余位:陳三立、鄭孝胥、江瀚、夏敬觀、李宣龔、李宣倜、汪辟疆、黃濬、陳方恪、汪精衛(wèi)、朱劍芒、陳柱、梁?jiǎn)⒊⒄率酷摗清怠㈥愘琮垺铉婔恕⒉芙?jīng)沅、林開謩、葉恭綽、陳中凡、謝無(wú)量等。這些人物中,陳三立、鄭孝胥、江瀚、夏敬觀、李宣龔、李宣倜、汪辟疆、黃濬、陳方恪都是清末以來(lái)最大的舊詩(shī)流派即同光派的主要詩(shī)人,汪精衛(wèi)、朱劍芒、陳柱是南社詩(shī)派的著名人物,梁?jiǎn)⒊峭砬逶?shī)界革命派的代表,吳宓是學(xué)衡派的代表,章士釗則是甲寅派的代表,其他諸如陳夔龍、楊鐘羲、曹經(jīng)沅、林開謩、葉恭綽、陳中凡、謝無(wú)量在當(dāng)時(shí)舊詩(shī)壇也都很有影響。可以說(shuō),中國(guó)現(xiàn)代新詩(shī)人中,沒(méi)有哪一位能像徐志摩那樣,與舊詩(shī)壇保持著如此廣泛而又友好的往來(lái)。比如徐志摩曾去鄭孝胥家觀其作字,一起聚餐,并贈(zèng)送過(guò)鄭氏《新月》雜志。
徐志摩稟賦卓異,個(gè)性溫和,胸?zé)o城府,且經(jīng)濟(jì)富足,故從無(wú)自卑心理,面對(duì)西方人如此,面對(duì)中國(guó)舊詩(shī)人也同樣如此。更重要的是,他的格律體新詩(shī)擺脫了早期白話詩(shī)散文化、淺俗化的弊病,融匯了中西詩(shī)歌的特長(zhǎng),因而獲得了當(dāng)時(shí)廣泛的贊譽(yù)。當(dāng)代人很難想象,一百年前新詩(shī)在受到光輝的西方詩(shī)傳統(tǒng)與偉大的古典詩(shī)傳統(tǒng)雙重壓力下所遇到的窘境。錢鍾書在《圍城》中說(shuō)過(guò):“只有做舊詩(shī)的人敢說(shuō)不看新詩(shī),做新詩(shī)的人從不肯說(shuō)不懂舊詩(shī)的。”這句話未必只是“小說(shuō)家言”。新詩(shī)從誕生以來(lái)就飽受爭(zhēng)議,直到徐志摩出現(xiàn),才逐步受到舊詩(shī)人的認(rèn)可。陳三立對(duì)新詩(shī)一向不過(guò)目,卻常讀徐志摩詩(shī),并稱其“似頗有線裝書氣味”(方瑋德《再談志摩》)。吳宓對(duì)于早期新詩(shī)不予認(rèn)可,而對(duì)徐志摩卻大為贊賞,稱其“依新依舊共詩(shī)神”,并將其與雪萊并論,認(rèn)為“使徐君而今不死,二人者必將篤志毅力,上企乎但丁,可知也”(《挽徐志摩君》)。林庚白則在其《孑樓詩(shī)詞話》中稱贊過(guò)徐志摩的新詩(shī)善于用韻。故而,曹聚仁總結(jié)說(shuō):“新詩(shī)人最為舊詩(shī)人所冷淡,只有徐氏,才為舊人所傾倒。”(《文壇五十年》)卞之琳也說(shuō):“過(guò)去許多讀書人,習(xí)慣于讀中國(guó)舊詩(shī)(詞、曲)以至讀西方詩(shī)而自己不寫詩(shī)的(例如林語(yǔ)堂等),還是讀到了徐志摩的新詩(shī)才感到白話新體詩(shī)也真像詩(shī)。”(《〈徐志摩選集〉序》)徐志摩的詩(shī)之所以獲得了廣泛的贊譽(yù),大抵由于他所實(shí)踐的“新格律體”的確在新詩(shī)與舊詩(shī)之間架起了一座不可缺少的橋梁。
徐氏逝世后,既有新詩(shī)人的深情追憶,也有舊詩(shī)人的深切哀悼。朱劍芒有《吊徐志摩》二詩(shī),其一云:“眼底崎嶇世路窮,詩(shī)人例合葬天空。他時(shí)倘化遼東鶴,應(yīng)泣關(guān)山戰(zhàn)血紅!”其二云:“化身鵬鳥滿天飛,少小凌云志不微。豈料一飛成羽化,人間從此不飛歸!”(載1931年《紅玫瑰》第七卷第二十八期)汪辟疆有《我所認(rèn)識(shí)的徐志摩》一文,回憶了1925年與徐氏相識(shí)的經(jīng)過(guò),高度評(píng)價(jià)了他的人格與文學(xué),并以流暢雋永的白話文動(dòng)情地說(shuō):“他只把他的身心交給大自然的神秘。他的心靈,也就如朝曦初出的園林的滿園的花,在曉風(fēng)里忻快的幽微的顫動(dòng)著。他那一種不出口的思想,任何分布在詩(shī)歌和散文和言談中,隨手拈出,自然使讀得到聽得到的人們,隨處都是妙諦。他的詩(shī)和散文的人格是一致的。像是一棵孤芳皎潔的松樹,他是托根在高山峻嶺的土地,上面發(fā)出清脆可聽的濤聲,永遠(yuǎn)使路上的行人感覺(jué)到一種和諧而美妙的調(diào)子。”(載1932年《讀書雜志》第二卷第九期)引得有點(diǎn)長(zhǎng)了,但被稱為“江西詩(shī)派殿軍”的汪辟疆,用如此美妙的白話文回憶一位新詩(shī)人,本身就是現(xiàn)代文學(xué)史中一件富有意義的事。可惜,程千帆在編《汪辟疆文集》時(shí)沒(méi)有將此文收錄進(jìn)去,于是我們就只知道一位“力矯時(shí)弊,以古為則”的汪辟疆,而不知道他與新文學(xué)的這段因緣了。由于其他原因,李宣倜、黃濬與徐志摩的關(guān)系尤其不為人所知,李氏的七律《哀志摩》與黃氏的五古《悲志摩》鮮見論者提及。陳從周《徐志摩年譜》文末所開列的悼念名單多達(dá)六十余人,卻仍不見李宣倜與黃濬之名。但作為徐志摩與當(dāng)時(shí)舊詩(shī)壇的一段交往,這兩首詩(shī)對(duì)于補(bǔ)充徐氏的生平經(jīng)歷,仍有其重要的價(jià)值。下面筆者試對(duì)此二詩(shī)作一些較為詳細(xì)的解讀。李宣倜《哀志摩》云:
橐筆來(lái)窺屋漏痕,哦詩(shī)亦欲睨韓溫。蕩胸碧漢捐枯骨,流夢(mèng)紅墻咽斷魂。風(fēng)雨凄凄悲子野,江潭渺渺念逢原。才長(zhǎng)命短千秋恨,螻蟻烏鳶豈足論。
所引詩(shī)收入李宣倜的詩(shī)集《蘇堂詩(shī)拾》。詩(shī)在入集之前已先行刊于北平晨報(bào)社編輯的《北晨學(xué)園哀悼志摩專號(hào)》(1931年12月),正文中作者署名“釋戡”(“釋戡”為李宣倜的字)。刊物版與詩(shī)集版異文甚多,引文第三句的“碧漢”作“碧落”,第四句的“流夢(mèng)”作“入夢(mèng)”,“紅墻”作“紅婪”(“紅婪”不好理解,當(dāng)為錯(cuò)訛),第七句的“才長(zhǎng)”作“寸長(zhǎng)”(“寸長(zhǎng)”不好理解,當(dāng)為錯(cuò)訛)。此詩(shī)首聯(lián)談徐氏之詩(shī)才高妙,第一句中“屋漏痕”原為書法術(shù)語(yǔ),謂落筆不一貫直下而如破屋墻壁間雨水之蜿蜒漏痕,筆畫自然而凝重;第二句中“韓溫”指韓愈與溫庭筠,所謂“睨韓溫”謂徐氏之詩(shī)不讓古代大詩(shī)人。頷聯(lián)第一句“蕩胸碧漢捐枯骨”指徐氏殉于空難一事;第二句“流夢(mèng)紅墻咽斷魂”當(dāng)指佳人之夢(mèng)魂縈繞、悲傷難抑。頸聯(lián)第一句之“子野”指晉人桓伊,不可能是裴子野或張先:桓伊性謙情深,善音樂(lè),尤擅作挽歌;第二句之“逢原”指宋人王令,此人詩(shī)才雄奇,然年未及三十而卒。前一句感徐氏多情善吟,后一句哀徐氏才高早逝。尾聯(lián)第一句承前,再次感嘆徐氏早逝而成千秋之恨;第二句贊賞徐氏雖早逝,卻絕非螻蟻烏鳶茍且之輩可以相提并論。
黃濬的《悲志摩》云:
識(shí)君始昔冬,一面意已熟。飲冰更稱君,可人溫如玉。滬濱雖數(shù)逢,立語(yǔ)惜匆促。今年屢見過(guò),排闥不有速。索我角花箋,贈(zèng)吾新歌曲。手持猛虎詩(shī),泥我再三讀。狀其威贙勢(shì),破彼音律梏。嗟吾若有會(huì),欲步又自恧。問(wèn)君南行期,答以旬往復(fù)。御風(fēng)夸泠然,何意禍所伏。魯山皆巖巖,誰(shuí)遣以頭觸?梁林久生天,邀約殆所夙。知君終不憾,八表云相逐。文章千古事,吾輩真一粟。射侯各不同,永愛(ài)清如鵠。適之最悲君,短句極凄篤。行行雪獅子,垂淚亦蹙跼。豈知霄漢上,微笑方張目。笑此地上人,跂行待沉陸。
此詩(shī)未收入黃濬《聆風(fēng)簃詩(shī)》,而刊于北平晨報(bào)社《北晨學(xué)園哀悼志摩專號(hào)》(刊物上詩(shī)題為《哀志摩》)。曹聚仁《筆端》亦收錄全詩(shī),略有異文。今據(jù)兩個(gè)版本,略疏詩(shī)義,擇善而從。第一聯(lián)首句刊物版作“識(shí)君始苳苣”,不通;《筆端》作“識(shí)君始昔冬”,較順。今從《筆端》版。黃濬與徐志摩之間相識(shí)較晚,鄭孝胥的日記1931年2月26日就記載:“約至東興樓午飯,晤楊子勤、江叔海、胡適之、徐志摩、李釋戡、黃秋岳、吳達(dá)泉。”其中的“黃秋岳”就是黃濬。第二聯(lián)第一句“飲冰”是梁?jiǎn)⒊诙洹翱扇藴厝缬瘛笔橇簡(jiǎn)⒊瑢?duì)徐氏的評(píng)價(jià)。第三、四聯(lián)云“滬濱雖數(shù)逢,立語(yǔ)惜匆促。今年屢見過(guò),排闥不有速”,表明黃濬與徐志摩在1931年往來(lái)過(guò)多次,且兩人認(rèn)識(shí)不久即很熟悉。第五聯(lián)首句“索我角花箋”是指徐志摩曾向黃濬討要過(guò)“角花箋”一事,在《花隨人圣庵摭憶》記載道:“其間差可紀(jì)者,怡邸有角花箋一種,特大方雅妙,此箋晚近真者已罕覯,予于民國(guó)初年,從德寶齋得數(shù)百?gòu)垼褚焉⑹员M,前數(shù)年徐志摩曾來(lái)索,贈(zèng)以少許,其后挽詩(shī)中仍及之。”次句“贈(zèng)吾新歌曲”自然是指徐氏贈(zèng)黃氏詩(shī)集,且根據(jù)第六聯(lián)首句“手持猛虎詩(shī)”,可知這部詩(shī)集當(dāng)是《猛虎集》。第七、八兩聯(lián)即道及徐氏的新詩(shī)創(chuàng)作,并自愧無(wú)法唱和。以上均是回憶兩人的來(lái)往經(jīng)過(guò),并順及徐氏之新詩(shī)。從第九聯(lián)“問(wèn)君南行期,答以旬往復(fù)”到第十五聯(lián)“射侯各不同,永愛(ài)清如鵠”,是悲徐氏之亡于空難,并高度評(píng)價(jià)徐氏的文學(xué)成就與人格品性。第十六聯(lián)提到胡適的悼亡短詩(shī),此詩(shī)當(dāng)為《獅子——悼志摩》。徐志摩曾住過(guò)胡適家,“獅子”是他最喜歡的貓兒。所謂“短句極凄篤”,亦可知黃濬對(duì)新詩(shī)并不排斥。第十七聯(lián)刊物上作“行行雪獅子,垂淚亦蹙跼”,《筆端》作“行行云獅子,垂淚亦蹐跼”。“雪獅子”是指徐氏喜歡的這只貓兒毛膚雪白,“云獅子”就不好解,當(dāng)以刊物版為是。“蹙跼”與“蹐跼”的意思相近,是從胡適的“獅子踡伏在我的背后,/軟綿綿的他總不肯走”兩句化出,暫從刊物版。最后兩聯(lián)表達(dá)了自己的憂患之情。曹聚仁評(píng)價(jià)此詩(shī):“悲感渲染,使人低徊不能自已。”
李宣倜與黃濬這兩個(gè)人,一個(gè)后來(lái)當(dāng)了汪偽政府的陸軍部政務(wù)次長(zhǎng),一個(gè)因泄露國(guó)府最高軍事機(jī)密而被處以極刑,他們的詩(shī)名也就漸漸被淹沒(méi)。但從這兩首悼亡詩(shī)中可以看到,民國(guó)時(shí)期的新舊詩(shī)壇絕不是兩個(gè)相互不通聲氣的世界,舊詩(shī)人并未一味反對(duì)新詩(shī),新詩(shī)人也未切斷與舊詩(shī)壇的聯(lián)系。從徐志摩與舊詩(shī)人的往來(lái)中,我們意識(shí)到“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dòng)以后的詩(shī)壇確實(shí)是一種“新舊交織”的狀態(tài),當(dāng)時(shí)的新詩(shī)人如胡適、周作人、沈尹默、俞平伯、聞一多、朱自清、郭沫若、梁實(shí)秋、戴望舒、馮至、梁宗岱等都與舊詩(shī)壇保持著一定的聯(lián)絡(luò),只不過(guò)在徐志摩那里,這個(gè)特點(diǎn)顯得尤其突出。我們當(dāng)有必要擺脫文學(xué)史敘事的束縛,重新回到歷史現(xiàn)場(chǎng),從而更為全面地看到那時(shí)詩(shī)壇的多元性與復(fù)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