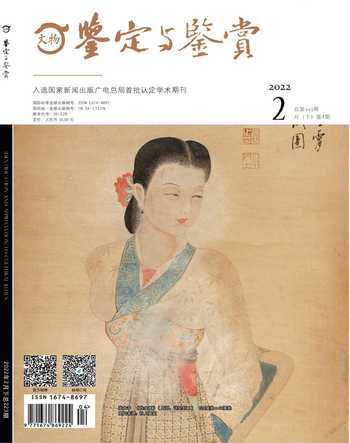對(duì)國(guó)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shè)與發(fā)展的幾點(diǎn)思考
袁磊
摘 要:建設(shè)國(guó)家考古遺址公園是大型遺址保護(hù)利用的新模式,如何做好川東地區(qū)已發(fā)現(xiàn)的巴文化遺址保護(hù)和利用工作,成為當(dāng)下四川文物工作中的一項(xiàng)重要任務(wù)。城壩遺址的發(fā)現(xiàn)為川東地區(qū)巴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寶貴材料。然而,當(dāng)前城壩遺址還存在著資源調(diào)查不足、力量整合不足、管理力量薄弱、展示利用欠缺等一些問題,要根據(jù)城壩遺址現(xiàn)有狀況制定有效的方案,形成有效的規(guī)劃設(shè)計(jì)方案,才能讓城壩考古遺址公園得到最大的保護(hù)利用。
關(guān)鍵詞:考古遺址公園;城壩遺址;保護(hù);利用
DOI:10.20005/j.cnki.issn.1674-8697.2022.04.052
2009年,國(guó)家文物局印發(fā)《國(guó)家考古遺址公園管理辦法(試行)》,提出了“國(guó)家考古遺址公園”這一概念,即“以重要考古遺址及其背景環(huán)境為主體,具有歷史文化意義及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考古遺址保護(hù)和展示方面具有全國(guó)性示范意義的特定公共空間”①。2010年,國(guó)家文物局公布了首批12處國(guó)家考古遺址公園和23處國(guó)家考古遺址公園單位。目前,國(guó)家文物局已陸續(xù)宣布對(duì)36個(gè)國(guó)家考古遺址公園進(jìn)行評(píng)估,批準(zhǔn)建立67個(gè)國(guó)家考古遺址公園。2018年,國(guó)家文物局發(fā)布《國(guó)家考古遺址公園發(fā)展報(bào)告》,進(jìn)一步明確了國(guó)家遺跡的定位,即“突出國(guó)家屬性、堅(jiān)持價(jià)值優(yōu)先、弘揚(yáng)優(yōu)秀文化、促進(jìn)融合發(fā)展”②。國(guó)家考古遺址公園的立項(xiàng)和建設(shè),進(jìn)一步完善了我國(guó)文物保護(hù)管理體系和制度,創(chuàng)新了大遺址保護(hù)與利用的發(fā)展模式和途徑,豐富了國(guó)內(nèi)外考古遺址保護(hù)理論體系。隨著四川考古事業(yè)的蓬勃發(fā)展,四川已有3處遺址公園被公布為國(guó)家考古遺址公園—三星堆國(guó)家考古遺址公園、金沙國(guó)家考古學(xué)遺址公園及邛窯考古遺址公園。而在廣袤的四川平原上,除了這3處極具價(jià)值的遺址遺跡外,在大巴山背斜地帶的川東地區(qū)還有著可與三星堆、金沙遺址相比擬的巴文化遺址。本文以城壩遺址為例,就如何保護(hù)利用好巴文化遺址,進(jìn)而促進(jìn)考古遺址公園建設(shè)與發(fā)展做了一些思考。
1 城壩遺址的發(fā)現(xiàn)與價(jià)值
1.1 城壩遺址概況
城壩遺址位于四川達(dá)州市渠縣土溪鎮(zhèn)城壩村及周邊村社,總面積約550萬(wàn)平方米,是構(gòu)成川東巴文化遺址群的又一處重要的聚落中心和古城遺址。自1979年以來(lái),城壩遺址不斷涌出重要的考古發(fā)現(xiàn)成果。經(jīng)過歷次考古勘探,得知遺址地下保存有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墓葬遺存和大量?jī)蓾h、六朝、兩晉時(shí)期墓葬和生活遺存。而再次引起人們重視則是2016年考古發(fā)掘出的一口漢井以及出土的數(shù)枚“宕渠”文字瓦當(dāng),這印證了史籍記載宕渠所在地的真實(shí)性。公元前316年,秦國(guó)滅巴國(guó),設(shè)巴郡,置宕渠縣(隸巴郡),后以巴王為蠻夷君長(zhǎng)統(tǒng)帥各部族,借以削弱巴郡殘余勢(shì)力,使川東地區(qū)的巴文化在與中原文化的交流融合過程中得以留存和延續(xù)。至漢初,該地區(qū)在某些方面仍然保留著巴文化面貌,甚至在西漢中期以后漢文化面貌已經(jīng)確立的大背景下,仍然表現(xiàn)了巴、楚、秦、蜀的多元文化特點(diǎn),有的還在吸收外來(lái)文化基礎(chǔ)上形成了具有濃厚地方特色的文化面貌,有別于中原地區(qū)的葬喪習(xí)俗。除了發(fā)現(xiàn)了“宕渠”文字瓦當(dāng)以外,還發(fā)掘了津關(guān)遺址,并在津關(guān)遺址中出土了數(shù)百枚竹木簡(jiǎn)牘,有文字的木牘上百枚,且內(nèi)容豐富,這也使城壩遺址在2018年中國(guó)考古學(xué)大會(huì)上被評(píng)為“田野考古一等獎(jiǎng)”。
1.2 城壩遺址歷次考古發(fā)掘及重要遺跡遺物
1.2.1 歷次考古發(fā)現(xiàn)
20世紀(jì)70年代以來(lái),文物部門通過文物征集、田野調(diào)查、文物普查等方式,城壩遺址收藏了大量珍貴的戰(zhàn)國(guó)、秦漢文物,包括一些具有典型巴蜀文化特征的青銅器,如虎紐于、青銅鉦、青銅罍、青銅佛缶、編鐘、劍、戈、鉞等。在此期間,為了支持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和基礎(chǔ)建設(shè),文物部門還搶救了一批漢代磚室墓、西漢木棺墓和巴蜀文化坑墓。
至20世紀(jì)80年代末期,全國(guó)開展第二次不可移動(dòng)文物普查,發(fā)現(xiàn)此處有大面積遺址。但直到1992年,重慶市博物館才對(duì)該遺址進(jìn)行試掘,發(fā)掘面積小,出土器物也少,不能更好地說(shuō)明問題。
2005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根據(jù)“二普”的資料和先前試掘的情況,積極向國(guó)家文物局申請(qǐng)主動(dòng)發(fā)掘。這也是文物部門對(duì)城壩遺址的首次正式發(fā)掘,此次發(fā)現(xiàn)了大量戰(zhàn)國(guó)晚期至秦漢時(shí)期的遺存,同時(shí)還對(duì)郭家臺(tái)城址進(jìn)行了初步調(diào)查。根據(jù)上次調(diào)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決定對(duì)郭家臺(tái)進(jìn)一步發(fā)掘。③
2013年,通過對(duì)郭家臺(tái)城址東城墻進(jìn)行解剖,加之分析城墻構(gòu)造與土質(zhì),發(fā)現(xiàn)東城墻經(jīng)過兩次夯筑的跡象。④
為了進(jìn)一步探索川東地區(qū)的巴文化,了解巴文化與漢文化融合的過程,以及秦漢帝國(guó)對(duì)西南地區(qū)的開發(fā)和管理,2014年至2018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渠縣歷史博物館連續(xù)5年對(duì)城壩遺址進(jìn)行了系統(tǒng)的考古調(diào)查、勘探和發(fā)掘,總面積達(dá)4000平方米,清理出包括墓葬、水井、灰坑、城墻、城門、房址、溝、窯址等在內(nèi)的各類遺跡445處,出土了包括銅鉦、銅壺、銅于、銅印章、陶罐、瓦當(dāng)、簡(jiǎn)牘、式盤在內(nèi)的戰(zhàn)國(guó)晚期至魏晉時(shí)期遺物千余件。⑤
2019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對(duì)城壩遺址進(jìn)行第6次考古發(fā)掘,在遺址的西北部首次發(fā)現(xiàn)了4座東周墓葬,其中3座保存完好,1座只保存了1件陶罐。墓葬是一個(gè)狹長(zhǎng)的土坑墓。大型墓葬的葬具是船棺,墓主人為屈肢葬或二次葬。在3座保存較好的墓葬中有1座墓葬規(guī)模較大,墓室底部一側(cè)設(shè)有器物坑,內(nèi)放置青銅器11件。該墓出土器物較多,包括銅器、陶器、玉器等70余件/套,其中銅器主要有浴缶、缶、于、編鐘、鉦、鈲、匜、劍、鍪、釜、釜甑、印章、龜?shù)龋掌髦饕獮楣蕖⒍梗袷鲃t有龍紋玉佩、瑪瑙環(huán)、蜻蜓眼琉璃珠、料珠等。⑥
1.2.2 重要遺存
①西城門。西城門位于郭家臺(tái)城址的西南部,東西向,垂直開在城墻上。經(jīng)過清理發(fā)掘,發(fā)現(xiàn)西城門為三次修筑。早期城門與早期城墻同時(shí)期,僅存門檻石;中期城門現(xiàn)在能看到的是石地栿、木地栿和排叉柱孔;晚期城門疊加在中期城門之上,清理時(shí)發(fā)現(xiàn)兩側(cè)墻磚倒塌堆積在城門的上部。
②津關(guān)。津關(guān)遺址位于城壩遺址鄰近渠江的二級(jí)臺(tái)地上,地勢(shì)平坦。從出土文物來(lái)看,津關(guān)應(yīng)為西漢到魏晉時(shí)期的一處水陸關(guān)口遺址。
1.2.3 重要文物
①虎紐于。于于2019年M45中出土,紐為一只昂首前傾的猛虎,虎身鑄刻有虎斑紋。同時(shí)出土了銅鉦、銅編鐘、銅缶、銅方壺等70多件器物。于作為樂器一般與銅鼓、銅鐘、銅鉦一起出現(xiàn),用于戰(zhàn)前鼓舞士氣。虎紐表現(xiàn)巴人崇虎的信念。
②“宕渠”文字瓦當(dāng)。“宕渠”瓦當(dāng)出土于郭家臺(tái)城址內(nèi),陽(yáng)文隸書豎排“宕渠”二字。“宕渠”瓦當(dāng)?shù)某霈F(xiàn),證明了城壩遺址應(yīng)為秦漢至魏晉時(shí)期的宕渠,宕渠城是秦滅巴蜀之后的賨人的核心。瓦當(dāng)文字中很少出現(xiàn)縣名,瓦當(dāng)?shù)难b飾特征進(jìn)一步表明,它一方面接受了中國(guó)文化的影響,另一方面又保留了自己的地方特色。
③竹木簡(jiǎn)牘。遺址共出土竹木簡(jiǎn)牘200余件,主要發(fā)現(xiàn)于郭家臺(tái)城址內(nèi)的水井、窖穴以及城外的津關(guān)。主要有簡(jiǎn)、牘、楬等,其內(nèi)容有書信、爰書、戶籍、薄書、識(shí)字課本、九九乘法表、習(xí)字簡(jiǎn)等。城壩遺址竹木簡(jiǎn)牘的出現(xiàn),是繼青川秦墓木牘和老官山漢墓簡(jiǎn)牘之后四川地區(qū)又一處重要考古發(fā)現(xiàn),不僅如此,這批簡(jiǎn)牘還提供了新的簡(jiǎn)牘形制和書寫方式,為簡(jiǎn)牘學(xué)研究提供了新的實(shí)物資料,對(duì)于研究簡(jiǎn)牘史具有重要參考價(jià)值。
1.3 城壩遺址的重要價(jià)值
城壩遺址是目前發(fā)現(xiàn)的川東地區(qū)分布面積最大、保存最好、內(nèi)涵最為豐富的晚期巴文化中心遺址之一,是嘉陵江流域晚期巴文化的核心區(qū)域,為嘉陵江流域古代文化的發(fā)展序列和川東古文化的分區(qū)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
1.3.1 歷史價(jià)值
經(jīng)過發(fā)掘,發(fā)現(xiàn)了從戰(zhàn)國(guó)中晚期到六朝時(shí)期的遺址,通過對(duì)遺址、遺址環(huán)境、出土文物的研究,反映了當(dāng)時(shí)當(dāng)?shù)厣a(chǎn)、生活的情狀,對(duì)研究我國(guó)古代巴地文化形態(tài)和經(jīng)濟(jì)狀況具有重要意義。特別是“宕渠”文字陶瓦當(dāng)明確了該城址的性質(zhì),印證了秦漢時(shí)期宕渠縣所在地。而出土的大量簡(jiǎn)牘,作為兩千多年前地方機(jī)構(gòu)遺留下來(lái)的文字材料,“宕渠”文字陶瓦當(dāng)對(duì)于了解漢代城壩遺址的性質(zhì)、縣鄉(xiāng)行政機(jī)關(guān)的運(yùn)作以及當(dāng)?shù)氐纳鐣?huì)歷史狀況具有重要的學(xué)術(shù)意義。這些簡(jiǎn)牘和瓦當(dāng)?shù)陌l(fā)現(xiàn)證明,秦漢時(shí)期建立了郡縣來(lái)有效地管理西南地區(qū),為探討秦漢時(shí)期西南地區(qū)的開發(fā)、經(jīng)營(yíng)和管理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物質(zhì)基礎(chǔ)。城壩遺址反映了戰(zhàn)國(guó)晚期至兩晉時(shí)期川東地區(qū)考古學(xué)文化的特點(diǎn)和發(fā)展序列,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其地域文化的復(fù)雜性,為進(jìn)一步探討秦漢帝國(guó)對(duì)西南地區(qū)的管理及其地方行政體制的建設(shè)提供了重要的資料。
1.3.2 科學(xué)價(jià)值
從夯筑技術(shù)來(lái)看郭家臺(tái)城墻,其采用了較為成熟的板筑技術(shù),與四川地區(qū)秦漢時(shí)期以來(lái)城墻的堆筑技術(shù)截然不同。城壩遺址出土眾多青銅兵器,表明巴人熟練掌握了青銅合金成分比例,其中青銅劍上的虎斑紋工藝,在同時(shí)期其他文化中未曾見過。
1.3.3 藝術(shù)價(jià)值
城壩遺址出土的青銅兵器是典型的巴文化器物,兵器上常見的所謂的“巴蜀符號(hào)”,表現(xiàn)了戰(zhàn)國(guó)中晚期到漢代巴族先民們的意識(shí)形態(tài)和審美藝術(shù),同時(shí)也是研究中國(guó)美術(shù)史和區(qū)域美術(shù)史的重要素材。
1.4 城壩遺址的保護(hù)利用工作開展情況
大型考古遺址公園是利用大遺址及其周邊范圍進(jìn)行規(guī)劃設(shè)計(jì),將遺址保護(hù)與公園設(shè)計(jì)相結(jié)合,對(duì)大遺址在保護(hù)的基礎(chǔ)上進(jìn)行重新整合、再生,在公園的范圍內(nèi)進(jìn)行展示。這項(xiàng)文物工程是以保護(hù)和展示遺址本體和周邊環(huán)境為基礎(chǔ)的,目的是讓前來(lái)參觀的游客置身于此、身臨其境,崇古惜今、繼往開來(lái),在重溫歷史、增長(zhǎng)知識(shí)的過程中不斷提高自身的文化素養(yǎng)和文化自信,進(jìn)而將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傳承并弘揚(yáng)下去。
2006年,城壩遺址被國(guó)務(wù)院公布為第六批全國(guó)重點(diǎn)文物保護(hù)單位,文物類型為古遺址,自此,城壩遺址的保護(hù)工作正式納入規(guī)劃編制中。直至2018年,由渠縣文物部門組織編制完成《城壩遺址保護(hù)規(guī)劃(2018-2025)》,對(duì)城壩遺址的保護(hù)、展示利用和管理進(jìn)行科學(xué)合理的統(tǒng)籌規(guī)劃,城壩遺址保護(hù)利用進(jìn)入了新階段。2020年,為保護(hù)城壩遺址的真實(shí)性、完整性和延續(xù)性,兼顧文物保護(hù)事業(yè)和人民群眾對(duì)公共文化服務(wù)需求的增長(zhǎng),切實(shí)發(fā)揮城壩遺址在渠縣乃至全省社會(huì)發(fā)展和經(jīng)濟(jì)建設(shè)中的積極作用,有效實(shí)現(xiàn)文物保護(hù)、生態(tài)修復(fù)、城鄉(xiāng)發(fā)展、民生改善的相互協(xié)調(diào),渠縣人民政府開始籌建城壩遺址公園。利用城壩遺址現(xiàn)有的資源,通過民居改造等手段,將城壩遺址博物館融入公園自然環(huán)境中來(lái),集遺址文物本體、環(huán)境保護(hù)、考古科研、展示利用、文化教育等多元一體,進(jìn)而帶動(dòng)城鎮(zhèn)公共文化、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生態(tài)環(huán)境發(fā)展的考古遺址公園范例與全國(guó)巴文化研究、宣傳與展示利用核心。
2 當(dāng)前城壩考古遺址公園建設(shè)存在的問題
2.1 資源調(diào)查不足,基礎(chǔ)工作尚待夯實(shí)
城壩遺址發(fā)掘面積相對(duì)較少,雖然發(fā)現(xiàn)遺址很多,但發(fā)掘力度不夠,從占地550萬(wàn)平方米的總面積來(lái)看,發(fā)掘累計(jì)不到100萬(wàn)平方米,并且發(fā)現(xiàn)的遺址相對(duì)于古蜀國(guó)三星堆、金沙的級(jí)別較低,需要更多的調(diào)查、發(fā)掘和研究來(lái)支撐遺址公園建設(shè)。
2.2 遺址保護(hù)不利,早期破壞程度較大
城壩遺址現(xiàn)居住居民密度較大,民居建筑的占?jí)汉痛迕窕顒?dòng)對(duì)城壩遺址地下遺存存在一定的影響。再加上遺址靠近渠江沿岸,每年河流沖蝕、地表徑流沖蝕等因素,對(duì)城壩遺址造成了較為嚴(yán)重的破壞。目前,渠江對(duì)臺(tái)地邊緣的沖蝕已導(dǎo)致河岸出現(xiàn)多處裂縫、崩塌,使處在渠江沿岸的遺址遭到破壞,危害津關(guān)等沿河遺址安全。
2.3 力量整合不足,缺乏系統(tǒng)文化研究
雖然近年來(lái)學(xué)術(shù)界發(fā)表了一些簡(jiǎn)報(bào)和研究論文,但往往是考古成果或地方文化研究單位進(jìn)行的研究,不夠完整,尤其是在理論和實(shí)踐一體化發(fā)展研究方面。如考古發(fā)掘單位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而制定規(guī)劃的是渠縣縣委、縣政府,理論與實(shí)踐兩張皮,造成規(guī)劃方案缺乏實(shí)物支撐。
2.4 管理力量薄弱,體制機(jī)制亟須改進(jìn)
目前,城壩遺址還沒有設(shè)立專門的管理機(jī)構(gòu),而是暫由渠縣歷史博物館代為管理,具體由當(dāng)?shù)卮逦瘯?huì)組織人員管理,缺乏正規(guī)專業(yè)的管理機(jī)制建制,這也使遺址得不到更好的保護(hù)。
2.5 展示利用欠缺,整體影響相對(duì)較弱
達(dá)州除了城壩遺址以外,還有12處巴文化遺址遺跡,其中羅家壩遺址的知名度遠(yuǎn)遠(yuǎn)大于城壩遺址。宣漢縣在境內(nèi)高速公路服務(wù)區(qū)中建設(shè)羅家壩服務(wù)區(qū),高速指示牌標(biāo)注“羅家壩遺址”,并單獨(dú)劃撥經(jīng)費(fèi),運(yùn)用國(guó)家級(jí)平臺(tái)《考古發(fā)現(xiàn)》《考古進(jìn)行時(shí)》等大型文化類節(jié)目宣傳羅家壩遺址,并早在2017年11月為羅家壩考古遺址公園奠基,計(jì)劃于2022年正式開館。而城壩遺址直至現(xiàn)在,僅有初步規(guī)劃方案,缺乏打造宣傳,與地方經(jīng)濟(jì)文化融合度不高,這也導(dǎo)致了城壩遺址的文化內(nèi)涵展示不足,宣傳利用程度不高,影響力偏弱。
3 城壩考古遺址公園建設(shè)的發(fā)展策略
城壩遺址自1992年試掘至今,已經(jīng)持續(xù)發(fā)掘20年,而城壩考古遺址公園的建設(shè)仍未見明顯成效,這也說(shuō)明城壩遺址的保護(hù)、展示和利用工作還任重道遠(yuǎn)。結(jié)合當(dāng)前城壩考古遺址公園建設(shè)過程中存在一些問題及現(xiàn)狀,提出幾點(diǎn)發(fā)展思路。
3.1 夯實(shí)基礎(chǔ),積極爭(zhēng)取
繼續(xù)夯實(shí)城壩遺址保護(hù)利用基礎(chǔ)工作,爭(zhēng)取各級(jí)政府、文物行政管理部門的支持,加快推進(jìn)城壩考古遺址公園項(xiàng)目規(guī)劃工作。同時(shí)加快城壩遺址考古發(fā)掘工作,為以后的城壩遺址博物館提供充足的文物資源。
3.2 區(qū)域發(fā)展,聯(lián)合協(xié)作
加強(qiáng)與周邊大型古遺址和公園的聯(lián)系與合作,深入探索考古和遺址公園保護(hù)發(fā)展聯(lián)盟工作機(jī)制,適時(shí)成立四川省考古遺址和公園合作發(fā)展聯(lián)盟,促進(jìn)考古遺址公園與巴蜀文物的保護(hù)、利用和區(qū)域文化發(fā)展,進(jìn)一步豐富巴蜀文化內(nèi)涵。
3.3 提升展陳,加大宣傳
協(xié)調(diào)省、市、縣文物部門和博物館單位,選擇合適的場(chǎng)地,策劃“城壩遺址出土精品文物展覽”,重點(diǎn)保護(hù)和利用城壩遺址展覽宣傳成果。同時(shí),對(duì)相關(guān)文物保護(hù)、管理、展示、使用等方面的工作進(jìn)行專題研究,并出版論文集。
3.4 文旅融合,打造品牌
以文化旅游一體化發(fā)展為契機(jī),整合巴文化遺產(chǎn)、巴文化主題博物館和博物館收藏的文化遺產(chǎn),多點(diǎn)展示,形成點(diǎn)線狀表面,促進(jìn)主題旅游線路的形成,積極打造巴文化的獨(dú)特品牌,進(jìn)一步增強(qiáng)巴文化的影響力。
4 對(duì)城壩考古遺址公園承擔(dān)社會(huì)責(zé)任的思考
4.1 與當(dāng)?shù)匚幕瘋鞒邢嘟Y(jié)合
達(dá)州是巴文化的核心區(qū)域之一,有著豐富的巴文化資源,然而到底什么是巴文化?哪些文化是巴文化?我們現(xiàn)在還能不能直觀地看到巴文化?這一連串的問題除了通過現(xiàn)有的歷史古籍來(lái)解答以外,就要從達(dá)州的巴文化遺址來(lái)闡釋了。
巴文化研究之初是與蜀文化并稱的,隨著三峽庫(kù)區(qū)搶救性發(fā)掘,出現(xiàn)了一批與蜀文化有著明顯不同的器物,將巴蜀文化成功分成巴文化和蜀文化。而城壩遺址自1979年首次發(fā)現(xiàn)青銅器以來(lái),陸陸續(xù)續(xù)的發(fā)掘采集中,發(fā)現(xiàn)了一批有別于蜀文化的器物。從2008年至今,城壩遺址發(fā)現(xiàn)了墓葬、房址、漢井、城墻、灰坑、窯址、道路等遺跡,同時(shí)還出現(xiàn)了一批東周到漢代的墓葬。上述發(fā)現(xiàn)的種種,都清晰地告訴我們,先秦時(shí)期,城壩遺址的這片土地上已有人類繁衍生息。這些遺跡,特別是墓葬中出土了一批器物,又一次地告訴我們,此地屬巴而非蜀。第一塊“宕渠”文字瓦當(dāng)?shù)某霈F(xiàn),證明了該城為宕渠城。2018年發(fā)掘一處房址時(shí)發(fā)現(xiàn)的竹木牘簡(jiǎn),這些木牘上記載了當(dāng)時(shí)生活中的方方面面。⑦大量的簡(jiǎn)牘和瓦當(dāng)?shù)陌l(fā)現(xiàn)證明,秦漢時(shí)期為了有效地管理西南地區(qū),建立了郡縣制度,為探討秦漢時(shí)期西南地區(qū)的開發(fā)、經(jīng)營(yíng)和管理提供了重要的物質(zhì)基礎(chǔ)。城壩遺址展示了川東巴文化的特點(diǎn)、發(fā)展順序及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其地域文化的復(fù)雜性,也為進(jìn)一步探討西南秦漢帝國(guó)的經(jīng)營(yíng)管理和地方行政體制的建設(shè)提供了重要信息。⑧城壩遺址見證了巴人從興盛到衰敗,再到與中原文化融合。雖然巴人已消失,但是通過城壩遺址展現(xiàn)出的巴文化仍在傳承。宕渠城的“城市”文化,全都融入城壩遺址公園中來(lái),城壩遺址博物館將收藏和陳列記錄巴文化的發(fā)展歷程,觀眾可通過館藏文物和遺址公園復(fù)原的場(chǎng)景觸摸到賨城的發(fā)展脈絡(luò),了解巴人的歷史文化傳統(tǒng),見證巴人社會(huì)生活的方方面面。
4.2 與公眾生活相結(jié)合
博物館具有社會(huì)性,單霽翔先生在《博物館的社會(huì)責(zé)任與社會(huì)教育》一文中曾提到,博物館關(guān)注全社會(huì)的精神文化需求,不分出身、性別、職業(yè)、民族、文化程度,突出最廣泛的社會(huì)特色。通過愛國(guó)主義教育和地方教育,使正確的價(jià)值觀念深入人心,使公眾的道德觀念和社會(huì)責(zé)任感轉(zhuǎn)化為自覺的行動(dòng)⑨。而巴人的精神一直被歸納為“忠勇信義”四個(gè)字,城壩遺址博物館主要就是傳承巴文化,弘揚(yáng)巴人精神。城壩遺址博物館的建成,將使人們對(duì)巴人的認(rèn)識(shí),從古代文獻(xiàn)轉(zhuǎn)到現(xiàn)實(shí)中來(lái),為普通觀眾搭建一座與歷史文化直接交流的橋梁,從書面冷冰冰的文字、高深的敘述、古老的書籍中走出來(lái),讓巴文化變得有親和力且具體化。
博物館公眾教育職能是博物館社會(huì)職能的核心職能,從而體現(xiàn)出博物館的文化責(zé)任。遺址博物館的責(zé)任顯得更加重要了,而城壩遺址博物館除了擁有博物館的身份以外,它還是一個(gè)考古遺址公園、旅游景區(qū)等,所以城壩遺址博物館的建設(shè),除了博物館自身的要求以外,還需要結(jié)合社會(huì)公眾對(duì)考古遺址公園和旅游景點(diǎn)景區(qū)的需求。隨著全國(guó)遺址博物館數(shù)量的不斷增加,特別是良渚遺址申遺成功,公眾對(duì)遺址公園的要求越來(lái)越高了。21世紀(jì)以來(lái),科技越來(lái)越發(fā)達(dá),人們往往注重新鮮事物,而淡忘了我們優(yōu)秀的傳統(tǒng)文化。年輕人沉迷于燈紅酒綠的現(xiàn)代生活,已然不適應(yīng)淡淡的田園生活了。城壩遺址公園除了展示城壩遺址出土文物以外,還可以讓觀眾們親身體驗(yàn)到古代巴人的生活生產(chǎn),讓觀眾體驗(yàn)優(yōu)秀的中華文化,感受優(yōu)秀中華文化的魅力。
4.3 與精神文明相結(jié)合
文化是一個(gè)城市演變發(fā)展的主體,反映著這個(gè)城市居民的精神風(fēng)貌。城壩遺址中所蘊(yùn)含的巴文化也是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城壩遺址博物館作為收藏、保護(hù)、研究、展示文化遺產(chǎn)的文化機(jī)構(gòu),將在今后不斷傳承、弘揚(yáng)巴文化,增強(qiáng)民族自豪感、凝聚力,從而進(jìn)一步加強(qiáng)青少年愛國(guó)主義教育,弘揚(yáng)“忠勇信義”這一巴人精神。達(dá)州作為巴文化的核心區(qū)域之一,而渠縣城壩遺址則是巴文化發(fā)生、發(fā)展、傳承的所在地,人們的民族認(rèn)同感更加強(qiáng)烈。建造一處展示巴文化的場(chǎng)所,能夠展示當(dāng)?shù)匕臀幕奶攸c(diǎn)、內(nèi)容以及現(xiàn)今對(duì)社會(huì)發(fā)展的影響。城壩遺址博物館的建設(shè)除了擁有陳列展示、收藏研究巴文化的功能以外,還成為一個(gè)巴文化交流的平臺(tái),充分利用其獨(dú)特的巴文化資源,增強(qiáng)人們的民族認(rèn)同感,增加人民的民族凝聚力,從而推動(dòng)巴文化不斷向前、有序傳承發(fā)展,實(shí)現(xiàn)普及巴文化的功能。
5 對(duì)城壩考古遺址公園規(guī)劃的一點(diǎn)思考
通過查閱《城壩考古遺址公園規(guī)劃設(shè)計(jì)》,筆者對(duì)其規(guī)劃設(shè)計(jì)有幾點(diǎn)認(rèn)識(shí)。文物與建筑物保護(hù)展示的結(jié)合為建筑物增添了文化氣氛和文化品位,但保護(hù)工作受到建筑規(guī)模、布局和體積的限制,需要做出一些讓步和妥協(xié);在遺址現(xiàn)場(chǎng)建造博物館,可以讓觀眾欣賞到遺址原有的環(huán)境和布局,但需要專門的人員和設(shè)備,并且需要大量的資金,露天環(huán)境對(duì)文物保護(hù)的影響更大,遺跡公園的建設(shè)可以讓游客在享受休閑娛樂的同時(shí),享受文化遺產(chǎn)的魅力,促進(jìn)當(dāng)?shù)芈糜螛I(yè)的發(fā)展,但這種保護(hù)措施只能針對(duì)大規(guī)模的遺址,需要具有很成熟的條件才能夠進(jìn)行建設(shè)。根據(jù)城壩遺址的地理環(huán)境特點(diǎn)、歷史文化內(nèi)涵以及當(dāng)?shù)卣纳鐣?huì)經(jīng)濟(jì)發(fā)展需要,積極采取有效的保護(hù)和利用措施。雖然保護(hù)手段多種多樣,但保護(hù)的目的只有一個(gè),即對(duì)遺址的合理保護(hù)、真實(shí)展示以及有效利用。對(duì)于國(guó)家考古遺址公園的規(guī)模和建設(shè)而言,地方政府不應(yīng)求大、求快,而要肩負(fù)起保護(hù)文物、傳承歷史的重任,真正抓好保護(hù)和展示遺址的核心價(jià)值,注重遺址本體及其周邊景觀環(huán)境的協(xié)調(diào),以發(fā)展的眼光、超前的理念、開放的態(tài)度去推動(dòng)遺址的保護(hù)利用工作,不斷促進(jìn)地方文物事業(yè)的可持續(xù)發(fā)展。
6 結(jié)語(yǔ)
單霽翔先生在《大型考古遺址公園的探索與實(shí)踐》中曾提到,考古遺址公園是許多國(guó)家經(jīng)實(shí)踐檢驗(yàn)證明切實(shí)有效,并已日趨成熟的一種考古遺址保護(hù)和利用模式⑩。城壩考古遺址公園建設(shè)的過程,是展示川東巴文化遺產(chǎn)價(jià)值的過程,也是突出巴文化特色、整合巴文化資源的過程;是實(shí)現(xiàn)城壩遺址整體保護(hù)的過程,也是創(chuàng)新保護(hù)展示理念、動(dòng)員社會(huì)各界參與保護(hù)的過程;是促進(jìn)地方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的過程,也是改善民生、滿足群眾日益增長(zhǎng)的美好生活需求的過程。做好城壩考古遺址公園建設(shè)工作,功在當(dāng)代,利在千秋。■
注釋
①國(guó)家文物局.關(guān)于印發(fā)《國(guó)家考古遺址公園管理辦法(試行)》的通知[Z].2009-12-17.
②國(guó)家文物局.國(guó)家考古遺址公園發(fā)展報(bào)告[Z].2018-09-26.
③劉化石.四川渠縣城壩遺址2005年發(fā)掘簡(jiǎn)報(bào)[J].四川文物,2006(4):5-27,97-100.
④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渠縣博物館.城壩遺址出土文物[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⑤⑥⑦⑧鄭祿紅,陳衛(wèi)東,周科華.四川省渠縣城壩遺址[J].考古,2019(7):60-76,2.
⑨單霽翔.博物館的社會(huì)責(zé)任與社會(huì)教育[J].東南文化,2010(6):9-16.
⑩單霽翔.大型考古遺址公園的探索與實(shí)踐[J].中國(guó)文物科學(xué)研究,2010(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