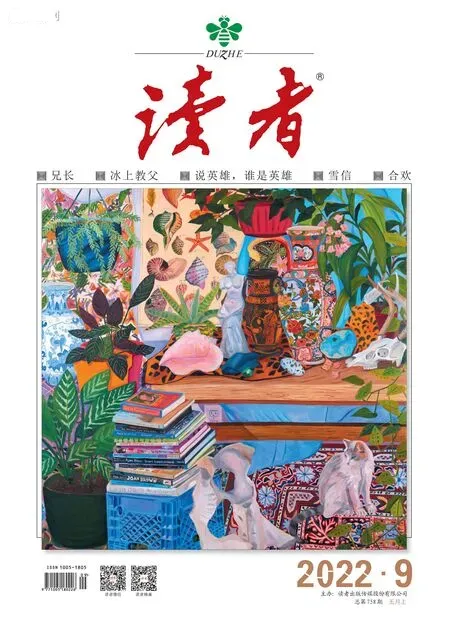無國界醫生
☉王耳朵先生

屠錚

蔣勵(左)
在人們徹夜逃離戰火的時候,有一群中國人,義無反顧地闖進死神的領地。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名字——無國界醫生。每逢危難,他們總是奔赴全球各大災區、戰區、疫區,向在最惡劣的環境中掙扎著的人們伸出援手。
1
中國無國界醫生的故事,要從一個女人開始說起。
她叫屠錚,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婦產科主治醫師。她是中國第一位參與無國界醫生海外志愿工作的醫生。
2007年4月,36歲的她遠赴利比里亞的首都蒙羅維亞,為當地婦女提供婦產服務及外科手術。那里剛結束內戰,上百萬人流離失所,故鄉成了一片焦土。
屠錚面對的,是不間斷的武裝沖突和極其脆弱的醫療系統。
當年,利比里亞有325萬人口,但注冊醫生只有121人。那里的孩子剛出生時是按出生日取名的,從星期一到星期日。一周以后,如果孩子還活著,父母才會給他取一個正式的名字。
為了救人,屠錚曾連續工作36個小時。她經常半夜被叫醒,站上手術臺。她不怕槍林彈雨,卻怕自己無能為力。
醫療器械匱乏,6個月中,她眼睜睜地“送走”6個孕婦,還有數不清的孩子——這比她過去從醫10年見證的死亡病例還要多。
高溫雨季,醫院沒有能力給除了手術室之外的地方安裝空調。屠錚的手術服在汗水和潮濕中銹得扣不住,同事急得不行,屠錚卻冷靜地撕下一塊膠布:“別慌,貼上!趕緊手術!”
醫院的救援項目中,有越來越多的名為“Zheng”的小孩出生。那是戰火紛飛中共同經歷生死關頭后,媽媽們為了記住這位美麗善良的醫生,而為孩子賦予的新生的意義。
2
2012年5月,做了幾年無國界醫生的屠錚,收到一封郵件:“屠老師,我想加入無國界醫生組織。我已做好準備,來迎接這個重大的轉折點。”
發信人是她的師妹,浙江妹子蔣勵。又一個中國姑娘扛起火炬,做暗夜中的點燈人。
2013年,蔣勵33歲,被指派到阿富汗霍斯特省。
醫院就是一排殘破的平房,只有3間屋子——一間是手術室,一間是病房,一間是醫生宿舍。蔣勵和另一位來自巴西的姑娘,就是這家醫院僅有的兩名婦產科醫生。
品管圈在規范ICU多重耐藥菌感染終末消毒流程中的效果明顯,應將品管圈成果標準化。向醫院信息平臺推送規范化,標準化地MDRO感染終末消毒作業指導流程圖,為環境清潔質量管理提供考評依據。
阿富汗的春天浸在戰火里。醫院旁邊就是警察局,經常遭到反政府武裝的攻擊。蔣勵和醫生們的宿舍外墻砌著一圈磚,就是為了防止被流彈打穿。
蔣勵顧不上恐懼,因為無國界醫生所在的醫院提供的治療全部免費,每天都會涌入大量的病患。她要面對的是每個月1200到1300個的分娩量。“待產室住不下,就在車上生、地上生。我進手術室的時候外面是一撥人,等我出來時已經又換了一撥人。”
每隔一天,蔣勵就要經歷一次24小時的完全當值。這24小時內,她隨時待命,沒有休息的時間。
在這個不倡導女性接受教育的地方,母嬰的死亡率很高,每天她都能遇到各種各樣的疑難雜癥。很多婦女在小診所接受了不正規的治療,被輸入超量催產素后子宮破裂。在國內很少見的重度先兆子癇的胎盤早剝癥狀、合并癥和并發癥,在這里隨處可見。
槍聲也無處不在。
一天晚上,蔣勵正在睡夢中,巨大的爆炸聲讓她從夢中驚醒。她驚慌失措,不知道該往哪里躲,害怕地給萬里之外的未婚夫打電話。未婚夫極力安慰她,給她發來馬友友的大提琴協奏曲,希望用音樂安撫她的情緒。蔣勵不停地安慰自己:“天亮就安全了。”
危險如影隨形,但蔣勵仍恪盡職守。原本在阿富汗,每10萬個孕產婦里面,就有四五百個死亡病例。但在蔣勵值守阿富汗的3個月里,她接生了幾千個新生兒,并且沒有一個產婦死亡。蔣勵創造了一個奇跡。
3
做無國界醫生,是沒有工資的,只有每個月922歐元(約合人民幣6500元)的補助金,和只夠生活成本的津貼。但他們放棄了和平與安穩,甘愿陷入危險和清貧。
做這一切,不過是因為醫者的仁心。
來自香港的趙卓邦,是一位護士主管。2013年,他辭去月薪3萬港幣(約合人民幣2.4萬元)的工作,加入無國界醫生組織。工作地點是也門的薩達。

趙卓邦
當時,那是十分動蕩的戰亂之地,幾乎每天都受到聯軍的空襲。不論晝夜,耳邊都是戰機、爆炸和空襲的聲音。
一天早上6點,“轟”的一聲巨響,炸彈直接炸毀了他們基地旁邊的一棟建筑物。對這類事情,他早就習以為常,直到2015年的冬至。那天,一個男人走進醫院的帳篷,在床上放下一張毯子和一個袋子后便離開了。
趙卓邦打開毯子,里面是一個小女孩的尸體。“她的臉已被煙熏黑,頭部右邊有大部分不見了。其他護士告訴我,袋子里裝的是人體殘肢。”恐懼和后怕在這一刻被放到最大,可眼前一個個求生的病患,讓他迅速冷靜下來。他是能給這些絕望之人帶去希望的人。
另一個在趙卓邦腦海中揮之不去的故事,是關于一個4歲小男孩的。小男孩每天都會跟隨祖父,一起到醫院更換包扎敷料。他的其他家人都在一場空襲中喪生。他的右臂在空襲中受創,需要截肢。為了逗他開心,趙卓邦每次都會在他的繃帶上畫一塊手表。
看著小男孩天真爛漫的笑容,他心里隱隱作痛——小男孩將永遠失去在右手腕上戴手表的可能。
有時候,趙卓邦會拿香港的孩子和當地的孩子做比較:“在香港,小朋友如果聽到飛機的聲音就會很開心,他們會喊‘長大后我要做飛行員’。但在也門,飛機帶來的從來都不是希望。”
4
做無國界醫生,最難的不是工作,而是如何活下來。
西非埃博拉疫情暴發時,趙卓邦也在第一線。一天,他穿好防護服準備前往高風險區。同事叫住他,邀請他一起祈禱。不同膚色、不同國籍的人,手挽手圍成一圈,虔誠地閉上眼。禱告完,大家都會為對方送上一句“保重”。
每個人都說得很沉重。走出門,誰也無法預知下一刻會面臨怎樣的危險,全身而退是最重要的。病毒通過血液和體液等介質傳播,會經傷口感染。那段時間,他不剃胡子,也不剪指甲。有一次,在疫區,趙卓邦的手被紙劃傷了,平常不需要處理的傷口,增加了感染病毒的概率。
那是他最恐懼的一次。盡管如此,趙卓邦還是在疫區待了一個月。這是執行埃博拉病毒防疫任務所允許的最長時限。
還有一位在剛果和南蘇丹執行任務的姑娘,周吉芳。她在政府軍、反政府軍武裝和部落武裝長期沖突的地方執行任務,經常能聽到槍響。
她說:“最危險的一次是武裝分子在半夜潛入了營地,他們應該是來搶劫的。有一位醫生從房間里出來,被劫匪打中了肩膀,好在得到及時救治,之后被送到比利時治療了很長時間。無國界醫生組織成立40多年來,有的醫生被綁架,也有的醫生在執行任務的過程中受傷甚至犧牲,意外是無法避免的,我們都要做好遭遇最壞情況的心理準備。”
盡管他們知道此去征程漫漫,前路艱險,辛苦異常,但穿上白大褂便是一身傲骨、一腔赤血。
行者無涯,醫者無疆。
(繁 星摘自微信公眾號“王耳朵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