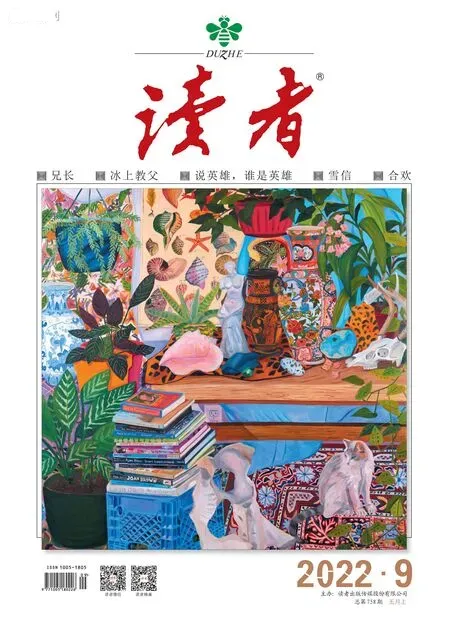冰上教父
☉摩登中產

七臺河體育中心短道速滑訓練場 謝劍飛 攝
一
2019年,王濛回東北,隨身帶著75塊金牌。過安檢時,工作人員十分吃驚:“你怎么得這么多金牌?”
她帶著那些金牌飛抵哈爾濱,沿哈同高速向東行駛400多公里,到達風雪的盡頭——小城七臺河。
那是黑龍江省偏東之地,多條鐵路的終點。小城中心修有一座冠軍館,王濛的金牌被安置在4樓,向上有觀光廳,遠眺可見在冰湖上飛快滑行的少年。
在冠軍館的2樓,立有一尊銅像——孟慶余,他是王濛的老師,冰上教父,也是這座城市的傳奇。
18歲時,孟慶余從哈爾濱來到七臺河,隨眾多知青一起下礦挖煤,礦名“勝利”,似乎有什么預示。
他每天在坡道上步行6000米,閑暇時就去野河滑冰。哈爾濱的琴聲燈影遙遠如夢,可他懷里揣著老師送給他的冰刀,“永遠都別放棄滑冰”。
他在礦區拿了冠軍,但時代給他的賽道有限,23歲時,他成為小城首批滑冰教練。
他走遍七臺河的小學,挑出20多個孩子,一戶戶勸說家長:“孩子將來能當世界冠軍,即使當不上也能當體育老師。”
業余少年速滑隊就此組建,訓練地點是城郊水洼,冰面上北風呼嘯,四野荒草叢生。
七臺河冬夜漫長,少年們常起早摸黑訓練。多年后,楊揚的教練董延海回憶,有一天少年們來到水洼邊,忽然發現野地里立著木桿,木桿上掛著碘鎢燈,燈下站著孟慶余,荒野上有一小團暖光。
過了這么多年,董延海還是想不明白:孟教練是怎么一個人把六七米高的桿子立起來的?
數年間,少年們輾轉多個水洼,最后在市內的舊體育場落腳。體育場裝有電燈,當地人稱之為“燈光球場”。
燈光球場簡陋空曠,孟慶余在看臺下搭好房間,作為速滑隊的隊員宿舍。宿舍四下透風,墻上結滿冰霜。入冬后,孟慶余每天半夜起床,裹上棉大衣,拉起鐵爬犁,到遠方取水。鐵爬犁上有鐵桶,能裝半噸多水。往桶里裝滿水后,孟慶余一個人拉著鐵爬犁,回到體育場,一圈圈澆冰。
澆冰需在寒夜最冷時進行,澆一次要兩個小時。澆完后,孟慶余的衣服也結了冰,像冰甲,他一走路衣服便嘩啦作響,脫衣服要先用木棍敲打,才脫得下來。
天亮后,少年們走上冰場,一圈圈滑到深夜,有時滑到全身凍僵,孟慶余就一個個將他們背回宿舍。
宿舍里,他一本正經地講聽來的口號——“沖出亞洲,走向世界”,少年們笑他吹牛。對礦區的孩子而言,奧運會太遙遠,哈爾濱就是世界的盡頭。
夏天,沒有場地,孟慶余帶著他們進行模擬訓練。少年們用長帶把自己攔腰綁在樹上,側身蹬地,想象自己踏著冰雪。
后來,孟慶余組織隊員進行自行車拉練。他們從七臺河出發,一天騎上百公里,半個月騎遍大半個黑龍江省。
有一次,騎著騎著,少年們發現他不見了,回頭去找,發現他摔在溝里,手肘鮮血橫流,露出了骨頭。
1985年,12歲的隊員張杰遠行參賽,一口氣包攬全國速滑少年組的5枚金牌。
這5枚金牌改變了少年們的命運,孟慶余獲準帶隊到哈爾濱訓練一段時間。少年們走進面積8000平方米的滑冰館,那里燈光明亮,空調恒溫,他們感覺“像走進天堂一樣”。
因為是業余隊,少年們要等省隊訓練完才能上場。每晚,孟慶余都央求看門的大爺晚一小時熄燈,讓少年們多滑一會兒。
在七臺河時,訓練之余,孟慶余會帶少年們闖夜路、跳冰河,錘煉心志。他說,無論面對什么樣的對手,腿都不能打哆嗦,運動員首先應該是英雄。
二
1985年,一位10歲的小女孩加入孟慶余的隊伍,名叫楊揚。
楊揚身材瘦弱,被體校拒收,孟慶余卻看中她的倔強和不輕言放棄的精神。
倔強的少年們奮力沖刺,渾然不知前路的命運。1987年,孟慶余向領導建議,希望七臺河的這支隊伍專攻短道速滑項目。表面理由是新項目,可以出奇兵,真正原因是七臺河沒有更長的冰道。1992年,短道速滑正式成為冬奧會項目。
時光就這樣滑入20世紀90年代,風雪無窮無盡,煤灰落了又揚,滑冰的孩子也越來越少。孟慶余的徒弟——已當教練的趙小兵,提著禮物上門勸說家長,但多數家長不愿意讓孩子練體育。

孟慶余
一切都在時光中腐朽。曾經的燈光球場塌了半邊,寂寥如古羅馬的斗獸場,跑道上荒草叢生,空地被改作廢品收購站,后來又成為客運站的物流場。孟慶余帶著僅剩的一些少年,遠走哈爾濱訓練,租住在一個地下車庫內。他找木匠在車庫內打了一層閣樓,女孩睡上層,教練和男孩睡下層。夏天潮熱,不少孩子身上生了瘡。
孟慶余身兼教練、采購、文化課老師以及炊事員,后來實在忙不過來,楊揚的母親自告奮勇,來哈爾濱給孩子們做飯,一做就是3年。
最窘迫時,孟慶余向王濛的父親借了3萬元。多年后,王濛回憶:“當時那是我家的全部家底啊。”
王濛1995年加入孟慶余的隊伍。那年她10歲,留著一頭短發,性格霸道,愛打架,在冰上的感覺極好,躲閃變向,敏捷過人。
孟慶余對她極為偏愛,但當面從無好臉色。每次王濛偷懶,都要被罰繞冰館跑100圈。跑到60圈時,王濛耍賴不動,但孟慶余不退讓,讓她無論如何都要跑完100圈。
那些年,孟慶余獨創體能漸進加量法,少年們每節課跑步里程要超過兩萬米。長大后,王濛說,因為小時候打下的基礎好,所以能承受超負荷的訓練。
每個寒冬的凌晨4點20分,孟慶余都雷打不動地叫所有人起床,少年們將其叫作“冰點”。跑圈時,他們對孟慶余愛恨交加,但能明白其苦心。礦區的孩子從小有野性、無畏,做夢都在翻越山丘。
1995年,楊揚在世界錦標賽上奪冠,坐在電視機前的王濛滿臉崇拜,孟慶余淡淡地說:“她小時候還不如你呢。”
不久后舉辦的亞洲冬季運動會,孟慶余帶著王濛等人看比賽,王濛順利要到楊揚的簽名,她第一次發覺自己離冠軍的世界如此之近。
那些從七臺河走出去的冠軍,多年來養成了一個傳統:他們回七臺河時,會和孟慶余帶的小師弟師妹們一起滑冰,然后故意落后一點兒,讓少年們覺得冠軍并非遙不可及。
2002年,美國鹽湖城,楊揚閃電般沖過終點,中國冬奧會首金誕生。外國記者沖上前,問她來自中國哪里,她說:“七臺河。”
2006年,意大利都靈,王濛奪金,開啟“濛時代”。2010年,在溫哥華冬奧會,她包攬短道速滑500米、1000米、3000米接力賽3項冠軍。
王濛奪金那年,老友從哈爾濱到七臺河看望孟慶余。歲月綿亙漫長又電光火石,孟慶余淚如雨下。
三
冰場之外,孟慶余沒有業余愛好,閑暇時就磨冰刀,磨到把相關心得都寫成論文發表,磨到全省高手有冰刀不合腳的都請他調。
1997年,七臺河讓他去上海參加會議,其實就是變相獎勵他旅游。他開完會就回來了,用省下的差旅費買了20塊磨刀的油石,分給少年們。
楊揚奪冠后,外省市有人出百萬元年薪挖孟慶余,孟慶余都拒絕了,他和這座小城一樣倔。
當地的家長調侃道:“一代代傻子教練帶著,一代代傻子跟著練,我們這幫家長也跟著變傻了,跟著走唄。”
有一年冬天,孟慶余看上徒弟趙小兵帶的學生,想接手帶,趙小兵不給:“您都這么大歲數了,干嗎跟我搶學生?”
孟慶余站在校門口,帶著哭腔說:“小兵,你不讓我帶學生,那我活著還有啥意思?”
2003年,孟慶余的學生中多了范可新。她家窮,哥哥輟學后,修鞋支持她滑冰。訓練要換新冰刀,她買不起,孟慶余花2500元買了送給她,并告訴她,努力能改變命運。
2006年8月2日,孟慶余開著面包車,趕往哈爾濱參加訓練課。出發前,他說范可新營養不良,想讓退休的老伴兒也去哈爾濱,照顧她。
當天上午9時7分,孟慶余遭遇車禍身亡,在哈同公路上,留下一身舊運動服、一部有裂紋的諾基亞手機,以及一塊秒表。
悲劇發生后,領導和媒體趕到孟家慰問。40平方米的小房內,沒有一件像樣的家具。孟慶余的老伴兒從臥室搬出幾把折疊椅——還是當年他們結婚時買的。
出殯當日,小城舉城同悲,數千名市民為他送行,那些長大的少年泣不成聲。冰上的人們不愿忘記他,關于他的報告會,最后一路開到國家體育總局。弟子們一個個上臺,講述總因哭泣中斷。
王濛上臺講完,滿心悔恨,含著淚說:“如果孟教練在天堂能聽到的話,我想對他說聲對不起。”她一直以為教練不喜歡她才對她嚴厲,孟慶余車禍遇難后,父親才告訴她,那是他們商量好的激將法,她其實是孟慶余最中意的弟子。
兩年后,一個攝制組來到七臺河,以孟慶余為原型拍攝電影《破冰》。小城只有雪與灰,只有黑白兩色,他們搖動鏡頭,逆轉時光,一點點還原理想、孤獨和純粹。
導演說,孟慶余不是一位英雄,不是一位模范,他首先是一個人,“有些人一輩子只做一件事情,他就是這樣的人”。
孟慶余走后,弟子們接過了教鞭,至今已傳承至第4代,他最早帶的學員張杰,從日本歸來,在小城里組建了特奧速滑隊。她說,在日本時,總能夢見孟慶余喊她:“起床、列隊、訓練。”
2013年,七臺河終于有了室內冰場。來自七臺河的運動員,已獲得173枚世界級比賽金牌、535枚全國大賽金牌,15次打破世界紀錄。短道速滑的1730名注冊運動員中,有1/5來自七臺河。
那座冠軍館的第一層,沒放金牌,放了上千雙被少年們磨平刀刃的冰鞋。那是冠軍的起點。
2022年2月5日,孟慶余的關門弟子范可新,和隊友們一起,奪得中國代表團在北京冬奧會的首金。
奪冠后,她說:“希望以后有更多的七臺河小孩,能接過我的這一棒。”
奪冠夜,爆竹聲響徹小城夜空,試圖驅散寒意。
有人離去,有人躺下,也有人咬牙行進。
黑龍江寬闊的冰面上,冬季總有鑿冰冬泳的人。冰面厚如山巖,水下冰寒刺骨,而給人信心和希望的,是咬牙一直游下去。
(苦樂年華摘自微信公眾號“摩登中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