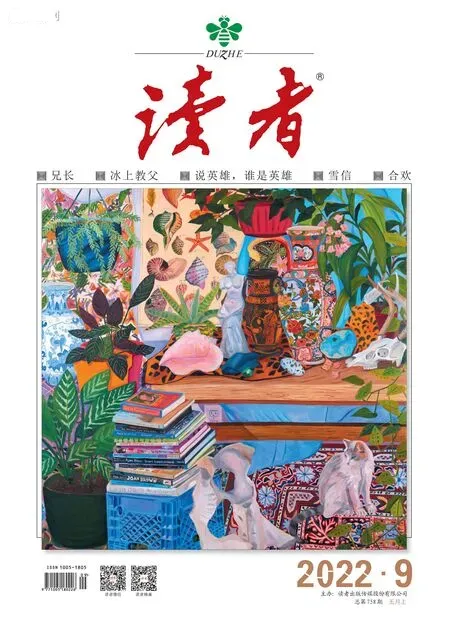青春期:尋找“天命”的旅程
☉陳 賽

青春期:進化的“陰謀”
想象這樣一個情景:某天下午,你坐在辦公室,鼻子里塞了一團棉花,有人剛剛在你的辦公室里烤了一個巧克力蛋糕。空氣里飄蕩著巧克力的香味,但因為你的鼻子被塞住了,所以你還是埋頭干活。直到你突然打了一個噴嚏,棉花掉了,香氣一下子撲鼻而來,于是你沖過去,抓起一塊蛋糕就吃。
從隱喻的意義上來說,所謂成年人與青少年的區別就在于,成年人的鼻子里整天塞著棉花,而青少年恰恰相反,他們天生能在百步之外聞到巧克力蛋糕的香味。
按照美國心理學家勞倫斯·斯坦伯格的說法:“當你處于青春期時,無論是友誼、性、冰激凌,還是在夏日的夜晚漫步,聽你最愛的音樂,它們帶給你的快感都比任何人生階段更加鮮明與美好。”
為什么會這樣?
按照神經學的解釋,青少年這種生命體驗的鮮明度與青春期時大腦的發育有很大的關系。科學家曾經認為大腦的發育到童年末期就差不多完成了,但新的研究發現,在10歲到25歲之間,大腦一直在發育。不過,青春期時大腦的發育不再是“生長”,而是“重組”,即大腦灰質與白質都在經歷廣泛的結構性變化、重組以及布線升級。
第一,大腦中一個叫伏隔核的區域(也叫“快感中心”)一直在擴張,到青春期擴張到極限,然后開始縮小。
第二,當一個孩子進入青春期時,他的大腦會分泌出越來越多的多巴胺受體,而且大腦對多巴胺的敏感度也會達到峰值——多巴胺能生成和激發大腦中有關獎勵(回報)的神經系統,從而幫助學習和決策。這可以解釋青春期時的大腦強大的學習能力、對于獎賞的渴望,以及對于成功和失敗過分熱烈的關注,甚至戲劇化的反應。
從某個角度來說,你甚至可以把它視為一種進化的“陰謀”:當一個人即將從家庭的安全環境進入一個更復雜的世界時,大腦已經做好了準備,鼓勵他對這個世界產生興奮感和好奇心,驅使他去探索、冒險,尋找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的位置。
科學家追尋人類智力的源頭,懷疑也許是某種浮士德式的瘋狂基因變異開始了智人的歷史——對古DNA的研究發現,大概4.5萬年前,現代智人到達澳大利亞,這一旅程意味著他們得跨越海洋。當直立人、尼安德特人都還忙著在舊大陸繁衍生息時,到底是什么讓智人選擇了向無邊無際的大海進發?在他們成功登上陸地之前,得有多少人葬身大海?他們為什么要做這件事情呢?為了榮耀?為了永生?還是因為幾個年輕的智人一時的血氣之勇?
離開家,無論對個人而言,還是對人類這一物種而言,都是很艱難的事情,但也是最重要的事情。在人類漫長的進化過程中,無論覓食、求偶、謀生,都要求年輕人走出家門,進入相對不安全的環境。越是尋求冒險和新奇,成功的機會越多。就像青春小說里的主人公,懵懂時離開熟悉的家,踏上冒險的征程,在經歷了種種挫折與險阻之后,歸來時對家和自我都有了一個新的、更好的理解。
青春期的另一個視角
無論現代社會,還是原住民部落,人類學家在幾乎所有的文化中都發現了青春期作為一個特殊階段的存在。青少年可以讓人很頭痛,美國著名女編劇諾拉·艾弗隆曾說:“家有青春期兒女,唯一的補救方法是養一條狗,這樣你至少還能看到一張笑臉。”但與此同時,他們也是最有適應性的人——他們開始獲得更高級形式的推理和執行能力,但他們的血管里仍然流淌著那些勇敢、野蠻、渾身長毛的遠古人類的能量。青春期的種種特質,比如熱衷于刺激、冒險、同齡社交,都是經歷了無數代的自然選擇后形成的,而它們之所以被選擇,是因為它們在人生一個關鍵的過渡期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這個時候,一個人必須離開安全的家而進入一個陌生的環境。
從這種視角來看,青春期不再是一個粗糙的半成品,一個只會帶來尷尬、麻煩與困惑的人生階段,而是一個高度功能化的階段,是在正確的時間做正確事情的階段。
比如青少年對刺激的熱愛。我們都喜歡新的、令人興奮的事物,但我們從來沒有像在青春期那樣渴求新鮮的刺激和血脈僨張的感覺。這種欲求從10歲開始,到15歲達到頂峰,然后逐漸下降。雖然這種欲求會導致一些危險行為,但也提供了一種根本性的沖動,讓你想要走出去,見識外面的世界,結識更多的人,探索更多的未知領域。
三是明確管護責任。針對不同工程的性質和特點,采取專業化管理、社會化管理和自主管理等多種方式,將工程管護責任落實到產權的所有者和使用者,同時健全管理制度約束管理主體,確保工程能夠正常地發揮效益,確保用水戶的利益不受損害。
在青春期同樣達到峰值的,還有一個人的冒險傾向。今天的青少年不必再在捕獵或者部落戰斗中冒險,但他們面對的是比在舊石器時代更多更讓人分裂的誘惑:酒精、毒品、汽車、半自動武器……14~17歲的青少年最容易以身犯險,不是因為他們意識不到,或者不理解風險所在,事實上,他們在認識和面對風險的方式上與成年人并無大的差異,甚至常常會高估風險,但他們權衡風險和回報的方式與成人不一樣:如果冒險能帶來他們想要的東西,他們就會義無反顧,因為他們比成人更看重回報。
斯坦伯格有一個簡單的游戲可以說明這個道理。在游戲中,你要以最短的時間開車穿過小鎮,當接近路口時,有時候綠燈剛好變黃,你必須快速決定是沖過去還是停下來。如果沖過去,就可以節省時間,得分更高,但前提是必須在紅燈亮之前開過去,否則就闖了紅燈,損失比停下來等待更大。所以,這個游戲鼓勵冒險,但懲罰過度冒險。
實驗結果發現,如果青少年是獨自駕車,他們冒險的程度和成年人相差不大;如果加上一些他們十分在意的因素,比如讓他們的朋友在旁邊觀看,他們冒險的概率就會增加一倍。相比之下,成年人在有朋友觀看的情況下,駕車行為幾乎不變。
這也帶出了青春期的另一個關鍵特征:極度重視與同齡人之間的關系。所謂青春期的“同輩壓力”,就是朋友要做同樣的事情,說同樣的話,穿同樣的衣服,遵循同樣的規則。一個16歲的女孩為什么要在肩膀上文身?因為她的朋友文了。一個18歲的男生為什么要上社交網站?因為他的朋友上了。他們互相慫恿,被彼此的勇敢和酷鼓舞著,體驗到強烈的團結、親密與尊重。
作為成年人,我們也許無法理解一個13歲的少年被朋友欺騙后的歇斯底里,或者一個15歲的年輕人因為沒被邀請參加朋友聚會而產生的巨大失落,但對他們而言,痛苦是真實而激烈的——一些大腦成像研究發現,青春期的大腦在面對同齡人的拒絕時,反應甚至比對威脅健康的事物來得更強烈。也就是說,在神經層面上,他們把社會性的排斥視為一種對生存的威脅。
這是年輕人的本性——正是構建自己身份的年齡,他們思考性、死亡,他們孤獨、害怕,他們必須尋找同盟,以穩固自己。從這個角度來說,這是一種非常實用的生存策略——我們由父母帶到這個世界,但一生大部分時間必須生活在由同齡人營造和重建的世界里。認識他們,了解他們并和他們建立良好關系,對今后人生的成敗至關重要。
發現屬于自己的“天命”
在青春期,我們經歷的是人生中最令人不安的一次身份危機。我是誰?是什么讓我感到興奮、充滿活力、得到尊重?是什么讓我覺得生命有意義?對每個人來說,成長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探索這些問題,而且這種探索是全方位的,包括生理、情感和認知上的。
英國教育家肯·羅賓遜用“天命”一詞來描繪這種境界——我們的“天命”使得我們喜歡做的事與我們擅長做的事完美結合。他認為,對每個人來說,發現屬于自己的“天命”都是至關重要的,這不僅是因為它讓我們對自身的生活更滿意,而且是因為未來世界的發展取決于它。
在他看來,全世界的公共教育系統都是一個拉長了的大學入學過程。他們不斷給學生灌輸一種狹隘的能力觀,并且只重視對某一方面的才智或能力的培養,而忽略或者漠視其他一些同樣重要的能力。
在這種教育體制之下,青少年通常只能有兩種反應,要么順從,要么反抗。我記得自己的中學時代,考大學就是人生的唯一目的。老師們忙于用各種知識將我們的大腦填滿,沒有時間也沒有興趣教我們欣賞詩歌、音樂,啟發我們思考,或者追問何為美好生活。
當然,也有人選擇反抗。反抗的方式有很多種,但極少能有好的結局。青春期的能量、冒險的欲望與探索的沖動,被現代消費社會的種種替代性誘惑刺激著——物質主義的、感官刺激的,有時候甚至是自殘性的。一個對現實感到挫敗的年輕人會通過撒謊、打架、嗑藥、酗酒、玩危險甚至殘忍的游戲,讓自己陷入各種各樣的麻煩。很多國家的數據都顯示一條相似的犯罪率年齡分布曲線——從13歲左右開始迅速上升,18歲達到頂峰,在成年初期迅速下降。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如果他們有更有趣或者積極的渠道進行“冒險”,這些青春期的問題行為是否就不會發生,至少會少很多?
不確定性的美德
青春期的大腦,進化的設計就是為了應對一個不確定的世界。他們在很多層面上被困難、不確定性以及冒險吸引。他們畢竟還年輕,心智尚未發育完全,網絡雖然賦予他們前所未有的獲取與使用各種學習資源與工具的能力,以及時時刻刻彼此連接的能力,但他們還沒有學會如何分析一個復雜文本背后深層的道德、心理和哲學的價值,他們的理性還不足以讓他們在各種互相沖突的價值觀與生活方式模型中做出明智的選擇,他們尚不懂得如何對歷史負起責任。
況且,網絡也有它的危險之處。世界著名心理學家霍華德·加德納就把這一代年輕人定義為“App一代”。他認為,App已經在某種程度上內化為當代年輕人的思維框架,他們在技術上尋求直接、快速、簡單的解決方案,甚至期待人生的方方面面都像App一樣,快速、高效、即時滿足,告訴你做什么、如何做,別人是怎么想的,你應該如何感覺,你對自己應該如何感覺。
他們24小時待在社交媒介上,卻避開更深層次的情感投入與更復雜的人際關系所帶來的脆弱性。數字工具降低了創造力的門檻,但他們也無法超越工具內在的限制。
加德納欣賞建構主義的學習方式——通過探索來獲取知識。他相信App是一種“抄近路”式的發現方式,會減少青少年對世界的參與度。很多年輕人甚至從來沒有迷過路,即使他們沒有定位導航設備,他們的父母也有。在人類的全部歷史中,迷路都是生活的一部分。沒有人會永遠處在迷路狀態,別人會找到你,或者你自己找到出口。但這樣簡單的事情其實是很深刻的。也許他們從不覺得有隨意漫步的意義或者必要,但在加德納看來,這是鍛煉年輕人獨立精神與靈活性的一種有益手段。
(七月安生摘自微信公眾號“橡果成長紀”,黎 青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