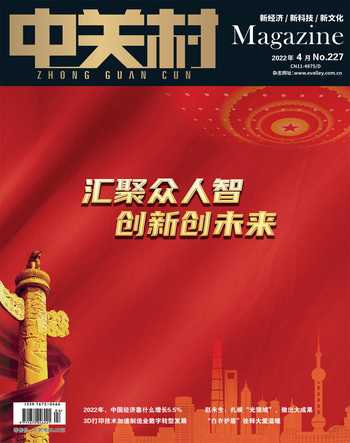2022年,中國經濟靠什么增長5.5%
江川

對中國來講,經濟增長速度是最大的“局”,因為要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新發展格局。如果經濟體量越大,并且服務業的占比越高,那么國內循環的比重就越大。
怎么讓經濟體量變大,讓服務業的占比提高?歸根結底還是要實現經濟增長。
衡量經濟增長的重要指標是人均GDP。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韓國在2002年的時候人均GDP就達到美國的50%。但是中國現在的人均GDP只有美國的20%多。要從20%多上升到50%,而且希望在2049年實現,中國必須要有比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
而現在,中國面臨全球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怎樣駕馭這個大變局?北大國發院名譽院長、北大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教授認為,中國經濟在2035年之前還有8%的增長潛力。他講的增長潛力是從技術層面來看的,是在不過度消耗各種資源的狀況下可以維持的經濟增長速度。當然有這樣的增長潛力并不代表每年都能以8%來增長,就像買汽車,它的設計時速雖然可以達到300公里,但并不是說每次開車就一定能開300公里,因為還要看天氣狀況、路況等因素。
在2035年之前,每年實現6%的增長,這是駕馭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基礎。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定的目標是5.5%,因為考慮到了俄羅斯跟烏克蘭的戰爭因素。俄烏戰爭爆發以后,國際石油價格猛漲,糧食價格猛漲,礦產資源價格猛漲。再加上美國對俄羅斯的制裁,給國際金融創造了很多不確定性。中國是石油最大的輸入國,也是各種原材料、糧食的最主要的進口國,肯定會受俄烏戰爭的影響。在這種狀況下,把經濟增長目標定在5.5%是一個合理的實事求是的目標。
在這種狀況下,經濟增長不能只靠要素投入的舊方式來發展,必須依靠創新,讓勞動生產率的水平越來越高。
現在一談到創新,通常強調的是發明,這實際上是受到主流經濟學的影響。因為主流經濟學來自于發達國家。而發達國家的技術已經是全世界最好的,再創新就必須要靠發明。發達國家的產業附加值也已經是全世界最高的,產業要再升級,也只能靠發明。
但不論是技術創新還是產業升級,發明的投入都非常大,風險也非常高。因此以TFP(全要素生產率)為主導的經濟發展創新方式并不適合現階段的中國。發達國家之所以可以靠發明的方式來取得創新,靠TFP來推動經濟增長,是因為從19世紀中葉到現在,經濟的平均增長速度是3%左右,人均GDP或者平均勞動生產率是2%左右,人口增長是1%左右。
中國現在還屬于追趕型國家,追趕型國家的創新含義有時候跟發達國家不完全一樣。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的技術跟發達國家還有差距,可以把發達國家的技術引進消化吸收,作為創新的來源。同樣在產業升級的時候,可以把發達國家已經成熟的、附加值高的產業引進消化吸收,通過這種方式創新,不僅成本比較低、風險比較小,而且速度比較快、TFP比較小。
實際上,中國改革開放以后取得的年均9%以上的經濟增長,絕大多數都是靠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事實上,不僅中國是這樣,日本處于追趕階段的時候,也是這樣。
中國現在人均GDP已經達到12551美元,很快就要變成高收入國家,但林毅夫認為,中國仍不可以追求以TFP為主導的經濟發展創新方式。回到中國實際的經濟狀況,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可以把產業分成五大類型:追趕型產業、領導型產業、勞動密集型產業、換道超車型產業、戰略型產業。
而中國現在的產業大多數還是追趕型產業。比如2021年,中國高新技術制造業的比重只占制造業的15%,也就是說還有85%的制造業并不是高新技術制造業,而是相對成熟的傳統產業。而追趕型產業最好的技術創新方式就是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這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取得快速發展的制勝法寶。
最近,習近平總書記在談到新舊能源轉換的時候,講了一個小故事:中國以前的工人很窮,經常在外面當苦力,靠一根扁擔挑東西。一天,有個苦力中了彩票,非常高興,覺得自己馬上就可以變成百萬富翁了,于是就把扁擔丟掉了。然而,當他去領獎的時候發現,怎么找都找不到那張彩票。后來他想起來,因為之前太窮了,沒地方住,怕彩票丟了,就把彩票藏在那根扁擔里面。現在他把扁擔丟了,百萬富翁的夢想也泡湯了。總書記講這個故事,是要強調,中國的傳統能源比較多,在還沒有新能源之前,不能一下子就把傳統能源都舍棄掉。
同樣,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關系到中國85%的制造業,這個法寶不能丟。

北大國發院名譽院長、北大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教授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政府工作報告都強調了經濟發展面臨著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所以5.5%的目標并不是輕而易舉就可以實現的。
從消費的角度看。去年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是65.4%,扭轉了2020年消費對經濟增長負貢獻的局限。但是它并沒有恢復到疫情前的水平。這里有很多因素,其中兩年平均的收入增速沒有恢復到疫情前的水平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另一個因素是,疫情期間收入差距有所擴大,主要表現是收入的平均數和收入的中位數之間差距拉大了,也就是說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速低于平均水平。
從投資的角度看。2020年二季度,投資對經濟的恢復起到了絕對的拉動作用,但是到2021年對經濟增速的拉動作用就非常小了,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只有13.7%,不僅遠遠低于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65.4%,而且低于進出口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20.9%。在“三駕馬車”中,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最小的,特別是到2021年四季度,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11.6%。
從進出口需求的角度看。從2020年下半年開始一直到2021年全年,進出口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非常突出的,去年是20.9%。但是今年的壓力會很大。一是因為發達國家的產能在恢復,二是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出口也在恢復。另外,2021年的基數比較高,今年回落的可能性很大。從今年1-2月份的數據已經可以看出,比去年同期有明顯的回落。
再從生產的角度看。有幾個行業值得關注:一是制造業。制造業在去年一季度增長26.8%,四季度增長3.1%,回落了23.7個百分點;二是建筑業。建筑業在去年一季度增長22.8%,三季度是-1.8%,四季度是-2.1%,回落了24.9個百分點;三是房地產業。房地產業在去年一季度增長21.4%,四季度是-2.9%,回落了24.3個百分點。這幾大行業增速的回落,都給2022年5.5%的經濟增長帶來挑戰和壓力。

盡管挑戰很大,但是北大國發院研究員、國家統計局原副局長許憲春教授認為,經過努力也是可以實現的。
從投資的數據看,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在今年1-2月份增長了12.2%,比去年全年加快了7.3個百分點。制造業投資保持高速增長,1-2月份增長了20.9%,會對2022年的經濟增長做出重要的貢獻;基礎設施投資在1-2月份增長了8.1%,比去年有明顯增長;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長了3.7%,雖然比去年回落了,但是降幅在縮小。從投資的角度看還是有望再回升的。
從工業來看,工業占GDP的比重高達30%,而規模以上工業占工業的比重超過90%,所以工業是很有代表性的一個行業。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在去年9月份只增長了3.1%,但10-12月份分別增長3.5%、3.8%、4.3%,今年1-2月份已經達到7.5%。可以看出,包括制造業在內的整個工業的增速在快速恢復。
從生產角度看,建筑業有可能會恢復正增長。而服務業中的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是很有代表性的行業。即使在2020年疫情最嚴重的時候,GDP下降6%以上,這個行業仍然在增長,對GDP有0.6個百分點的貢獻。而2021年的貢獻率達到17.2%。2022年仍然會保持較快的增長。隨著疫情的好轉,其他如批發零售、住宿餐飲、交通運輸、租賃和商務服務等行業可能還會得到恢復。
所以無論是從需求的角度還是從生產的角度,經過努力,5.5%的目標是有可能實現的。
5.5%的增長并不是一個容易達到的目標。過去兩年平均是5.2%,今年要提高到5.5%,還是有難度的。
基建投資是政府財政支持力度最大的,但是基建投資從2018年開始一路下行,每年也就在2%-3%,轉化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就是很小的數字。這里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經過20多年的高速發展,現在地方政府發現值得做的好項目越來越少,比如高鐵,中央已經發了文件,不能再以從前那樣的速度建了,因為很多高鐵線路是不賺錢的。二是,從2018年去杠桿以來,中央對地方政府去杠桿的要求越提越高。地方政府就陷入了兩難境地,一方面現在需要他們投資,但是中央政府給的資金支持又不夠,3.65萬億是不夠的,地方政府所要的投資是30萬億,這相當于好幾年的計劃。地方政府如果要想把這個項目做成,就得去市場上融資,就要負商業性債務,而中央政府不允許這么做。2020年,城投債增加了4萬多億,2021年上升到6-8萬億,而且都是商業性債務,期限都很短。地方政府如何償付?很明顯,又得來一次債務置換。這樣下去顯然是不行的。
過去兩年,出口增速很快,去年在20%以上,回到了本世紀前十年的水平。今年的增速大概率還會在10%-15%,但是折算成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大概就是1.5%-2%,剩下的得靠國內的需求。
投資上不去,出口貢獻有限,拉動經濟還得靠國內消費。怎么提升國內消費呢?北大國發院院長、南南學院執行院長、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姚洋教授認為,不能靠所謂的內生性消費,要刺激自主性消費,簡言之就是給老百姓發電子貨幣現金,并且要求必須三個月內花完。比如今年是3.65萬億,如果拿出三分之一,基本上每人可以分到1000元,這個消費是非常直接的,如果消費乘數是3-5的話,一下可帶動4.5-6萬億的消費規模。
把整個國內的消費激發起來,是今年保5.5%增長最重要的一個方面。
(本文根據3月15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舉辦的“中國經濟觀察報告會”整理,未經演講者本人確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