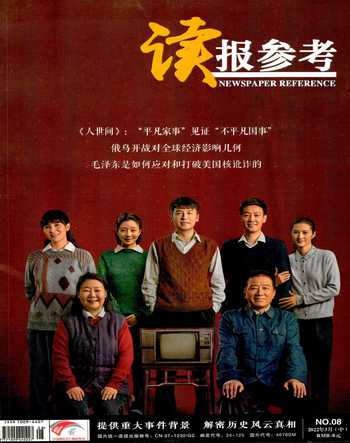毛澤東是如何應對和打破美國核訛詐的
趙叢浩
? 新中國成立后,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艱苦奮斗,自立自強,始終與威脅我國國家利益的風險挑戰作斗爭,有力維護了國家獨立和民族尊嚴。在這一歷史過程中,來自美國的核訛詐曾嚴重威脅了我國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和國家主權。對此,毛澤東沉著冷靜,多措并舉,領導我國應對和打破了美國的核訛詐,維護了我國國防安全和主權完整,充分展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遠見卓識和治國安邦之道。
恰如其時地作出研制核武器的戰略決策
1955年1月15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聽取關于原子能及其利用等問題的匯報,討論并作出發展原子能事業的戰略決策。毛澤東指出,原子能事業“這件事總是要抓的。現在到時候了,該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認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來”。
毛澤東之所以在這個時間節點作出發展原子能、研制核武器的戰略決策,是結合我國面臨的風險挑戰、自身發展條件等一系列因素后,慎重作出的。
當時我國的國內外局勢頗不平靜。國際方面,美國對剛剛建立只有數年的新中國頻繁施加核訛詐。如在抗美援朝戰爭爆發之初,美軍在中國人民志愿軍的打擊下節節敗退,為了挽回敗局,美國政府就揚言在朝鮮戰場使用核武器。隨著抗美援朝戰爭的進行,盡管美國在常規武器裝備上擁有絕對優勢,卻未能打贏戰爭,也就促使其將最后希望寄托在核武器上。如在朝鮮停戰談判期間,美國為了攫取對自身有利的談判結果,就威脅對朝鮮戰場和我國大陸地區使用核武器。國內方面,盤踞在臺灣等東南島嶼的國民黨反動派和國內其他地區的殘余反革命勢力,與境外反華勢力頻繁勾結,妄圖憑借所謂“第三次世界大戰”與“核優勢”死灰復燃。
? 為了保衛人民政權,維護來之不易的主權獨立和人民自由,我國不能任人宰割,帝國主義者也決不會自動放下武器。因此,要實現和平、維護和平,就必須具備消滅敵人、打贏戰爭的能力。這就要求新中國必須掌握自己的核武器,增強保衛自己的底氣與威懾侵略者的能力。正是在這種局面下,毛澤東指出,“原子彈、氫彈、導彈,我們都搞出來了,世界大戰就打不成了”“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
此外,毛澤東還有更加深遠的戰略考量,那就是通過研制核武器,推動我國的科學技術大發展,助力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新中國成立后,尚在醫治多年的戰爭創傷時,一些世界大國就已經邁入了“原子時代”“噴氣時代”的門檻,我國迫切需要在科學技術領域縮小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1955年3月,毛澤東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對全黨提出:“我們進入了這樣一個時期,就是我們現在所從事的、所思考的、所鉆研的是,鉆社會主義工業化,鉆社會主義改造,鉆現代化的國防,并且開始要鉆原子能這樣的歷史的新時期。”研制核武器這類高精尖武器,無疑正是順應時代潮流,有利于大力帶動我國現代科學技術向前發展,從而為迅速恢復和發展生產力奠定深厚基礎,對整個國民經濟的長遠健康發展十分有益。
實事求是地根據國情提出應對核訛詐的多層次準備
在打破核訛詐方面,研制并掌握核武器無疑是極為有效的方式,但不管手中有無核武器,新中國都決不屈服于核訛詐,而是從國家整體戰略出發,制定符合國情特點、能夠發揮自身優勢的對策措施。這就是毛澤東指出的:“我們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讓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彈,我打手榴彈,抓住你的弱點,跟著你打,最后打敗你。”
? 新中國奉行防御性的國防戰略。從這一前提出發,要應對和打破核訛詐以及打贏核戰爭,就意味著我國必須在面對侵略戰爭時,以防御承受住敵人的第一擊。關于進攻和防御的關系,毛澤東以辯證的觀點明確指出:“世界上的事情,總是一物降一物,有一個東西進攻,也有一個東西降它。”也就是說,有進攻就有防御,進攻和防御各有長短,在一定條件下,二者還可以相互轉化。毛澤東結合兩次世界大戰的歷史,從戰略角度作出論證,兩次戰爭“都是防御者勝利,進攻者失敗”。以進攻實施侵略,不得人心,注定失敗;以積極的防御實施自衛戰爭,是保家衛國的正義之舉,必然勝利。但是,勝利不是自然而然或輕易就能取得的,只有積極行動,提前部署,才能保存自己、消滅敵人。對于核打擊,如果預先做好防御,是可以大大減輕其造成的損害的。因此,毛澤東指出,“戰爭歷來都需要攻防兩手”,既然在進攻武器方面,“比原子彈的數量,我們比不贏人家”,那么必須“要注意防御問題的研究”“要搞地下工廠、地下鐵道,逐年地搞”。
? 核武器的特點是適于打擊高價值目標集中的區域。由于新中國成立后,工業設施大都集中于東北、沿海等少數地區,毛澤東曾擔心敵人用10顆原子彈就可以摧毀我國的工業中心,嚴重破壞我國工業骨干力量,大幅破壞我國現代化建設成果。因此,利用我國大縱深國土空間和自然地理特點,分散布置工業設施和人力資源,是應對核戰爭的必要手段。1960年代中期,毛澤東著眼以戰略防御應對帝國主義可能發動的侵略戰爭,統籌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布局,提出實施三線建設的設想,力求建設鞏固的戰爭大后方。黨中央據此作出了開展三線建設、加強備戰的重大戰略部署。毛澤東指出,“在原子彈時期,沒有后方不行的,要準備上山,上山總還要有個地方”,通過三線建設,“把鋼鐵、國防、機械、化工、石油基地和鐵路都搞起來了,那時打起來就不怕了”。后來,他在聽取制定“三五”計劃情況時,專門指出要重視防御核打擊的問題。
? 擁有核武器、做好防御等反侵略準備,是應對和打破核訛詐的有效方式,但敵人不會等待我們一切準備就緒才發動進攻。事實上,正是由于我國沒有掌握核武器,缺乏抗打擊能力,美國才會有恃無恐地頻頻對我國施以核訛詐。毛澤東就這種情況指出,“我們現在只有手榴彈跟山藥蛋。氫彈、原子彈的戰爭當然是可怕的,是要死人的,因此我們反對打。但這個決定權不操在我們手中,帝國主義一定要打,那么我們就得準備一切,要打就打”“就用常規武器跟他們打”。也就是說,即便沒有核武器,面對侵略,中國人民也決不會束手投降,而是會根據自身實際,在反侵略戰爭中揚長避短,將手榴彈等手中可用的常規武器的最大效能發揮出來。當然也要看到,常規武器和核武器一樣,都不能包打天下,二者各有優缺點。但總體上看,以常規武器應對核武器是以弱敵強的不對稱舉措。如1957年5月,毛澤東在會見外賓時就指出:“我們軍隊現有的這些武器,對付原子彈是沒有辦法的。所以要提高武器的質量,減少人數。”此外,毛澤東一直認為核武器的主要作用是“嚇嚇人,壯壯膽”,判斷未來發生的戰爭依然是常規戰爭。他引用時任美國三軍參謀長泰勒所寫的《音調不定的號角》一書,指出,美國雖然作了核戰爭和常規戰爭兩手準備,但他們的方針還是打常規戰爭,以此強調我國為打好反侵略的常規戰爭作好充分準備,不僅僅是未掌握核武器條件下以弱敵強的無奈之舉,也是針鋒相對地遏制美國發動常規戰爭,進而遏制其發動核戰爭的必然之舉。
廣交朋友,在全世界筑起反對核訛詐之“墻”
? 核武器誕生后,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僅僅掌握在美國等少數幾個大國手中,成為它們干涉他國內政、破壞世界和平的工具。因此,反對核訛詐和核戰爭,不僅是我國維護主權完整和國防安全的迫切需要,而且是世界大多數國家和民族反對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維護自身獨立與自由的必然要求。如時任世界保衛和平委員會主席的弗雷德里克·約里奧·居里就旗幟鮮明地反對美國的核訛詐政策。
? 約里奧·居里于1951年6月的一天,約見即將回國的中國科學家楊承宗時說:“你回去轉告毛澤東,你們要保衛和平,要反對原子彈,就要自己有原子彈。原子彈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彈的原理也不是美國人發明的。”不僅如此,他還幫助新中國的科學家在歐洲購買開展核武器研制所需的器材和圖書,為我國原子能事業的起步作出了貢獻。
對此,毛澤東抓住要害,闡明了全世界最大多數人民追求和平的共同愿望,深刻地指出:“世界人民是反對用原子彈殺人的。”他主張團結世界上一切可能的力量共同反對核訛詐和核戰爭,把這項工作比喻成“筑墻”,提出努力團結更多力量、爭取更多支持,“把墻筑高筑厚”。1954年10月,毛澤東就指出,新中國“雖然號稱大國,但是力量還弱。在我們面前站著一個強大的對手,那就是美國。美國只要有機會,總是要整我們,因此我們需要朋友”。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在應對和打破核訛詐方面,這一問題同樣十分重要。那么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團結的對象?毛澤東認為,美國人民和中間地帶國家都是我們可以爭取、團結和聯合的對象。他強調,“美國內部也是有矛盾的”“對美國這樣的國家也不是沒有文章可做”,要把美國人民和美國的帝國主義分子區分開來,“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國人民都是我們的朋友”。他還指出,亞非拉國家要“普遍地保衛和平,反對戰爭,反對殖民主義,反對戰爭集團,反對使用原子彈和氫彈”。對于資本主義國家,毛澤東也認為有團結其力量的可能。比如,盡管日本是美國的盟友,但“日本人民,包括某些政府人士也反對核戰爭”。毛澤東多次指出,由于美國與中國等國不直接接壤,因而美國若發動戰爭,必將首先針對“中間地帶”,目標是占領中間地帶國家,“欺負它們,控制它們的經濟,在它們的領土上建立軍事基地,最好使這些國家都弱下去”。到了1960年代,毛澤東進一步明確指出“中間地帶”的范圍:“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個中間地帶;歐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個中間地帶。日本也屬于第二個中間地帶。”
? 這一系列論斷是毛澤東科學研判各國力量消長、世界戰略形勢及其發展變化趨勢后,針對美國戰略政策及其影響作出的,已被歷史證明是符合實際的正確判斷。與我國具有不同發展水平、不同歷史文化背景,尤其是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政治立場的中間地帶國家,毛澤東都認為有團結的可能。他結合世界形勢的變化指出,“幾個大國要控制小國是不行的”,西方國家所謂的團結也只是“在美國的控制之下,在原子彈下面要求它的大小伙伴們向美國靠攏,交納貢物,磕響頭稱臣”,這“勢必走向所謂團結的反面——四分五裂”。由于美國的擴張政策,一些資本主義國家也不愿參與美國挑起的沖突,但作為美國的盟友,也很可能因美國的軍事冒險而被動卷入戰爭,甚至全面核戰爭。如1950年代,以美國為主的北約軍隊的作戰計劃完全是“建立在使用原子和熱核武器”上,但根據模擬計算,“即便是在最好的設想情況下,看來也將會有200萬至2000萬歐洲人死亡”,這使得一些歐洲國家領導人意識到戰術核武器的使用“將不能防衛歐洲,而是要毀掉它”。新中國奉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認為國家不分大小、強弱一律平等。但是,美國以應對蘇聯為理由,在雙方戰略核力量趨于平衡后,仍然大量擴充核武庫,大大增加了對中間地帶國家的軍事優勢,逼迫其向自己靠攏,必然引發包括其盟友在內的中間地帶國家的反對。
? 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新中國在1960年代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第一顆氫彈,并成功完成空投核試驗、導彈核試驗等相關任務,具備了核武器實戰能力,從而徹底打破了美國的核訛詐。但這一過程是艱難的。毛澤東用全面、發展的觀點看問題,在對我國國情和世界戰略格局的精準分析、把握與預判中,著眼應對和打破美國的核訛詐,不僅高瞻遠矚地作出研制核武器的戰略決策,堅持辯證思維和底線思維,在物質和精神兩個層面積極主動作為,把核訛詐這一外部風險挑戰,化為我國現代化建設的一次歷史機遇,團結教育了全黨全國各族人民,調整了全國產業布局,推動了我國科學技術發展和人才隊伍培養,促進了國防和軍隊建設均衡發展,擴大了國際影響力,彰顯出毛澤東巨大的勇氣和智慧。
(摘自《黨史博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