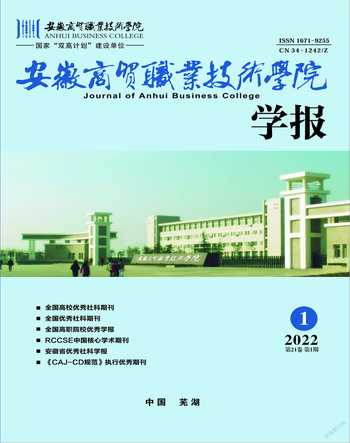從女性主義視角看莫言小說中的女性人物形象
楊陽
摘? 要:在中國現(xiàn)當(dāng)代文壇,莫言是一位具有旺盛創(chuàng)作力的天才作家。他筆耕不輟,寫出了《天堂蒜薹之歌》《蛙》《紅高粱家族》《豐乳肥臀》等一系列小說。在莫言幾乎所有的小說中都刻畫了諸多形象豐滿、個性鮮明的女性人物形象。基于女性主義視角解讀莫言小說中偉大無私的母親形象、勇于擔(dān)當(dāng)?shù)钠拮有蜗笠约蔼毩⒆灾鞯膫€體形象,并從早年生活經(jīng)歷的影響、對女性生存現(xiàn)狀的關(guān)照以及鄉(xiāng)土文化的浸潤三方面來探究莫言筆下女性形象塑造的主要成因。這些充滿自我解放意識的女性形象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
(三)獨立自主的個體形象
莫言筆下的女性獨立果斷、敢愛敢恨,即使出生低微,遭遇命運的無情捉弄,也不愿向殘酷的現(xiàn)實低頭。《紅高粱家族》中,“我奶奶”被貪財?shù)母改冈S給了將死的單扁郎,不甘于將自己的一生交給一個麻風(fēng)病人。在出嫁的轎子里,她與健壯、勇敢的轎夫余占鰲互生情愫。在三日后回門的路上,當(dāng)余占鰲把“我奶奶”從毛驢背上劫到高粱地里,她沒有抗拒,而是拋棄了所謂的倫理道德,大膽追求屬于自己的幸福。“我奶奶”臨死前對天呼告:“天,什么叫貞節(jié)?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惡……我的身體是我的,我為自己做主。”[9]這是一個敢于挑戰(zhàn)封建倫理、大膽追求自由和幸福的女人的吶喊,這一聲吶喊強烈批判了封建社會的倫理綱常,至今仍有著振聾發(fā)聵的效果。在面對日寇的侵略,看到羅漢大叔被殘忍殺害后,“我奶奶”主動走上了抗日的道路,不僅動員男人們上戰(zhàn)場殺敵,自己也親自參與戰(zhàn)斗,展現(xiàn)出超越傳統(tǒng)女人的見識與膽略。她幫助猶豫不決的余占鰲整頓軍紀,設(shè)計阻斷鬼子逃跑的路線,和同村的女人們在后方做飯送湯。正是在給余占鰲的隊伍送飯的路上,她遭到了日本鬼子的射殺,死的時候異常悲壯。《白棉花》中的方碧玉,年輕貌美、正直勇敢,而她的戀人李志高卻軟弱無能、毫無擔(dān)當(dāng),在兩人的戀情被發(fā)現(xiàn)后,連站出來庇護她的勇氣都沒有,而是躲到了干部子女孫紅花的背后。莫言借小說中馬成功的嘴感嘆道:“女人的愛情之火一旦燃燒起來,就很難撲滅;而男人,在關(guān)鍵時刻總是像受了驚嚇的鱉一樣,把膀子縮了起來”。[10]方碧玉為了愛情義無反顧、無怨無悔,無奈所托非人,結(jié)局令人嘆惋。小說《蛙》的主人公萬心是一名婦產(chǎn)科醫(yī)生,從十七歲開始就幫人接生,一生中迎接了成千上萬新生命的到來,被人親切地稱為“送子觀音”。與此同時,人口的迅速膨脹給經(jīng)濟社會帶來了巨大的壓力,計劃生育已成為基本國策。為了響應(yīng)國家的號召,她堅定地執(zhí)行著計劃生育政策,為人結(jié)扎、引產(chǎn),因而被一些人視為“殺人惡魔”。其實,她自己的內(nèi)心也備受煎熬,但是為了大局,為了國家和民族的未來,即使人們對她惡語相向,她仍然無怨無悔地履行著自己的職責(zé)與使命。她是一個有著濃郁的英雄氣息、充滿家國情懷和責(zé)任擔(dān)當(dāng)?shù)摹按髮懙呐恕薄?/p>
二、莫言小說中女性形象塑造的成因探析
(一)早年生活經(jīng)歷的影響
弗洛伊德指出:“早期的精神狀態(tài)可能在后來多少年內(nèi)不顯露出來,但隨時都可能成為頭腦中各種勢力的表現(xiàn)形式。”[11]由此可見,早年生活的記憶對一個人的一生有著難以磨滅的影響。在童年時期,由于調(diào)皮搗蛋、其貌不揚,莫言曾多次受到來自外界的嘲笑與欺凌。12歲時,莫言在工地當(dāng)小工,由于饑餓難耐,偷吃了生產(chǎn)隊地里的一根紅蘿卜,因此受到了工地領(lǐng)導(dǎo)的懲罰。這件事情給他幼小的心靈造成了一定的創(chuàng)傷,他于1985年創(chuàng)作的《透明的紅蘿卜》就是對這段經(jīng)歷的真實寫照。與男性相反,莫言身邊的女性總是對他溫和而友善,給他帶來了精神上的慰藉。其中,莫言的母親對于他的性格形成和后期的創(chuàng)作影響深遠。在莫言的記憶中,母親和藹可親、待人和善,對他十分寵愛,在生活上給予他無微不至的庇護。母親雖然是一個農(nóng)村婦女,但卻懂得尊重知識,竭盡所能地為孩子們提供良好的教育。母親身上的優(yōu)良品質(zhì)對莫言有著潤物無聲、潛移默化的影響,在他的人生觀、價值觀形成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母親去世后,莫言十分悲痛,一直想寫一部書獻給她,但是心中千頭萬緒,不知從何處提筆。1990年秋天的一個下午,在北京的一個地鐵口,他偶然看到一位農(nóng)村婦女坐在地上給兩個又黑又瘦的孩子喂奶,那位母親苦瘦的臉被夕陽照耀著,仿佛雕像般莊嚴神圣。這位母親的形象深深觸動了他,令他百感交集,忍不住淚流滿面。他頓時找尋到了靈感,把對母親的愛化作了寫作的動力,創(chuàng)作出《豐乳肥臀》這部鴻篇巨作。在該書的序言中,他寫道:“謹以此書獻給母親的在天之靈”。此后,他又創(chuàng)作出《糧食》《歡樂》《兒子的敵人》等作品,塑造了諸多淳樸善良、偉大博愛的母親角色,這些作品也是他為世間所有默默無聞、無私奉獻的母親們所做的贊歌。
(二)對女性生存現(xiàn)狀的關(guān)照
在我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女性終其一生都受到封建禮教的制約,“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很少有受教育的權(quán)利,在社會上幾乎沒有立足之地,只能淪為男權(quán)的附庸。20世紀早期的新文化運動使得以男女平等為核心的女性主義思潮傳入我國。新中國成立后,女性的地位不斷提升,毛主席提出“婦女能頂半邊天”的口號一時間響徹大江南北。由于“男尊女卑”等傳統(tǒng)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女性地位的改變與提升不是一朝一夕能夠?qū)崿F(xiàn)的,在現(xiàn)實生活中她們?nèi)曰蚨嗷蛏僭馐艿礁笝?quán)、夫權(quán)的壓制與束縛,這種現(xiàn)象在生產(chǎn)力和經(jīng)濟水平較為落后的農(nóng)村地區(qū)尤為明顯。莫言早年主要生活在家鄉(xiāng)高密,親眼看見了身邊女性的悲慘遭遇,包括自己的祖母、母親、姑姑等,對他們所經(jīng)受的苦難感同身受。他看到無論是男權(quán)文化的壓制,還是苦難現(xiàn)實的打擊,都沒有壓垮這些女性,她們抑或隱忍,抑或掙扎,抑或奮起反抗,在社會與歷史的夾縫中頑強地生存。莫言筆下女性形象的塑造很多是來源于對現(xiàn)實中女性生存狀態(tài)的體察。這些堅韌頑強、獨立勇敢的女性為他的小說創(chuàng)作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啟悟與靈感。
(三)鄉(xiāng)土文化的浸潤
莫言的故鄉(xiāng)在山東高密,這里地處膠東半島一隅,位于三個縣的交匯處,屬于古代齊國的領(lǐng)地。齊文化開放多元、灑脫奔放,婚戀觀念相對比較開放,高密的民間文化受齊文化的影響較深。故鄉(xiāng)的一人一事、一景一物都為莫言后期的創(chuàng)造帶來了源源不斷的靈感,其中,民間故事與傳說給莫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為其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的寶貴素材。距離莫言家鄉(xiāng)大約三百里地就是大作家蒲松齡的故鄉(xiāng)。蒲松齡《聊齋志異》中那些散發(fā)著自然美、人性美的花妖狐媚形象給莫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同于閨閣女子的膽怯與嬌羞,這些女子率真自然,從不忸怩造作,常常大膽、主動地追求愛情,而且比男子還要深情、果敢。葉舒憲先生在《閹割與狂狷》中指出:“從宋江到賈寶玉,中國文學(xué)史中的男性主人公的陽剛本性幾乎喪失殆盡……而在蒲松齡的狐鬼故事中,異類女子(不管是人是獸是仙是妖)已經(jīng)完全被表現(xiàn)為男主人公(往往是中性化的書生)的希望之星和拯救之神。”[12]莫言自己也曾說過:“讓我難忘的女性形象,不是貂蟬也不是西施,而是我們山東老鄉(xiāng)蒲松齡先生筆下的那些狐貍精。她們有的愛笑,有的愛鬧,個個個性鮮明,超凡脫俗……”[13]他在小說中營造的神秘氛圍以及刻畫的一些古靈精怪、個性張揚、敢愛敢恨的女性人物無疑受到了蒲松齡《聊齋志異》的影響。88BE0778-88A2-4018-9D86-1309C66DC97A
三、莫言小說中女性形象塑造的現(xiàn)實意義
在莫言的小說中,讀者看到的是一種“陰盛陽衰”現(xiàn)象,這種現(xiàn)象背后折射出作者創(chuàng)作的女性主義情結(jié)。在這種情結(jié)的支配下,莫言將自己的生命體驗融入對女性形象的塑造中,一改中國傳統(tǒng)文學(xué)中女性弱不禁風(fēng)的病態(tài)審美觀,打破了傳統(tǒng)文化中女性必須賢良淑德的角色定位。他筆下的女性勇于沖破世俗觀念與封建道德的枷鎖,渾身洋溢著蓬勃的生命力,充滿了原始的生命張力。這些女性勤勞勇敢、淳樸善良、敢愛敢恨、坦蕩無畏,具有鮮明的叛逆?zhèn)€性,顛覆了世俗與傳統(tǒng)的倫理觀念。莫言毫不吝惜自己對女性人物的溢美之詞,對她們勇敢叛逆、頑強不屈的生命力進行了濃墨重彩的書寫與贊揚。相反,其筆下的男性人物形象反而黯然失色,如上官家祖孫三人、羅小通、趙家父子等,膽小怯懦、生性愚鈍,一代不如一代,呈現(xiàn)出“種的退化”的傾向。
正如諾貝爾文學(xué)獎評委、瑞典文學(xué)院成員作家瓦斯特伯格在頒獎致辭中所言:“莫言是個詩人,他扯下程式化的宣傳畫,使女性從茫茫無名大眾中突出出來。”他對于莫言筆下女性形象塑造的價值給予了充分肯定。不論是寬厚堅忍的“大地母親”上官魯氏,敢愛敢恨、獨立自強的“我奶奶”戴鳳蓮,還是風(fēng)流俏麗的“狗肉西施”孫眉娘,為愛癡狂、無怨無悔的癡情女子方碧玉,現(xiàn)在讀來,她們的生動形象與個人魅力依然躍然紙間,具有深深的藝術(shù)感染力,成為當(dāng)代文學(xué)長廊中一道道靚麗的風(fēng)景,她們身上善良果敢、堅毅頑強的可貴品質(zhì)至今仍散發(fā)著女性自我解放的光芒。
參考文獻:[1]利沙·塔特爾.女權(quán)主義百科全書[M].倫敦:朗曼有限公司,1986: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