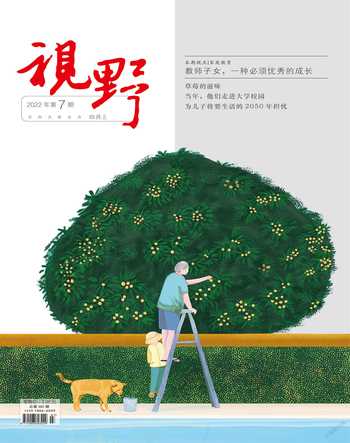當年,他們走進大學校園
姜猛

馮沅君,1900 年生,河南唐河縣人,1917 年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國文專修班。
1917年夏天,河南唐河縣祁儀鄉馮家,馮友蘭的妹妹馮沅君茶不思,飯不想。
馮沅君自幼學習古文,五六歲時就能吟詩填詞,還讀過私塾和學堂。后來,看到大哥馮友蘭和二哥馮景蘭先后考學離家,她也萌生了出外讀書的念頭。放暑假時,在北京大學讀書的馮友蘭帶回一個消息,說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新增設的國文專修班面向全國招收四十名學生。馮沅君聽后欣喜若狂。
母親聽說女兒想報考京城的學校,擔憂道:“你纏了腳,還許配了人家,能跑那么遠的路?”馮沅君很堅決地說:“能!”母親猶豫了半天,勉強同意了。就這樣,馮沅君在哥哥馮友蘭的陪同下趕往省城開封應試,最終以一篇極富才情的文章一舉考中,成為中國第一批文科女大學生。
9月中旬,馮沅君跟著哥哥馮友蘭、馮景蘭一起來到北京。初入大都市,她看什么都覺得新鮮:那兩個細細圓圓的輪子,怎就能馱著人往前跑而不會倒?那沒有纏腳的妙齡女子,走在大街上果真是輕快飄逸……
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首屆國文專修班的四十人中,北京本地學生十三人,其余多是各省省城考生,只有馮沅君一個人來自偏遠的鄉村。同學們給一身土布衫褲的她起了個綽號叫“鄉下妞”,但這個“鄉下妞”在第一堂課上就鎮住了全班同學。當時,顧震福教授歷代文選課,開講前讓大家自行選背一篇不少于三百字的名篇佳作,只有馮沅君一人站起來,從容背出了東漢王粲的《登樓賦》。
作為中國第一所國立女子高等學府,當時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會聚了多位“新潮派”和“歐美派”教師。受他們的教誨和引導,馮沅君積極投身各種活動,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急先鋒”。有兩件事使她名震京華:1919年6月1日,北京多校學生約定4日凌晨齊聚新華門上書總統府。馮沅君是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演講團成員,她帶領學生砸開校門,向新華門進發。這惹惱了校長方還,他揚言要開除參加示威游行的學生。馮沅君執筆起草了《驅方宣言》,細數方還十大罪狀,要求撤換校長。是年7 月,北洋政府教育部撤掉方還并任命了新的校長。另一件事發生在1920年秋天,國文專修班學生李超因不滿包辦婚姻郁積而死。此事激起馮沅君對封建禮教的憎惡,她把古樂府詩《孔雀東南飛》改編成宣揚戀愛和婚姻自由的話劇搬上了舞臺,全城巡演,在廣大北京市民中產生巨大影響。李大釗觀后拊掌贊嘆此劇“比任何政治家的演說都見效”。
1922年,馮沅君從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畢業后,以優異成績考取北京大學國學門攻讀古典文學碩士,又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女研究生。
季羨林,1911年生,山東清平縣(今臨清市)人,1930年考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
1930年的夏天,對于出身貧困家庭的十九歲小伙子季羨林來說,太陽火辣得令他窒息。
事情得從頭說起:6月,季羨林從山東省立濟南高中畢業。為搶到一只“鐵飯碗”,他遵從父親和叔叔的嚴令先后參加了濟南郵政局和山東鹽務稽核所的招工考試。當時,郵政局、鐵路局和鹽務稽核所是旱澇保收的單位,進其中任何一家做工都能衣食無憂。季羨林的文化課成績名列前茅,但面試時老外考官看他不像那塊材料,先后把他“斃掉”了。不得已,季羨林只好另尋出路,最后決定進北京投考大學。
那時,北京有很多大學都在招生,但需要繳納報名考試費用。季羨林攜帶盤纏不多,只報考了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最后,兩所大學都錄取了季羨林,而季羨林出于留洋“鍍金”(清華的前身是留美預備學堂,專門培養并輸送青年學生到美國學習,學成后可進入大學做教授,端上“好飯碗”)考慮,選擇了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成為錢鍾書和萬家寶(曹禺)的學弟。
秋天開學后,季羨林很快融人大學生活。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教授陣容強大,有陳寅恪、吳宓、葉公超、溫德等中外著名教授為他們授課。
陳寅恪是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主講“佛經翻譯文學”課程。他要求學生“凡上這門課者,先去買一本《六祖壇經》”。季羨林跑了很多書店都沒有買到,最后還是從一座寺廟住持那里借得了一本。陳寅恪在課堂上總能提出新穎的見解,令人茅塞頓開。季羨林經常研讀陳寅恪的學術論文,或邀約同學前往王靜安先生紀念碑前共同誦讀陳寅恪撰寫的碑文,以此繼續“向陳老師學習”。
朱光潛是北京大學的教授,在清華大學中文系兼課,主講“文藝心理學”課程。他上課不用講義,直接口述,吩咐學生記筆記。上了幾堂課后,季羨林發現,朱光潛講課時從不直視學生,而是兩眼往上盯著天花板的某一處地方,將西方哲學、西方美學流派和中國的老子、莊子、孟子以及古體詩詞娓娓道來,沒有一句廢話,令學生大呼過癮。聽得多了,季羨林對朱光潛的許多理論比如“感情移入說”等銘記于心,以至于時隔多年仍認為“是真理,不能更動”。
后來,季羨林追憶這段歲月時如是說:“陳、朱二師的這兩門課,使我終生受用不盡……如果說我的所謂‘學術研究’真有一個待‘發’的‘軔’的話,那個‘軔’就隱藏在這兩門課里面。”
汪曾祺,1920年生,江蘇高郵人,1939 年考入西南聯合大學中國文學系。
與季羨林的刻苦學習相比,后來成為著名京派作家的汪曾祺則完全是另一副狀態。
1938年,汪曾祺斷斷續續地讀完高中后,隨家人藏身于家鄉高郵一個小村莊里躲避戰亂。那時,他很想上大學,聽人說北京大學的學生上課自由、考試隨意,更是對北大向往至極。1939 年夏天,汪曾祺得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在云南昆明聯合成立了西南聯合大學,決定前去投考。
其時,日本侵華,烽煙四起。為安全起見,汪曾祺選擇從上海搭船,經香港到越南海防,然后乘坐滇越鐵路火車往昆明。不想,在走滇越段時,汪曾祺染上了惡性瘧疾,上吐下瀉,持續高燒,他一度甚至考慮“要不要給家里寫一份遺書”。好在疾病痊愈,他最終考進了西南聯合大學中國文學系。
那時,日軍戰機經常飛臨昆明上空。一次,在刺耳的警報聲中,汪曾祺跟著大伙兒拼命往郊外跑。返城時,他邊走邊看,發現昆明的街市、風土、書肆、衣食等與家鄉高郵大不一樣。這異鄉風貌吸引了他,此后他常常逃課出去逛街。
清早,汪曾祺夾著書離校,逛累了就尋一家心儀的茶館,坐下來喝茶、聽曲、吃餅、看書,有靈感了就寫文章,直至夜幕降臨才返回學校。日復一日,汪曾祺跑遍了昆明的大街小巷,也結識了不少“同好”。后來,他在《泡茶館》中寫道:有一個陸姓的同學,真是泡茶館冠軍。有一個時期,他盥洗用具就放在這家茶館里。一起來就到茶館里洗臉刷牙,然后坐下來泡一碗茶,吃兩個燒餅,看書。一直到中午,起身出去吃午飯。吃了午飯又是一碗茶,直到吃晚飯。晚飯后,又是一碗茶,直到街上燈火闌珊,才夾著一本很厚的書回宿舍睡覺。
這個陸姓同學身上,就有汪曾祺自己的影子。
在這種閑逛中,汪曾祺發現并經歷了許多美好的人和事,待經過心與腦的醞釀和打磨后,就成了流淌于筆尖的優美文字。
雖然西南聯合大學學風自由,但對于汪曾祺的連番逃課,還是有教授忍無可忍,朱自清就是其中一位。每次上課前,朱自清都會點名,發現汪曾祺不在,就趁晚間找到汪曾祺的宿舍,當著大家的面批評他,語氣嚴厲,毫不留情。然而汪曾祺依然如故。
聞一多就比較寬容,上課不點名,課下不批評,只是私下里找到汪曾祺,要求他“能寫出好文章就行”。汪曾祺也很爭氣,不斷在校刊《文聚》上發表小說和詩歌,漸漸成為西南聯合大學的才子。
不過,汪曾祺從不逃沈從文的課。大一時,汪曾祺聽了沈從文的一堂課,深為沈從文的語言和風格所吸引。到大二時,汪曾祺一口氣選修了沈從文三門課,每次上課總是提前進教室坐在最前排。汪曾祺寫出文章后,也總是先拿給沈從文看。沈從文詳加批注,遇到好文更會推薦給報社和雜志社的朋友,請他們幫忙發表。這令汪曾祺大為感動,兩人由此建立了深厚的師生兼朋友情誼。
逃課的后果是,1945 年,在留級一年后,汪曾祺還是沒有考過所有必修課程,也就無法獲得西南聯合大學的畢業證書。離校后,他前往上海,但因沒有文憑,找工作時四處碰壁。絕望中,他給沈從文寫信,傾訴苦痛,感嘆不如一死了之。沈從文很快回信,臭罵了他一頓后說了一句:“你怕什么?你手里有一支筆!”這句話震醒了汪曾祺。自此,他埋頭寫作,很快寫出了《雞鴨名家》《戴車匠》等小說。1949年4月,巴金主編“文學叢刊”時,選了汪曾祺的八篇小說結集為《邂逅集》出版,這是他的第一本小說集。從此,汪曾祺開啟了新的人生航向,最終成為“汪是一文狐,修煉成老精”(賈平凹語)。
莫言,本名管謨業,1955年生,山東省高密縣(現高密市)人,1984 年考入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
張藝謀導演的電影《紅高粱》,改編自剛剛從大學畢業的莫言寫的一部中篇小說。
作為一個出身中農家庭的孩子,莫言上大學的夢想發端于少年時代:20世紀60年代初期,莫言的大哥考入華東師范大學,在村里引起轟動。那段日子,村鄰們羨慕不已:“別看這家房子破,可是出過大學生的!”“這家是老中農,竟然出了一個大學生!”莫言心里很得意。寒假時,大哥回來過年。有一天,莫言偷偷摘下大哥衣服上的校徽戴在了自己胸前,跑出去到處炫耀。有小伙伴哂笑道:“是你哥上大學,又不是你上,你燒包什么?”莫言立刻泄了氣。從那一刻起,他暗下決心:我要好好學習,爭取像哥哥一樣考上大學,當一名真正的大學生。然而,世事難料,幾年后,“文革”爆發,大學停止招生,他亦因出身中農家庭而失學。他雖氣憤,但又無可奈何,只好找沒人的地方讀書解愁。
后來,大學開始招收工農兵學員。根據招生簡章,莫言判定自己不屬于“地富反壞右”分子,并且勞動積極,就興沖沖地跑去公社懇請推薦參加考試,結果被公社領導一句“沒有名額”頂了回來。
1973年6月,發生了張鐵生的“白卷”事件。莫言似乎看到了希望,決定效仿之,便給時任教育部部長的周榮鑫寫信,表達自己想上大學的強烈愿望。不久,莫言收到了回信。大意是說:希望在農村安心勞動,好好表現,等待貧下中農的推薦。雖是套話,但莫言大受鼓舞,隨后接連給省、地、縣、公社的招生領導小組寫信,但再無回音。村里人知道了這事,一見他就說:“你這樣的能上大學,連圈里的豬也能上!”莫言聽了傷心地號啕大哭。
直到1976年,數度因出身被刷下來的莫言,借著公社武裝部部長的兒子參軍的機會一道“混”進了部隊。
在部隊時,莫言在參加軍事訓練之余,閱讀了大量文學、哲學和歷史類書籍,這為他從事文學創作奠定了堅實基礎。1981 年,他在《蓮池》發表了處女作短篇小說《春夜雨霏霏》,隨后又陸續發表了《售棉大路》《民間音樂》等作品,其中《民間音樂》還得到了著名作家孫犁的好評。這時期,中國恢復高考制度,莫言的大學夢想再度被點燃。
1984年,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恢復招生。莫言得到消息時,報名工作已經結束。他帶著幾篇發表的作品,匆匆找到了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主任徐懷中。徐懷中看了他的作品,直接交代招生人員:“給他報上名。即便文化課考試不及格,我們也要了。”人幫天也助。文化課考試時,莫言從容做完了語文和政治試卷,但在做地理試卷時被“與我國接壤的國家有哪些?”一題難住了。他無意中一抬頭,看到教室的黑板正上方赫然掛著一幅世界地圖和一幅中國地圖,心里竊喜,飛快寫出了答案。就這樣,莫言以作品最高分和文化課考試第二名的優異成績考進了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這一年,他二十九歲,距他心中生發大學夢想過去了整整二十年。
在大學里,莫言和李存葆、李荃、宋學武、錢剛同班同宿舍。李存葆、李荃來自濟南軍區,宋學武來自沈陽軍區,錢剛來自南京軍區,都已獲得過文學大獎。那時,他們的生活既簡單又瘋狂,白天上課,晚上大家哪兒也不去,就貓在宿舍里寫作,你寫你的我寫我的。寫到半夜寫累了,就用“熱得快”煮方便面吃。有一次,外邊瘋傳方便面要漲價,四個人湊錢一下子買了幾大箱整整八十包囤著,足足吃了兩個月。后來,每當回想起這一幕,莫言就“嘿嘿”直笑,說那是人生中最美好最難忘的時刻。
也正是這種緊張而充實的學習,令莫言的寫作水平得以突飛猛進:1985 年,他發表了中篇小說《透明的紅蘿卜》,這是他的成名作;1986 年,他發表了在文壇引起轟動的中篇小說《紅高粱》,次年被張藝謀改編成電影后,一舉斬獲了第三十八屆柏林國際電影節金熊獎。
自此,莫言在文學道路上越走越順,一篇篇優秀小說接連出爐,2012年成功摘取諾貝爾文學獎桂冠,成為第一位獲得該獎項的中國人。
(余娟摘自《名人傳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