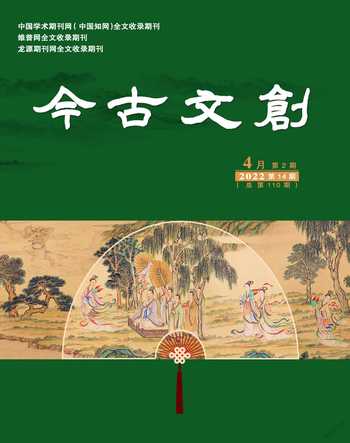淺析扎米亞京戲劇《洞穴》的悲劇性
【摘要】 俄羅斯白銀時(shí)代作家扎米亞京的短篇小說(shuō)《洞穴》改編為戲劇后,重構(gòu)了原小說(shuō)的一些情節(jié),一定程度上增強(qiáng)了小說(shuō)原有的悲劇性,將情節(jié)立足于人物的對(duì)話,深化了人物與人物、人物與環(huán)境的矛盾沖突。本文結(jié)合時(shí)代背景,通過(guò)文本分析法解讀《洞穴》戲劇內(nèi)容及對(duì)比在小說(shuō)情節(jié)上的改變等,分析其作品的悲劇色彩及藝術(shù)特色。
【關(guān)鍵詞】 戲劇;扎米亞京;《洞穴》;悲劇性
【中圖分類號(hào)】I106? ? ? ? ?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 ? ? ? ? 【文章編號(hào)】2096-8264(2022)14-0007-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14.002
葉甫蓋尼·伊萬(wàn)諾維奇·扎米亞京(1884-1937)是20世紀(jì)俄羅斯文壇上一位杰出的作家、批評(píng)家,被人們尊稱為“語(yǔ)言藝術(shù)大師”。他的一生創(chuàng)作時(shí)間并不算長(zhǎng),只有二十幾年,但他卻在二十世紀(jì)俄羅斯文壇中占據(jù)著獨(dú)特的位置。他的長(zhǎng)篇小說(shuō)《我們》被認(rèn)為是20世紀(jì)的第一部反烏托邦作品,并與奧爾多斯·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1932年)和喬治·奧威爾的《1984》(1949年)一起被譽(yù)為世界著名的反烏托邦文學(xué)三部曲。《洞穴》這部戲劇是扎米亞京于1928年改編自他創(chuàng)作于1920年的同名小說(shuō),通過(guò)短短兩幕的情景展示了十月革命后的俄羅斯正經(jīng)歷“戰(zhàn)時(shí)共產(chǎn)主義”政策下的物資匱乏,展現(xiàn)了20世紀(jì)初知識(shí)分子艱難、矛盾的處境,探討了人性在極端環(huán)境下的異化與掙扎。戲劇在小說(shuō)的基礎(chǔ)上進(jìn)行了一定情節(jié)的變動(dòng),將小說(shuō)的內(nèi)容刻畫到人物的對(duì)白中,使戲劇的沖突更為凸顯,使作品悲劇性的塑造更為深刻。
一、創(chuàng)作背景——悲劇的源泉
扎米亞京曾在《在后臺(tái)》一文中回憶起自己創(chuàng)作《洞穴》的起因:“1919年,冬天,夜班,在室外。跟我一同值班的同事,一位凍餓交加的教授,抱怨自己的身體狀況:‘哪怕只是偷點(diǎn)劈柴呢!可最痛苦的是我辦不到,即使去死,我也不會(huì)去偷。’第二天,我坐下來(lái)寫小說(shuō)《洞穴》。” ①1920年創(chuàng)作的小說(shuō)是戲劇架構(gòu)的雛形。這一時(shí)期的俄羅斯正處于“戰(zhàn)時(shí)共產(chǎn)主義”時(shí)期,物資極度匱乏,人民忍饑挨餓,戲劇中也體現(xiàn)了這一背景,比如馬丁的一段對(duì)白:
(第一幕)
馬丁·馬丁諾維奇(繼續(xù)):嘿,你看我,難道有人會(huì)相信我曾經(jīng)坐在寬敞的大廳里彈鋼琴,人們鼓著掌,笑著鬧著,歡呼著嗎?連我自己都不信,我知道我是個(gè)穴居人,是個(gè)野蠻人——我們都是。現(xiàn)在我們需要什么?是爐火、食物……今天有5個(gè)土豆,不是冷凍的,是新鮮的,我就很幸福了……可明天呢……可什么是“明天”呢,只有今天……像“明天”“后天”這種東西,人類還要過(guò)個(gè)一千年才能搞明白……
戲劇與小說(shuō)不同之處就在于戲劇僅依靠人物的對(duì)白和動(dòng)作推動(dòng)情節(jié),闡明背景,而沒(méi)有第三人稱的敘述,因此只能將背景通過(guò)人物的對(duì)話表現(xiàn)出來(lái)。從馬丁的對(duì)白可以看出,馬丁曾經(jīng)也是一個(gè)知識(shí)分子,生活優(yōu)渥,受人追捧,而現(xiàn)在他卻窮困潦倒,只要有5個(gè)新鮮的土豆就很滿足,缺乏最基礎(chǔ)的生存物資“爐火”“食物”,他自稱為“穴居人”“野蠻人”,對(duì)“明天”,即未來(lái)毫無(wú)憧憬,甚至可以稱之為絕望,可見(jiàn)“戰(zhàn)時(shí)共產(chǎn)主義”政策下知識(shí)分子艱難的處境。可以說(shuō)《洞穴》這部作品是扎米亞京短篇小說(shuō)的巔峰之作之一,他在戲劇中無(wú)法像在短篇小說(shuō)中一樣,運(yùn)用大量“隱喻”,用“洞穴”暗示當(dāng)時(shí)的彼得堡、用“馬丁和瑪莎”暗示那個(gè)時(shí)代知識(shí)分子的一種普遍的狀態(tài),只有巧妙地將背景融入到人物的對(duì)白中,由主人公自己將他們窘迫、無(wú)助的生活說(shuō)出口,這極大地加深了戲劇的悲劇性。
二、矛盾沖突——悲劇性的塑造
按照傳統(tǒng)的戲劇理論來(lái)講,構(gòu)成戲劇的第一要素就是戲劇沖突,也就是說(shuō)沒(méi)有矛盾與沖突,也就構(gòu)不成所謂戲劇。《洞穴》這個(gè)標(biāo)題就蘊(yùn)含著矛盾與沖突,作品的故事背景是在1920年的圣彼得堡,20世紀(jì)的彼得堡已經(jīng)屬于現(xiàn)代社會(huì)了,但作者卻將標(biāo)題定為“洞穴”這樣一個(gè)帶有石器時(shí)代氣息的名字,這即是矛盾之一。作者借“石器時(shí)代”的荒涼、難以生存這一特性,影射了當(dāng)時(shí)彼得堡人民的困窘的生活,其原因有二:語(yǔ)言上的創(chuàng)新,將熟悉的話題陌生化,更好地傳達(dá)所談事物的特征,“石器時(shí)代”與現(xiàn)代文明形成強(qiáng)烈的對(duì)比,暗指人民過(guò)著近乎原始的貧困生活;二是當(dāng)時(shí)俄羅斯嚴(yán)格的書刊檢查制度,迫使作者只能借古諷今,虛實(shí)相間 ②。
戲劇沖突主要表現(xiàn)為三種形態(tài):其一,劇中人物由于目的和動(dòng)機(jī)不同,交織成了人與人之間錯(cuò)綜復(fù)雜的矛盾沖突。或者,是由于劇中人物性格的差異,他們對(duì)待事物的態(tài)度、追求的理想、所采取的手段各不相同。而在相互撞擊中形成的人與人之間的沖突。《洞穴》中人與人之間的沖突③是相對(duì)直觀的,是在于身為知識(shí)分子的馬丁和鄰居奧別爾特舍夫之間的沖突。兩人產(chǎn)生矛盾是由于馬丁偷竊了奧別爾特舍夫家的柴,雖然兩人并沒(méi)有發(fā)生面對(duì)面的爭(zhēng)吵,但是毫無(wú)疑問(wèn)兩人是站在對(duì)立的立場(chǎng)上。馬丁在第一幕中曾向奧別爾特舍夫禮貌地借過(guò)柴,但奧別爾特舍夫卻在得到了馬丁的幫助時(shí)拒絕了他的請(qǐng)求,引發(fā)了馬丁偷柴的舉動(dòng),他們之間的矛盾是最直接的。
同為知識(shí)分子的馬丁和瑪莎同樣也有著矛盾,瑪莎想在自己命名日當(dāng)天和馬丁重溫往日的快樂(lè),她希望至少能在自己命名日那天屋子能溫暖一些、馬丁能像過(guò)去一樣為她彈鋼琴,但馬丁是無(wú)法滿足瑪莎的愿望的,他們已經(jīng)沒(méi)有柴了,這是瑪莎的需求和馬丁無(wú)法滿足的矛盾。與這種矛盾相類似的還存在于馬丁和居委會(huì)主席謝利霍夫之間,居委會(huì)主席謝利霍夫受到鄰居奧別爾特舍夫的委托來(lái)調(diào)解馬丁與其之間的問(wèn)題,要求馬丁歸還木柴,但在瑪莎命名日那天,馬丁已將木柴燃燒,無(wú)力償還,這是謝利霍夫的要求和馬丁無(wú)法滿足其要求的矛盾,這種矛盾是間接的,其根本還是指向馬丁與鄰居奧別爾特舍夫。
由此可見(jiàn),短短一篇二幕戲劇,四個(gè)主人公之間,馬丁作為劇情中心支撐的人物,與另外三人都有著或直接或間接的矛盾沖突,這就非常突出戲劇藝術(shù)的色彩,并為整部戲劇的悲劇性奠定了基礎(chǔ)。
其二,人物的思想、感情、意志、愿望和理想的不斷成長(zhǎng)變化與調(diào)整中形成的矛盾斗爭(zhēng),通過(guò)人物的獨(dú)白揭示出來(lái)的內(nèi)心沖突 ④。小說(shuō)中馬丁在偷柴之前有一段內(nèi)心的掙扎,但在戲劇中,這段內(nèi)心掙扎的部分變成通過(guò)人物動(dòng)作來(lái)展現(xiàn)。
(第一幕)
馬丁·馬丁諾維奇回到書房。瑪莎在睡夢(mèng)中喃喃發(fā)出囈語(yǔ)。馬丁·馬丁諾維奇在她身旁站了一會(huì)兒,雙拳緊握。他思考著。突然,他果斷地在已經(jīng)穿上的夏季大衣外面又套上一件大衣,往口袋里放了刀子和鉗子。鉗子掉落,在驚慌中僵住了。
通過(guò)在瑪莎身邊站了一會(huì)兒、雙拳緊握和思考這些動(dòng)作或狀態(tài)可以清楚地看出馬丁為了妻子不得不偷竊的內(nèi)心掙扎。作為一個(gè)接受過(guò)教育的知識(shí)分子,馬丁曾經(jīng)也生活優(yōu)渥、受人追捧,但如今饑寒交迫,為了滿足生病妻子的小小愿望,短暫的掙扎后,決定放下自尊去鄰居那里偷一點(diǎn)柴回來(lái)。而這是一種理想屈從于現(xiàn)實(shí)的悲哀。
其三,劇中人物與自然環(huán)境、社會(huì)環(huán)境之間形成的外部沖突。外部沖突在《洞穴》中更多的是社會(huì)環(huán)境造成的。在社會(huì)大環(huán)境下,忍饑挨餓、苦受嚴(yán)寒已經(jīng)是家常便飯,這個(gè)時(shí)代人人自危,大家在一個(gè)個(gè)“洞穴”中從“人性”走向“獸性”。瑪莎對(duì)過(guò)去的美好回憶即是這種沖突的體現(xiàn):
(第二幕)
瑪莎(對(duì)進(jìn)來(lái)的馬丁·馬丁諾維奇):我的信,這是給你的。你知道嗎,從我開(kāi)始讀信,我的心像瘋了似的,一切是如此清晰,如此清晰,好像不是五年,而是昨天……馬爾特,我親愛(ài)的,你還記得那天晚上:我的藍(lán)色的房間,鋼琴裝在套子里,在鋼琴上有個(gè)煙灰缸,還有馬頭形木雕,我的老天啊,一切都這樣清晰……我彈奏著鋼琴,你從后面走過(guò)來(lái),我第一次抬起了頭……(不再作聲)
這里作者花費(fèi)了大段篇幅讓瑪莎回憶往昔,讓瑪莎陷入對(duì)過(guò)去幸福生活的回想,與現(xiàn)實(shí)中的寒冷饑餓、走投無(wú)路形成了鮮明的對(duì)比。瑪莎對(duì)重回過(guò)去那樣美好時(shí)光的向往,與冰冷殘酷的現(xiàn)實(shí)環(huán)境之間有著激烈的矛盾沖突,但瑪莎只是眾多矛盾共有者的其中一員,與社會(huì)大環(huán)境站在矛盾對(duì)立面上的是在這樣糟糕的環(huán)境下深受苦難的所有人。
可以看出,《洞穴》這部作品中處處是矛盾、處處是沖突,這些矛盾與沖突無(wú)一不彰顯了戲劇的悲劇情調(diào)。馬丁和瑪莎只是在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遭受痛苦,艱難求生的普通人的一個(gè)縮影。這些矛盾與沖突展現(xiàn)的是整個(gè)社會(huì)的悲劇,人性在痛苦中逐漸走向扭曲,走向“獸性”。同時(shí),人性的斗爭(zhēng)也在馬丁的身上得到體驗(yàn),最終馬丁意圖選擇死亡,選擇用“文明”打破“野蠻”,以死亡來(lái)結(jié)束這絕望、無(wú)止境的“洞穴”生活。
三、戲劇情節(jié)重建——悲劇性深化
戲劇由小說(shuō)改編的過(guò)程中增減了一些情節(jié),使情節(jié)更具有悲劇性,也更符合戲劇的形式。首先,作者在小說(shuō)中設(shè)計(jì)的情節(jié)是馬丁去鄰居奧別爾特舍夫那里接水,而在戲劇中將二者立場(chǎng)調(diào)轉(zhuǎn),變?yōu)榱肃従尤ヱR丁家接水,這是戲劇中一個(gè)非常大的變動(dòng)。這種變動(dòng)實(shí)際上使人性的異變表現(xiàn)得更為深刻,在戲劇中,奧別爾特舍夫并非簡(jiǎn)單地拒絕了馬丁的請(qǐng)求,而是在自己受人恩惠的同時(shí)選擇了不去幫助馬丁和生病的瑪莎。這種行為實(shí)際上凸顯了人性的“自私”,而這種“自私”的形成是可悲的,其成因一部分來(lái)源于艱難的社會(huì)環(huán)境,另一部分則源于奧別爾特舍夫本身個(gè)性。但在小說(shuō)中奧別爾特舍夫沒(méi)有收到馬丁的幫助,這種情況下的拒絕就顯得沒(méi)有那么荒誕,沒(méi)有那么無(wú)奈。對(duì)社會(huì)的悲劇感也一定程度上降低了。
其次,由于戲劇中將奧別爾特舍夫接水的情節(jié)進(jìn)行了改動(dòng),那么馬丁去鄰居家偷柴的情節(jié)也隨之發(fā)生了一定變動(dòng)。在小說(shuō)中,馬丁在去奧別爾特舍夫家接水回家的路上就產(chǎn)生了激烈的心理活動(dòng),然后決定偷柴。但在戲劇中,馬丁的猶豫不安、慌張的心情體現(xiàn)在其動(dòng)作上,他“在瑪莎身邊站了一會(huì)兒”“雙拳緊握”“思考”,毅然決然地決定偷柴,但是這種犯罪行為讓他非常慌亂,于是他在匆忙中將鉗子掉到了地上,吵醒了熟睡中的瑪莎,在小說(shuō)中是沒(méi)有這一段情節(jié)的。
(第一幕)
瑪莎(醒來(lái)):是你嗎,馬爾特?你要去哪兒?
馬丁·馬丁諾維奇:等一下……我要去居委會(huì)……我馬上回來(lái)。(不經(jīng)意地?fù)炱疸Q子,放到背后)
瑪莎:別忘了……別忘了帶鑰匙。不然你進(jìn)不了家門的時(shí)候,我就得起床……
增添了這段情節(jié)是為了與后文中瑪莎決心喝下毒藥,要馬丁離開(kāi)時(shí)說(shuō)的話相呼應(yīng):
(第二幕)
瑪莎:現(xiàn)在……去吧,散散步。別忘了帶鑰匙,不然砰的一聲關(guān)上門,沒(méi)人……沒(méi)人再給你開(kāi)門了……
兩幕中都有瑪莎提醒馬丁帶鑰匙的情節(jié),但第一幕是日常的提醒,瑪莎病得很重,不想起床給馬丁開(kāi)門,而第二幕卻是訣別,不過(guò)短短一天時(shí)間,夫妻二人就要面臨永別,生活的沉重壓得他們想以死亡來(lái)解脫。小說(shuō)中僅有結(jié)局時(shí)的一次提醒,顯然戲劇中兩次提醒——平凡日常和生離死別成為了一種對(duì)照,加深了戲劇的悲劇性。
另外,除了夫妻二人,居委會(huì)主席謝利霍夫這個(gè)配角也被作者加了戲份,謝利霍夫因馬丁偷柴一事來(lái)馬丁家拜訪,與女主人瑪莎寒暄時(shí),多了這樣一段話:
(第二幕)
謝利霍夫:對(duì)……今天我排隊(duì)買面包了,買了兩塊八分之一大小的,然后我看到了,在高爾基居住的房子對(duì)面的科隆韋爾克斯基的拐角處,一個(gè)女孩正站著哭著。看著八九歲的樣子。我一下就心軟了,走近她,我想:“如果她請(qǐng)求要點(diǎn)面包,對(duì)天發(fā)誓,我會(huì)給她掰一塊”,“你怎么了”我說(shuō),“小女孩兒,你在哭嗎?”而她突然轉(zhuǎn)向了我:“你欠揍嗎?”她說(shuō),然后我就蹲了下來(lái)。(哈哈大笑)
作者為謝利霍夫所加的這段話,其實(shí)是對(duì)謝利霍夫的人物形象的補(bǔ)充。從這段謝利霍夫的臺(tái)詞中可以看出他內(nèi)心善良的一面。謝利霍夫?qū)︸R丁和瑪莎的稱呼為“先生”“太太”,與他們對(duì)話時(shí)用“您”,而他對(duì)奧別爾特舍夫的稱呼則是“狗崽子”,可見(jiàn)謝利霍夫?qū)χR(shí)分子的尊敬,而對(duì)奧別爾特舍夫則是一種輕蔑不屑的態(tài)度。但謝利霍夫雖然內(nèi)心善良,但落到實(shí)事上他對(duì)馬丁一家的困境卻毫無(wú)幫助,他來(lái)向馬丁問(wèn)責(zé),要馬丁歸還木柴的這些行為實(shí)際上也是推動(dòng)馬丁一家走向悲劇的原因之一。謝利霍夫這一人物形象也許是同時(shí)代背景下的大多數(shù)人,他們本性不壞,內(nèi)心也是善良的,但在這樣冷漠的社會(huì)環(huán)境下,只能選擇明哲保身,對(duì)其他受苦難的人主動(dòng)選擇視而不見(jiàn),這樣一群人的出現(xiàn)也展現(xiàn)出了社會(huì)“吃人”的一面,在這樣的社會(huì)環(huán)境下,人性的扭曲已成常態(tài),人們自己活著已是不易,更別提幫助其他陷入泥沼的人了。作者添加的這段對(duì)白,讓謝利霍夫這個(gè)人物形象更加豐富、飽滿,也突出了社會(huì)環(huán)境對(duì)人性的迫害,增添了作品的悲劇情調(diào)。
四、結(jié)語(yǔ)
隨著現(xiàn)代社會(huì)的不斷發(fā)展,悲劇藝術(shù)也逐漸從史詩(shī)中的英雄人物走向的平民大眾。扎米亞京通過(guò)短短一部作品展現(xiàn)了那個(gè)幾塊劈柴就能逼死人的時(shí)代悲劇,一方面表達(dá)了對(duì)受苦難人民的同情和憐憫,一方面表達(dá)了對(duì)不合時(shí)宜政策對(duì)底層人民壓迫的諷刺。《洞穴》的悲劇是平凡人的悲劇,但也是時(shí)代的悲劇。普通人在社會(huì)環(huán)境的影響下沒(méi)有選擇的權(quán)利,馬丁偷柴是無(wú)奈之舉,但即使他放下自尊去做了這些他本不愿做的事,良心備受折磨,也僅僅能得到一時(shí)的喘息。戲劇中的主人公是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的縮影,他們代表的是那個(gè)年代、那個(gè)社會(huì)的一群人。在這種拼命掙扎,卻依然得不到解救后,只能選擇死亡來(lái)求得解脫。
注釋:
①符·阿格諾索夫著、凌建侯等譯:《20世紀(jì)俄羅斯文學(xué)》,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1年版。
②陳汝嵐:《試析扎米亞京在小說(shuō)〈洞穴〉中的隱喻》,《名作欣賞》2020年第11期,第148-151+162頁(yè)。
③④李貴森:《西方戲劇文化藝術(shù)論》,中國(guó)傳媒大學(xué)出版社2007年版。
參考文獻(xiàn):
[1]Замятин Е.И.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3.-Москва:Русская книга,2004.
[2]陳汝嵐.試析扎米亞京在小說(shuō)《洞穴》中的隱喻[J].名作欣賞,2020,(11):148-151+162.
[3]陳學(xué)貌.淺析葉·扎米亞京短篇小說(shuō)《洞穴》中的陌生化手法[J].俄羅斯語(yǔ)言文學(xué)與文化研究,2006,(3):82-88.
[4]符·阿格諾索夫.20世紀(jì)俄羅斯文學(xué)[M].凌建侯等譯.北京: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1.
[5]李貴森.西方戲劇文化藝術(shù)論[M].北京:中國(guó)傳媒大學(xué)出版社,2007.
作者簡(jiǎn)介:
宋昕桐,女,漢族,吉林長(zhǎng)春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俄語(yǔ)語(yǔ)言文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