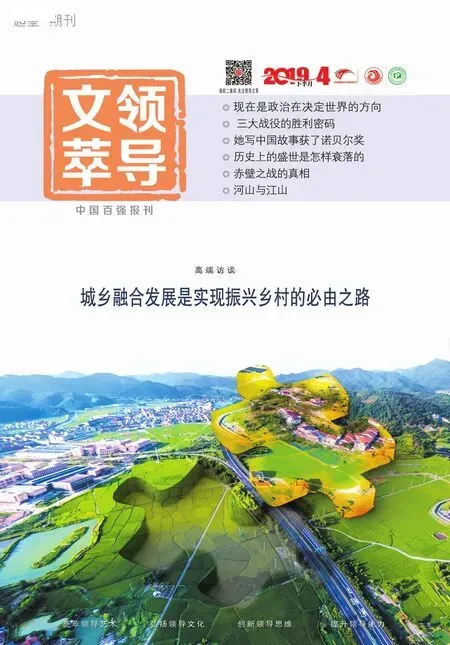抓鬮組內閣,崇禎咋想的
劉志斌
大明天啟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明熹宗朱由校駕崩,兩日后,他同父異母的弟弟朱由檢繼位登基,是為大明第十七任皇帝。人們更熟悉他的另一個稱謂——崇禎帝。
崇禎登基后,首要任務是重組內閣。何謂內閣?明代無相,唯有內閣。洪武皇帝朱元璋最初承襲元制,下設宰相;開國數年之后,他的政治閱歷不斷增長,深感相權掣肘令他寢食難安,數次沖突后,他終于痛下殺手,汪廣洋、胡惟庸、李善長這三名實權宰相被團滅。
這之后,朱元璋痛定思痛,于洪武二十八年對斗爭經驗進行了總結,道是“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并不曾設立宰相。自秦始置宰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既然開汽車有出車禍的可能性,那干脆把車賣了吧!
朱元璋敢想敢干,此后明朝不設宰相,政府機構直接向皇帝匯報工作。為了避免后世不肖子孫再立宰相,讓小人弄權,朱元璋特地在《皇明祖訓》首章中明文約定:“以后子孫做皇帝時,并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從理論上來說,宰相是非常有必要的。大一統王朝政務如此繁多,已經超越一個正常人的處理能力。因此,皇帝必須讓渡一部分權力,否則要么日理萬機最終累死,要么政務無法正常運轉,政權轟然崩塌。
明代皇帝很快另辟蹊徑,找到了一個能夠協助自己高效處理政務、又不違背祖訓的辦法——“內閣”。內閣肇始于永樂一朝,名義上只是翰林院的下屬機構,但實質是輔助皇帝的秘書班子。
祖訓說不能設宰相,設一個“內閣”分擔政務,不算違背祖訓吧?一是內閣并非正式機構,“入閣”雖然榮耀無比,卻缺少正式任職的名分;二是嚴格說,內閣并無制度性實權,必須牢牢依附皇權才能生存。所以,內閣與皇帝之間的關系極其微妙。
天啟年間,魏忠賢權傾朝野,閣臣無不隨聲附和。因此,崇禎繼位之后,一方面清除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另一方面,則借此機會重組內閣。對這些臣子來說,一旦入閣,自己便站到了大明官僚系統的頂點,只要運作得當就是數十年的榮華富貴。只可惜誰也沒有想到,天啟七年的這次內閣重組,崇禎皇帝竟然動用了前所未有的遴選手段——抓鬮。
由此,紛亂不斷的崇禎政局拉開了帷幕,在短短十七年間,五十名閣臣如走馬燈般在大明的權力頂端輪番登場,最終迎來了明王朝的覆滅。崇禎一朝“十七年五十相”的亂象,也被后人當作是大明國祚已盡的有力證據之一。
為什么崇禎帝選擇用抓鬮來遴選閣臣呢?實際上,大明已歷二百余年,在遴選內閣大臣這個問題上,已經有了一套約定俗成的辦法——“會推”與“特簡”。
所謂“會推”,是由吏部會同九卿、科道推舉若干名人選,然后由皇帝挑選;所謂“特簡”,是皇帝繞開其他步驟,直接欽點。
天啟七年十二月,在外朝已經推選出十二名候選人的情況下,崇禎皇帝忽然命令采用抓鬮的方式來選拔最終的勝利者,這委實讓在場眾人吃了一驚。后世有學者認為,這說明崇禎皇帝初登大寶,尚未準備好承擔遴選閣臣的政治責任,因此“敬求之天”,不過也有人認為,崇禎皇帝此舉是想打破閹黨對內閣的控制。
那么,他的目的達到了嗎?
在崇禎登基之初,內閣中的四人全是閹黨,唯魏忠賢馬首是瞻。這次抓鬮之后,有六名新人入閣,原有的四名隨即致仕,朝中局面“為之一清”。可以說,崇禎皇帝以非閹黨內閣替換閹黨內閣的計劃勉強算成功了,這些入閣之臣中幾名“打醬油”的閑人,則在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后,迅速退位讓賢,將舞臺讓給了更為合適的人物。很快,閹黨勢力逐漸清除干凈,被魏忠賢排擠的重臣陸續回到朝中。隨著昔日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韓爌的還朝,一個新的內閣——東林內閣,橫空出世!
東林內閣以韓爌為首輔,以李標、錢龍錫、劉鴻訓等人為骨干。他們與東林黨人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因此被稱為“東林內閣”。對內,他們遵循崇禎帝的主張,對閹黨進行進一步打擊;對外,依靠門生袁崇煥督師遼東、對抗后金。崇禎初年,東林內閣一度政績斐然,為人稱道。
可惜好景不長。崇禎二年,袁崇煥因罪入獄。袁崇煥的倒臺對明朝軍事上的打擊先不提,其入獄直接導致了東林內閣的垮臺。首先是錢龍錫,他與袁崇煥在殺毛文龍一事上達成共識,而這也讓他第一個遭到彈劾。然后是韓爌,他是袁崇煥科舉考試的主考官,是袁崇煥的老師,因此被彈劾致仕。原本在抓鬮過程中入閣的李標雖幸免于難,但自崇禎元年以來的種種鬧劇已經讓他對這位皇帝徹底失去信心,因此在崇禎三年三月主動請辭。
至此,東林內閣,分崩離析。
正如前文所說,內閣必須緊密依附皇權,皇帝的性格、能力,則直接決定內閣的前途。崇禎皇帝少年繼位,他前半生在宮中小心翼翼,養成了猜忌之心,只要他稍稍抓住一點蛛絲馬跡,便在心中無限放大,無端聯想到結黨營私、朋黨作亂上面。所以,如何能在這位年輕帝王身旁生存下來?答案只有一個——將刀子狠狠地捅向你的同僚。
下手越狠,地位越穩。在這樣的環境下,有一個人脫穎而出。他的名字叫溫體仁,史載此人是“機深刺骨”。在崇禎初年,他人望尚低,甚至連參加抓鬮的資格都沒有。不過,他抓住了崇禎皇帝善猜忌的性格特點,此后動輒攻訐大臣,斥責他們結黨營私,屢屢幫崇禎皇帝“印證”心中的猜忌,逐漸在崇禎皇帝心中占據了一個特殊的位置。
在東林內閣垮臺后,他展開了更加華麗的表演。先是聯手“性警敏、善伺意指”的周延儒,一起斗倒了性格寬厚的首輔成基命,將周延儒推上首輔之位;繼而又利用周延儒貪財枉法的弱點,對他大肆攻訐,將周彈劾。從此,溫體仁一家獨大的時代開始了。
溫體仁意識到,對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來說,沒有什么比一味逢迎更讓他貼心。因此,他在內閣期間對崇禎皇帝可謂予取予求,張嘴“主上神圣”,閉嘴“臣愚無知”。同時,他深刻吸取經驗教訓,努力推舉庸人入內閣,以至于京師甚至一度將他把持的內閣稱為“妓館”,說崇禎皇帝“遭了瘟”。
崇禎皇帝“遭了瘟”——說的自然是崇禎皇帝遇上了“溫”相,以至于八年時間里國事日漸糜爛,終于發展到無可挽回的地步。
崇禎十年,張獻忠出湖廣、皇太極征朝鮮、李自成入四川。氣急敗壞的崇禎皇帝終于換掉了溫體仁。
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恰如溫體仁雖然離開了內閣,但他在內閣中作出的“示范”,被后人所銘記。閣臣在內閣中互相攻訐,以逢迎上意、把持權勢為己任;崇禎皇帝在國事日漸糜爛的情況下,對諸位大臣的猜忌日勝一日,動輒貶斥閣臣,忽而又因為某次大臣入對,馬上生出奇妙的希望,將這個大臣提拔入閣——從崇禎十年開始,內閣中的成員真正開始了“走馬燈”式的輪替。
對崇禎皇帝來說,他在朝堂上的每一分鐘都是煎熬。他有滿腔的抱負,手握偌大的帝國,擁有無數的子民,卻找不到一個合適的執行者協助他。最重要的是,崇禎皇帝害怕成為亡國之君。
崇禎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建國西安,大軍奔赴北京。關鍵時刻,崇禎皇帝想到了調吳三桂入關,而吳三桂入關則意味著放棄關外的土地。崇禎皇帝希望內閣能“主持擔任”,讓自己不會在后世遭人非議;而內閣則“久議不決”,拖延一月有余,硬生生將崇禎皇帝逼上了絕路。同年三月,李自成大軍圍京,揚言要分割西北,崇禎皇帝再度與首輔商議,卻只換來個“默然不答、鞠躬俯首而已”的結果,憤怒的崇禎皇帝最后推倒龍椅,揚長而去。
崇禎不信任內閣,內閣也同樣不信任他。
在北京城被攻破之前,崇禎皇帝曾有“文臣皆可殺”之語,然而他似乎沒有想過,這些人的種種奇葩舉動,又何嘗不是自己種下的果呢?
(摘自“國家人文歷史”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