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物器官移植,“路障”在哪里
陳忠華

最近,美國連續報道4 例將豬器官移植給人的異種器官移植病例。這些臨床的最新進展,徹底打破了該領域持續30 年的沉寂。其中手術之一,2022 年1 月7 日,一顆經過基因工程改造的豬心臟成功移植給一名終末期心臟病患者——57 歲的大衛·貝內特。術后,患者心臟功能良好。這引發了全世界的轟動和關注。
然而,就在接受豬心心臟移植兩個月后的3 月9 日,大衛·貝內特因病情惡化,搶救無效死亡。盡管這一異種器官移植手術再次以失敗告終,但它仍然讓器官移植專家和廣大器官衰竭患者看到了重生的希望,值得我們梳理一下這項技術的發展脈絡。
近30 年來,異種器官移植實驗研究進展較快,但臨床研究一直處于停滯狀態。基因工程動物器官已經能在非人類靈長類動物模型中長時間存活。在這些實驗中,預存抗體、補體激活、凝血狀態等機制參與的超急性排異反應,基本上都被有效控制。很多專家認為,異種器官移植離臨床應用就差“臨門一腳”。
然而,關鍵的問題是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逐步過渡到標準的一期臨床研究。因為存在“跨物種傳染病”的風險,異種器官移植直接在志愿者身上進行一期臨床研究,在很多國家都屬于倫理或法規的禁區。但如果缺少這一步,任何新的治療手段都無法證實其安全性和有效性,臨床應用也就無從談起。

在器官移植最初,其實前輩們最先想到的就是異種器官移植。17 世紀,西歐就有人嘗試用羊的腎臟來挽救尿毒癥患者。1920 年,以甫洛諾夫為代表的一些醫生為了給患者注入“活力”,將黑猩猩等動物的睪丸切片植入老齡受試者的陰囊。此后10 年,據不完全統計,有11000 多名醫生參與了類似植入手術。其中,美國堪薩斯州一位名叫克林科里的推崇者,利用自己家的私人電臺招募到16000 多名受試者,最終因為療效不確切而被叫停并受到制裁。
下面簡要梳理一下異種器官移植史上四次破冰之旅。
1923-1960 年, 異種器官移植經歷了長達37 年的“第一次冰河時期”。在此期間,人類開始探索同種器官移植的可能性。
1960-1970 年,美國,有人用豬和狒狒的肝臟,離體或在體灌流,治療急性肝功能衰竭。
1963 年,大約有7 名患者接受了狒狒的腎臟移植。
1969-1973 年,美國,有人實施了3 例將黑猩猩肝臟移植給人的肝移植手術。同一時期,南非,有人實施了2例將靈長類動物心臟移植給人的心臟移植手術。
以上案例均以失敗告終,并直接導致臨床研究退潮。
1973-1984 年,異種器官移植又經歷了長達11 年的“第二次冰河時期”。
在此期間,同種器官移植技術及器官捐獻都得以快速發展,但供需缺口仍然很大。異種器官移植研究再次回潮,但由于技術條件有限,屢屢失敗。
1984 年,美國洛杉磯,一位醫生給一個早產女嬰做了狒狒心臟移植,女嬰存活1 周后死亡。1992 年6 月,美國匹茲堡,一位醫生再次嘗試把狒狒肝臟移植給2 名患者。第1 名患者于術后70 天死于復合性感染,第2 名患者于術后26 天死于膽道并發癥、腹膜炎。1992 年10 月,美國,因等不到同種肝,一家醫院嘗試將豬的肝臟臨時移植給一名暴發性肝昏迷患者,患者在移植手術完成后24 小時死亡。
以上4 個失敗案例,引發了不少爭議,最終直接導致異種器官移植臨床應用被禁。這一停就是30 年。
1992-2021 年, 異種器官移植進入長達近30 年的“第三次冰河時期”。
在此期間,雖然同種器官捐獻和移植得到充分發展,但器官仍然供不應求。
基因工程技術全面突破并得到廣泛應用。大量非人類靈長類動物實驗基本上回答了人們最為關心的兩大問題:如何克服超級性排斥反應和跨物種感染。這些成就催生了一系列“異種移植亞臨床研究模型”的問世。
2021 年年底,美國的兩組醫生先后完成了3 例腦死亡者的經基因編輯豬腎臟移植。
臨床前研究、亞臨床研究、0 -期臨床研究,這三個名詞基本上是一個含義。腦死亡者豬腎臟移植模型并非真正意義上的臨床研究,而是一種建立在“腦死亡=死亡”前提下的“ 臨床前研究”。
腦死亡狀態下的人體研究,既類似于臨床研究,又不完全等同于臨床研究。
這些異種器官移植的亞臨床實驗,為推進異種移植進入真正的人體臨床觀察提供了科學依據。
2021 年9 月- 2022 年1 月, 異種器官移植進入“快速冰河消融期”。
2022 年1 月7 日,美國馬里蘭大學醫學中心的巴特利·格里菲斯團隊將一顆經基因編輯的豬心臟移植給患者大衛·貝內特。貝內特因身體虛弱,被判定沒有資格接受捐獻的心臟移植手術,動物器官移植是唯一的選擇。貝內特在術前表示,“要么死去,要么移植。我想活下去。我知道這次移植就像在黑暗中開槍一樣,但這是我最后的選擇。”術后1 個月,患者心臟功能良好。
然而,在存活了59 天后,貝內特還是去世了。目前為止, 馬里蘭大學醫學中心尚未披露其去世的確切原因。基于目前所獲得的有限信息,貝內特的死亡原因可能有:免疫抑制治療過量或不足引起的肝腎毒性或急性排異反應;預防或治療復合性、耐藥性感染所用的多種抗生素引起肝腎毒性;包括心臟在內的多器官功能衰竭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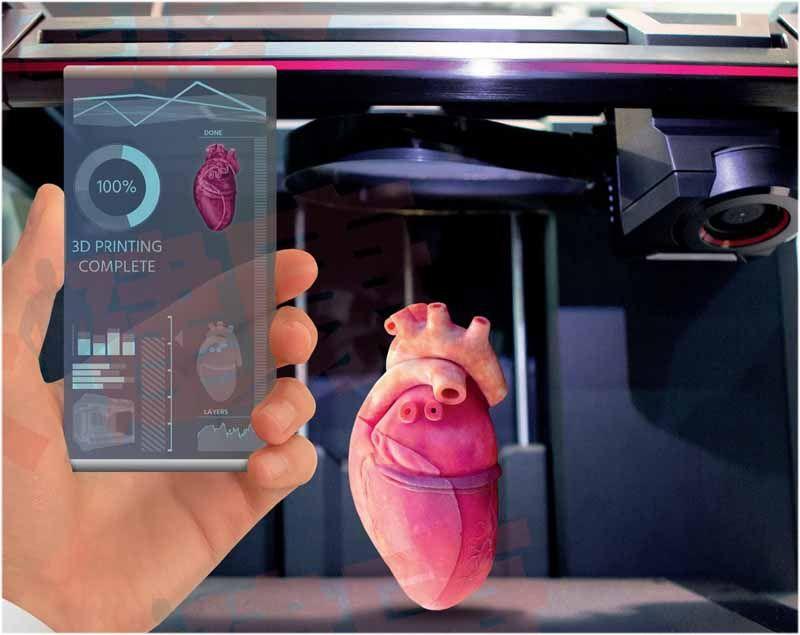
美國馬里蘭大學醫學中心的豬心臟異種移植取得了3 個方面的初步成功:一、成功完成豬心臟移植到人體的手術;二、完全克服了超急性排斥反應;三、豬心臟的血流量、流速、壓力符合人體血液循環動力學要求。
為什么選擇豬?第一,因為豬不是保護動物,涉及倫理學的障礙相對較少。第二,豬主要臟器的大小和人類基本接近。第三,豬的繁殖能力強,生長周期短,適合大規模培育。第四,基因工程豬的制備相對成熟。
為什么首選心臟移植? 相對而言, 心臟承擔的功能比較單一, 沒有太大的生物適配性問題,只涉及尺寸大小和泵血力度的問題。心臟基本上不承擔人體內分泌和新陳代謝功能, 相對容易成功。腎臟既有排泄功能,又有分泌促紅細胞生成素的功能。肝臟則更為復雜, 不僅參與人體各種新陳代謝,還合成各種蛋白質和酶。
如何避免跨物種傳染病風險?針對豬可能傳播疾病的潛在風險,美國這4 次移植的器官均來自特殊環境下培育的醫用無菌豬(無指定病原體的醫用供體豬)。作為一個潛在的臨床醫療資源,醫用無菌豬在2020年底獲得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使用批準。這也說明了無菌豬在生物危險性方面,已經達到了高級別的管控標準(包括內源逆轉錄病毒)。
異種器官移植優勢顯著。這樣的器官可以批量生產,供給不受時間的限制。人捐獻的器官肯定是最理想的,但是數量有限,而且什么時間、什么地點有適合的器官都無法確定。盡管人工機械心臟也有這些優勢,但是它卻需要電池和充電。
異種器官移植剛剛到達臨床試用的第一站,未來仍然有四大問題需要解決:免疫排斥、生物安全、跨種適配、倫理和心理。
現在還不清楚,移植手術后的急性排斥反應和慢性排斥反應是否能得到徹底解決。這需要長期的觀察。一般急性排斥反應的高發期是接受手術后的3 個月內。即使3 個月過后,如果沒有控制好,急性排斥反應也有可能隨時發生。
所謂生物安全問題,就是醫用豬心臟會不會給人類帶來豬的病毒和細菌的危害。
跨種適配問題就是醫用豬心臟是否能夠與人的機體一直保持尺寸合適。它是會停止生長,還是會繼續生長?如果繼續生長,會不會擠壓胸腔,導致血壓過高或過低、血液輸出量過大或過小?這些都還不清楚,有待觀察。
美國的這幾例手術也給倫理學提出了新的課題。在安全、有效、科學、理性、可控的五大前提下,將醫用無菌豬器官用于人體,基本上不會有特別大的倫理學障礙。但是從心理學上來說,人們肯定不愿意接受動物器官。盡管如此,總有一天,“量產的醫用無菌器官”會成為現有資源體系的一種補充性、替代性資源。
1998 年2 月8 日,美國“保守派”提出成立新的異種器官移植立法委員會,以立法的形式暫停和延遲異種移植臨床應用。此提案遭到“推進派”的反對。“推進派”提出應當小心行事,而不是停止或延遲,因為已有很多患者在等待中去世。
因為有生物安全性問題,異種器官移植不能直接應用到臨床。非人類靈長類動物如猴、狒狒、猩猩等的實驗結果再多、再好,也不能完全等同于人類的結果,哪怕只有1% 的基因差異也不能直接應用到臨床。但如果沒有直接在人類中進行的“安全性+ 有效性”研究,如何證明安全有效?這就是異種器官移植的臨床悖論。
歷經百年、四個階段的破冰之旅,異種器官移植終于抵達臨床試用的第一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