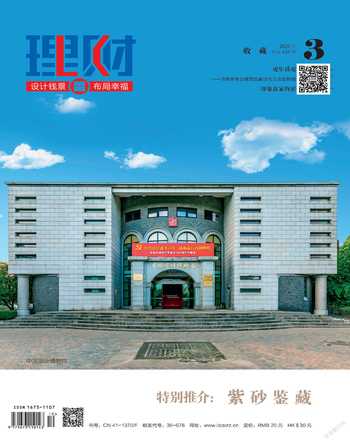河南文物中的虎文化
李文琪
虎作為猛獸和古代圖騰文化的代表之一,人們對于虎的認識、信仰、觀念形成了我國特有的虎文化。河南地處中原,歷史悠久,文化源遠流長,全省文物資源豐富,截至2019年,全省共有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420處。在2017年第一次全國可移動文物普查數據公報中顯示,河南全省470家收藏單位共有藏品4783457件,占全國可移動文物數量的7.47%。
在眾多的河南文物中,其中不乏與虎有關的歷史遺跡,河南文物中的虎文化,涵蓋了遺址、建筑、地名、人文,以及書法、繪畫、石刻等方方面面,我們可以從中獲得眾多河南文物與虎文化的淵源,發現河南文物的文化魅力與其獨特的根源文化。
自然崇拜與圖騰文化——濮陽西水坡龍虎墓(圖1)
早期的人類,為了生存與野獸進行斗爭,同時也依靠捕獲獵物或采食野果生存,這種活動逐漸形成了一種原始的自然崇拜,將自然界的一些動物視為神物。由于工具的不足,人力的缺乏,人類就會把那些兇猛的野獸當作一種崇奉的對象,進而變成一種信仰、一種崇拜,從而形成一種獨特的文化功能,即圖騰文化。老虎體型龐大,性格兇猛,自然就成為人類早期自然崇拜的對象,以虎作為圖騰,從而形成早期的虎文化。
1987年,在河南濮陽西南角西水坡,人們修建一座引黃供水的調節池,考古工作者在配合施工的調查過程中,發現其西南部有一處仰韶文化聚落遺址,距今約6000多年。其中最為神秘的是一座編號為45號的古墓,在這里考古學家發現了由蚌殼排列而成的龍虎形圖案,譽稱“中華第一龍虎”。
45號墓是一座土坑豎穴墓,其南北長4.1米,東西寬3.1米,南邊圓曲,北邊方正,東西兩側還有一對弧形小龕,墓主人為男性,其頭朝南,腳向北呈仰臥狀態,在其周圍還葬有三具殉人。而在墓主人的東西兩側,各有一只用蚌殼排列成的龍虎形的圖形,東方為龍,西方為虎,虎頭微低,雙目圓睜,張口露齒,虎尾下垂,四肢交遞,如行走狀,形似下山猛虎。按其下葬的方位,虎在左邊,龍在右邊,按照夏代和殷商時期的華夏族文化來看,當時的人們都有尚左的習慣,應是以虎為首位。
商代獸面紋青銅建筑構件(圖2)
1989年,在鄭州市小雙橋遺址出土了一件青銅建筑構件,整件文物高19厘米,橫18.8厘米,縱16.3厘米,重6千克。整體器呈現“凹”形,其正面近正方形,上下兩邊均向內折;左右兩側面近平行四邊形,中間還有豎長方形方孔。因為這件構件的出土地附近發現有大型的夯土建筑基址,所以考古學者推斷其應是鑲嵌于建筑物上的構件,因此其定名為“獸面紋青銅建筑構件”。
這件器物正面是單線陰刻的獸面紋,而在其兩側長方形孔周圍分別裝飾著龍虎搏象圖,紋飾線條精致細膩,既有莊重之感,又不失威嚴之氣,是我國目前發現最早的青銅建筑構件。從其獸面和龍虎搏象造型的裝飾來看,此處建筑有著極高的規格,應是商代的貴族建筑。由此可知,虎文化已經融入商人的日常生活和習俗中。
小雙橋遺址位于黃河南岸,面積達144萬平方米,發現有大型宮殿遺址、祭祀遺址、青銅冶鑄遺存和朱書文字等,也是目前發現處于鄭州商城和安陽洹北商城之間唯一一個具有都邑規模和性質的遺址。
“中爯父”銅簋(圖3)
1981年,在南陽市北郊磚瓦場出土了一件西周晚期的青銅簋。這件銅簋腹部兩側有龍形雙耳,圈足之上飾有三個虎頭,蓋上和器身上飾有瓦紋和竊曲紋,蓋上及器內還鑄有44字銘文。從銘文內容得知,這是申國之相中爯父為祭祀其祖、其父兩代人所作。據史料記載,西周末期,周宣王將申伯封在南陽建邑立國,史稱“南申”,春秋時期被楚所滅。“中爯父”銅簋的發現,驗證了史書上的“南申”一說,更為古申國存在的真實性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簋是古代盛放食物的器具,用來盛裝煮熟的黍、稷、稻、粱等,相當于現在的大飯碗。商周時期,簋除了作為盛放食物的器皿之外,它也是重要的禮器,特別是西周時代,它和列鼎制度一樣,在祭祀和宴饗時以偶數組合與以奇數組合的列鼎配合使用。我們可以從這件簋圈足上的三個虎頭,清晰地看到周人將虎文化與飲食文化融合在一起,以供其貴族所享用。
龍虎紋鏤空儀仗銅戈(圖4)
1984年,河南省鄢陵縣王店村發現的這件龍虎紋鏤空儀仗銅戈,整件器身裝飾龍虎形象。這件龍虎紋鏤空儀仗戈,是典型的春秋時期的戈,戈的援由兩條相向的龍組成,龍身為多體虬結鏤空的蟠螭紋。在戈的內上還裝飾有一只臥虎,頭成戈闌,虎尾上卷,形象逼真。這件戈的胡與內間有橢圓形銎,銎上塑一夔龍,胡下還有兩個不規則形穿。
戈是一種橫向安裝在木柄一側刃頭尖銳呈刀劍形狀的金屬武器,是商周時期最為常見的格斗兵器。在作戰時的用法是橫擊和勾啄,由于銅戈尖部銳利,壓強大、阻力小,所以穿透力極強,殺傷性能也十分顯著。當時的步兵裝備主要是戈和盾搭配,盾也稱為干,這就是成語“大動干戈”的由來。金文中凡是與兵器或軍事有關的字,大多以戈作為象形偏旁,如戟、武、戎、伐。
虎在中國文化中代表神武、力量和王者風范,龍更是有著無比崇高的地位,龍虎紋飾同時出現,表明這件戈的主人,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和權力。
戈作為中國古代特有的青銅兵器,它的影響已經超越了兵器本身,滲透到了古代禮儀中,龍虎紋鏤空儀仗銅戈工藝之考究、紋飾之精美,是春秋時期儀仗兵器中的珍品,同樣也體現了當時虎文化在冷兵器時代的影響力。
四神云氣圖壁畫(圖5)
四神云氣圖壁畫,也稱為“柿園漢墓壁畫”,1987年揭取自河南省商丘市永城芒碭山柿園漢墓的主室頂部,柿園漢墓的墓主人為西漢早期的梁國諸侯王。
壁畫長5.14米,寬3.27米,整體面積約16.8平方米。壁畫主體圖案以朱砂紅為底色,上面用白、綠、黑等顏色繪有青龍、白虎、朱雀、怪獸等四種神禽異獸,以及靈芝、花朵和云氣紋等吉祥圖案。 圖中巨龍尤為醒目突出,身呈“S”形彎曲,占據整幅畫面的中央,龍身長約7.5米,龍舌卷住一怪獸的尾部,龍身覆滿鱗紋,背生有雙翼,足踏云氣、長枝花朵等。龍舌卷住的怪獸為鴨嘴、長頸、魚身,身覆魚鱗紋,背生羽翼。下方白虎前爪攀附在仙山上,口銜長枝花朵。上方朱雀長喙啄住龍首的一只長角,長長的雀尾上揚飄擺。四周邊框裝飾有連線穿璧紋和云氣紋等。
中國古代青龍、白虎、朱雀等神獸既表示空間方位,亦可保護生者免于災疫傷害,死者免受鬼魅的侵擾,為人們心目中的吉祥瑞獸。壁畫以圖繪神獸等象征漢代人們想象中的天界,以仙山等象征仙人居住的仙境,表達了人們趨吉求福,渴望長生升仙的思想信仰。
白虎星座畫像石(圖6)
白虎星座畫像石,東漢文物,南陽縣出土,高60厘米,長138厘米,厚40厘米,畫中刻一白虎,昂首翹尾,疾步云端,虎前有六顆星,分兩組,橫三豎三,虎體下排列有三顆星,構成了西宮白虎星座圖像。
天象圖是漢代畫像石中常見的題材,我們祖先最早的生產活動主要是畜牧業和農業,古代先民需要觀測天象、掌握自然界的變化規律用以制定法歷來指導農牧業的發展,因此我國的天文學是自然科學中較早發展起來的一個學科。
漢代天文學家把周天恒星分為二十八宿,以東、西、南、北四方為“四宮”,并以“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四方之神來命名,每一個方位分區七宿。其中“參宿”是白虎星座中的主要星宿。畫像石上的白虎星座雖未刻全七宿,但白虎物象上的參宿是顯而易見的。虎身下三星,據其相對于虎身的位置,從左至右應為天狼、九游、土司空三星。這些神秘的天文圖像反映了漢代人民豐富的天文知識,展現了漢代天文學的卓越成就,為研究我國古代天文學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三彩虎形枕(圖7)
瓷枕始于隋代,盛行于唐宋金時期,尤其以宋代的瓷枕藝術成就最高。按用途分為生活使用枕、隨葬明器和醫用脈枕。其形狀各異,有六角形、長方形、橢圓形、雞心形等,紋飾題材異彩紛呈、種類繁多。金代的三彩虎形枕,就是這一時期瓷枕的代表。
這件三彩虎形枕,金代文物。枕呈伏虎狀,形體雄渾健壯,長尾卷附于腹側,前爪貼于頜下底托之上,虎背作凹形荷葉狀枕面,虎身一側倚靠鏤雕的洞石與闊葉樹木。虎頭及全身皮毛斑紋以黃褐兩色繪出,并順著一個方向呈抖動之勢,尤其枕面為點睛的神來之筆,頗見繪畫與釉色的匠心獨運。從這件虎形枕,我們可以看到金人把瓷枕與虎文化融為一體,將人們對虎文化的崇拜運用到生活的每個部分。